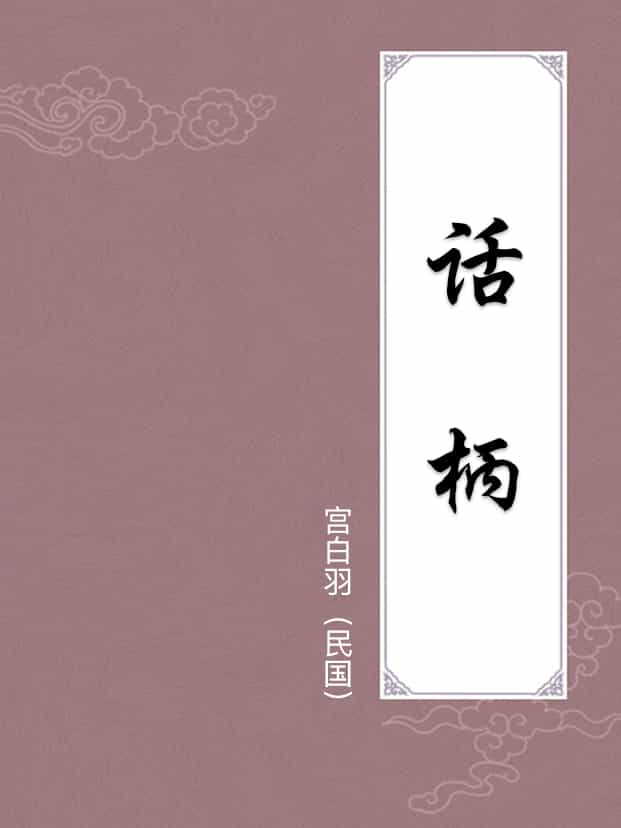然而环境迫着你干,不干,吃甚么?我就干起来。豁出讨人嫌,惹人厌,要小钱似的,哭丧着脸,访新闻。遇见机关上人员了,摆着焦灼的神气,劈头一句就问:“有没有消息?”人家很诧异的看看我,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那是当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来,编好,发出去,没人用,那也是当然。几十天的碰钉,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也慢慢的会用钩拒之法,诱发之法,而探索出一点点的“特讯”来了。
渐渐的,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的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狯,而阴沉,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今日之我”转换成另一个人。
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这四个字。
由于当外勤,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转回了报界。
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
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
当我在北京时,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而我依然处处失脚。自从到津,当了外勤记者以后,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而步步多踏稳——这是甚么缘故呢?
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
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
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
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办稿,编刊物,做宣传;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
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的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而还得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
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的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这样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弃养;喘哮不堪,也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的昼夜扶侍。先母死了,个个人都失了形,我可就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又以某种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异地疗养,非钱不办;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乡下,教中学国文——决计改变生活方式。我友劝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变起了,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转防空洞,跳墙,避难。廿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笔墨,再为冯妇,于是乎卖文。
对于笔墨生活,我从小就爱。十五六岁时,订报,买稿纸,赔邮票,投稿起来。不懂戏而要作戏评,登出来,虽是白登无酬,然而高兴。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晨报》译着短篇小说为止;一得稿费,渐渐的也就开始了厌倦。
我半生的生活经验,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么?也未必。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创作态度么?
我对人生的态度是“厌恶”。
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厌倦”。
“四十而无闻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