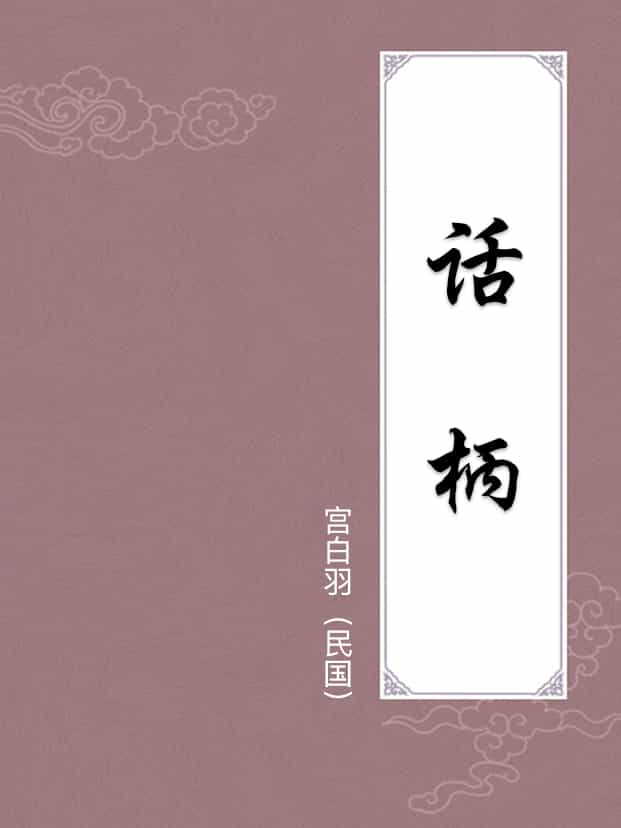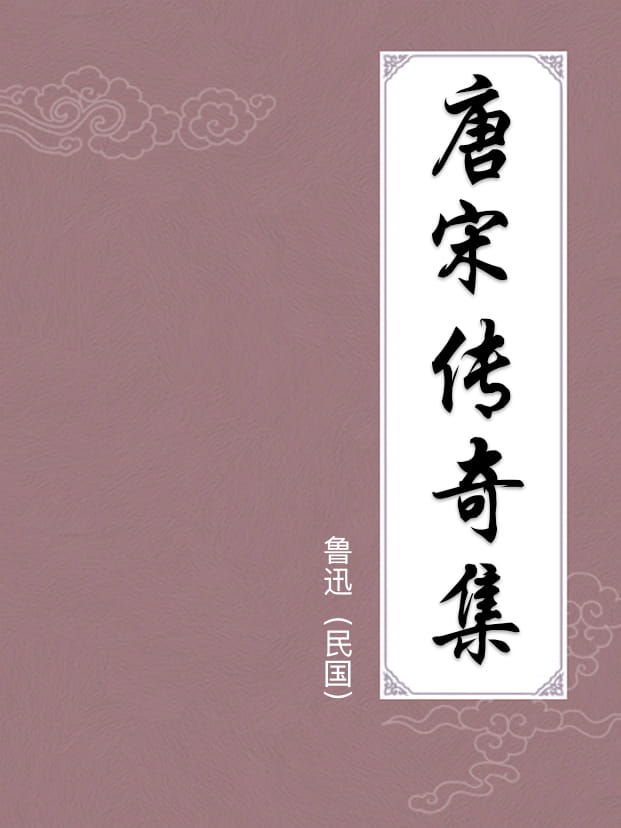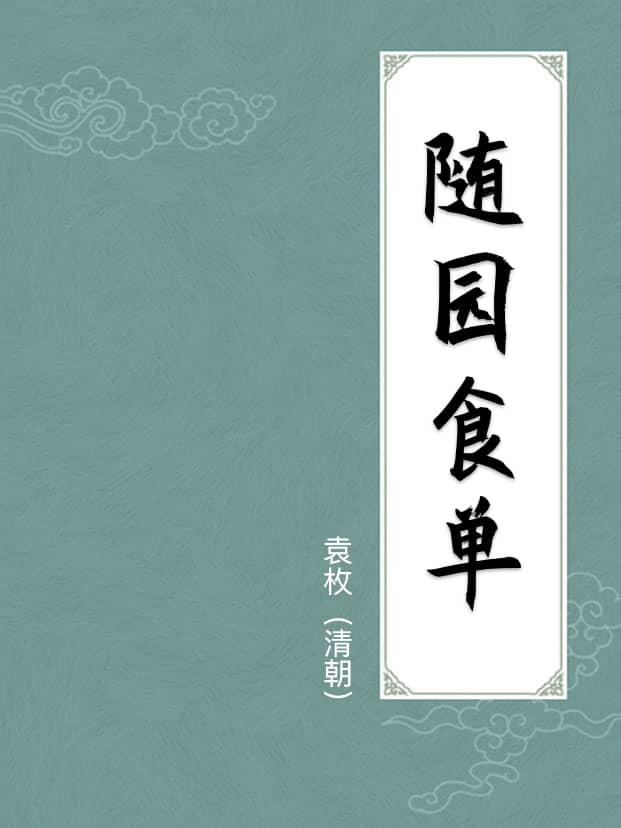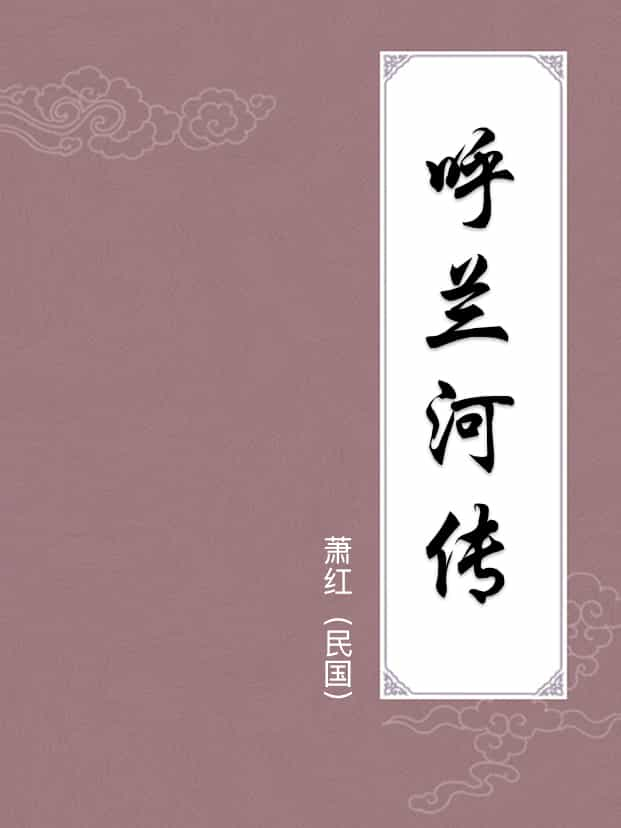我由民元到北京,于民十七夏跳出如火坑似的古都,逃到天津。初在报馆做事,后来由编辑当了外勤记者。我访的是政治新闻,就时常到市政府去。市府秘书长是老书生,我和他很谈得上来;他拿我当小孩子看待,有一次我分明听见他对别人说:“×社的那个小孩来了没有?”
到民二十,政局改变,秘书长接任××局长。我服务的那报社有停刊讯,盘算到将来的退步,心中正烦闷;直到下午三点,我才由家出来采访。我刚走,家中就来了信差找我,教我快到市府去。
我施施然到了市府,劈头看见四辆汽车。“这是有事!”立刻触动了我的新闻鼻,跑过去正要采访,而秘书长和几位随员出来了。
我迎上去问:“秘书长哪里去?”
“到××局接收去;来,你帮我忙忙去。”
我懂了,我说:“秘书长大喜!”
然而我没有全懂,我的一个朋友,在市府当科长的C君在旁笑说:“秘书长大喜,你也小喜!”大家笑了,我这才明白:所谓“帮我忙忙去”,并非要我登“就职消息”。我遂匆遽间做了六个接收员之一。但是我很为难:“我不会公牍呢?”
“那没有甚么,你一学就会。”
我这么糊里糊涂的入了政界,做了小职员。一开始,在科主稿,出外陪局长视察,会议作记录,又办宣传,很忙很红。但我是书呆,所以老书生的秘书长才看取我;但终于不久,我在局长做了一件呆事。查办某附属机关,我竟认真的查起来了,结果弄了一身刺。
又不仅此,长官拔取四个被救济的女子做本局练习生;因为视察,选取,都是我陪同局长办的,这四个女子入局之后,自然任谁也不认识,而只认识我;因为认识我,自然有了难事,就烦我替她们转达,而又由此弄了一身刺。
这机关女同事很多,足够一打;我服务的那一部分也有两三个。内中一个,就称为密斯L吧,她才十九岁,她是浙江人,有未婚夫的;她却孑然一身,跑到北方来做事;因而局中对她有种种揣测。这个女子却乖觉,和男同事接近,单找已经结婚的,貌丑年老的。于是同事斜眼C与我合了她的避嫌条件;有时她向长官请示公事,反而转求我们做她的翻译,她的南方话和长官的山西话果然是格格不投的。
当新旧交代时,因为也算是“换派”,全局旧员扫数解职,宿舍空了,密斯L的宿舍连电灯也没有了。她大概害怕,请求装电灯,又托我在外找房。相处熟悉了,也常在一处弹棋,打球。我们的直属上司,现在姑且称之为长脖科长,年纪轻,自以为很漂亮,大概很愿和密斯L亲近,因此尤嫉妒斜眼的翻译差事。
一次L和斜眼打球,长脖科长来了。
“科长打么?”
“打一打。”接球拍时,不知是故意,还是不小心,他的手抓着密斯的手了,密斯L把球拍一摔,甩手走出去。长脖科长很僵,既愧且怒。
斜眼常请密斯看电影,吃饭。科长也要请,她拒而不去。科长恼了,用他的土腔,一顿一顿的质问:“怎么,一样的同事,他请你就去?”斜眼请了半天假,说是到车站接亲戚;同日密斯L头痛,告假两小时,而科长不准:“怎么,她请假你也请假?”
斜眼有点担承不住,不知用甚么方法怂恿她,到底科长也花了一元大洋,把这个女同事请了一回。
这些事与我不相干。不过后来,斜眼不知因着何事,被L看不中,忽然疏远了。而斜眼是本科主稿,颇有一两月,拿公事挤兑密斯L。科中传为笑谈。
这些女办事员又向来无事可办的,从前她们以剪报为重大工作,但现在有了剪报室,(月薪二百元的一位秘书,率领月薪十五元的四个女练习生,一天到晚忙,口口声声太累;阅读,剪报,分类黏贴之后,便是呈阅,盖章,归档;归档之后,支架尘封。)科中剪报工作没有了,当她们或他们(男办事员)填工作报告时,只有“在科办公”四字好填;有的呆鸟居然填“在科阅报”。
她们为了找事做,便找主稿人员要点抄件。主稿的,只有我和斜眼的抄件多。密斯L既与斜眼闹别扭,当然愿欲找我,把我编的本局公布消息,记录,报告,用小楷腾誊清,算是能登功劳簿了。
我后来教她们一法,在工作报告上填写:“上午在科办公,下午调卷,整理本科文卷,缮写签呈及报告。”再发表点工作意见,足可交卷了;这总比“在科看报”强得多。
密斯L忽然病了。她命局役请我到宿舍,一看,脸黄黄的,坐在床上,衣襟未掩,露出肥白的大腿,蓬了头发。我踧踖的站着。四个女练习生与她同舍,寒暄让坐。我就问了问L,依她的意思,给她的朋友T打了一个电话;但这时打不得,须到下了班没人时候。为甚么呢?“怕他们造谣!”当然,我照办了。
然而L很苦闷,常对我诉苦。局中同人惯造谣污蔑她们,她一想起就忿忿。当新旧交替时,她说,她命局役去请她的旧上司W科长,问问他:她当怎么样?辞职呢,还是等着下条子停职?请W替她盘算一下。
女宿舍一片空房,只剩她一人,又要退房,又撤了电灯,请W科长给她想法;因为女子住旅馆开房间不好听,有没有地方可以借住。如此而已。
但经局役一番传话,就改了词了:“W科长,L小姐请你,她在宿舍,一个人骇怕。”这已经够受,而隔日有枝添叶,经过多人的传述,居然在“她一个人骇怕……”之下,加了“……请W科长过去做伴。”并且说的亲眼活现——当局役请W科长时,正在旧局长座次,旧局长也变了色说:“这L办事员是怎么说话!”W科长也羞得满面通红的,赶紧退了出来,云云。又隔了些日子,居然人们说:“W科长是日果然来做伴了。”
像这些谣传,又险些弄到我身上来。一个门房嘀嘀咕咕的对我讲:“K先生,我报告您一件新闻。你们科里的L小姐,昨夜九点钟打电话,邀她的情人T出去了,到十二点还没回来。”我故意问:“甚么时候打的电话?”说是“九点钟”。我又问:“谁打的电话?”
“L小姐自己呀!您瞧,这是甚么事,她能托别人打么?”
我听了一笑。门房所以报告给我听,因我是报界出身,要向我打听T和L的秘密到底怎样。他却不知昨晚六点半,替L打电话邀T的就是我。可是,到底我也惹了一身毛,那已在半月之后。
我上午在科办公,下午到宣传室招待记者,公布新闻。招待室恰在女职员新宿舍隔壁。有一次L和我和惠君弹棋,我输了六瓶汽水。她们故意敲我,知道我从来不请客。汽水买来,不是时候,没加冰镇,打开来尝,温暖的,一点也不好吃,我一笑下班了。我对这六瓶汽水,正要叫听差拿去;恰巧下班,四个女练习生从窗前经过,内中一个说:“K先生今天请客?”我笑了:“你们喝汽水不?一人一瓶。”她们说:“嚇,K先生今天真请客?”我从笑声中回家了。
第二天,我就觉着古怪。又隔了几天,长脖科长吞吞吐吐对我说了许多话,一点不得要领,我不懂他甚么意思。又过几天,新闻界朋友也向我说了一些话,我还是糊涂。直过了半个多月,我和友人秋白夫妇,密斯L及T偕赴南开看戏;这是他们几人故意逼我破钞请客。我没法子规避,我说没钱,而L小姐拿出五元来说:“我借给你。”我只可认头,一哄上了南开。听了张伯苓的演说,又看了王君直的侄女的新剧《太太》,旧剧《探母》,还有粤剧《貂蝉》,草裙舞。
在会场遇见市府科长友人C,他把我调开,告诉我几句话,请我检点,不要和练习生接近。局长那个老书生,还怕点我不透,一日他自己又附耳劝告我:“少跟她们女练习生说话,她们没有自主的知识能力。”
这未免冤枉。若说我和密斯L接近,还有点道理。我们本来不错,L每晚到秋白夫妇家玩耍,就是我的介绍。
我疑闷了许多日子,直到××局改组,才发觉了真相。给我造谣的竟是姓H的门房,他对内中一个女练习生G怀着企图,因而对我生了疑忌。G曾对我诉苦:“门房不拿我们当职员看待,H尤无理,曾直叫我们的名字。”可是天下事出人意外,等到闹出了笑话,四个女练习生被送回家时,而这个G竟下嫁了门房H,做了他的侧室。
××××
我初入局一时很红,半年后为了几件小事,惹得长官不高兴。头一件自然是“少跟女同事说话”;又一件是为索公务员出勤车费,当时各局照例都有,本局前任也有;第三件是办函稿答复一个要敲竹杠的家伙,措词太直了,长官认为缺欠公牍上照例的圆滑。本来在公牍上打笔仗,也太那个了;第四件,是看出我有失官体,“不像机关人样”。
末一件事很可笑。我在宿舍放了一份铺盖,我却天天回家睡觉,除了值班时候。我的家就在局后一条小巷内,巷狭室隘,没有男厕。有一早晨,我急匆匆往官厕跑,想必科头倒屣,衣貌不整,教长官瞥见了。他猜想我是这样从局中宿舍跑出来的,一个公务员,可是穿短衫,大清早往街上跑,这真真的有失官体了。
长官很不悦,当欢送他高升时,他对新闻记者我的旧同事批评我:“××工作很忙,也是个好手,就是不像机关人。他的手笔是好的,但是文字有毛病,话太硬。”
有一夜,我访友人秋白夫妇,偏偏他没在家;我隔着铁门往里探头,想看看他那房间的窗上有灯光没有。没有光,我回去了;隔了半小时,又去扒门缝,我可就被密探警察缀上了。我竟不晓得那里刚出过盗案。直缀到我家,把我盘问一遍,直到我拿出名片来才罢。可是当这探警押着我往家走时,又被局中人瞥见了。
我说:“糟!”恰巧这一天,我刚听见长官对我的讥评。我想赶明天可不知出甚么谣言呢。我一想,写了一件签呈。这件签呈措词很可笑,自己看着也忍俊不禁,曾录入日记中。现在,我就把女同事一案,和失官体一案的日记记载,都摘抄下来。
二十年七月一日
俗谓:六月六狗淴浴,秋白适诞生此日,零园昨以见告。秋白孩子脾气,好恼人,不去恐他不乐;偏余仅存二元半,不得为礼。是晚空手往祝寿,饱谈而归。临行,秋白大声曰:“谢谢。”
七月二日
下班时,L语予:“欲投稿《一炉》半月刊。”长脖科长讥之曰:“以若所作,可登《大公报》儿童版。”城来自平,买草帽一顶
七月三日
L愤然告我:伊未婚夫来信,有“我十二分放心你,但又十二分不放心你,因为时间过久了。”及“愿勿浪漫”等语。并诘L现寓何处,“能告诉我么?”L因此大恚。
一周前干儿子×××突厉声问L:“闻若欲归,何犹未走?”以是知殆有进谗者,意有未足,更离间人家未婚夫妻,心劳计拙,何苦来哉!一旬前,局长忽耳语我:“少与女同事说话。”殆庄孙等合谋见诬。L为人黑白太明,于所不屑,色拒千里,此所以招怨也。
七月四日
傍午女练习生M到科,当众谓予:“K先生,L先生找您。”何不避嫌乃尔?视之宿舍,则病矣,欲就医,惮于独往。予慰以勿过生气,闲话谣言宜淡视之,苟求无愧我心耳。小恙容觅医诊视。下午三时,以友人传医师住址付L。L色黯淡,汪然欲泣,促就医,则谢不往;以为孑然女子身,至不便。即欲为延医来诊,则仅存五元,发薪不知何日。拟同往就诊,顾当谣言孔张,心实不敢。言次喟然曰:“真难!”L本羁旅一女,年甫二十,幼丧生母,谋归不得,寓局不便,时见中伤,而二三妄人挟卑鄙心来相冒渎,L忍之不堪,拒之贾怨,伤哉!
T来,L之友也,谓庄孙适警彼:“宜检点,矜名誉;少找L女士”云云。吾早知庄孙戏L已非一次;既碰钉,乃以司阍为耳目,欲寻L隙,而L一天真漫烂少女耳。秘书室雪亦尝峻拒庄孙,徒以雪有手腕,庄遂计无所施。予因告T:“不妨一言自辩。”
七月五日
午间,L就与予语,谓新旧交替,苦无退步,问应如何则可。继谓时蒙诬谤,心殊拂郁,日来悲泣五次矣,更无一人相慰,即可与计决疑之人亦无之,诚孤儿之不若也。予慰曰:“某虽不足分忧,尚可决疑。T乃君之良友,亦足与商。”L桀然笑曰:“于今共话,即等犯法做贼,又焉得畅诉无忌?”予默然,忽长脖闯然入,贼眉鼠眼,窃诘何语。
七月六日
星期日,嫁婢来告贷,口出怨言。予于五月两次移居,六月值端午节关,又逢减成发薪,又值陕灾捐赈,官场更不时有小应酬,竟益不支。亲友不察,疑我富有;于是无地告贷,有人求帮,处境反愈窘矣。
七月八日
请领出勤车资,被痛驳。
七月九日
放假一日,天雨。昨夜愤惋通宵,今日怅惘无聊。读《清代通史》。
七月十日
××来函,述失业赴平,多寒暄语,知其意别有在;此其第一函,故未及谈耳。伊前闲居旧京,屡诉窘苦求荐,其辞恳恳引予为同调。比稍得意,面目骤更,口吻尖刻如故,且噬陷荐者,大为同辈不齿。今甫抵平,故态又萌,予已待之矣。
七月十一日
早得××快函,不禁令人有“又来了”之感。剖视之,果阅报知C长××处,欲为孟和谋事。而不知彼之穷则摇尾,稍纾则“一百个奏不着”,同辈于其退出×报时,早已目笑存之矣。午后孟和果来见访,告以已得××函,自当说项,但恐事迟无效耳。
七月十二日
士林洋洋然来,彼从出×报,即任××通讯社外勤,而以社长自命,颇在外做不要脸的活动,自谓领各机关津贴,××四十元,×局×局各二十元。此次欲见局长,请所谓稿费十五元。局长命予代表与谈,彼乃云:“局长业许之矣。”此子庸妄,庄孙之流亚也。耘薪来访,飘飘然以玩世自命,予独洞肺肝,盖嬉皮笑脸之小滑头也。白林美之曰:“滑得可爱,此子乃愈得意。”
七月十四日
午,偕L访秋白夫妇,盖为L找房也。四人遂聚谈时许,秋白留餐。予先偕秋白出;L留与秋夫人谈时许归局。秋乘间诮予:“此即她耶?”予曰:“吾子七岁矣。君所谓她之他,名×××。”
七月十五日
L就予大谈秋白夫妇,言次意似甚悦。独昨日予请伊刊小照于《北画》,伊逊谢谓:“不好看。”秋释之曰:“倒不在乎好看。”L乃引为不足,今日犹介介也;可知女子爱美,自矜其貌。每予戏谀伊漂亮好看,或谀其天真,则往往郝然有得色。其实伊不为美,特意度天真,体态苗条,时露小儿女态,为可爱耳。然其人实有判别力,于诸男同事龌龊相,辨之甚明,盖颇有鉴人之力,为可异也。
今日L嬲予偕往秋白家,言欲拜秋夫人为师。秋夫人温柔仁蔼,贤明识大体,同辈皆敬之,有母仪天下之概,无怪L一见倾心,欲常过从,此拜师之用意也。予与L过从渐密时,即怂恿L往访秋夫人,其意有二:一、L只身在津,常苦孤寂,得此良伴,可慰其情。且同为女性,又均南人;二、L在津无保护人,苟遇缓急,男友不如女友。即如上街,若独行无伴,辄被匪类钉梢;今予使与秋白夫人为交,当免许多是非,亦可息却谣喙。
七月十六日
L又怂恿我往秋家要书,并问拜师看房。早班后到秋家,秋突谓我:“你与T为L吃醋打架,满城风雨矣!”真怪事!老T欺我瘦弱,常思摔我。不意日前戏角力,连被我颠扑数次,最后将他扳倒在地。彼吃亏大嚷,逢人告诉,谓我用沸水泼他了。问其故,彼仅云:“开玩闹急了。”闻者却替他补出闹急的理由,说是因为L。T真浑虫!
我与秋白谈起L来,论到她的未婚夫×××和她在局情形。谓伊对同事太严冷,又好淘气,且只身做客,故对她谣言最多。因嘱秋夫人照应她。夫人说:“房钱可设法核减,包饭却麻烦。”
七月十九日
与L访秋白夫妇,吃饭打牌,游××花园,闹了小半夜,耘薪及T均偕。L拜老师师母,对秋白叫老师师母,叫得凭响,这小女子真有趣。
七月二十日
秋白邀L及予游湖,我托病未去,携子上街买书。
七月二十日
L说游湖之乐。晚,秋白抱两个西瓜来看病。于是又到秋家玩牌,L已先来。十一时,一同出来。
七月二十二日
昨夜大雨,闹臭虫,困极,又迟到。
八月七日
本局发现奇弊,司阍私拆并擅扣职员函札,且窃取函中五十元汇票。女办事员李××数月前由籍汇来五十元,竟未收到,往返函查,乃收据上赫然见传达室之戳记。
局中又出新笑话,宿舍男女职工早晚出入,饬均登记,司其事者则委诸H、W二门房,可谓有权。不知谁出此妙计也!行之数日,闹出不少笑话:
一、H出去,三点半不关门;两司阍在局,十二时即上锁。职员观电影、游花园纳凉者,皆锁在外;
二、司阍对女职员皆无礼,(对女宾亦然,秋夫人访L,碰一钉子。)藉此登记,大张威权;女职员吓得一步不敢出,以免被他们登记时,故意颠倒时间;
三、男职员刘、马二君闻登记事大骂,故意迟归;徘徊马路,至三时半,容H嫖完归局,关门上锁,然后叫门;
四、工役王某因事迟归,司阍欲登记;王正色曰:“要登记须公道,你们别忘了三点半。”司閽竟软化。
八月八日
私拆函件,窃取汇票案,闻将由调查入手,妙不可言。事发几日矣?闻干儿子令司阍负调查责,尤妙。
八月十三日
李××上签呈,请严究不法工役。事关局誉,及局员书信自由,料长官当拘讯涉嫌者,或径送公安局,然而不然!铁忱自南来,秋白设宴,邀予及L作陪。白林、叶唐、永清均在座。铁忱大赞予所作《家风》,谓为有力讽刺。白林怕我借钱,口称只剩一角;及到冷香室吃冰,初云写账,终拿出十元钞票。于冷香室才见所谓“南北瘟”迷死妙,略有姿色,脂粉甚浓,作笑靥傍秋白而坐,俨然××也。铁忱舆予向秋大开玩笑,秋白怕登报,力说噤声,隔壁有人识秋也。
八月十五日
晚访秋白,与L同游河畔,彼此郁郁不乐,于目前生活颇感厌倦。散步共谈,忽一男子周旋左右,吾辈行则行,止则共止,殊可厌。L因告我:“我一人不敢出门,即惧此辈。”予因语以荷妹在校时,亦被不相识男子追逐。
八月十八日
今日本局二周年纪念,演说摄影后,开始游艺。局长荣任×省教厅,言中已露别意。
八月二十日
局长大放起身炮,新委者数人,加薪者多人。闻新任夹带中人颇多,人皆自危。
八月二十二日
次儿病。晚与秋白夫妇及L作竹战。伊好翻张揭底,一语讥诮,惹恼小姐。僵持良久,我戏惊呼,唬伊一跳;伊勃然而起,誓曰:“明日不理你了。”群哗笑:“若不理,何必明日?”
八月二十三日
向L赔情,她负气不理。聆风及T告我,局长批评庄孙及予,仍不脱记者习气;谓予工作尚忙,庄孙直是来拿干薪。又谓我言行不检,曾目睹我科头短衫,徜徉街头,太不像机关人样。真冤枉人,局长不知我之科头短衫,乃自家中出如官厕也。
晚六时,礼堂公宴新旧局长。久候新官始到,貌癯身长,似一师爷,犹未及旧任尚有学者气。照例演说后遂开宴;予因谣喙纷集,心怏怏不乐,引杯大醉而归。九时访秋白,因睹临街楼窗电灯未明,小伫旋回,即赴官厕,乃为警探踪迹!比经解释,疑窦始消,乃因此触动前此故被嫌事,大恚怒,又不知明日作何谣传也。忿握笔作签呈,一吐积闷。
八月二十八日
辟谣签呈缮就,先携访秋。秋白读之失笑,然以为末台戏不必得罪人,但我忍耐不得,终送到局长公馆。
呈首云:
本局近来蜚语纷腾,殆缘一部职工枉顾大体,或无知而造奇谣,或有心而肆恶谑。甚则将谣进谗,借无根之谈,为修怨之具。一吠百和,资为话柄,言者无罪,闻者滋疑。事不干己,谁肯揭穿?身既被诬,辩亦无当……末谓:前者×由河北移居××里,恰当局址后身,相距数武。×家无厮养,日用所需旦夕购备,固统须自出。偶有一二次,与局内职工相值道周灯下,不谓身系蹀躞自家门前巷口,竟疑夤夜临局,意果何为?
又有一二次,×科头短衫,出寓如厕,实为内急,初非出游;或复意为衣冠不整,徜徉街头,无乃有失官礼?讵知×家湫隘如笼,更无男厕;短衫频赴街头,只为趋登厕所。夫如厕谓之更衣,断无正其衣冠,如见大宾之理!不意因此传为笑柄,阖局全知。抑系旁敲侧击,微讽轻谑之辞,既不容认真,尤难于置辩。窃以此等琐节,固无伤于大体,然使颟顸颓废之状,有愧毕呈,殊非青年官吏所宜有,亦至贻笑于大方。除克日移居,俾离局稍远,并嗣后律身益加检点,如厕必着长衫外,合亟陈明,仰祈鉴察……
这便是我的日记“局中人语”的一部,中间有删节。这个签呈到底投上去了,其结果乃是长官老书生从此不理我,我也不在乎。
我的生平,颇经波折,独少桃色的一页;这一页聊备一格吧。至于L小姐,我和她不久也通话了,那是在“换派”时,我们的地位都飘摇不定,各忙着想办法。在马路上相遇,密斯L先下了车,我只好也下车,匆匆立谈数语。
她又说:“这一派没有认识人,要辞职回南。”我安慰道:“不要紧,我或者也能想想法。”后来我和她的地位都得保留,就此恢复了友谊。但是她已经隐有去志:一者谣多;二者她的薪额减少十元,几乎没法维持了。她曾请我看过电影,吃过茶,(当然我没请过她,我就从来没请过客。)但我应她邀请时,我不独去,把我的七岁儿子带着;我家千里驹给我丢了一个丑。出门时候,她说:“坐洋车还是坐电车?”吾家千里驹说:“坐电车省钱。”L小姐笑了。
我终和L小姐疏远了。当我们无端被新任减薪时,全局怨言载道,可是不敢有所表示。书记室人心最齐,曾先发难,我们也相继有所联合。科长秘书们看闹得不像话,以调人的口吻来排解,来钩稽主谋。密斯L临阵退缩,几乎有卖友之嫌,且以与穷书记联名为羞。我怫然不悦,愿意受,就不该出怨言;想复薪,不要怕开革!“小姐到底是小姐,女人到底是女人!”把她排揎了一顿。
虽她认错,已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而在这之先,从别方面又听见关于她的出身的奇谣。她观人处事,于女气稚气中,保持着充分的老练,这不是二十岁女子所能有,到底她是怎么个来历,成了奇迷。
一日下班,我把L叫住,法官似的审了她两个小时。这更可讶,一个人无端被盘诘,被诬猜,乃至被揭破隐情,必然着恼、愧耻,至少也要激昂,而她不。她口头力辩,表情上很恬然;她的心灵并没被我这意外突击扰动,她能这样镇定么?这越发是个迷了。
我们渐渐疏远。忽一日,又是换派。早晨,我于于然进科,来到自己办公桌上,写字版角,留有她的小小一张名片;女练习生也带来她的告别的话。从这小名片上,我才晓得她的号,姓L名××字×琴,名很雅,号极俗。
她走了。但在我脑中留下残影。
(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