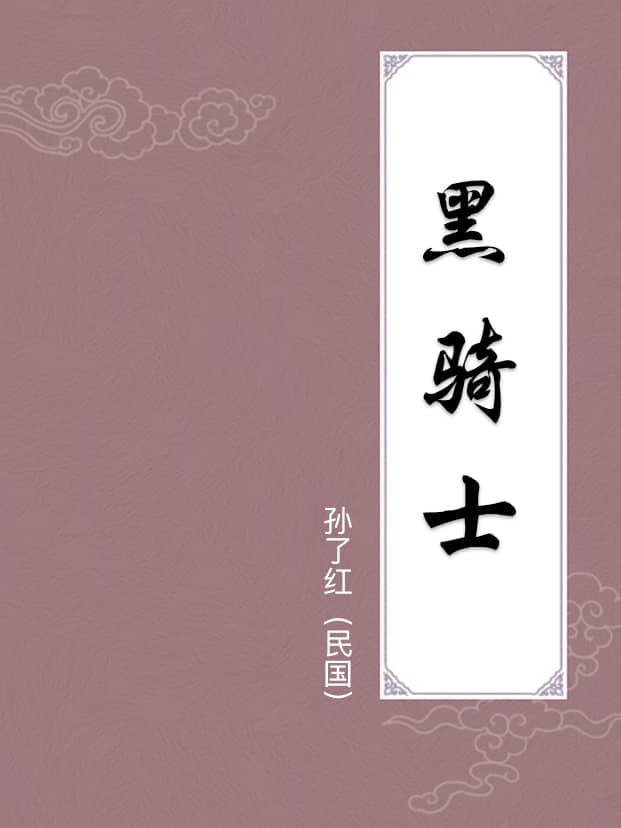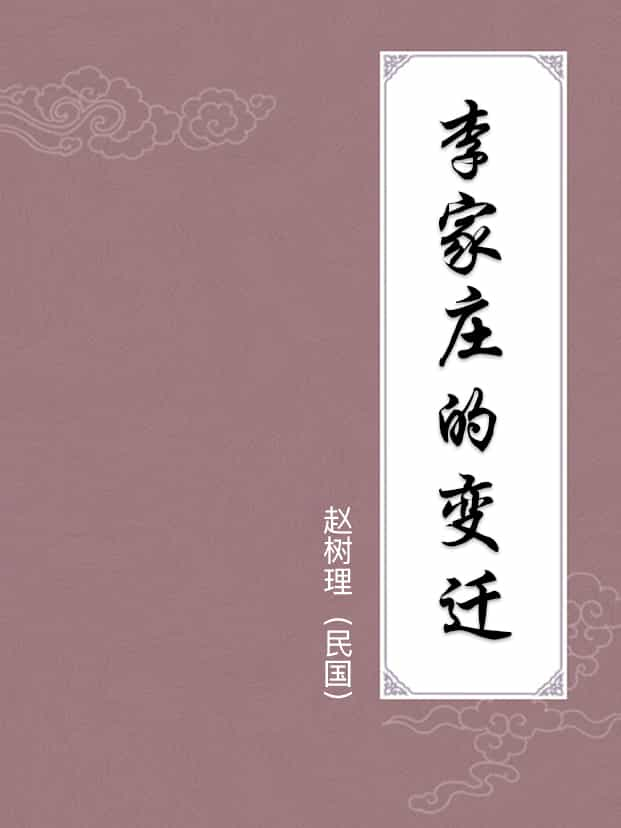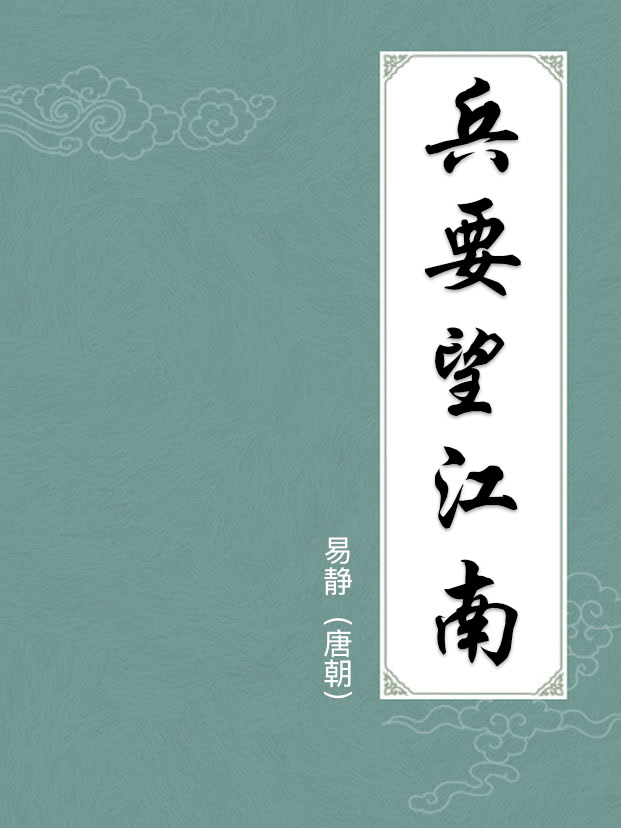民国九年的秋季里,天空中满布着愁云惨雾,好似上帝预知这大好神州,又将发生一种不幸的事情,故此先期布下这种悲剧的布景,好教我们有防患的准备似的。
我这故事的起点,在一所很小的密室里。这所密室,位置在全屋的中心,一切布置,非常精致,四边陈列着许多日本雕刻品,使人一望而知这屋主是很富于美术观念的。
在这许多陈列品中,有一座大理石琢成的女神像,那面貌的美丽,玉肌的莹洁,使人瞧了怪可爱的。再有一座用古铜盔甲堆砌而成的日本古甲士像,形式的高大,完全和真人相等,蓦地里见了,却很容易使人吃惊。
密室的主人翁,唤作马士骥,是一个退职的外交总长。他虽已退归林下,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仍占有一部分的潜势力。他的年齿,约摸在五十左右。身躯肥胖得很,宛比一尊弥勒佛像,圆圆的面庞,满现着一派和蔼之色。从外表看来,谁也料不到他是一个心地龌龊的人物。
这时马士骥独坐在密室里的一只沙发上,不住拈着唇际的燕尾须,双眸呆望承尘,正自想得出神。原来近几月来,马士骥正和日本特派委员大刀川松井氏,磋商一种丧权辱国的密约。这项条约,虽已拟议了好久,直到现在,方始谈判妥洽,约定后天夜间九时半,由松井秘密赶到马士骥家中,准定十点钟,两方在密约上签字。
外界对于这一件事,虽已稍知消息,只是不能明白这密约,到底含的什么性质。因此国内许多爱国的人们,明知马士骥又将实施他的阴谋,可是总得不到充分的证据,却不能向他提起反抗来。
此时马士骥想到签字之后,自己又可得到一种很丰厚的报酬,不觉得意万分。圆圆的脸上,顿时满罩着一股满足的笑容。
当他笑意还不曾消减以前,陡见他那只柚木的写字台上,有一件可异的东西,直刺进他的眼帘,却是一个绯红色的小信封。
马士骥见了,煞是诧异,趁手把那小信封取了过来,拆开一看,只见里面一张绯红信笺上写道:
若果允将滦州诸矿开掘权,悉让于某国者,则若之祖冢,亦必有人一一掘而碎之,如某国人之开滦州诸矿然。当汝得此警告之日,而犹不将此条约废去者,则署诺之时,余必有术取此密约去,布诸天下,俾众咸知。余言必践,汝其凛诸。
祖国之魂
马士骥读完这信,心房渐渐震动起来,暗想:“这所密室,可算得全屋最深邃的地点,倘由外面入内,须经过八九重门户。平常无论人们不能轻易到此,就是张着翅膀的小鸟,一时也未必能飞将进来,那么这一封可怪的恐吓信,又怎么会到这室中来呢?不但如此,并且觉得这写信人的行动,也非常可惊。因为这密约的内容,从来不曾泄漏过,此人竟能够知道是关于滦州开矿的事情,岂非是不可思议?”
马士骥一壁乱想,不知不觉,伸手去按那桌上的唤人钟。一阵玲玲的大响,同时便有一个仆役应声进内。这个仆役,却是马士骥最亲信的心腹,除了他,余外的仆役们,是都不准踏进这密室一步的。
马士骥那时心中很怒,一手颤巍巍的捏着那张绯红信笺,冷笑道:“阿俊,今天有人到这室中来过没有?”
阿俊望了望马士骥的面色,很恭敬地答道:“不,没有……”
马士骥愈加暴怒,把那绯红信笺,向仆役一掷,狠狠啐道:“既没有人进这屋子,这东西是哪里来的?难道是长着翅膀飞进来的不成?”
马士骥才一说到“长着翅膀飞进来”这一句,心中又觉一愣,觉得如此机密的所在,那投书人竟能来去无阻,真好像飞将军从天而下啊!再一想投书的人,神通如此广大,难怪无知识的仆役,要被他瞒过,于是便斥退了阿俊。
阿俊去后,马士骥总觉忐忑不宁,暗忖:“那自称‘祖国之魂‘的,不知究竟是何等样人?万一到了签约的时候,他果真来实行信上的话,未免有些危险。如今非得先预筹一个抵制方法不可。”
他踌躇了一回,忽而哑然失笑道:“今天的事情,因为不曾防备,所以不知什么时候,被那人悄悄地掩了进来。”
仔细一想:“那人这种下劣的恫吓手段,只能取快一时,到底也未必就能如言实行,愁他做什么呢?到了签约的那天,倘真放心不下,不妨加意防备,看那人还有什么诡谋,可以施展出来。”
马士骥想到这里,眼瞧着那古甲士雄赳赳、气昂昂的立在一边,好像是正在保护着他,于是他的勇气,又恢复了许多,便不再把那恫吓信放在心上。
光阴好似飞机般的驶行着,匆匆已过了两天。
这一天清晨,马士骥又接到一封署名“祖国之魂”的信,却是从邮局里投递来的。信上略谓前次的警告,不蒙容纳,令人可恨!你既一定要实行你的事,我也一定要实行我的话了。
马士骥看了,只是嗤的一笑,并不十分介意。
当夜九点钟时,飞霞路上,远远地来了一辆精美的汽车,车前射出两条很强烈的灯光,光线由远而近,直向马士骥家射来。
一会儿,这汽车便驶进铁栅门。铁栅门里,本是一片小小的草场,中间有两条煤屑铺成的弧形短径,合拢来恰成一个圆圈。
这时汽车取道于左边的短径,缓缓停在石阶之前,车门开处,里边悄悄地走出一个人。那人身材很矮小,穿的是一身西装,唇上留着两撇仁丹式胡子,不问可知就是那松井了。
当他从右阶上拾级而升时,马士骥早已在那里恭候,于是一同进了密室。
二人坐定,谈话了一会,只听得宅前门楼上那座四面钟,铛铛的接连鸣报十下,马士骥遂八一正一副两份密约,取了出来,同松井仔细审读一遍。刚提起笔来,要在密约上正式签字,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抬眼向室中瞟了一周,面部歘的现出一种狞笑。
长天如漆,只有几点疏星,闪烁作光。飞霞路上,突有一个黑衣骑士,跨着一头神骏的阿刺伯黑马,好像一团黑烟,风驰电掣般飞滚而来。杂乱的蹄声,踏破了宁静的空气。那黑衣骑士,飞马到了马士骥家门前,倏的弯身翻下马背,恰巧那四面钟,正报着十句钟的最后一下。
马士骥的笔尖,还不曾着纸,蓦地通室的电灯,完全熄灭,顿成了黑暗世界。同时室中忽发生了一种微细的金属物接触声,可惜马士骥与松井二人,都在慌乱之中,不曾觉得。
等到仆役们取了灯火赶来,马士骥手边两张纸,早已不知去向。大家在室里搜检一会,并不曾发见别的动静。马士骥又是冷笑一阵,自言自语道:“嘿,幸而这两份密约是假的,饶你‘祖国之魂’诡计多端,可已先中了我的诡计咧!”
第二天,各报都接到署名“祖国之魂”的投函,详述马士骥最近卖国的经过情形,信中并附有那两份密约的原文。
再过一天,各报便把此事,源源本本在报上详细披露,于是马士骥的罪恶史,在短时期中,已通国皆知,全国国民,顿形骚扰起来。有的痛骂着马士骥,不该做出这种汩没良知的举动;有的互相庆贺,此次幸亏有祖国之魂,在暗幕中打破他们的阴谋。就中还有一班人,纷纷向各报馆去询问,祖国之魂到底是何等人物?并且要求报馆,宣布他的真姓名。其实各报馆对于这些事情,正和询问的人,一样不知底细,却用什么话回答呢!
这一天,鲁平看见了报上的记载,笑向他部下柳青道:“好了,这一来,那卖国贼马士骥,真无可逃罪了。中国的同胞,倘还稍有一些子血性,我知决不肯将他轻轻放过咧。”
柳青道:“是啊,其实那晚的事情,在我们也危险得很,真可谓间不容发啊……当时我依了你的计划,贿通阿俊,乘隙由阿俊引进密室,把古甲士像的盔甲,拆卸下来,装在自己身上。那甲士本有一个铜面具,五官皆备,好好掩住我的脸部。我扮好以后,在密室里,自六点钟起,足足直立四小时,丝毫不敢动弹,简直像埃及的木乃伊一般。老实说,首领!你知道那马士骥,他是何等乖觉的人啊!倘我呼吸稍重些,我们的事,可就全局破裂咧!
“后来好容易等到钟楼上钟鸣十下,我在那铜面具的眼孔里,向外一窥,只见马士骥开了铁箱,取出几张纸来。我的心不觉在腔子里剧烈跳动,满望你这时候,在外边剪断电线,我方好乘机行事。谁知细数钟声,自一下以至十下,却不见电灯熄灭。我心中真焦急极了,暗想,倘再迟一回儿,电灯还不熄去,等他们字已签定,把密约收好,那么我们岂不是空费心思,白白冒这一场险么?”
鲁平道:“是啊,那晚我本来预算九点半时,可以直达马士骥家,谁知临时又发生了件很重大的事情,非等我解决不可,因此竟耽误了时刻。看看时光已十分迫促,我不得已,只好跨了一匹快马,连加几鞭,飞也似的赶将来。距离马士骥家,约摸一二十码外,已隐约听得钟声,我在马上突然想起,他们虽然预定十点钟签约,但未必不迟不早,适当钟鸣时行事,所以我也非常惶急,恐怕已经误事咧!倘预知他们第一次取出来的是赝鼎,我早就预备向松井拦路劫取,何必定下这种偶图侥幸的计划,使你冒这种险呢?只因为我生平有一种特性,情愿出奇制胜,却不愿干那剪径的勾当啊!”
柳青道:“你说这种计划,乃是偶图侥幸,真是一些不错。须知我潜藏在甲士像中,随时有破露的危险,当电灯熄时,我伸手到马士骥桌上,不防身上的铜甲,竟互触了一下。幸亏他们百忙中,不曾听悉;否则我此时早就铁索锒铛,进监狱去了。其次他们满室搜检,我的地位,也很可虑,但这难关,居然也被我轻轻逃过,岂非侥幸!不过我们费了偌大的心机,临了仍旧中了马士骥的圈套,取得的是两张废纸。如今一想,却未免令人切齿。假使你首领,不是素抱着不流血的宗旨,我早晚教他身上多一个透气的洞儿。”
柳青说到这里,不觉怒容满面。
鲁平看了笑道:“傻子!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别的事还去争他做什么?”
柳青道:“首领!那真的密约,怎么会进你的手?可以告诉我么?”
鲁平耸肩道:“告诉你么,其实事情也平淡之至,并没有什么奥妙……原来那晚我在马士骥家门前跳下马背,四望并无人迹,便把一副软玻璃手套,加在手上,又拿了一柄利剪,猱升到电线木杆上。把电线割断之后,一想你在里边,未必一定能够得手,因此我跳下电杆,重又悄悄掩进铁栅,伏在那石阶旁侧,一带冬青树底。浓密的树叶,恰巧遮住我的身子,不愁有人瞧破。
“一会儿,只见马士骥和那松井,带笑带说的从门口里出来,一步步走下石阶。我仔细观察,觉得他们的面色,十分兴奋,暗想他们倘然失去了密约,态度上决不会如此镇静。于是我便蹑手蹑足追踪在二人背后,直到马士骥送松井进汽车时,松井把马士骥的手,很亲密的握了一握,边操着日语低声道:‘今天的事,幸亏你细心,否则……’以下的话,却听不清楚。
“我细味他们的语意,心知不妙,趁松井汽车开时,急忙攀身在车后。不一刻,车已开到人迹稀少的地方,我遂取出刚才剪电线的剪刀,在左边的后轮上,用劲刺了个窟窿。松井那辆汽车,本是双轮制动的,经这一下子,驶行力自然立刻停顿。那时我从车后跳将出来,抢前一步,用手枪镇住松井并与那汽车夫,结果那位松井先生,倒很客气,双手捧了这密约,恭恭敬敬的赠给了我。我也不敢谦让,只索生受他了。”
柳青听到这里,禁不住好笑起来。鲁平却燃了支纸烟,慢慢地踱至窗前,掀开窗帷,向外一望,只见天空中的愁云惨雾,早已完全消失,远不像前几日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