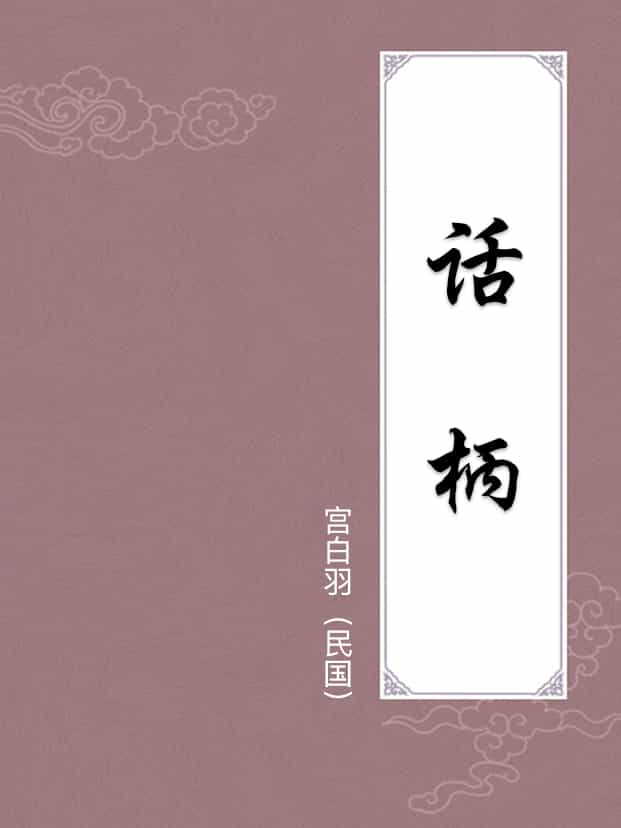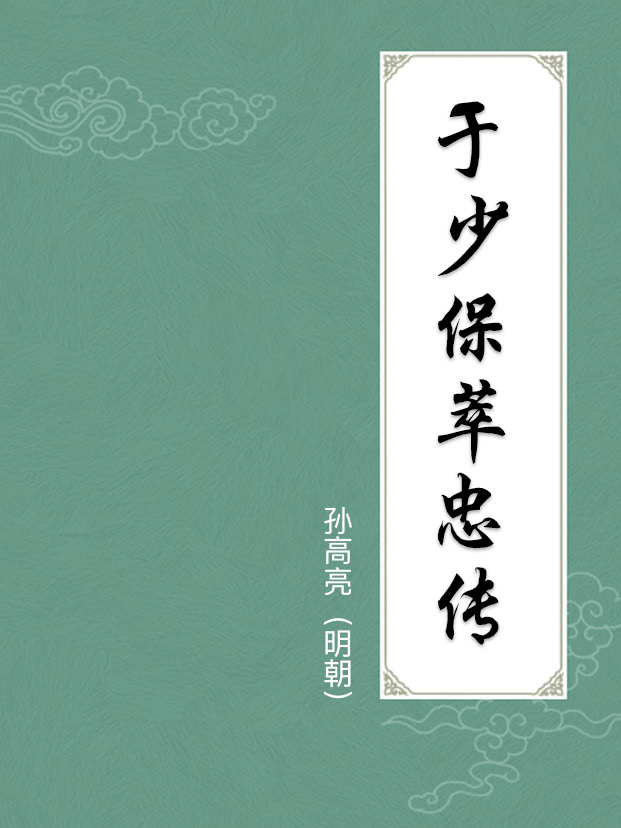大概在十五六岁小学毕业前后,开始了投稿生活。
我是很鲁钝的,当我考入小学高等一年级时,首次年考只得七十二分,名列乙等第末。我们的级任教师王先生(朴)最喜爱“小迸豆”;同学如丁朝树,吴国桢,都在十岁以下,人小而聪明,在班中很活跃。我与陈宾仓,李××之流,那时被叫作“傻大个儿”的,功课既不好,年长而又笨,王先生当然不喜欢我们,虽然我最敬爱他。
到了高小二年,我们这些傻大个儿忽然开了心窍,功课猛进:年考的分数,我已获得八十四分七。等到高三,我便与陈、李二君包办了月考前三名。大约我和陈君考第一的时候最多;记得一次月考,我十二门功课,有五门得一百分;年考的分数是九十二分几。
这些年幼的同学全被压下去了。我们傻大个是北方人,开悟的迟,这几个小孩是南方人;又且吴国桢们家中都请了教师补课,而我们是自己摸索。我的功课所以不好,最吃亏的是英语,因为我是由私塾编级入校,连二十六个字母还认不全。我自己实在没法,找到一家英文夜馆,只补习两个月,便已超列甲等了。
我在班中的地位,高一时代也是很不好的,既吃亏是外乡人,而又是傻大个,笨货,到高二,同学等便刮目相看了。同学中受了小说迷,和谜语热,做过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君受《镜花缘》的影响,拿铅笔纸册,写他的《君子国》。陈宾仓君就撰造八个英雄,以李乾,张坤,八卦为名,要破阵盗宝;他分明受了三十六友的影响。
其时我呢,读小说最多,却没有下笔。我那时已经开始翻译小说了。第一步入目的是石印本,文言的言情小说,我不很懂;第二部是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情侠》,和些侦探,探险小说。
当吴、陈二君撰述君子国、八卦阵的时候,我开始构思大侦探家了。但实际开始投稿,却是作戏评。
民国三年,高小毕业。我们是春季始业的,由是年起,改制秋季始业;我们要耽误半年,才得升考中学。我于是闲居无事,买书看杂志,炽起投稿热。我向母亲嫂嫂搜求民间口碑,要写稿寄给上海的小说周刊《礼拜六》;但是不知为甚么,那时并没投成。
第一篇的投稿是“戏评”。月出十四个铜元,定阅一份《戏剧新闻》(日刊),天天看,自己试着撰“菊国春秋”,署名“菊厂”。而且很认真,自定课程,每星期至少作两篇。这当然无酬,连一份赠报也得不到;但是一见登出来,虽然赔邮票稿纸,仍是很高兴。还闹了一个笑话,我用了“于戏”二字,其时还不懂这两字就念“呜呼”;自己望文生义当作“噫嘻”用,报上也照刊出来。有时候那编辑先生孙古纫、章弃材也给我删改。有一篇《灵芝说》,和《吉祥观剧记》,自以为文笔古典雅洁。那时候,袁项城正要称帝;《戏剧新闻》和别的剧刊,正为捧刘喜奎,大打笔仗。
入冬考入朝阳大学的附中,其时我甫结婚,我却搬到学校附近的公寓里去住。中二同学陈君曾问我:“报上的菊厂是不是阁下?”我得意极了。
在中华的《童子界》,商务的《少年》,《学生杂志》,也都投过稿;有时是小文,有时是一幅画,有时翻译英文课本中的小故事。《少年》杂志登了我一篇《财神与乞丐》,我第一次获到酬金,是六角书券。随后《礼拜六》周刊复活,改由周瘦鹃主编。我投去三篇小稿,得到瘦鹃的一封回信,我什袭珍藏的保存下来,然而丢了。稿也登出两篇,《茗盌余话》和《京津道上》;说是有酬金,到底没给钱。
在朝大附中修完二学年,附中因人少而解散;我改入京兆一中,结果倒退了差不多一年。从前我的文因胡乱模仿,非常怪诞,到此才稍稍入了正轨。
××××
大时代跟着到来,五四运动震撼了青年人的心。我们学校首先受了新文学运动的刺激的,是同班刘丹岩君和我。我两人同砚联席,同看新刊物,同读白话诗,还辩论过多少次。校中第一篇用新标点写的白话文,便是刘君和我的文章。题为《美国改持霸国主义论》,刘君作的是赞,加了许多叹号;我却是很长的一篇语体论文。
结果发文的时候,我向来在前六七名的,此次直耗到末后,国文教师才将我两人的大作发还。原文一字未改,并且说:“作演说是可以的。”作文当然不合了。等到毕业考试,监考员到场时,和学监闲谈,问到学生们有作白话文的没有?我和刘君遂给学校露了脸,学监谦以为傲的说:“第五班的某某作过。”又笑说:“新标点用的不对。”但校中图书馆管理王醒吾先生头脑很新,他的令郎又与我同班,我们就组起读书会来,《新潮》,《新青年》,新刊物都买。因为月捐图书费,我和同班评剧家的刘君,几乎冲突起来。
当五四大时代到来时,也正是我惨遭父丧之时;世界主义,互助论做了我精神的慰藉。毕业之后,急于找出路,曾到先父供职的那军队里挂名候差,这与我的希望趣味相差太远。
王醒吾先生和《持平报》有关系,我就大量的投稿,希望在报馆做点事。初写的小说不免有北京小报的气息;文言的短篇小说力仿林释,曾有《镜圆》一篇。又辑了些古笑林,名为《绝缨录》;并写了些短评。周作人先生译的《点滴》,和“晨报小说集”,当时对我们影响极大;我这才开始写新小说。有《厘捐局》,《两个铜元》,《哑妇》等篇;《两个铜元》是我妹莳荷写的,我修改了一遍,字数皆不及千,但自己很满意。时在民九。
××××
正经投稿,是民十在《北京晨报》附刊,鲁迅先生介绍的。那时,我已经考入邮局,从快信处得知周作人先生的详址,我试投了一封信,志在请他介绍投稿,头一封信却是找他借书,可是又以设立借书处做引子。自以为措辞很巧妙;不数日回信来了,署名周树人。说“周作人患肋膜炎,现在西山碧云寺养病,由我代答。”另外送我愿借的《域外小说集》,《欧洲文学史》,并借给我《杜威讲演》。原信是这样的:
××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页,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现特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七月二十九日
往来通讯,讨论文艺;以后又求见面。其时我厌倦了邮局的机械生活,头一天日夜工作二十二小时,第二天就休息二十四小时,如此轮流,实在歇不过来。我决计退职,拟考高师,信中顺便告诉了周树人先生。又把那篇《厘捐局》,《两个铜元》抄寄,请他介绍,说要从此以文为业。先生对我这两篇不满千言的作品,认为是随笔,不是小说,但仍给介刊《北京晨报》附刊和《妇女杂志》。对于我这辞了职业考学校,卖文章供学费的计划,周树人先生认为失计。函云:
××先生:
来信早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仅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颇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号数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未载。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八月十六日
××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作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每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购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作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甚么名字?再先生报考高师,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总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八月二十六日
由这信看,树人先生要介绍我译述小说了。我的回答是英文还可以勉强译述。又批评新小说,我说我最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说很雅逸。
先生复函承认鲁迅就是他自己,又谓冰心的文章虽雅逸,恐流于惨缘愁红;先生称许叶绍钧和落花生的作品不错。
这一封信,可惜我找不到了。但鲁迅就是和我通讯的周树人,却令我失惊而且狂喜。唠叨的写了一堆惊奇的话,所以九月五日先生的回信有“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正如今日的白羽姓白名羽一样。然而“不算甚奇”一句话,我和我妹披函都有点赧然了。
××先生:
前日匆匆寄上一函,想已到。《晨报》杂感本可随便寄去,但即登载,恐也未必送报,他对于我们是如此办的。寄《妇女杂志》的文章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问商务印书馆,除上月份之外,也没有一册;我日内去问上海本店去,倘有便教他寄来。《妇女杂志》知已买到,现在寄上《说报》八月份一本,但可惜里面恰恰没有叶、落两人的作品。
周树人,九月五日
我去拜访鲁迅先生,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坐在两个文学家之前,大谈一阵。鲁迅先生透视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温柔敦厚的面容和谈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此后又拜访三两次,承作人先生把契科夫小说的英译借给我;我译出五六篇,都由鲁迅介登《晨报》,得了千字一元的稿费。我自己又买了几本外国小说。但是我的英文很坏,抱着字典译书,错误仍然很多;鲁迅先生,作人先生都给我改译过。
青年人在一个名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恨不得把自己的乳名都要告诉他;我于是天天去麻烦,不久闹得鲁迅先生不敢见我了。正与我的同学刘丹岩一样,他也是因为倾慕胡适先生,天天去起腻,终于被胡适之热赶出来了:“请你到那边谈谈去吧。”
这也是循环往复,我至今也是天天要收到几封信,不时接见不相识的朋友。
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不外学生生活;鲁迅指出这一点,我就附和说:“是的,这样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在写了。”鲁迅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着同情与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我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变换题材了。”鲁迅又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是的,这只在乎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手法。他一连几个“但是”,当时很使我诧然。
我的那篇《厘捐局》,写一个卖鸡蛋的老人,被厘捐局压榨,曾用“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这样的句子,鲁迅先生特意给我一封信,指出“可怜”二字近乎感叹;可否换用“只是”二字。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为人来:第一,他告诉我作小说不可夹叙夹议;第二,他告诉我他的不苟精神。“世故老人”是长虹攻击他的恶报,我却以为这四字正说尽了鲁迅的特长。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认为满意的是《孔乙己》,他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但我喜爱的却是他那篇《药》,和《彷徨》中的《伤逝》。
××××
我不听鲁迅先生的劝告,果然卖文求学的计划归于失败。等到举室南迁被匪,一败涂地,又逃回来;我就不得已在通州就了私馆,从此断了求学之念。我的束修不足赡家,受了朋友劝告,正式开始了投时的卖文,译作小说,搜辑趣话,给北京《益世报》,每月得六七元,稍补家用,每千字赚得一元。
我旋失业,经过了极大困苦,极大挣扎,认识了《世界日报》的何仁甫君,承他陌路援手,推食解衣,介绍投稿;以千字一元的代价,于一个月内,给《世界日报》的“妇女界”写了一万一千余字;给酬时却被主者核减为大洋四元。我因一怒,从此搁笔。何君自觉对不住我,我去了一封信,解释权不属彼;偏偏这封信又被编者看见了,但这事与编者也无关,引起了误会。
但是一万一千字稿费四元,到底给了我很重的打击,深信鲁迅之言非欺我也。这样子累死也吃不饱饭。
何君又告诉我,《共和新报》,《民立晚报》新出版,我就每处去了一封自荐信。数日后,《共和新报》来信很客气,《民立晚报》来信很简捷,但说一时没机会,容后设法。但只隔了半个月,《民立晚报》招了我去,当校对兼写稿版,月薪二十元。却是发薪时,又被社长太太扣了四元。说是给他十二元,他也干。结果是十六元,果然我干了。不干怎么办呢?我失业已一年了。
不数月,《民立晚报》因登《萍水相逢白日中》,而被停刊,我又失业,可是暂时不敢卖文了。
直到民十五,《世界日报》明珠版招聘特约撰述,我又承何君指示,以通夕之力,写了短稿七篇,投寄了去。由明珠编辑张恨水评定,结果就选中了我。到宣内未英胡同,和恨水接洽;我诧异这个文人,如此巨眼响喉,但他的嗅觉却灵敏。面谈之下,他说:“K先生可以每天给明珠写一篇稿子,有功夫再给夜光写一点,三五百字就行。哈,每月十元,而且是每日两篇。”
我方才醒悟,那一万一千字的稿费四元,并非稀奇事,一向如此的。但我不能不做,就作了起来。事后才听说,这次特约撰述,实在只选中我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恨水先生,那时的稿费也不过千字二元。文人是如此的不值钱,至少在北方是这样的。现在我的稿费版租固然较多了,这无非是投时,侥幸;而况且俾夜作昼,弄出心跳、肋痛、吐血的病来。扶病卖文,只怕不是快愉的事吧!然而没法子避逃。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