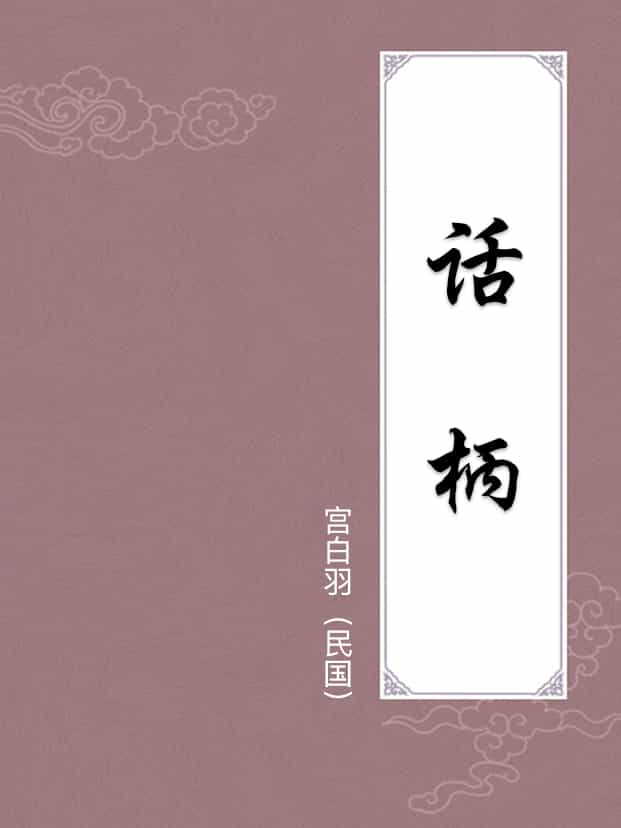惠及禽兽和泽及枯骨,都是古圣先王,尧舜禹汤之流干的大德行事;史官振笔揄扬,难得的很。但是说出来像很自负,此等区区,究竟算不得大不了的事。故事多的我,从小早就干过几椿了;或者“从小看大”,我真是天纵圣哲的人,亦未可知。然而现在,倒霉不惜再三的我,竟落到这步田地,王不成王,圣不成圣,提起来好不惭惶。
有人说:“是耽读《石头记》,误了圣王的前程。”此话不为无理。又道是这大约就是所谓“质美未学”,所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那么后天的环境,巨然断送了一个伏地圣人。于此可见“寒门式微”,着实可叹!而且中国时局这么乱,想来也就无怪其然的了。
因此无人时,自己往往怜惜自己;虽是一事无成,半生潦倒;转想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云:“如此如彼”;我这倒霉,也许事非偶然。有朝一日,若我为王,自有那直笔史官们,把我来颂扬;我若成圣,也当有护法门徒们,替我鼓吹;或者不惜重资,径编一本《白羽先生言行录》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岂不甚好?无奈时到于今,我还是个文丐,这宗盛举,兀自无人代办。固是来日方长,事尚可缓;但恐一旦溘先朝露,少时之风流余韻,难免传闻失实。倒莫如趁早由我自己动手,掉一句文说:“子又安忍以‘今日之我’之不肖,致泯没‘昨日之我’之至行大德哉!”那么此刻,就让我接着说一说:我是如何以七八岁的小孩子,而惠及禽兽。
××××
我七八岁时,随父宦游,住在八棵树;父亲就是那地方马步元字军的长官。虽然叫“军”,只得一营;干脆说,当过二十年营长的父亲,彼时还是营长。而八棵树自然是地名,属当时奉天省的开原县,又叫清河沟。
这山沟子地方,胡匪是多的,不时出没,所以要官军驻扎,安民缉盗。但是,当地的大富户、大地主,为求保全生命财产,一方要结纳官府,同时还得应酬盗魁,双管齐下,才得安居乐业。一个打点不到,地僻人稀,红胡子抽冷子来了,当然要撕票。而红缨帽呢,给他个勾结土匪,窝藏大盗的罪名,谁能受得了!因此那地方的富家,一个个都是畏官如盗,畏盗如官,两方面都得应付到。甚至家大业大的人,往往叫他们的子侄辈一个从军当兵,一个入伙为盗,以期面面周到。有的来了,都是自家人,有个照应。然而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只在前清时代。
而我的父亲呢,是关里人;虽然“久历戎行,老经练达”,哪懂关外这些事故?只知有盗捕盗,无盗练兵;分外一点,不过是应酬上司同官,延纳当地绅董罢了。所以一年后交卸时,在省垣遇见久住关东的岳父,他叫着父亲的号,羡慕不置的说:“你这回可发财了,我想你至少也有十万。”父亲却诧异了,因为实际上,他连几千还没得挣上。
这不是父亲的廉隅。我只能吹我自己,我不便替父亲吹。他老人家不过是做事小心谨慎罢了,所以当地大财主无缘无故,送几千几百银子来,决不敢收。岂止不敢收,而且煞费疑猜。至于几百几十,只要是干礼,也是立即拒绝的。
这一来吓坏了大财主,误以为父亲食嗓大,不知要弄甚么大事故呢。于是想尽方法,打通内线,花了百数两银子,从父亲手下旧人口中,打听明白了底细;才晓得这任新官,是个胆小的没外汉,这才放了心。从此传播出去,大家改送湿礼,袍料皮货,首饰玩物不用说,甚么人参鹿茸,甚么獐狍麋鹿,逢年过节,便一车车送来。父亲呢,是东西少了便收,价钱贵了便吃惊。他只恐上官查出来,落个贪赃诈财的罪名,有性命之忧。他老人家哪料想发财的地方不发财,反倒辜负了所谓恩上特委肥缺的好意呢!
于是一年过去,父亲终于晓得了;晓得这是当地风气。新官到任,富绅巨室照例奉送白银;并且又晓得前任官三年光景,落了二十万(这自然做得太歹毒了。)岳父在不如八棵树的地方,驻防十几个月,家产也增到五六万。然而父亲不收干礼的廉名,已然传出去了,而且转年移防,好机会从此错过。
但是父亲临行时,毕竟也略有所得,那就是装在两只大木箱尚且装不了的万名伞,德政匾。
××××
当我还没有出关时,我就听说:“关东城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等到我随父宦游,侨居八棵树那个山沟子的时候,这三宗宝我都看见了。
这里所谓宝,自然说的是当地的特产。但我那时还小,七八岁的小孩子,猛听说宝,立即联想到《封神榜》上李靖的塔、土行孙的绳;以为这总是关东镇省的法宝了。及至目睹,“原来是这样”,我便大失所望了。从此对这关东省三宗宝,感觉不出兴趣。
然而关东的物事,引起我的兴趣的,也不是没有;像那活鹿,活獐,尤其是活狍子,我都爱看。狍子这东西,像驴而身小,像鹿而无角;那大小极似香獐子;但它脐上没麝香,所以它只是个杀材货,除了吃肉,没有人养豢它作玩物的。然而我家是例外,为了我嫌鹿大,我家就养活着这么两个,是一公一母。
起初,我父先到八棵树,随后才派人入关接家眷,已经快到旧年底了。当地富户照新官到任的老例,趁这机会纷纷送礼。送白银固然干脆,无奈“这位大人外行胆小”,于是改送湿礼。人参鹿茸、貂皮狐腿、钟表尺头,是不用说了;獐狍麋鹿百十只,可惜都是死的;至于活的,才仅仅一对。
野鸡是可以做汤的,这些死狍子可怎么吃呢?关外人初到关里,免不了露怯;关里人乍出关外,又何尝不如此?于是整块炖吃,不受吃;切丝炒吃,也不受吃;试尽法子,煎炒烹炸,吃着都不是味儿。没法子,腌了几只;其余便转送了别人。
转过年来,忽然想起那腌着的,取出来这么一蒸,这么一尝;这回可是味儿了,比板鸭火腿还香。异味真是异味,早知如此,一只也舍不得送人,都腌上它;是的,都把它腌上。现在吃完了,也没人送了;因为那时父亲已经卸任回省了,只家眷一时还未及搬取。
至于那一对活的,乃是当地一个绅士派人送礼,听了我闹着要活的,特地找寻来,给少爷玩的。果然这一对,我很爱惜它们;把它们装在一只大木笼里,我天天看着它们吃豇豆,喝凉水。不久这狍养豢熟了,便放出笼外;满院乱跑。它们拉的干而圆的粪球,也是我的玩艺儿;把来当作丸药,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给这个一包,给那个一包。
“少爷,脏!”
“不脏,好玩。”
关外草搭得后房檐,是矮到小孩子都可以爬上去的,而前沿却很高。我天天追赶着狍子玩耍,把它们追急了,就从后簷跳上房去乱跑,我也就追上去;把好好的草房,践踏得不成模样。大人们又怕我摔着,又怕踩漏了房,不断地吆喝着,我是满不理会。
忽然一天,发生不幸的事了。前院房东家的大狗扑进来,这一对狍子吓得乱窜。狗就很凶的嗥叫着,追,咬,把一双狍子又追到后房檐上去了。于是狗和狍子在房顶上乱窜起来,由后山追到前山。急的我大叫:“看狗看狗!”然而晚了,追的太凶了,这只猎狗叼住了狍子的脖颈,狍子挣命的摆脱,在房上翻滚起来。房上的茅草很滑,那狍子和狗一齐从前沿摔下去。前沿及地一丈四五尺高,狍子吱的一叫,后退竟摔折了一条。那可恶的狗也摔得汪的一声叫,撒嘴跑开了。
我的狍子摔折了腿,我的心充满了愤恨与悲哀。大人们说:“坏了一条腿,宰了吃吧。”我哭着说:“那不成!要宰就宰那狗。”于是不宰了,我也就从此多事了。第一,我先央告大人,(这自然是最爱我的二伯父了,别人谁管呢?)叫把营中的刀伤药,给狍子敷上。又仿照从前听过的折腿燕子的故事,叫拿棉花木板,替它缠上腿。然后,把它养在二伯父屋里,同我一块睡觉;它的窝也用稻草烂棉花铺上,还有豇豆、凉水,一一都摆在它面前,教它可以不必起来,就能够着吃。
我仍不放心,怕它吃喝完了,没人给它添食添水;所以我每天早晨上学,必要嘱托二伯父一遍:“千万不要忘了抓豆倒水。”下晚放学回来,进门头一句就问:“喂了狍子了么?”偶然二伯父忘记了喂它,当我下学回来,一看狍子面前的豇豆凉水没有了,我就大哭大闹起来。这还不算,又把那没伤的狍子,也放进屋里来,为的是给它做伴。
这样一来,我的一颗心,都系在瘸腿狍子身上了。小孩子吃喝玩闹,心里本来没有一点牵挂;而现在,竟害得我这样,甚至在学房还惦记豇豆凉水;没人时还独自流泪,愤恨大人不好好替我照料它。这痛苦不一定是哀怜狍子,替它担忧分苦。那只是心中凭空横插着一件事,搁又搁不下,放又放不下,实在是我从未经过滋味,太教我不自在不自由了。因此我唯一的愿望,只盼它早占勿药,免得存在我心里是块病。至于大人们的奚落,说“它是我哪辈子的媳妇”,这一类话,我倒是不怕的。
终于狍子快好了,它居然一瘸一拐地往院里跑了,我的心也觉得轻松多了。
但意外的事忽又发生了。
有一天,我上学去了,那只大狗又钻进来了。于是瘸腿的狍子被它咬住咽喉,狍子的保护人不在,院中没有一人,狍子的性命终于葬送在狗口之中了。大人后来看见了,为了我的缘故,大大吃了一惊。他们说:“怎么好,T儿回来,又要心疼的造反了。”于是他们想趁我不在,把它的尸体埋藏起来;然而我这时恰巧回来了。
他们藏之不迭,束手无计的看着我。他们猜想:“咬伤”了还不依,而现在可是“咬死”了,一定有一番打闹……
“哈哈!”他们都没猜着。我立在狍子尸体旁边,验看了一遍,看它的确是死了,我从此再不必牵挂着豇豆和凉水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从此落地了。
“我可熬出来了!”我说:“腌起来吧。”
(十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