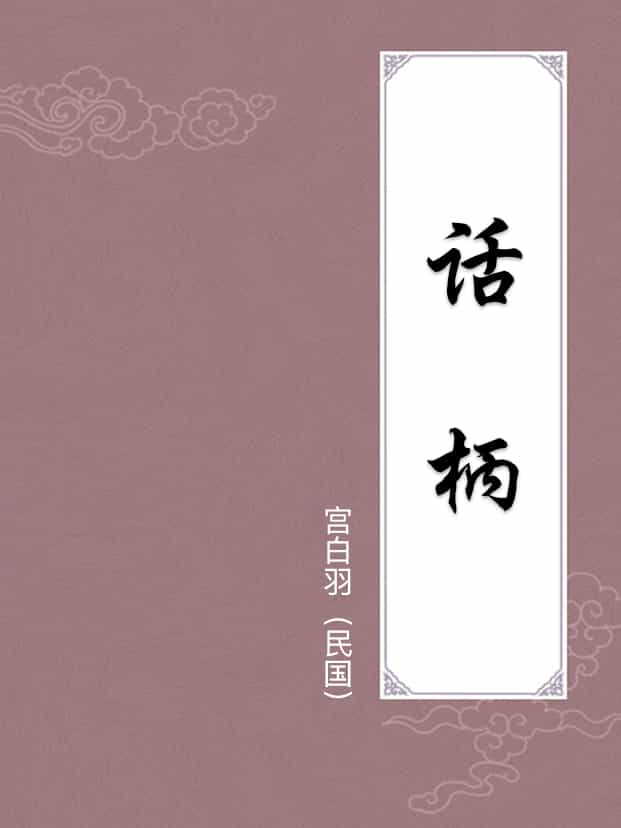我会看小说了,可喜可贺!
小说不叫小说,那时叫闲书。我会看闲书了,大约是在七岁至九岁时。方其时,我家正住在奉天省昌图县,而家中请着一位姓李的李老夫子,教给我念书、写字、画小人、下棋、看闲书。
向日哄着我玩的小福子,原是我父亲部下的一个老兵的儿子,和他母亲跟我们同院住。他本来略识书字,年约十四五,也是他的父母的宠儿,这时就做了我的伴读。另外还有一个,是童仆小憨头,一个无父之儿,长我七八岁,不甚识字,常被我骂为“贼种”的。(这里面自然有点缘故。)
父亲不在家,老师太和气,书房中由着我们几个反;画小人、看闲书的功课,往往夺了念书习字的钟点。
旧时的塾师对待学生,都不准看所谓闲书,说怕散了心。而这位李老师独不,他素来有些“痰气”,他性格儿又软,而他又是混饭吃的,据做饭的大师傅张发财说。因此学生们看闲书,他是不肯管的,而且有时候他反倒奖励。他何以要奖励呢?因为这样子,书房中反倒消停些。
然而奖励看闲书,又不止和气的李老师,还有我的母亲。
每天下学了,吃饭了,掌灯了,喝茶了,“小福子过来,说段书听。”于是母亲坐在床上听;小福子的娘弄茶弄水,坐在他的儿子对面,满脸含笑地听;而我呢,更是得意,喜孜孜地走着跳着听,无休无止地听。
小福子说得舌焦唇敝,打哈欠,揉眼睛,装蒜,他娘心疼。他娘便说:“小福子困了,太太,叫小福子睡去罢。”于是小福子放了赦,娘俩预备着走,而我还是不依不饶;而小福子不理我,他去睡他的。
我怒了,勃然怒了。我之怒很有理由,小福子最怕得是说闲书;然而他可是装困回家之后,并不就睡。他往往跟同院一个学生,或小憨头,或别的几个年齿相仿的,凑在一处,津津有味地你一句,我一句,大谈黄天霸、姜太公,一谈半天,毫无倦意。但教他照本说时,他又道累了,困了,舌头干了;跟人家谈,一样地费唇舌,怎么不困不累?这岂非欺人太甚么?
我扳着脖颈,发词诘责他。他却道:“随口谈不吃力,照本说累人。”这话于今想来,委实有理,在当时我可哪理会呢!当时是我断定他,分明晓得我不会自己看,所以故意的拿捏我,彆闷我,于是我勃然怒了。
我怒了,大哭大闹;之后,也就奋然地立定志气,我将不受你这坏蛋的拿捏了,我将自己看。然而,其始,我之看闲书,不过看“绣像”,看小人;现在,为和小福子赌气计,我将决计要自己去看正文了。
自己看不懂,我太小了;我刚念了不到一年书,而且又不曾正经念,我当然看不懂了。但是,我有法子了,我看熟书,我看小憨头常唱过的“狗儿邦邦咬喂,奴的心好焦唉”的唱本,和小福子说过的《瓦岗寨》鼓儿词。
这样子,自己“顺文”往下蒙着看,于是“忽听大门外呀,有人叫一声唉”之类,不久朗朗上口了。并且秦叔宝、程咬金们,也再度和我相见了。好在书房中有现成的问字师;照此也就是过了十天半月光景,居然我自己连别的书也会朦了,连评词也敢看了。终于《大八义》、《小八义》、《说唐》、《说岳》、《施公案》、《彭公案》,以至于比较看着吃力的《水浒》、《西游》、《封神》、《三国》等书,待到随父宦游,移居安达时,早就一一得饱眼福了。
当那时,我真真快意极了,于是我说:
“妈巴子的,不用彆人,我也会看了。”
“少爷骂人?”
“骂的就是你!”
××××
当我初看《水浒》时,我是何等快乐呢!梁山泊上,替天行道,一百单八将,个个呵活,个个在我眼前晃;甚至睡梦中,也和他们相见。但是小孩子的读法,是和金圣叹不同的,宋江之阴柔奸诈、林冲之悲愤、石秀之刻毒,以及什么,“乱自上生”的话头,我看了都不屑理会;我最倾倒的,乃是武松、鲁达、李逵,这几个人。他们的武艺不用说了,他们的鲁莽,实在爱杀人。他们能吃能喝,大酒大肉,狼吞虎咽,更教人看着眼热,说来口谗。
有那么一天,吃完了午饭,正抱着书本,躺在床上,眈眈的欣赏时,可就恰恰遇到黑旋风大吃牛肉,大喝烧酒那一节上了。他一顿就是牛肉几盘,烧酒几斤,而且又吃得这么香甜,不由招得我心中艳羡,口中流涎。于是我,武松打虎似的,从床头蓦地一跃而起,立刻打定主意,要做英雄。
但是仓促之间,也没有牛肉,也没有烧酒。于是我一阵风跑到厨房,打开柜橱,柜橱里也是没有牛肉烧酒。奈何?两个大馒头,一盘子炒肉,“姑以代之”,端了过来。酒呢?又跑到书房,把先生的一瓶五加皮偷来。
馒头,酒,肉,一一摆在面前;而《水浒传》,始终没有抛开,手中还捏着一卷。都收拾好了,于是吃起来。
我也想大口喝酒,我也想大口吃肉,我也想狼吞虎咽……然而我太不济了,太不英雄了。酒,我口对瓶口,只灌了一下子,便辣得吐舌流泪。馒头也只吃了多半个,肉也只吃了几口,便都格格不入了,我太饭桶了!不,连饭桶的资格也够不上。总之,我实在充不起英雄!
几分钟过去,“酒泛上来”;一方面,身子悠悠忽忽。没看《封神》,竟架起云来;另一方面,没摆群英会,竟装了周郎,大吐特吐起来,把刚才吃的午饭都给倒出来了。最爱我的二伯父吓了一跳。
“T儿,怎么了?”
我不敢说偷了先生的酒,我只说:
“有点不舒泰。”
是的,有点不舒泰,尤其是肚里。
“黑旋风,你害苦了我了!”
(十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