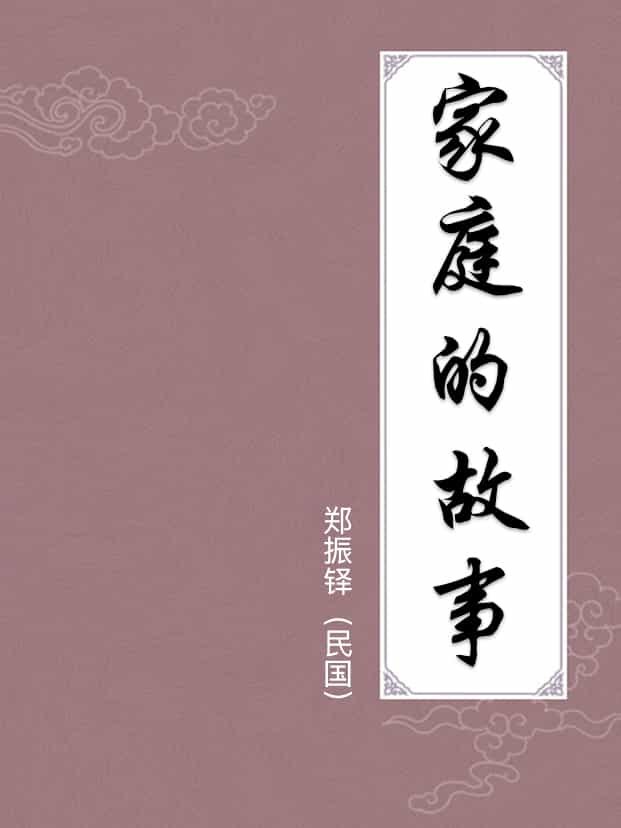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四叔是生了不到几个月便死的,我对他自然一点印象也沒有,家里人也从不曾提起过他。二叔景止,三叔凌谷,在我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曾給我以不少的好印象。三叔凌谷很早的便到北京讀書去了。我还記得很淸楚,当我九、十岁时,一个夏天,天井里的一棵大榆树正把綠蔭罩滿了半片砖鋪的空地,連客厅也碧阴阴有些凉意,而蝉声在浓密的树叶間,嘰——嘰——嘰——不住的鳴着,似乎催人午睡。在这时,三叔凌谷由京中放暑假回家了。他带了什么别的东西同回,我已不記得,我所記得的,是,他經过上海时,曾特地为我买了好几本洋装厚紙的練习簿,一打鉛笔,許多本紅皮面綠皮面的敎科書。大約,他記得家中的我,是应該讀这些書的时候了。这些書里都有許多美丽的图,仅那紅的綠的皮面已足够引动我的喜悅了。你們猜猜,我从正式的从师开蒙起,讀的都是乾乾燥燥的莫測高深的《三字經》、《千字文》、《大学》、《中庸》、《論語》,那印刷是又粗又劣,那紙张是粗黃难看,如今却見那些光光的白紙上,印上了整洁的字迹,而且每一頁或每二頁便有一幅未之前見的图画,画着尧、舜、武王、周公、刘邦、項羽的是历史敎科書;画着人身的形状,骨胳的构造,肺脏、心脏的位置的是生理卫生敎科書;画着上海、北京的风景,山海关、万里长城的画片,中国二十二省的如秋海棠叶子似的全图的是地理敎科書;画着馬呀、羊呀、牛呀、芙蓉花呀、靑蛙呀的是动植物敎科書。呵,这許多有趣的書,这許多有趣的图,眞使我应接不暇!我也曾听見尧、舜、周公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們是哪样的一个神气;我也知道上海、万里长城,而上海与万里长城的眞实印象,見了这些画后方才有些淸楚。祖父回来了,我連忙拿書到他跟前,指点給他看,这是尧,这是周公。呵,在这个夏天里,我不知怎样的竟成了一个勤讀的孩子,天天捧了这些書請敎三叔,請敎祖父,似欲窺那这些書中的秘密,这些图中的意义,我的有限的已認識的字,眞不够应用,然而在这个夏天里我的字彙却增加得很快。第一次使我与广大外面世界接触的,第一次使我有了科学的常識,知道了大自然的一斑一点的內容的,便是三叔給我的这些紅皮面綠皮面的敎科書。三叔使我燃起无限量的好奇心了!这事我很淸楚的記得,我永不能忘記。他还和祖父商量着,要在暑假后,送我进学堂。而他給我的一打鉛笔,几本簿子,在我也是未之前見的。我所見的是烏黑的墨,是柔輭的烏黑的毛笔,是墨磨得淡了些,写下去便要暈开去的毛边紙、連史紙。如今这些笔,这些紙,却不用磨墨便可以写字了,不必再把手上嘴边,弄得烏黑的,要被母亲拉过去一边說着,一边强用毛巾把墨漬擦去。而且我还偸偸的在簿子里撕下一二张那又白又光的厚紙下来,强着秋香替我折了一两只紙船,浮在水缸面上,居然可以浮着不沈下去,不比那些毛边紙做的紙船,一放上水面,便湿透的,便散开了。呵,这个夏天,眞是一个奇异的夏天,我居然不再出去和街上的孩子們“擂錢”了,居然不再和姊妹以及秋香們賭弹“柿瓤子”了。我乱翻着这些敎科書,我用鉛笔乱画着,我仿佛已把全个世界的学問都握在手里了。三叔后来还帮助我不少,一直帮助我到大学毕业,能够自立为止,然而使我最不能忘記的,却是这一个夏天的这些神奇的贈品。
二叔景止也不常在家。他常常在外面跑。他的希望很大,他想成一个实业家。他曾买了許多的原料,在自己家里用了好几个大鍋,制造肥皂,居然一块一块造成了,却一块也卖不出去,沒有一个人相信他所造的肥皂,他們相信的是“日光皂”,来路貨,經用而且能洗得东西乾凈。于是二叔景止便把这些微黃的方块的都分送了亲戚朋友,而白亏折一大笔本錢。他又想制造新式皮箱,雇了好几个工匠,买了許多张牛皮,許多的木板,終日的在鋸着,敲着,釘着,皮箱居然造成了几只,却又是沒有一个人来領敎,他們要的是旧式的笨重的板箱或皮箱,不要这些新式的。他只好送了几只給兄弟們,自己留下两只带了出門,而停止了这个实业的企图。他还曾自己造了一只新的舢板船,油漆得很講究,还燃点了明亮亮的两盞上海带来的保险挂灯。这使全城的人都紛紛的議論着,且紛紛的来探望着。他曾領我去坐过几次这个船。我至今,仿佛还覚得生平沒有坐过那末舒服而且漂亮的船。这船在狹小的河道里,浮着,駛着,簡直如一只皇后坐的画舫。然而不久,他又覚得厌倦了,便把船上的保险挂灯、方桌子、布幔,都搬取到家里来,而听任这个空空的船壳,系在岸边柳树干上。而他自己又出外漂流去了。他出外了好几年,一封信也沒有,一个錢也不寄回来,突然的又回来了。又在計划着一个不能成功的企图。在我幼年,在我少年,二叔在我印象中眞是又神奇、又伟大的一个人物,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不大理会我,但我常常在他身边詫异的望着他在工作。我有时也曾拾取了他所弃去的余材,来仿着他做这些神奇的东西。当然不过兒戏而已,却也往往使我离开童年的恶戏而专心做这些可笑的工作,譬如我也在做很小的小木箱、皮箱之类。
然而最使我紀念着的,还是五叔春荊。
三叔常在学校里,两年三年才回家一次,二叔則常飘流在外,算不定他什么时候回来,于是家里便只有五叔春荆在着。父亲也是常在外面就事,不大来家的。
說来可怪,我对于五叔的印象,实在有些想不起来了,然而他却是我一个最在心中紀念着的人物。这个紀念,祖母至今还常时叹息的把我挑动。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自然到了現在,已記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然而祖母却时时的对我提起他。她每每微叹的說道:
“你五叔是如何的疼爱你,今天是他的生忌,你应該多对他叩几个头。”这时祖先的神厨前的桌上,是点了一双紅烛,香爐里插了三支香,放了几双筷子,几个酒杯,还有五大盌热菜。于是她又說起五叔的故事来。她說,五叔是几个叔父中最孝順,最听話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說,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給她打过駡过。他是温温和和的,对什么人都和气,讀書又用功。常常的几个哥哥都出去玩去了,而他还独坐在書房里看書,一定要等到天黑了,她在窗外叫道:“不要讀了罢,天黑了,眼睛要坏了呢!”他方才肯放下書本,走出微明的天井里散散步。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是从沒有对丫头,对老媽子,对当差的,說过一句粗重的話的,他对他們,也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兒。“当他死时,”祖母道:“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連小丫头也落泪了,連你的奶娘也心里难过了好几天。”这时,她又回忆起这伤心的情景来了,她默默的不言了一会,沈着脸,似乎心里很凄楚。她道:“想不到你五叔这样好的一个人,会死的那末早!”
当我从学堂里放夜学回家,第二天的功課已預备完了时,每到祖母的烟鋪上坐着,看着她慢慢的烧着烟泡,看着她嗤、嗤、嗤的吸着烟。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这时,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每对我說起五叔的事来。有一天,我在学堂里考了一次甲等前五名,把校长的奖品,一本有图的故事集,带了回家。这一夜,坐在烟鋪上时,便把它翻来閑着。祖母道:“要是你五叔还在,見了你得了这本書,他将怎样的喜欢呢?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你現在大約已經都不記得了罢?你五叔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有一次,你二叔曾喜喜欢欢的从奶娘怀抱里,把你接了过来抱着。他一个不小心,竟把你摔堕地板上了,这使全家都十分的惊惶。你二叔从此不抱你。而你五叔就从沒有这样的不小心,他沒有摔过你一次。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見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那时,你还是很肥胖呢,沒有現在的瘦——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們都說他比奶娘还会哄騙孩子呢。当你哭着不肯止息时,他来了,把你抱接过去了,而你便見笑靨。全家都說,你和你五叔緣分特别的好。象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唉,可惜你五叔死得太早!”
她又說起,五叔的身上常被我撒了尿。他正抱了我在厅上散步,忽然身上覚得有一陣热气,那便是我撒尿在他身上了。那时,我还不到一岁,自然不会說要撒尿。他一点也不憎厌的,先把我交还了奶娘,然后到自己房里,另換一身的衣服。奶娘道:“五叔叔,不要再抱他了,撒了一身的尿。”然而他还是抱,还是又稳重、又有姿势的抱着。我現在已想象不出那时在他怀抱中是如何的舒服安适,然而我每見了一个孩子睡在他的搖篮車里,給他母亲或奶媽推着向公园綠蔭底下放着时,我每想,我少时在五叔怀抱中时一定比这个孩子还舒服安适。有一次,他抱了我坐在他膝上,翻一本有图的書指点給我看。我的小手指正在乱点着,乱舞着,嘴里正在呀呀的叫着时,忽然內急,撒了許多屎出来,而尿布又沒有包好,于是他的一件新的蓝布长衫上又染滿了黃屎。奶娘連忙跑了过来,把我抱开,說道:“又撒了你五叔叔一身的屎!下次眞不該再抱你玩了!”而他还是一点也不憎厌,还是常常的抱我。
祖母又說起,家里的杂事,沒人管,要不亏五叔在家,她眞是麻煩不了。一切記賬,吩咐底下人买什么,什么,都是五叔經管的;而他还要讀書,常常讀到天色黑了,快点灯了,还不肯停止。她又說起,我少时出天花,要不亏五叔的热心,忙着請医生,亲自去取藥,到菩薩面前去烧香許願,眞沒有那末快好。她說道:“你出天花时,你五叔眞是着急,天天为你忙着,書也无心念了,請医生,取藥,还要煎藥,他也亲自动手。一直等到你的病好了,他方才放心。你現在都不記得了罢!”
眞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的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認識了一位和藹无比、温柔敦厚的叔父。不知怎样,这位不大認識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之一。
五叔写得一手好楷書;我曾見过他鈔录的几大册古文,还見到一册他自己做的試帖詩,那些字体,个个都工整异常,眞是一笔不苟,一画不乱。我沒有看見过那末样細心而有恒的人。祖母說,他的記賬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用工楷写下来。大約他生平沒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沒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
祖母曾把他所以病死的原因,很詳細的吿訴过我們,而且不止吿訴过一次。她凄楚的述說着,我們也黯然的靜听着。夜間悄悄无声,連一根針落地的响声都可以听得見,而如豆的烟灯,在床上放着微光,如豆的油灯,在桌上放着微光。房里是朦朧的如被罩在一层阴影之下。这样凄楚的故事,在这样凄楚的境地里述說着,由一位白发萧萧的老人家,顫声的述說着,啊,这还不够凄凉么?仿佛房間是阴惨惨的,仿佛这位温柔敦厚的五叔是随了祖母的述說而漸漸的重現于朦朧的灯光之下。
下面是祖母的話。
祖母每过了几年,总要回到故乡游玩一次。那时,輪船还沒有呢。由浙江回到我們的故乡福建,只有两条路程。一条是水路,因“閩船”运貨回家之便而附搭归去;一条是旱道,越仙霞岭而南。祖母不願意走水路,总是沿了这条旱道走。她叫了几乘轎子,自己坐了一乘,五叔坐了一乘——大概总是五叔跟护着她回去的时候为多——日子又可縮短,又比閩船舒服些。有一次,她又是这样的回去了。仍旧是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我們的祖姨——祖母的最小的妹妹——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一同出来,搬到我們家里来同住。她夫家是一个近房的亲戚都沒有,她自己又不曾生养过一个孩子,在家乡是异常的孤寂。于是她踌躇了几时,便也同意于祖母的提議,决定把所有的家产都搬出来。她把房子卖掉,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便专雇了一只閩船。她因为船上很淸凈,且怕旱路辛苦,便决意坐了船。祖母則仍旧由旱路走。有五老爹伴侣着她同走。五叔則和几个老家人护送了祖姨,由水路走。船上一个杂客也沒有,一点貨物也沒有。头几天很順风,走得又快,在船上的人都很高兴。祖姨道:“这一趟出来,遇到这样好风,运道不坏。也許要比走旱路的倒先到家呢。”海浪微微的撫拍着船身,海风微微的吹拂着,天上的云片,如輕絮似的,微微的平貼于晴空。水手高兴得唱起歌来。沿船都是小小的孤島,荒蕪而无居民。有时还可遇見几只打漁的船。这样順利的走出了福建省境,直向北走,已經走到玉环厅的轄境了,不到几天便可到目的地了。突然,有一天,风色大变,海水汹涌着,船身顚簸不定,側左側右。祖姨躺在床上起不来,五叔也很覚得头暈。天空是阴冥冥的,似乎要由上面一直傾落下来,和汹涌的海水合而为一,而把这只客船卷吞在当中了。水手个个都忙得忘記了吃飯。他們想找一个好海湾去躲避这場风浪。又怕遇到了礁石,又不敢离岸过远。这样的飘泊了一天两天。天气漸漸的好了,又看見一大片蓝蓝的天空,又看見輝煌的太阳光了。船上的人,如从死神嘴里又逃了出来一样。正在舒适的做飯吃,正在扯滿了篷預备迎风疾行时,忽然船底澎的一声。船身大震了一下,桌上的碗和瓶子都跌在船板上碎了。人人脸如土色,知道是触礁了。祖姨脸色更白得死人般的,只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五叔也一筹莫展。船上老大进艙来說了,說这船已坏,不能再走了,好在离岸很近,大家坐舢板上岸,由旱路走罢。船擱浅在礁上,一时不会沉下去,行李皮箱,等上岸后再打发人再取罢。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細軟,和五叔老家人們都上了舢板。这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还不能靠岸。于是所有的人,都只好涉水而趋岸。五叔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在水中走着,还負着祖姨一同上岸。遇了这場大险,幸亏人一个都沒有伤。祖姨全副財产,都在船上,上了岸后,非常的不放心,她迫着五叔去找当地的土人代运行李下船。然而,这些行李已不必她費心顧虑到。沿岸的土人,一得到有船擱礁的消息,便个个人都乘了小舢板,到了大船边。上了船,見了东西就搬,搬到小舢板不能載为止。有的簡直去了又来,来了又去,連运了三四次。大船上的水手們早已走了,誰管得到这些行李!等到五叔找到搬运的人,叫了几只舢板,一同到大船上时,已經来迟了一步,几十只皮箱,連十几张椅子,几张細巧的桌子、茶几,等等,还有許多厨房里的用具,都已为他們收拾得一个干凈了,剩下的是一只空洞洞的大船。祖姨气得几乎暈了过去,她的性命虽然保全,她的全部財产却是一絲一毫也不剩了。她的微蹙的眉头,益发紧紧的鎖着。她从此永无开顏喜笑之时了。五叔先从旱路送了祖姨到家中,留下两个老家人在催促当地官厅迫土人吐还祖姨的皮箱。經了五叔自己的屡次来催索,經了祖父的托人,当地官厅总算捉了几个土人来追索,也居然追出了三四只皮箱。然而还是全乡的人民的公同罪案,誰能把一乡的人民都捉了来呢?于是这个案子,一个月,一个月,一年,半年的拖延下去,而祖姨的財产益无追回的希望了。
为了这件事,祖母十分的难过,覚得很对祖姨不住。現在祖姨是更不能回家了。只好紧鎖着双眉,在我們家里做客。不到两年,便郁郁的很可怜的死去了。而比她先死的还有五叔!
五叔身体本来很細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覚得不大舒服,时时的夜間发热,但他怕祖母坦心,一句話也不敢說。沒有人知道他有病。后来,又迭次的带病出去,为祖姨的事而奔走各处。病一天天的深,以至于臥床不能起。祖母祖父忙着請医生給他診看,然而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于是到了一个月后,他便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到临死时,还是温厚而稳靜的,神智也很淸楚。除了对父母說,自己病不能好,辜負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他們不要为他悲愁的話外,一句别的吩咐也沒有。他如最快活的人似的,平安而鎮定的死去。祖母至今每說起五叔死时的情形,还非常的难过。她生平經过的苦楚与悲戚也不在少数了:祖父的死,大姑母的死,二叔的死,父亲的死,乃至刚生几个月的四叔的死,都使她异常的伤心,然而最給她以难堪的悲楚的,还以五叔的死为第一!在她一生中沒有比五叔的死損失更大了!她整整的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今,已經二十多年了,說起来还是黯然的悲伤。她見了五叔安靜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她的心碎了,碎成片片了!她从此,开始有了几根白发,她从此才吸上了鴉片!
祖母常常如梦的說道:“要是五叔还在,如今一定已娶了亲,且已生了孩子了!且孩子一定是已經很大了!”她每逢和几个媳妇生气时,便又如梦的叹道:“要是五五还在,娶了刘小姐,怎么会使我生气呢!”她还常常的把她所看定的一房好媳妇,五叔的假定的媳妇刘小姐提起来,她道:“这样又有本事,又好看,又温和忠厚的,又孝順的媳妇,可惜我家沒福娶了她过来!不知她現在嫁給了誰家?一定已有了好几个孩子了。”
她时时想替五叔过繼了一个孩子,然而父亲只生了我一个男孩子,几个叔叔都还未有孩子;她只好把我的大妹妹,当作一个假定的五叔的繼子,俾能在灵牌上写着:“男○○恭立,”且在五叔生忌死忌时,有一个上香叩头的人。每当大妹妹叩完了头立起来后,祖母一定还要叫道:“一官,快过来也叩几个头,你五叔当初是多么疼爱你呢!”
前几年,我和三叔同归到故乡扫墓时,祖母还曾再三的囑咐我們,“要在五五墓前多烧化一点錫箔。看看他的墓頂墓石还完好否?要是坏了,一定要修理修理。”
我們立在蔭沈沈的松柏林下,看見面前是一堆突出地上的圓形墓,墓頂已經有裂痕了,裂痕中靑靑的一丛緣草怒发着如剑的細叶。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損,但还依稀的認得出是“亡兒春荆之墓”几个大字。“墓客”指道:“这便是五少爷的墓。”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夕阳淡淡的照在松林的頂上,烏鴉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枝树上去。
山中是无比的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