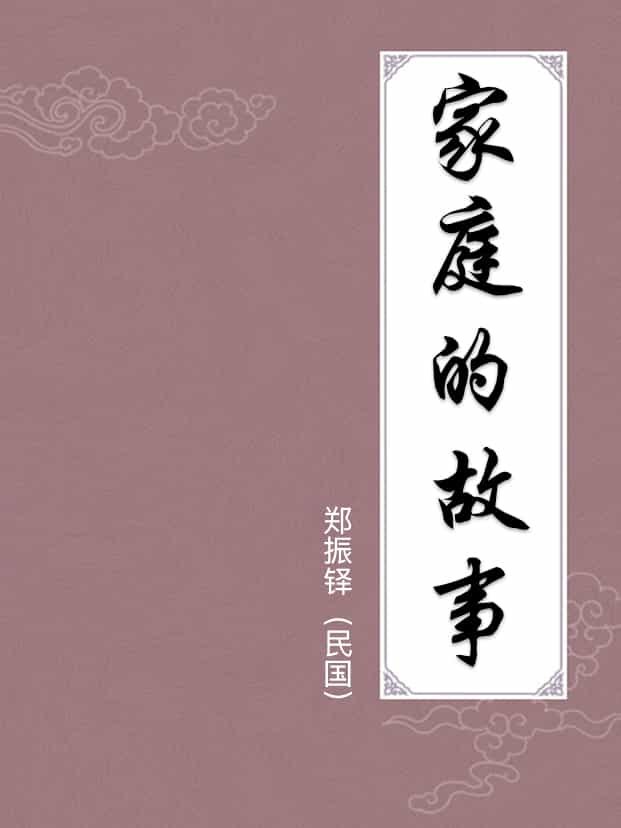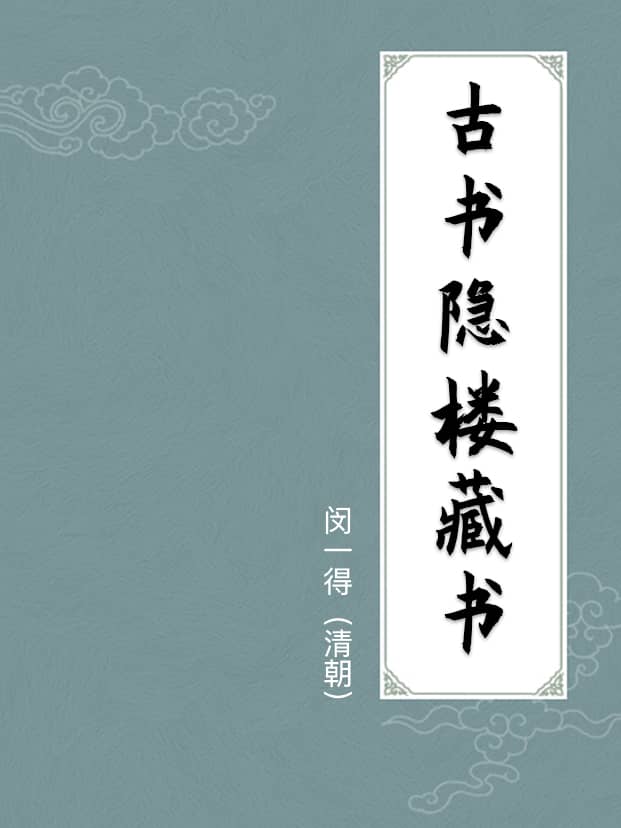外面是无边的黑暗,天上半顆星兒都沒有,北风虎虎的吹着,伸出檐外的火爐的烟通,被吹得閣閣作响。屋內秋迂、仲宣、亦公和子通,围爐而坐。爐火微紅,薄酒半酣,花生的硬壳抛了一地,而他們的談兴正浓。
秋迂似有所感的輕叹了一口气,說:“人生是不可測的……今天晚上,是四个人围爐而坐,是喝着薄酒,吃着花生米,是高高兴兴的酣談着。但誰晓得明天的事。也許我病了,也許你又遇到什么了。象亦公后天就要往南边去,今夜此乐,岂可再乎,人生是不可測的……誰看得見。……”
子通举了盛酒的茶杯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尽說这些扫兴的話做什么!干一杯,秋迂!”
亦公也說:“秋迂要罰干一杯!此地只宜談风月,說什么渺茫而辽远的人生,人生!”他也举起了他的茶杯。
秋迂神情不屬的,并不答理他們,似乎沈入深思。
爐边的伴侣,一时都沈靜而敗兴。
寡言的仲宣問道:“秋迂,你在想什么?”
“我正想到一个人的事,覚得人生眞是渺茫,眞是不可測之极了!”
子通盛气的說道:“人生有什么不可測的。我們向前走,我們自己的前途,明显的展开在那里。种什么子便开什么花,一点也不会錯。有什么不可測的,高的,远的,深的,我們都不必問,我們只切切实实的生活着,努力着好了。如走山上岭一样,走了一段,似乎山頂就在面前,却还要再走一段,再走一段,再走一段。这样一段段向前走的精神,把人生弄得光明了,灿烂了。走路,只要走路,便是人生,便是幸福。空想者是最苦恼的人,忧天堕的杞人是絕頂的儍子,聪明人是不断的向前走着。……”
秋迂挡住他再說下去,笑道:“你的話不差,但这样冠冕堂皇的理論,須得到公共講台上講去。我所感触的却是事实的詔示。譬如疾病……”
子通又搶着說了:“就譬如疾病吧,虽說‘生老病死’是人生四大苦,但就有人在疾病中得幸福的。你如果有了爱人,而你病了。沈寂的病室里,一縷金黃的日光射在地上,时鐘的嗒的嗒响着,这其間你的爱人带了含苞的鮮花,以及医生所允許而你爱吃的食物来了。她双眉微蹙着,如薄霧里的春山,更显得美丽可爱;她坐在你的床沿,——如果你不病,她决不会坐在你的床沿的——她低声的安慰着你,說些无关紧要的話,报吿些无关紧要的消息,讀些輕妙的詩篇。她竟会这样坐在你的床沿大半天。——如果你不病,她决不会留得这末久的。——她心里是泛溢着爱的輕愁,你心里是泛溢着爱的愉悦。爱神站在你枕头上微笑着,她送来的花朵站在床边小桌上的胆瓶里也微笑着。她走了,你心里还泛溢着愉悦,你脸上还泛溢着微笑。这不是‘偶然小病亦神仙’么?如果你沒有爱人,那末,年少美貌的看护妇……”
亦公笑道:“好了,子通他自己在画招供呢,你們听听看。”
秋迂道:“别再打岔了,我的話还一句沒說呢,我說的也正是爱神,也正是疾病,却不是一个微笑的故事,如子通所說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可怜沒有子通那末好的幸福,他为了他的病,……唉!我不忍說他!”
亦公道:“你說吧,不准子通再米插嘴。他再来多話,等我来封閉他的小嘴!”
子通对他白白眼。
秋迂叹道:“說起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呢,想你們几位都也認識的。他便是苹澗。”
子通道:“自从五年前分别后,我沒有再見过他。听說他近来住在上海,生着肺病。現在怎样了?”
亦公道:“我去年經过上海时,还曾見过他一面。他事情很忙,身子很瘦弱,还时时干咳着。”
秋迂道:“現在他的病更深了。上个月我在上海时,曾到他家里去过几次。临行时,还到他家里去吿别,他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說道:‘秋迂,再見。你下次南来时,决不会再見到我了。我自己想想,大約不会再見两三度月圓了。’他随又叹道:‘苦生不如善死!这无用的躯壳多見几次日出月落又何必!見到北京諸友,煩吿訴他們說,苹澗是不能再見他們了!’他桌上还放着我們几个人在香山瓔珞岩下拍的照片。他回头見到这张照片,不禁凄楚的长吟道:‘当时年少春衫薄……’我的眼眶里几乎盛滿了热泪,我哪忍立刻离开了他。我眞想不到我們豪气盖世的苹澗,竟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場!”
秋迂的声音有些顫抖了,眼眶边有几点泪珠,在灯光下熠耀着,爐中新添了煤,火光熊熊的。戶外北风似乎急了,鉛皮的烟通,不住的閣閣的响着。
“現在离了他又有一个多月了,哪晓得他还在人間吐吸着那一絲半縷的气呢,还是已經安眠在綠草黃泥之下了。我那时眞不忍离开他;多耽擱一刻就是一刻不会再有的时光。我們要說千万句話,而都格在心头,格在喉头,一句也說不出。我們默默的相对。我不忍正視苹澗的脸。你們想,他在北京时是多末瀟洒淸秀的一个少年。脸色是薄薄的現着紅潤,浓黑的柔发,一小半披拂在額前。暮春时节,他穿了湖色的綢衫,在北河沿高柳下散步,微风把他的衣衫拂拂的吹起,水影里是一个丰度絕世的苹澗。他的朗朗如銀鈴的声音,哪一次不曾吸住了朋友們的听聞,不曾难倒了反对方面的意見。他的理解力,办事的才干,又哪一件不超越过我們。子通,你的事,要不亏他替你設計,替你策划,替你奔走,你哪里会享到現在的艳福,子通,恕我不客气的这样說。——而今呢?相隔不到五六年,他完全換了一个人了;靑春的气概不再有了,美秀的容顏消失了,翩翩的风度灭絕了。如今与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骸。走一两步路都要人扶挟,双腿比周岁的孩子还軟弱,說話是不上三五句便要狂咳。脸呢,我不忍形容,比干枯的骼髏只多了一层皮,只多了一双失神的大眼,两排的牙齿是嶄嶄的露着。他那双手,也瘦得如在X光底下照出的,握住它,如握住了几根細木。唉,当年的苹澗,如今的苹澗,人生是可測的么?我不忍正視他的脸,我避开他,在他屋里四望着。屋里是比前一次我来这里时更混乱齷齪了。床前的痰盂,盛着他一絲絲的带血的痰块的,有好几天不曾拿出去換水了。桌上的瓶花,干枯如同床上的主人,已有几瓣变了色的花瓣落在桌上,也沒有人来收拾了去,画片上、桌上、窗户玻璃上,滿是灰尘。地上废紙、瓶塞乱抛着。床上的被窝,显見有好几天不曾整理过。几张桌子上都散乱无序的放着藥水瓶、报紙、杂志、詩集、小說,还有咬剩半块的苹果,吃剩了半支的香烟头。靠近房門边,又放着一张小的单人床,那是他夫人睡的,被褥也散乱的放着,沒有折迭起。
“‘你的夫人呢?’我不覚順口問他。
“‘还不是又出門去了!’他說着,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她哪一天曾在家里留着过。总是早出晚归,抛我一个人在床上。飯是老媽子烧好了端来放在桌上,也不管我吃不吃,也不問我要吃什么,’說到这里,一陣急咳把他的話打断了。至少咳了两三分鐘,脸上涨得通紅;慢慢的喝了我递給他的一杯水,方才复原。‘倒藥水也要自己做,要水要茶,喊了半天还沒有人来。房里沈寂如墟墓。你看我还有一口气,其实是已死的尸体,被放在这空闊的‘棺室’里。倚着枕,看見日光由东墙移到地板上,再移到西墙;看見窗外那株树的阴影,长长的照在天井里,漸漸的短了,又漸漸的长了。看見黑猫懶懶的睡在窗口負暄;走了,又来,黃昏时,又走了。那墙上的挂鐘,已經停了三天了,也沒有人去开……’又是一陣狂咳迫着他,停止了他的話。
“我后悔不該問了他那句話致引动他的憤慨。我只得又倒了半杯水給他喝,劝他道:‘不要多說話了,多說話是于你有害的,息息吧。’
“他說:‘不,謝謝你。我已看得很淸楚我的运命了;死神的双翼,已拍拍的在半空中飞着,他的阴影半已罩在我的脸上。不在这还能說話时对好友多說几句,再也沒有时候可說了,而况你明天就要走了,現在是最后一次听見我的話声了。……’
“外面有人敲大門。接着便听見女人的口音問道:‘黃媽,有客人在房里么?’她随即进了房門。这便是他的夫人紫涵。把她和苹澗一比較,是可惊异的差歧:一个是充滿了生气,虽然双眉紧蹙着,脸上現出几分憔悴的样子,而掩不住她的活泼、灵动和血气的完足;一个是,刚才已經說过了,与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尸’,只剩了奄奄一息。她坐在床沿,和我敷衍了几句后,便低了头,沈默着。
“房里寂如墟墓,幕色隐約的籠罩上来,我便立起来說道:‘太晚了,不坐了。苹澗,好好的保重自己!再見,再見!’握了握他伸出的小手,輕輕的。他凄声的說道:‘再見,恕不能起来送你。’
“我心里沈沈的,重重的,似沈入无底的深渊,又似被千万石的鉛块压住,說不出的难过。这凄楚的情緒,直把我送到北京,还未完全消失。”
亦公道:“他們俩不是前年冬天在上海开始同居的么?我还記得他們俩刚刚同居时是如何的快乐。每个星期日的午后,苹澗总和她同游环龙花园;如一对双飞的蛺蝶似的,在园中并肩紧靠着走,并肩紧靠着坐在水边,甜蜜蜜的低說着。春天似乎泛溢在他們俩的脸上,春光几乎为他們俩占尽。垂柳倒映在池面,他們俩也倒映在池面。并坐着,低語着,手互握着。不知羡煞了几何走过这一对鴛鴦面前的男女。不料結局却是如此,眞是想不到的。”
仲宣道:“爱情比蛺蝶还輕,飞到东,又飞到西,这是常事。”
秋迂叹道:“也不能怪紫涵,我們要設身处地替她想。一个将死的病人,一間沈寂如墟墓的病家,能把一个活泼、灵动、血气完足的靑年女子終天关閉、拘留在那里么?我初到上海,第一次去看苹澗时,他已經病得不輕了,但还沒有睡倒在床。他終日坐在廊前晒太阳,看看輕松的小說和詩歌。紫涵也終日陪伴着他坐着。时时忙着替他拿藥水,拿报紙,拿書,拿茶,拿痰盂。他的脾气却一天天的随了身体而变坏。动不动便生气,一点小事不对,便不留情的叱駡她。茶太冷了,書拿得不对了,牛奶沸得太慢了,件件事都駡她,仿佛一切事都是她有意和他为难。而駡了几句后,便狂咳不已。
“‘我病得这样了,你还使我生气。恨不得叫我早一天死,你才好早一天再嫁别人!’象这样的話也常常駡着。有一天,紫涵偸空跑到我家里,向內子吿訴了大半天,几乎是連哭带說的,不知她心里是如何冤苦、忧悶、悲伤。她道:‘为了他,我什么苦都肯吃。我見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恨不得把我的肌肉割补給他。我一天到晚侍候着他,而他总沒有好脸对我,不是駡,便是叱,而且什么重話都駡得出口。我从孩子时候起,活了二十多岁,哪曾受过这样的駡,哪曾吃过这样的苦!我为了他是病着,一句話也不敢回答。有苦只好向自己腹里吞,有冤屈只好背地里自己流泪悲伤。为了他的病,我几曾安舒过一天,安睡过一夜。我向来不信佛,不信神;而今是許願、求签,什么事都来。我願冥冥中的大神,早一天賜給我死,而把我的余年給了他。我的苦吃够了。人生的辣味也尝够了,眞不如死了好!而他这几天来,更无时无刻不和我生气。医生戒他不要多說話,他却終日駡人,駡了便要咳嗽,这病哪里会好!还不如我避了他,使他少生些气好。’她更曼长的叹了口气,如梦的說道:‘过去的美境,过去的恋感,如今辽远了,辽远了。未結婚时,他是如何的殷勤,我要什么,半句話还沒有說完,他連忙去代我拿来了;結婚后,他是如何的温存,只有我嗔他埋怨他的份兒,他哪里有对我回說半句重話。而今这幸福已飞去了,辽远的辽远的飞去了,不再飞来了。只当是做了一場美梦,可惜这美梦太短了,太短了!’她愈說愈难过。回忆勾起她万縷的愁恨,不禁伏在桌上嗚咽的泣着。良久,良久,才抬起了头,說道:‘这样的生,不如死好!’泪珠一串串的挂滿了她的脸,內子只有陪着她叹息,一句劝慰的話都說不出。
“后来,听見內子說,苹澗是,一天一天的,生气时候更多了。紫涵为了免他見面便动气之故,只好白天避开了他。我第三次去看苹澗时,紫涵果不在家里。他独自睡在床上。房間里是如此的阴慘、沈寂,似乎只有盘伏在窗口負暄的黑猫是唯一的生物。这里的时間,一刻一秒似乎有一年一月的长久。我不知沈浸在病海中的苹澗将如何度过这些悠久沈悶的时間。他也叨叨罗罗的吿訴我許多关于紫涵的話,而最使他切齿的便是她天天出外,太阳沒有晒进屋便走了,太阳已将落山还未归来,抛他一个人在家,独自在病海中掙扎着。他微吟道:‘多病故人疏!不,如今是,多病妻孥疏了!’他脸上浮着苦笑。
“对墙挂着一幅放大的他們俩的照片,背景是絲絲的垂柳,一塘的春水,他靠在她肩上,微笑着。在他們俩的脸上都可看出甜蜜的爱情和靑春的愉乐是泛溢着。
“这是一个永不再来的美梦。”
秋迂凄然的不再說下去。屋里的四个人悵然的相对无語。
爐火微紅,北风狂吼,伸出檐外的烟通被吹得閣閣的响着。外面是无边的黑暗。
一片片的白雪,正瑟瑟的飘下。屋瓦上,树枝上已都罩了一层薄薄的白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