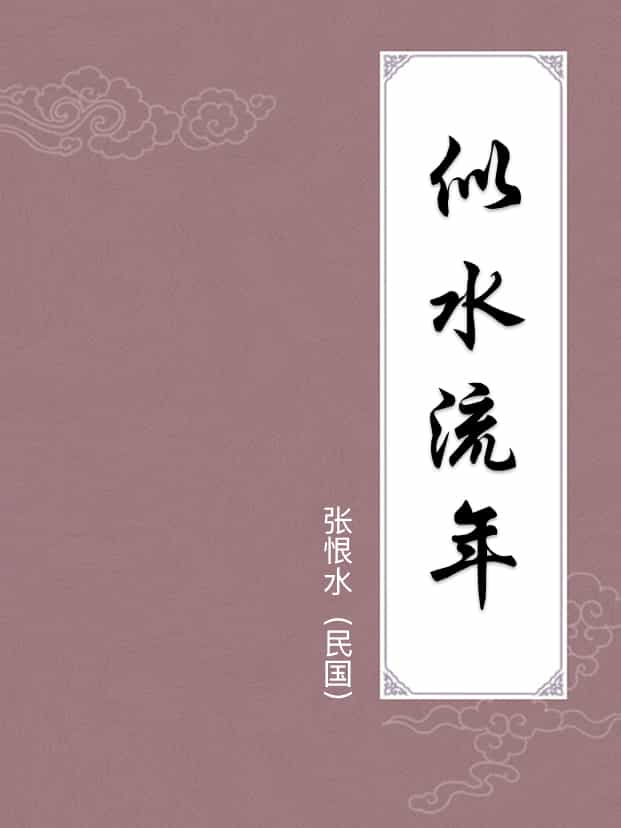却说黄惜时当得了十几块钱,正要回家去,走到半路上,忽然变起计划来。心想:我要做一番事业,非发一笔浑财不可。刚才由大街上经过,看到电车上挂的广告牌,有“头奖志喜”四个字,这不知道是谁人中了奖券。这个人假如也是像我这样的穷光蛋一个,有了这笔钱,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多么痛快呢!管他呢,我也去碰碰看。如此想着,他就吩咐车夫跑上大街,向彩票店里来。
那彩票店门口挂着大红绸彩,上面缀着斗大的金字,一幅上是“头奖志喜”,一幅是“又中二奖”。柜台外面悬了好些红牌字,上面写了粉字,乃是各种奖券的名字和开彩日期,其间有块加大的牌子,上写着:“头奖五万元,本月十日开奖,每张五元,每条五角。”惜时看了,心里不觉一动,一张五块钱,我就是买一张,也不过去我所有的三分之一,于我的经济状况,绝没有什么损失,绝对不用犹豫了,于是走进店去,就掏出一张五元钱钞票,要买一张五万元头奖的彩票。店伙收了他五元钞票之后,将一个印着红字的封套套了一张奖券,两手捧着,隔了柜台,连向惜时笑道:“恭喜恭喜!上次我们卖出那张头奖去的时候,有个蟢子在上面爬着,当时我们就说,准可以中奖。现在我们给您拿这一张奖券的时候,也有个蟢子在上面爬着,这岂不是一个好应兆吗?”说着,把那奖券交到惜时手上。
惜时抽出奖券来看时,上面列着的数目字是五个,每一个数字隔上一个圈,非常地整齐,心里想着:这张奖券真有些奇怪,好几个应兆碰在一处,莫非我真是要中头奖吗?接着奖券在手里,犹豫了一阵,嘴角微笑了一笑。那店伙道:“这里还有几种奖券,开奖的日期更近,你先生还要不要呢?”惜时心里想着:难道靠这一回,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去拼一下子吗?他心里想着时,人就靠了柜台站住,两手不住地颠倒着那奖券封套,人就出了神。
那店伙看他那犹豫的样子,知道他还有购买奖券的可能,便笑着向他一点头道:“您贵姓?”惜时答应是姓黄。伙计又道:“你府上住在哪儿?将来您要是中了奖,我好到您府上去报信。”惜时听了这话,不由心里一动,便道:“现时我住在太平公寓,将来也许我要搬到会馆里去住,好在开奖的日子,我一定要到这里来一趟的,你想,有钱可捞,我还有个不来的吗?”伙计听他的话,简直就是接受了再来两张,于是又把头奖一万元、头奖二万元的奖券卖了五张给他,一共又是十块钱。
惜时身上所剩已无几了,不过他花了这笔钱,是抱有无限希望的。一种抛砖引玉举动,以为此后一线生机,都靠这十几块钱去转圜。这十几块钱,绝对不能认为是白花,所以把那些买的奖券向店里要了一张报纸,整整齐齐地包好,揣在身上,然后坐车回公寓而去。
坐在人力车上的时候,想着奖券有如此之多,若是全中了头奖的话,大概有十几万元,那还了得?想着,自己又摇了摇头,天下没有这个道理,所有头奖的奖券都在北京,都由这家店里卖出,都由自己买得,天下固然有巧事,可是也不能巧到这种程度。这许多张奖券里面,能中那张五万元的,是千好万好!或者中二万元的,勉强也可以敷衍,若是只中一万元的那张,对于自己用途的支配,就有点儿左支右绌。买了这多张奖券,大概总不能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吧!
想时,又在身上把买的奖券都拿了出来,将号码的数目字各念了几遍,然后闭着眼睛,心里把那数字再念上几遍,于是再套好了揣到身上去。可是这奖券不是一张,记得这张的数目,就记不得那张的,就算记得,又把五万元头奖的,当了一万元头奖的。越默记越糊涂,只好又把那些奖券拿出来重看一遍。心里可又想着:不必看了,若是抽出来送进去,抽得丢了一张,也许那张就是头奖,丢了多么可惜!这样想着,不由自己吓了一跳,立刻把所买的奖券一张一张从头数了一遍,一张也不少,这才每张用他自己的封套一齐套好了,然后叠着揣到袋里去。揣到袋里的时候,而且用手按了一按,怕是搁在衣袋里会弄丢了,而且那只手就是这样隔住衣服按着口袋,一直等到了公寓门口下车掏车钱,才把那手放了。
到了公寓里,第二个感想跟着就来了。自己不是说了大话,今天拨付房饭费吗?现在身上的钱都买了奖券了,哪里拿得出一二十块钱付公寓费?心里只这样一动,似乎脸上就露出了畏缩的样子。那账房先生刚由里面出来,一见了他,就半鞠着躬道:“您回来啦?”这在北京生意买卖人是一种极平常的礼节,可是惜时听了,仿佛就像人家含有一种讥笑的意思在内,以为以前说了大话,这几个房饭钱不算什么,何以到了现在一毛钱也没有掏出?但是这个哑谜不能让人家随便猜破,能瞒一时就是一时,于是乎挺了胸脯,板着面孔向账房点了一下头。
这种做作似乎有点儿效验。茶房由后面跟了来,先抢着开了房门的锁,其次便是掀开白炉子盖,放出煤火来,也不必惜时吩咐,捧了他的洗面盆就去打水。水打来了,接着便是沏茶。沏茶之后,而且倒了一杯茶,两手捧着放到惜时坐的桌子边,然后倒退一步,向他道:“您这就吃晚饭吗?”惜时鼻子先哼了一声,接着又道:“叫厨房里和我添两个饭菜,不用得记账,明天上午,我一齐付给他。放心吧!我决计少不了你们一文钱的。”茶房哪里还敢多说什么,只是笑着说:“是。”
一会儿菜饭都送来了,自然是很丰盛的。这餐饭依然吃得痛快。不过心里想着:大话说了又说,明天算账,却把什么钱来付人家?想到这里,焦上心头,再也坐不住了,背了两手在身后,只管就踱起方步来。这样子走了许久,自己忽然将脚一顿,好像他已决定了一种事要办。他两眼望了自己那口衣箱摇了摇头,他又坐下了。原来他想着,这个日子,要和人家讲交情借钱,讲交情赊账,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既然今天已经当了一批衣服,走这条简捷易到的道路,那还只有当当,什么都完了,靠留着几件衣服,又中什么用?他有了这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来,又把所剩下的几件中装衣服再送到当铺里去。今天比昨天所当的更少,共总还不到十块钱。就是要在这公寓里再住一个礼拜,也是不能够,这倒不如就是这样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先花光了再说,现在是不容犹豫的了,立刻就搬出公寓去。当时也不动声色,吃过了早饭,却叫茶房把账房请到房间里来。
账房以为是客人要给钱了,心里高兴得很,把昨天就开好了的账单子揣在身上,就笑嘻嘻地走到惜时房间里来。只走到房门口,他就鞠着躬下去,然后一点头向里面走一步,走到惜时面前,笑道:“黄先生今天还没出门?”惜时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圈椅上,向他微微一勾头,板住了脸道:“我老实告诉你,我的钱都用光了。”账房又向他笑:“黄先生,您还生气。”惜时道:“我实在不是生气,我今天就要搬出去了,你们见谅点儿,不要照什么规矩算账。我虽过了两天房期,照日子算给你,你可不要按一个月算。”账房看他那样子,似乎是真要搬,便笑道:“伙食钱呢?您可以吃一顿算一顿,房钱都是按月算的,若是按日子算起来,跟黄先生一个人,那不要紧,可是将来别位客人都这样算起来,我们这买卖就不好做了。”说毕,又嘿嘿地笑了一声。
惜时依然板着脸道:“你们不要我走,我也就不客气,在这里住。可是我要拿不出房饭钱的时候,你可不能逼我要钱。”账房笑道:“黄先生要找好些的公寓住,我们也不敢拦着,可是您也别让我们没法子交代。”惜时站起来道:“你们不听我的话,我也没有法子,我为了免除将来的麻烦起见,我可要找个警察来当面声明一下,将来我要是给不起房饭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别来找我,你干不干?你不干让我自己去找警察也行。”说着,向门外提高了嗓子喊道:“茶房!来和我收拾铺盖行李。”说毕,将两个枕头叠起来,放在被褥当中,就做个要卷行李的神气。
账房站在屋子里,犹豫了一阵子,便道:“好吧!让我去算算账看。”偷眼看惜时的神气,也不理会,悄悄地走了。惜时见公寓里不致留难,倒好像逃出了一个难关,立刻叫茶房进房来帮着收拾行李。他当的那十块钱,有一张五元的钞票,他将五元的钞票放在外面,里头用一元的钞票和铜子票衬托着,做了一叠,拿在手里,当了茶房的面,将五元的钞票交给他,让他到账房里去交账。那茶房接下了钱,并不因为他是要走的客人就怠慢着他,笑嘻嘻地接着去了。也不知是何缘故,账房说是不能破坏规矩的,依然是按了日期算账。五块钱还找回零头来了。惜时也不惜小费,赏了茶房两块钱,茶房很高兴地道着谢,问惜时要搬到哪里,好和他雇车。惜时想了一想说,是要搬到亲戚家里去住,让他雇车雇到会馆的那个胡同里去。于是一辆车子坐人,一辆车子拉东西,拉到会馆里来。
这时会馆里的人天寒岁暮都回家过年去了,屋子更是空着。惜时和长班商量着,随便挑了一个屋子住了。可是这样一番迁移之后,买炉火,买灯油,买吃食的东西,长班张罗了半天,他就耗费了两三元,今天当的钱又所剩无几了。不过住在会馆里,却有一种好处,现在人少房多,像公寓里那样杂乱的声音却是没有。房子里笼着了一炉煤火,炉子上放着一把白铁水壶,响着细微的锣鼓声,暖气烘烘的。隔了玻璃窗子,看看屋脊上,昨天下的雪还积得很厚,眼前一片白色,窗子外的院子,有两株松树和两棵落了叶子的树,上面落了雪,染着雪白的枝干,就像银花玉树一般,非常之好看。
自己斜躺在床上,架了两只脚,抖着文气,心里可就想着:假使这会馆里并没有什么人住,永远是这样地清闲,我也很可以在这里住着。又转一个念头道:我若是没有金钱的接济,就是这一炉煤火、一把开水壶,也会生问题。让我住会馆,难道就这样干躺在屋子里不成?这样看起来,唯一的救星就是这几张奖券了,我若是中了五万元的奖券,我立刻就搬到最大的旅馆——北京饭店去住,何必还住在会馆里?当的衣服,那都不必去管了,应该重新制一千块钱的西服,因为天气还冷,一件狐皮大衣是少不了的。从前米锦华很羡慕人家带着钻石戒指,我一定买两个带着,至多也不过一千多块钱罢了。我穿了狐皮的大衣,坐着汽车,一定到寄宿舍里去拜访一次,我猜着到了那个时候,她不能不见我吧!不但如此,我还要预备三千块钱带回家去,把我所花家里的钱一齐交还父亲。那个时候,我要说两句俏皮话,问问父亲,我是不是个无用的人?那个时候,父亲当然无话可说了吧!至于母亲呢,我把单夹皮棉纱的衣服,一样和她预备几件,算是做儿子的尽了一点儿孝心,就是那寡妇嫂嫂和那小侄子也都预备着,送他们二三百元东西,让大家欢喜欢喜。假使白行素还可以和我做朋友的话,我必定要重重地报答她一阵,她现在还没有回南,假使她有回南的意思,我就定下火车上一个头等包房,和她同住。记得由南京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们同在三等火车上认识的。现在回南,依然同车,可是坐了头等车了,这不但值得纪念,而且是十分安慰的了。本来我和她翻脸是我不好,她对我虽然冷淡下来,可是没有一点儿恶意,于今我竭力恭维她,也许她回心转意,可以嫁我了。那个时候,我和她同由南京同坐轮船回安庆去,并肩倚栏,看江上的山景,那是多么快乐!只要她愿意,我还可以把她带回乡去,一同拜见父母,让乡下人看看,我什么都有了,我果然是个无用之人吗?
这样想着,一个人笑了起来,因为所想的种种幻象都是由几张奖券而起,把那奖券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些什么号码。因为隔了许久的时间,号码的数字都记不清楚了,于是再打开箱子,把奖券取出来,躺在床上,将数目字看了一遍,眼睛看着奖券,心里依然不免揣想那中奖以后的滋味。
正想着,忽然有人在窗子外喊道:“这里住着位黄惜时先生吗?”惜时答道:“哪一位找我?”只这一声,院子里噼噼啪啪、轰天轰地地响起爆竹来,立刻有两三个人抢进房来,向他拱着手道:“恭喜恭喜!黄先生中了头奖了。”惜时听了这话,心里一阵乱跳,只见那个贩卖奖券店里的店伙手上提了一个大皮包,笑嘻嘻地放在桌上,然后向他一鞠躬道:“您中的五万块钱,我们给您带来了。”说着,将皮包打了开来,惜时上前看时,里面一卷一卷的钞票,比字纸篓里的纸还要充满。那店伙伸了手进去,将钞票几叠拿出来,都放在桌上。他笑道:“黄先生,你点点数目吧。”惜时于是将钞票拿起,一张张地掀着,点起数目来。这些来送钱道贺的人真是爽直,连小账也不要一文,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钱真是样好东西,无论什么人都得为了它而屈服。黄惜时偶然回头看时,只见米锦华穿了粉红色的旗袍,笑嘻嘻地站在身后。惜时正想说她两句时,她握着惜时的手,将头偎着他的肩膀,用很平和的声音向他道:“惜时!你还怪我吗?”惜时说:“哼……”锦华拉着他的手,同在床上坐下,笑道:“我现在很后悔,您饶恕我吧!”惜时被她拥抱着,心先软了,就是想说她两句,心里想说,口里也说不出来。结果,是让她麻醉了。
只在这时,房门一声响,拥进十几个人来,把桌上的钞票一阵乱抢,完全拿了走。惜时跳了起来,要上前去抢,被一个强盗反手一掌,打得自己向后一倒,出了一身臭汗,两眼漆黑,眼前的东西完全都看不清楚了。这一吓更非同小可,莫非是我双眼睛瞎了?于是竭力将眼睛睁着,打算恢复光明的原状,可是全身只管用力,人动转不得,只管要喊叫,可是口里叫不出来。挣扎了许久,好容易睁开了眼睛,向前面一看,倒有些模糊的白影,却是离着好远,用手摸摸身边,倒很柔软,原来并不倒在地下,却是睡在床上。闭了眼睛定定神,再睁眼向前看,这才看出,那模糊的白影是院子外屋脊上的雪,天空上有几点星光,在玻璃窗子里,还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天色黑了,屋子里没有上灯,所以并非被人家打得如此,身边并没有女子,院子里静悄悄的,也没有什么强盗,分明是自己做了一场梦,梦中中了头奖了。不过人是醒过来了,依然懒得起身,躺在床上,静静地想那桌上叠着钞票的滋味。固然,这是一场梦,可是有一天我真中了奖券,那滋味又何尝不是这样?记得睡觉的时候,奖券是拿在手里的,手捏了一捏,奖券并没有拿着,不由得跳了起来,赶快找奖券。只是这屋子是今天新搬来的,一切家具的位置都不大熟识,如何可以摸着灯火?所幸炉子里的煤火依然还抽着火焰。屋子四周,还映射着看得出来。自己立刻跑了出去,和长班讨了一盒火柴来点灯。
这馆里的长班以前和惜时见过一面,知道他是黄守义的同宗,后来因他打听黄守义的下落而后匆匆地就走了,看那样子好像很懊丧,心里想着:不要这个人就是黄老先生的儿子。这次惜时搬进来了,看他那魂不附体的神气,用钱又一点儿打算没有,更猜了几层准。于是见着会馆里寄住的先生,就把这事报告一遍。照住馆的章程,本来要先得会馆值年的馆董认可,然而这时会馆里有的是闲房,馆董又因家事很久不曾到会馆来,所以惜时自行搬进来,并没有人注意到他。这时长班到处报道,不认老子的那个姓黄的来了!他一搬进会馆之后,笼一炉子火,就在床上躺着发愣,原来给他预备了火柴、油灯的,可是他坐到黑过了一点多钟,才出来找火点灯,这个人怕有什么毛病。
黄守义被儿子驱逐这一幕戏,大家都是听够了的,一听黄守义的儿子也来了,大家当是一桩新闻,都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子。这时惜时正亮上了灯,会馆里人悄悄地走到窗户边,由壁缝里向里面张望进来。见他一人在屋子里,很是忙碌,时而打开箱子乱翻一阵,时而搬出网篮,将里面的东西都抖乱起来,时而打开桌子抽屉,时而掀起床上的被褥。看他的样子,很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越急越找,越找也就越乱,网篮已是捡过一次的了,有些东西还不曾捡了进去,这次又再捡一次。这个屋子里也不过是他一个人和两三件行李,倒弄得乱作一团。
有两个人起了疑心,立刻找着长班告诉他道:“我看这个姓黄的,多少有些神经病。不要搬过会馆来,就出了乱子,你可以到他屋里去瞧瞧。现时他在屋子里满屋子乱转,看他是在干什么?”长班听到这话,就提了一壶凉水,假装和惜时添水,走进他屋子里去。
惜时正将箱子放在床上,打开了箱盖,自己斜靠了箱子站定,只管低了头傻想,虽是有人进来了,他也不理会,只当不曾看到一般。长班将炉子上那壶盖掀开,用凉水斟了下去,搭讪着向他道:“黄先生!这炉火快不行了,我搬出去和您添上一炉煤吧!”惜时依然在那里低头想着,他说的话,似乎听到,又似乎没听到,随便地点点头。
长班望着他许久,才道:“先生!您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找着吗?”惜时还是点点头。长班道:“也没有第二个人进来,东西丢不了的。丢了什么呢?我替你找一找吧!”惜时这才说话,向他道:“有几张要紧的稿件,现在不见了,找了半天,始终也没有找着。”长班道:“那纸有多大一张呢?”惜时道:“不多大一张,是信封套套着的。”长班道:“那样子小,也许您顺手一揣,揣在袋里了吧?您摸摸看。”惜时听说,果然伸手一摸,掏出手来看时,一大束信封捏在手心里,不由得哎呀了一声。长班道:“就是这个吧?”惜时将信封拿在手上检点了一番,并不少一张奖券,但是不好意思说全找着了,点点头道:“还差一两张,找不着,就算了。”长班笑着捧了炉子出去添火,也就不说了。这样一来,倒让惜时加倍地难为情。坐着定了定神,反是头晕眼眩起来。箱子网篮,一概都懒于检理,就这样躺下了。
到了次日,他走出房来,见会馆里同住的人都目灼灼地向自己张望,倒有些莫名其妙,而且有两个人在一处的时候,当自己走过他们面前,他们就窃窃私语起来,虽然不知道人家说些什么,可是他们没有好意的批评,那是绝对无疑的了。自己虽然想少出房门,可是住会馆和住公寓不同,会馆里住上几十人,只有一个守门的长班伺候,哪里管得许多,所有饮食起居的事情,差不多完全自己料理。
在这冬天,第一便是这炉火,自己醒过来之后,在床上便喊着长班,打算学住公寓的时候一样,等茶房送进炉火来以后,屋子里热烘烘的,然后再起床。不料由早上八点钟熬到十点多钟,长班依然不曾进来,只好自己下床,将炉子搬到屋檐下,放下纸片木炭,擦了火柴,把纸点着。那炉口里烧出来的青烟,向人脸上直扑,眼泪水抛沙似的滚了出来。眼见炉口里冒出火焰来,这可以添上煤了,可是煤球和木炭都堆在窗户台下的,那木炭可以用指头钳着,放到炉子里去,这煤球可不能一个一个用指头钳着。踌躇了会儿,望着煤球堆出神。
那炉口上的火焰更冒着汹涌了,不能再等,只好两手在地上捧了煤球向炉里放进去,两手立刻染上一层黑漆。眼睛被烟熏着,也不能用手去揉擦,抬起袖子在眼上擦了几擦,看看这两只手,实在忍不住。走到房里去,想找点儿水洗手,脸盆又是干的,只好右手拿了茶壶,将冷茶向左手淋着,淋过了,再淋右手,两手淋得湿湿的,撕了两张报纸将手擦着,虽没有干净,但手凉着,也再受不住冷茶淋了。再跑到外面来看时,那炉子里一丝烟也没有,原来火势冷过去了,炉子里的煤球已是添得满满的,要重新引火,非把煤球取出来不可。昨天安置家具,又不曾买得火钳火筷子,如何取得出来?要将炉底翻转来,将煤球倒出来吧,这白炉子很像一口坛,它是泥质的,而且套着一个铁片架子,倒得不留心,就要把炉子碎了。没有法子,只得再用手把煤球一个个地向外钳出来,可是一炉煤球总有一二百个,等他把煤球全钳出来时,连两只袖口都染成了两个黑圈。头发披到口里,灰尘扑了满身,都不能用手去管理,而且这屋檐下的雪风吹到身上来,是十分地难受。鼻子里拖出两道清水鼻涕,一直拖到嘴唇上来。两只手不但是黑,而且冻得皮肤全打起皱来,在廊檐下,简直是站不住了。火又笼不着,只好蹦跳着来去,借此取暖。
到底还是长班的妇人向后院来送茶水,看到黄惜时那个样子,很是不过意,就笑向他道:“这位先生初到北京来,大概不会笼火吧?让我来替你笼上吧!前面门房里有水,您自己带盆去舀吧!”惜时听到这活,真像得了皇恩大赦一般,就到屋子里去拿了脸盆到门房里来。这门房的房门用铁绷簧绊住,拉开门来,后又关上了。那屋子漆漆黑的,中间一个大铁煤炉子,里面火焰冲出一尺多高。炉口四围放了两把铁壶、一大堆煤球。那壶里的水沸腾起来,把水洒在煤球上,哧哧作响,透出一种恶劣的臭味,加之炉圈上又放了一双男鞋、一双尖头女鞋,烘烤出那股汗味来,简直熏人的头脑子。
那屋子坐着一个老妇人,是长班的母亲,她看到惜时进来了,倒是讲规矩,抢着上前,接了脸盆过来,就把壶里的水给他斟上。破桌子边,放了一口冷水缸,桌上有煤油灯,有整束的大葱,有破旧的灰色香炉,还有两双破污袜子。那老妇人就在袜子边拿了一只破碗,就在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向盆里掺着。她道:“先生你先回房去吧!你还得沏茶,我把开水壶提着,送到你屋子里去。”惜时在这屋子里,实在受不了这一股子臭味,也只好依了她的话,先回屋子去。不多一会儿,是长班将水送了来。他也不征求惜时的同意,在茶叶瓶里抓了一把茶叶,就和他放到茶壶里去倒了一壶茶。
惜时洗过脸,又喝一杯热茶,算是有了一些暖气,可是喝着茶的时候,凝神想了一想,那长班屋子里的水缸,环境非常之肮脏,而且那缸是不曾盖着的,壁上的灰尘真个如堆花山水一般,那上面又不曾有生漆和胶水粘着,当然很容易落下来,而且桌子上摆着臭污袜子,今日如此,平日当然也如此,这缸里可难免落下脏东西去的了,这种水喝到肚子里去,可是有点儿不起好感。如此想着,这杯茶可就喝不下去了,只好渴着。
约莫过了半小时,长班代笼的那炉火算是着了,他就代搬进来,而且上了一壶凉水,在炉口边放着。惜时对于水既是怀疑,当然对这壶水也不大放心,可是这会馆里的自来水机头就在长班屋子里,若不由那缸里经过,要干净点儿,以后只有自己去放水喝了。于是茶壶里的茶不要,水壶里的水不要,自己拿了壶到自来水机头去放水,好在屋子里有了火,暖和得多,做事比较有精神,索性拿出钱来,叫长班去买了做饭的东西来。桌上于是摆了一个碗大的报纸口袋,那盛的是米,一张五寸见方的报纸,托了一块豆腐、一片青菜叶,包了一块巴掌大的生猪肉,又当菜,又当荤油使。一只缺口茶杯子,装了两个铜子酱油,一个铜子大的纸包,那是盐,还有一棵大白菜,也压在桌面上。
吃的东西是有了,还要自己来做。脸盆洗了米,先向长班借沙罐焖饭。其次向外面舀了水来洗菜;又要借菜刀、砧板来切,又要借菜锅勺、锅铲子、菜碗、饭碗、筷子、小勺子,越是怕与会馆里人见面,越是想起了许多事要进进出出。好容易把饭菜做成功。饭既是夹生的,豆腐煮白菜,放多了盐与酱油,几乎咸得不能上口。胡乱吃完,把家具送走,累得伸不直腰,又躺下了。本来这种事是生平第一次干的,以前不但不愿做,看了别人做,还嫌他小家子气,现在自己为了经济的逼迫,也只好做起厨子来了。想到这里,悔恨自己以前把钱看得太松了,于今来吃这种苦处。又想到这种局面,也断断不能持久,不但自己不愿做,而且每日拿钱去买柴米油盐,也无以为继。你看会馆里这些同乡,又是在我背后私议,他们不是笑我贫酸吗?还是那一句话,假使我中了头奖,我一定天天坐汽车回来,还带两名听差在我后面跟着,就是听差穿的衣服,也让他们各穿着一件皮袍子。到了那个时候,摆出十足的威风来,看他们是不是还窃窃私议。
一人躺在床上想着,觉得无论一件什么事,若是自己想去解决,都非等着中头奖不可。在床上躺着想还不算,又跳下床来,就着桌上的纸笔,列起一张预算表来。第一笔开的是置房产一万元。第二笔是买汽车三千元。第三笔是预备一个小书库,经费约三千元。第四笔是制衣服二千元。第五笔回家费一万元。第六笔结婚费五千元。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定期存款二万元。写到这里不觉从头校对一番,竟是超出了五万元的数目,果然有了钱,不能这样挥霍,还得仔细审查一下。于是把列的预算表全盘推翻,又再列过一张。冬日天短,他足不出户,又是上灯时候了,这少不得又要做晚饭吃。但是上午那一餐午饭,把自己已闹得精疲力竭,现在哪里还能做第二回?简单一点儿,还是买几个烧饼和一毛钱酱肉,就这样对付一餐吧。如此想着,一个人悄悄地照办了。就这样度过了一天。
次日醒来,已领教昨日炉火的滋味,一切不忙,只缩在被里睡着,等长班代为笼过火以后,然后再起来,已是十一点多钟了。算着日子,正有两张一万元的奖券是今日开奖,在今天晚上,全部可以发表,中与不中,就在这几个钟头之内,决定命运的了。假使今天中了小奖,不见得还能中五万元的头奖。那么,就要另造一个预算表,照一万元的款项来支配了,反正在屋子里烤火,也没有别的事。于是乎又造起较小规模地预算表来,忙到两点钟,才出去找了家小饭馆,吃了三毛钱的饭,回来依然继续地造表。可是到了晚上,到奖券店里去对号码时,连附奖不曾中得一条。
寒风凛冽中步行了回来,心里还自慰着,不中一万元的奖券也好,我的好运气留到中五万元头奖的奖券上去发泄,省得中了小的不能再中大的。他如此想着,在整个星期之中,他都是预算着中五万元头奖的事,同时他也日日估量着他自己箱子里的存款。原来他搬到会馆里的时候,只有五六块钱了,添着东西,和逐日的食用,已经耗费得只剩两块钱了,若是每餐到小饭馆里去吃三毛,又只能维持三天,三天以后,又将如何呢?为延长日子起见,还只有那个办法,自己来做饭吧!买十个铜子的米,十个铜子的油盐菜,五分洋钱就可以吃一餐,每天只要一毛钱的伙食罢了。于是把前几天所认为烦腻的事又干了起来。
这个日子,所买奖券的兑奖券日期都依次而过去,到了最后一个日子,便是五万元的开奖期了。他经过了许多日期,知道中奖不是件容易事,所以也并不怎样注意,心里淡淡的,把这个日期混过去,直到过了一天整的,然后才到那个奖券店去,远远地看到那家奖券店门口,红艳艳地挂了许多红绸帐幔,正中那幅红绸缀了四个大金字:“头奖志喜”。呀,这家店果然卖出头奖去了,买主不要就是我吧?想起来,心中立刻怦怦乱跳。及至到了大门口,只见一张大红纸上大书几行黑字:“本期慈善奖券,头奖为四五六三号,由本号售出,为大发银行赵君购得。”原来购得头奖的另有其人,不是自己,还是银行里的人中头奖,真是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但是头奖不中,别的小奖能中一个也好。于是走进店去,要了十二奖的号码,仔细检查一番,又是一个也不曾相符,而且自己奖券上的号码最末一字,也不和任何一奖末字相同,就是附奖也没有希望的了。算了,一场发财的梦到此完全告终。
垂头丧气走出店来,向回会馆的路上走,心里可就想着:要是不买这十几元奖券,在会馆里足可以维持一个半月,于今只剩了几毛钱,下午不但要吃饭,而且还要添炉火,就是今天已经不能过了。两手插在衣袋里,扛了两只肩膀,在马路上只管低着头走。忽然呜啦呜啦一阵乱响,汽车喇叭叫着,抬头看时,嘎叱一声,一辆大汽车在迎面停住,自己吓得赶紧将身子闪开,不免向开汽车的车夫瞪了一眼。那开汽车的是穿军服的人,他不但不怨自己莽撞,反向惜时瞪眼道:“差一点儿,没有压死你这小子,便宜了你。”惜时尚待说他时,看那车上有个穿皮大衣的女子偎在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小胡子先生怀里。那人是谁?不就是培大之花米锦华吗?自己为她落魄到这般地步,她又在别人怀抱里看着自己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