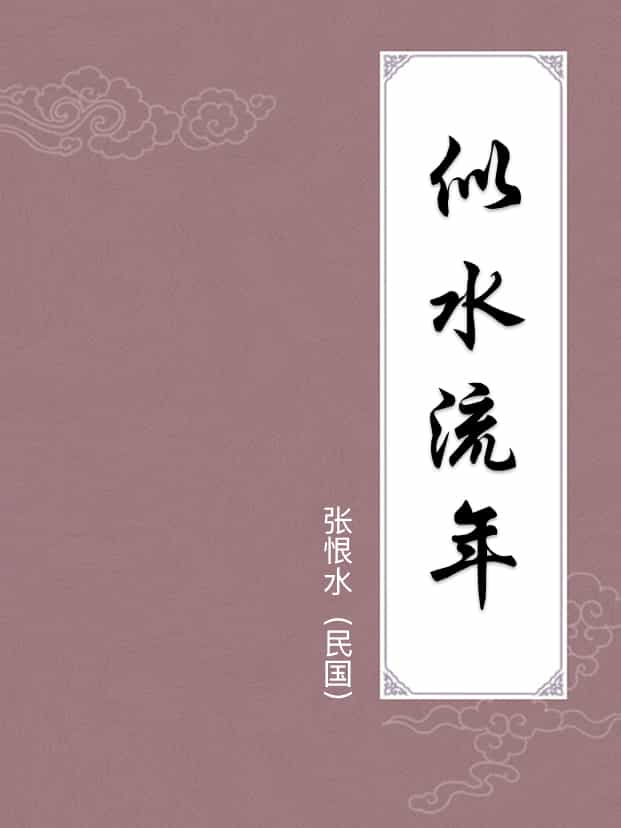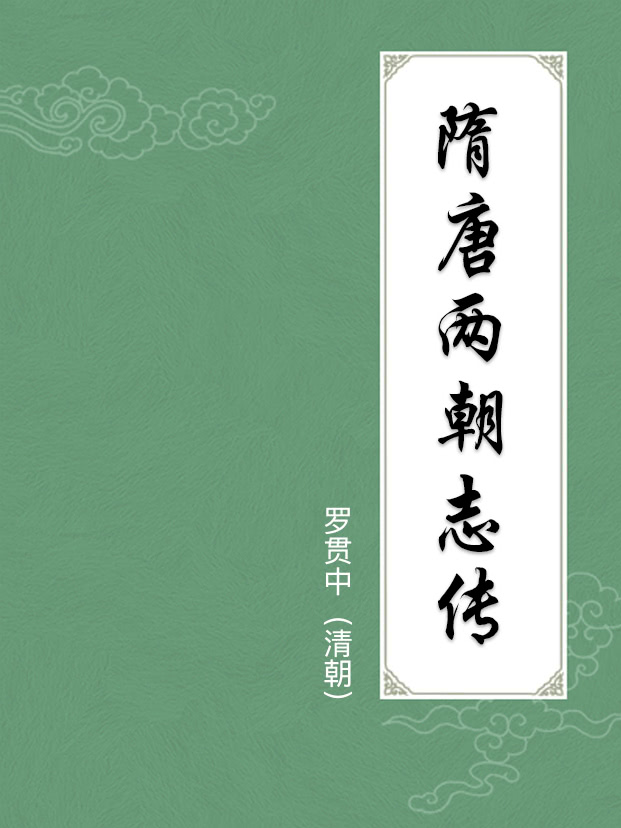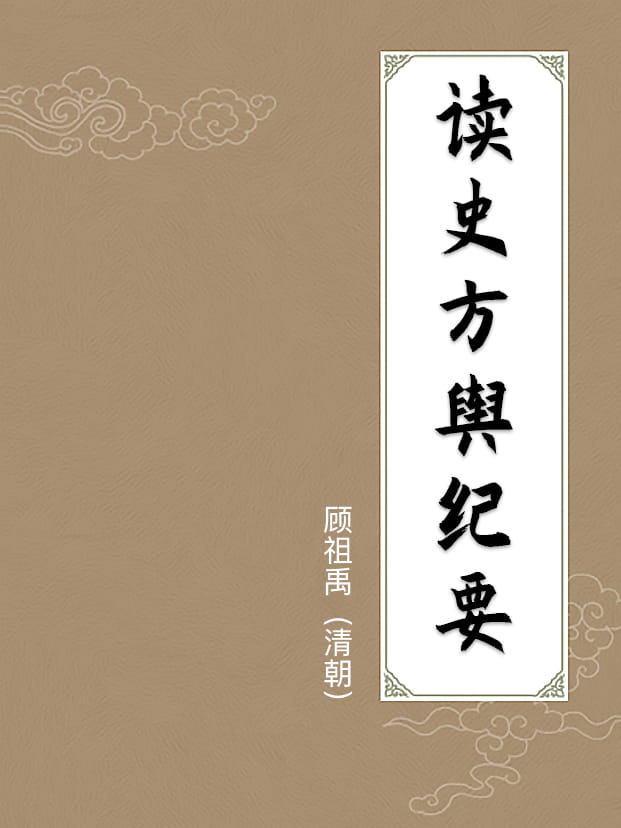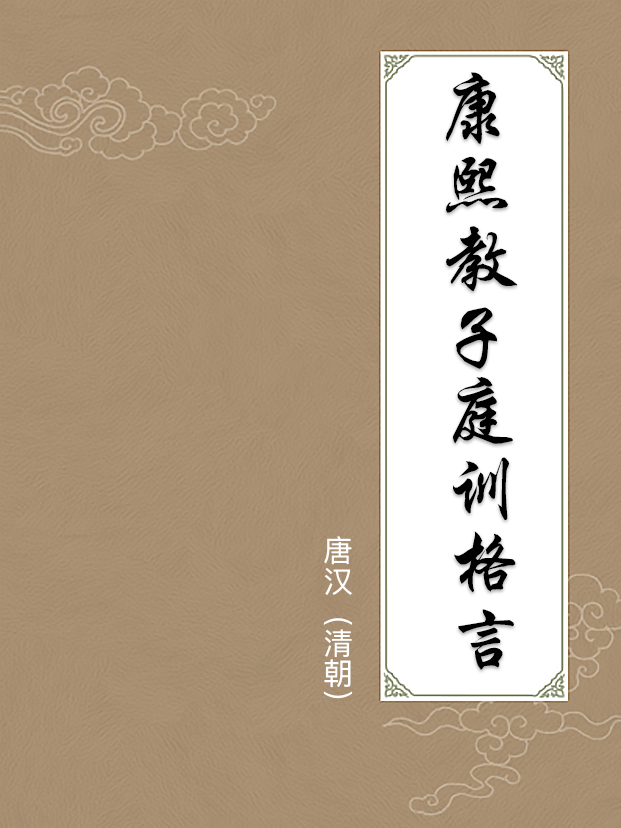上回书说到黄惜时在大街上经过,看到米锦华和军官同坐一辆汽车,带着微笑过去,真个是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一种酸甜苦辣掺和的滋味简直把自己麻醉了。他站在街上,待了半天,一步也移动不得,还是一个人力车夫拖了一辆车子过来向他兜揽生意,他这才回醒转来,坐了车子,就回转会馆,给了一毛钱车钱。身上的钱又少了几分之几,这钱一方面的事,简直不能想。所幸那炉火还是其势熊熊的,屋子里充满着暖气,连那件破大衣也不脱,随身向床上一倒,就躺着不动。
可是他外表这样静止,心里头却是加倍地浮躁,前前后后的事仔细一想。想过了之后,又要后悔。悔着想着,在床上直躺到天色昏黑,才叹了一口气。跳将起来,买了几个烧饼在炉口上烤着吃了。桌上放了一盏高不到一尺的煤油灯,倒罩着桌上放了一叠中奖以后的预算表,汽车算买了,洋楼算盖了,自己依然靠住了白炉子吃干烧饼。
正这样想着,忽然噗的一声,响入半天,自己想起来了,这已是旧历年边,旧京住户过旧年的思想很深,开始放年爆竹了。年年这时在南边,一担行李向乡下一挑,家人团聚,其乐融融,每日吃饱了饭,并无别事,不是背了手在河沿上看人打鱼,便是捧了一本书,坐在打稻场的稻堆上晒太阳,到了夕阳落山之下,看看那远山上,放着一丛丛的野火,非常有趣。南方虽到了严冬,也不过冷上两三天,其余的日子,依然可以在田陌上往来。尤其是下雪天以后,成千成百的斑鸠,它们到处寻找食物,庄稼人家的耕牛,放到干田里去吃草。那斑鸠有的站在牛犄角上,有的站在牛背上,那牛也并不知道,只管拖了那斑鸠走。这种景致在北方决计看不到,像这一类的事情,越想越多,更是想到南方的好处了。
一人如此沉沉想着,那爆竹声依然是霹雳一响冲入半空。听了这响声,就由过年上面,连续不断地想到家乡。看起来,在北京这样无目标地挣扎,哪有多少希望?一个人恋家乡,最浓厚是三个时期,一个是害病的时期,一个是天寒岁暮的时期,一个是投奔无路、衣食不给的时期。论到惜时的现在,几乎与三个条件都吻合,所以他回乡的心意又浓起来,只是这种计划已经晚了。由北京回家乡去,火车、轮船,至少也要三十块钱的川资,现在衣服差不多当光了,只有两条被褥还可以值几个钱,这个是不能当的,假使当了,就“衣食住”三个字索性全发生问题了,他自思自想,熬到深夜。
次日上午醒来,继续着又发生了煤火早饭的问题,待要不理会,只好饿着冻着,待要理会,买了煤火,就没有吃午饭的钱,预备了午饭,可又没有买煤火的钱。这个时候实在是不好办,到长班屋子里去,要了一盆热水洗脸,漱了漱口,连茶也不曾喝,就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只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那长班在他屋子门口过来过去两次,看看窗户脚下堆的煤球,已经只剩一二十个,炉子冷冰冰地放屋子里,也不曾移动。看那样子,自然是不预备笼火。只望了一眼,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就走开了。
惜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也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仿佛这样踱着步子,就能踱出什么办法来似的,足足地踱了两个钟头,也不曾停止一步。俗言道得好:饱暖饱暖,一个人吃饱了,身上自然会和暖,反过来说,一个人肚子饿了,自然身上也格外觉得不能抗冷。所以惜时转着转着,身上哆嗦着,有些支持不住,只好转身在床上坐了。想了许久,除了当当可以马上救急而外,其余没有别的好法子,然而以当当论,又只有床上的一被一褥是值钱的,当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他忽然用手拍着床,跳了起来道:“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一阵风似的,将两床被褥一卷,用一条半旧的洋线毯子一齐包了起来,自己跑到门口去,雇好一辆人力车,将铺盖提了出来,跨上车去,就让车夫拉上了当铺。
这个日子当被褥,当然比以前当皮袍子还吃紧,当铺里的人看在天时分上,对于这种当当的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当给惜时六块钱。照着典当规矩,当价不过本三成,说起来这两条被褥,已是估价二十元,当然不算少了。惜时有了六块钱,拿在手上掂了两掂,然后向袋里揣上,自己微微一笑,走出当铺门外。这日的天色虽然还十分晴和,可是北方的天气,只要一些寒风吹动,那冷气扑到人脸上来,就痛如刀割。惜时将破大衣的领子向上扶着,自己微笑了一笑,又抬着头看了看天空。他摇摆着头,又哧的一声笑起来。送他来的人力车夫,还在门口等着呢!看了他这情形,心里就想着:难道这人疯了?三九寒天,扛了棉被来当,当了还是这样乐着。这个人力车夫所猜的,果然有几分相对。他笑道:“是你拉我来的吗?你再拉我到前门正阳楼去,我要吃羊肉涮锅子。”车夫心想:羊肉涮锅子倒是冬天应该吃的,不过当了棉被去吃羊肉,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算盘。他如此想着,知道这个人不会少给钱,将车子拉过来,就请惜时上车,并不说多少价钱。惜时也不问他要多少钱,坐上车子,就让他拉了跑。
到了正阳楼,付了两毛钱车钱,一直冲到后进的雅座里,就叫伙计端火锅,端羊肉,真高兴得了不得。伙计正忙着张罗生意,对于这样一个穿破大衣的人并不怎样理会,只掀着帘子,走进来向惜时点了个头,笑着道:“您来啦!”说毕,放了一双杯筷到惜时面前转身就走开了。惜时坐在一张木炕上,手拍了寸来厚的布垫道:“坐得很舒服,穿了破大衣的人,那就不配坐了吗?”说着冷笑了一声,看那炕后面,高高地有个布枕头,伸了个懒腰,就向枕头上靠着,两腿弯了起来道:“只管慢慢儿地吧!屋子里有火,我先躺一会儿。”于是就闭了双眼,打着呼声,很舒服地睡了起来。
伙计因为这屋子里不曾叫唤,也就没有来,事情既忙,几个转身一打,就把这屋子里的主顾忘了。惜时见伙计不来,抬头一看,屋角里的铁炉子,火势烧得正是很旺,屋子里暖烘烘的,正好睡觉,就不理会,便稳稳当当地去睡觉。正睡得有些兴味的时候,那门帘子的下档啪的一声将门打了一响,惜时抬头看时,屋子里进来四五个主顾,正各人脱了大衣,要坐下来,忽然看到木炕上坐了一个穿破西服的人,都道:“这屋子里有人的,伙计为什么把我们让了进来呢?”他们就一迭连声来叫着伙计,伙计走了进来,半鞠着躬笑道:“先生要什么?”他们都说:“这屋子里有人,为什么把我们让了进来?”伙计看到,笑着哎哟了一声,连连打拱笑道:“对不住!对不住!重找一个屋子吧!”说着,他已抢着掀开帘子,让这班人出去。
惜时依然不作声,只是在炕上坐着,又等了十分钟的工夫,并不见伙计进来。惜时微笑道:“怎么,又不来人了?你不来,我再睡觉,我家里哪里有这样暖和的屋子呢!”自言自语地说着,又在高枕上躺了下去。这时,那伙计掀了门帘,弯腰走向前来,笑道:“先生!你就是一个人吗?”惜时笑道:“你有买卖,只管去张罗,我这里慢慢儿来没关系。我是当了棉被来吃涮锅子的,回家去,抗不了冷,你这儿屋子暖和,我在这炕上多睡一会儿,倒也不坏。”伙计听说,赔着笑脸道:“今天忙一点儿,短张罗,你别见怪!”惜时笑道:“我真不说假话,你不信,我拿当票子给你看。”伙计依然再三赔着不是,只是问他要些什么。于是惜时才说要一个锅子、半斤黄酒。伙计格外地巴结,将烧着热腾腾的一个大火锅子送了进来,锅子四围摆着十几个碟子,盛着酸菜、豆腐、粉条之类,又是几个小碗,盛着酱油汤、醋、虾油、青椒油之类。他笑道:“先生,您是一个人,先给你来三碟子肉吧!”惜时点了点头,他立刻捧了三碟子肉进来,那切着五寸长不到一分厚的羊肉片,铺在碟子里,作胭脂色,尤其是那瘦肉上,连着的肥肉丝儿,如白棉花一般衬托得好看。伙计是加倍地恭敬,两手代掀开锅盖,里面的开水沸腾着乱滚,热气直升到屋顶上去,他将酸菜、白菜、冻豆腐等等陆续地向水里放下,用一个小碗,调和了酱油、青椒油、芝麻酱,放到惜时面前,笑道:“葱蒜你自己加,南方人有不吃这个的,可是到北方来吃羊肉,总得加上点儿。”说着,捧了一壶酒进来,用大杯子斟上一杯,放在面前。惜时笑着点头道:“你自便吧!我也不是第一回吃羊肉。”伙计总觉得怠慢了这位先生,惹得人家总不适意,所以格外客气一点儿。现在惜时老是用话讥讽着,只得退出去了。
惜时夹了一大片羊肉,向锅里一浸,在水上涮了几涮,夹了出来,在作料小碗里蘸得饱满,向口里塞将下去,真个是香脆鲜嫩四字俱到,然后端起大杯子来喝了一大口酒。虽然这是一个人吃喝,不觉得拿了筷子向桌子上一敲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快活一天,就是一天。”自言自语地说毕,又涮着羊肉,吃了起来。这一顿大吃大喝,真个痛快之极。那火锅子的炉胆里,几根木炭烧着火焰直冒,那青烟带着锅子里沸腾的蒸汽,弥漫了半间屋子,同时自己身上也不住地向外冒着热汗。北方人吃羊肉涮锅子,必定要做到脱了皮袍子那一步,才觉着酣畅淋漓,所以惜时也就把大衣脱下,一脚架在板凳上,只管喝着吃着。
一会儿,伙计送了一碟子烤熟了的烧饼来,酥香利口,又拿上捏着吃了两个,这实在是肚子饱了,将筷子向桌上一丢,口里喊着道:“伙计!算账。”伙计进屋来,笑道:“你够了?”于是捡过碗碟,倒上一杯热茶来,走到柜上去,领了一张纸条,交到惜时手上,笑道:“我候着。”惜时看时,乃是一块五毛钱,在身上掏出两块现洋,当的一声向桌上一扔,笑道:“你别瞧我穿破大衣,不至于少给你们的小费吧!”伙计笑着连连点头道:“您多礼!”惜时也不再说什么,哈哈大笑了一声,披上大衣就走了出来。走出大门来,依然不问价钱,坐了车,就回会馆里来。
这屋子里,除了两只空箱子而外,便是些书本和零碎物件,冷冰冰的屋子里,除列着一副床铺板,这就更显得凄惨。惜时站在屋子中间,将东西都看了一看,不住地微笑。最后将桌上堆的一大沓书清理了一遍,在书本中找出两张相片,一张是米锦华的,一张是白行素的。他将米锦华的相片看了许久,向她微点着头道:“我领教了。”向字纸篓里一丢。再看那张相片,却是白行素的,他用手掌托了那相片,伸到远处看看,又拿着紧对了面孔看看,叹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是谁负了谁。”于是放在桌上,且不动她,接着就把字纸篓里的纸片和米锦华的相片,一齐倒进白炉子里去,擦了一根火柴,由炉子眼里向上点着,把所有的字纸全燃烧着了,火头伸出炉子口来,差不多有两三尺高,屋子里当然就有了暖气。惜时坐在一边笑道:“这倒不错,省了买煤的钱了。”他烧得高兴起来,索性把桌上的书整本地向炉子里塞着烧去。也不过一小时,把所有的书本都烧了。自己看看,屋子里还有些换洗的小衣和零碎物件,于是捡捡拢拢,全收到手提箱子里去,白行素的那张相片,随手拿起来犹豫了会子,也放到小箱子里去。
那会馆的长班看到屋子里火光熊熊,倒吓了一跳,赶快跳了进来,看到惜时在烧书,心里才镇定了,便笑道:“我的先生,你怎么在屋子里烧这个。”惜时笑道:“我要回南去了,不愿留下这些字纸,这屋子里的东西,我没有带走的都送给你了,有人到会馆里来打听我,你就说我回南去就是了。”说完了,提了手提箱子,挺着胸脯就走出去了。长班因为得了他许多零碎东西,心里很是感激。跟着后面,送了出来,只见惜时坐上一辆人力车,头也不曾回转过来,就径直地让人拉走了。
惜时这一走,却是出人意料之外,他并不向东西车站出去,却坐了车子,向那上西山的大道西直门来。这城门口有个长途车站,每日有两道长途汽车通到万寿山去的,惜时就搭了车子,向万寿山来。万寿山乃是颐和园的别名,园门口有一道小街,却也应有尽有,这街向南,有个很大的军营,乃是西苑营房,终年是驻着兵的,往北有一座延寿寺,是个乡村古刹。
惜时由长途汽车上下来,问明了路径,毫不犹豫地提了那小提箱,直向这延寿寺来。这寺门口有一片寒林,百十来棵树木,高入云霄,可是树叶子都已落光,在寒风怒号的长空里,摇着光杆子呼呼作响。树是那样高,矮短的红墙,拥着个小庙门,越是觉得这古庙的低小了。那两扇庙门在半阴半暗的空气里紧紧地闭着,门外却有几十只寒鸦站在树枝上呀呀乱叫,走上前,将庙门上的门环连连敲了几下,里面才出来一个人,将庙门开了。他头上虽然戴着一顶和尚帽,可是他身上穿的衣服不是那样大袖郎当,只是俗家穿的一件大棉袍子。看去大概有五十以上的年纪,瘦削的脸上长满了斑白的胡茬子,这样子,大概是这里和尚一分子,便向他点了个头。那和尚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的是一身西服,便道:“你先生是来逛万寿山的吗?这是一座破庙,没有什么可逛的。”惜时点头笑道:“破庙要什么紧,破庙才是古迹啦!”他口里如此说着,人已提脚跨过了门槛。那和尚看他有必逛之意,拦也是白拦,只得跟着他走了进来。
惜时走上正面的佛殿,看那佛龛外的幔帐都变成了灰黄色。这个地方没有人理会过,也就可想而知。桌上只摆了一套洋铁的五供,却有一大半是长了锈的,其间还有个黑色的香炉,也不知道是瓦质的还是铁质的。正面佛龛的两边也有两处配祀的小佛龛,只是泥涂的佛身都已丹垩剥落。右边观音大士手上拿的净水瓶子,只空了手,左边一尊长胡子的佛像,只剩了耳朵下十来根,断的其余都没有了。这样一个庙,其穷寒可想而知,不用得问了。
那和尚跟在后面道:“先生!我不冤你吧!这里是什么看的也没有。”惜时道:“这庙里就是师父一个人吗?”那和尚合掌道:“阿弥陀佛,先生!你看这庙里还能容多少人?”惜时道:“这里还有佛殿吗?”和尚道:“后面还有一所佛殿,已经倒了,就剩下两间房,留着我住。”惜时想了一想道:“我有件事和老和尚商量,不知道可能答应?”那和尚料着一个穿西服的游客,也不会和这破庙里的和尚要求什么,便笑道:“有什么话,你先生请说吧!”
惜时道:“我老实告诉老师父,我是一个大学生,只因看破了红尘,想找个地方出家,但是那些大庙里,都富丽堂皇的,不像是出家人修行之所,我立意要找个老庙,在家里我听到人说,有个同学在你这庙出过家,后来转到大庙里去了。当时我听在心里,预备有一天出家,就来拜访,这也是有缘,今天居然来了。”
老和尚合掌啊哟了一声道:“不错!是有这样一回事,三年多了。那位先生,是个情场中失败的人,他书也不念,就跑到我这里来修行。我告诉他,出家不是一件容易事,请他还去念书,不料他无论如何劝不转,总要出家,在我这里住了半年,倒是真出家了。但是他心里可丢不开,后来一天比一天消瘦,闹成了很重的肺病,我这里没有法子和他治病,他就走了。你先生怎么样,也学他的样吗?”
惜时道:“我并不是情场失败……一个人要出家,不能说假话,虽然也有一点儿,但是以前的事了。”老和尚和他说着话,一双眼睛可不住地在他周身上下打量,便道:“你先生既知道出家人是要说真话的,我也可以很老实地告诉你,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们可不敢收容。”惜时道:“这个我也知道,不过在大庙里收容,或者疑心我会拿去什么。像宝刹这样清净,我会拿去什么呢?出家人慈悲为本,何不把我收留了?”
老和尚对他手上提的小箱子又看了看,问道:“你就是这一件行李吗?”惜时道:“一个人出了家,四大皆空,还要行李做什么?不过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绝不能白吃白喝,我身上有四块钱,先交给老师父买些吃的,晚上我只要有个容身的所在,那就行了。”说着话,就掏出身上所剩的四块大洋一齐交到和尚手上去。
老和尚手上捏住了四块钱,待要不收留他时,简直是把上门买卖推掉,而且他一出手就给四块钱,行囊里大概还有几文,且让他在庙里住下,多少可以补贴庙里一点儿,只当他是赁庙住的,至于他出家不出家,那就不必去管了。如此想着,就现出很踌躇的样子道:“你要在庙里住也可以,可是话要先说明,我这样一个穷庙,可不能添一口人,以后你得常拿出钱来补贴用费。从前那个人在这里出家,也是一个月贴我八块钱,你这四块钱,只好算我们半个月的嚼裹罢了。”惜时这才明白,就是出家,也不少于酒色财气的“财”字,不过有了这四块钱,可以混半个月的了,过了半个月再说。当时就点头道:“这个好办,依着老师父就是了。”
这老和尚于是替他提了皮箱,走到后面住房里去。这里只有一个大土炕,上面铺张炕席,一床蓝色的布褥子,和一床灰色的薄被,卷成两个卷儿,塞在炕角里,倒是屋子里暖烘烘的。原来炕眼里塞了个小火炉子,把炕烧暖和了。这半边屋子里倒也清爽。除了这张土炕而外,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半边屋子却当了厨房,一个白炉子上熬了一锅粥,一张半边桌子堆了白菜萝卜、锅盆碗盏之类,地下堆了一捆大葱,又是煤球、散柴棒子、零碎报纸,墙上也贴了一张木刻版的观音像,旁边却挂了一大把大蒜和两个茶壶大的干葫芦。这屋子里陈设便是如此,别的罢了。这些东西让暖气一烘,烘出一种奇怪的味儿来,向来在文字上所认识的和尚都是非常之高雅的,如今看起来,事实恰是与理想相反。老和尚道:“你没有铺盖,先分我一条垫褥去睡吧!”惜时看那被褥都是油腻了的,料着这屋子里一种怪气味,有不少是由那上面放出来的。便道:“老师父也就只两条被褥,我怎能分你的,我就在炕上练习打坐得了。”老和尚这一垫一盖,实在也不能分给旁人,就也不去勉强,他就端下粥锅,在屋那头切着萝卜,做起晚餐来。惜时趁着这工夫,溜出屋来,在庙前庙后仔细看了一遍。
这庙里不但没有什么经卷,而且和尚用的法器也不曾在外陈列着,若不是这正殿上有三尊佛像,简直要误认这是个平常人家了。在这种地方出家,能得些什么道学?好在自己一身之外已无多长物,混一天是一天,又不曾拜这老和尚为师,管他行为如何呢!如此想着就也不曾追问,胡乱地在庙中住下。当天和老和尚吃了一餐粥,晚上和着衣在炕上睡了一宿暖炕。
到了次日,又吃了两顿窝头,这时大体已经知道老和尚为人。他叫智通,原来是庙里香火工人,因为老方丈死了,他就顶着这庙里的产业,住持下来。这庙里产业虽不多,但是收起来的粮食,一个人实在吃不了。智通不认识多少字,又没有学过佛事,索性关上庙门,就坐在庙里闷吃。到了第三天,惜时知道一切了,又觉此行来得孟浪,四块钱,他只允许吃半个月,半个月以后,自己没有了钱了,岂不要被他轰出门外?为今之计,赶快先去找一条出路要紧。
他如此想着,在寒风里听到一阵军号声,自己忽然得着一个感想,与其这样消极地做和尚,还不如积极地去当兵,只是这一条路,除了有招兵的人,然后应征而外,绝不能够突然到军营里去投效。这颐和园大门口有一条小街,西苑军营里的人,总少不得有到那街上去消遣的,自己何不也到街上去溜溜?只要有机会认识两三个人,或者就可以向军界里进身的。摸摸身上,还有几毛钱,于是乎披上破旧大衣,走到这半乡半城的街上来。
这样三九天气,所有的店铺都已经紧闭门窗,除是在那门外的厚棉帘子上有白布 的字可以分别出这都是些什么店铺。街中间有家铺子,用棉绳穿了四块小木板,悬在屋檐下,那上面写着“龙团雀舌”的名字,这很可以看出来,乃是一家茶铺。这门口用纸糊了两个长方灯架子,一个上面写着“张乐亭今日白天准说《反唐》”,又一个上面写“李子和今晚《西游》”,原来这茶馆是靠了说书先生来号召的。这茶馆门外,虽然没有什么人,里面却人声哄哄,像座客不少。惜时知道这种茶馆是花钱不多的,于是一掀棉布帘子钻了进去。只见这里面一行行地摆了长桌子长板凳,上面也有个像学校里教室讲台的情景,有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说书的人还不曾上去,长板凳上坐满了人,喝茶抽烟,说着闲话。惜时觉得回庙也是无聊,就挑了桌子尽头处板凳上坐了,这种座位,是两条丈来长的板凳,夹着一张丈来长的窄桌子,所以座客都是对面地坐着。惜时对面恰好是个军人,他将军帽和一根瘦小的马鞭子都放在桌子上,抬起一只腿来,将腿架在上面,他见惜时是穿西服进来,向他看了一眼。惜时倒是很客气,反向他点了个头,那军人虽没有理会他,却也有点儿笑意。
一会儿见伙计来和惜时张罗茶水,惜时将茶壶茶杯摆得远远的,离开着那军帽,那军人倒过意不去,将帽子戴到头上去。惜时看见有提篮子卖瓜子花生的,于是买了十个铜子的大花生,放在桌上,向那军人道:“老总!吃一点儿。”那军人道:“不客气。”惜时又买了三支烟卷,敬他一根,他不便推却,只得抽了。于是开始谈起话来,他叫孟占鳌,是个排长,最爱听书。他一排人就驻在颐和园门口,所以他天天有工夫来听说书。惜时也告诉他寄住在延寿寺里,只说跟和尚认得,却没有提起“出家”二字,到了说书的上台,孟排长有不大了解的,惜时又替他补充一两句,孟排长很是欢喜。听完了书,约着明日见,各自回家了。
回得庙来,天气转变了阴暗,这旷野中的西北风比城里的西北风也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风刮得脸上痛得像要裂开缝来,只好开着跑步跑回庙去。这时智通又在屋子里蒸窝头,自己连大衣也不脱,立刻站到白炉子边,伸了两只手,遥遥地围了炉子取暖。智通拿了个瓦钵子,将切碎了的白菜完全向里面倒着,他两手捧着瓦钵子掂了几掂,向惜时问道:“你在街上回来,都不带一些菜回来吗?”惜时道:“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智通道:“倒不是我要你带菜来吃,因为早上我看到你吃熬白菜,好像很没有味似的,下午也许你会带些吃的回来了。”惜时心里这可就想着:岂单白菜我不愿意吃,就是窝头我也没法子再吃了。现在闻到蒸窝头的这种气味,似乎就要做恶心,漫说还要继续地向下吃,我倒佩服这个老和尚,竟是餐餐蒸窝头,不做第二想。
智通见他对了白炉子上的小笼屉只管出神,料想他是想到了窝头的问题上来,便道:“明天上午,咱们包一餐角(读如“饺”)子吃吧!豆腐白菜馅,你只要拿出四毛钱来,全办得了。”惜时身上所有的也不过这个数目,对于智通的话,就没有加以答复。智通见他不理会,也不再说,将蒸的小笼屉拿下,放上瓦钵子去,自言自语地道:“咱们是吃窝头的命,吃就吃到底,别三心二意的了。”
惜时只当没有听到,且在炕上躺着,等白菜熬汤熬得了,将钵子放在炕沿,两人就站在地上,一手拿窝头啃着,一手拿了筷子,向瓦钵子里连汤带水夹着白菜吃。这菜里头荤素油都不曾放,只是倒了一撮盐在汤里头,实在吃不出个味来。这窝头是吃过三天的东西,真有点儿够了,只吃了一个,实在吃不下去,就不想吃了。一个窝头当然是不够饱的,便是到了这天晚上煮饭的炉子先灭,屋子便减少了许多热气,那烧炕的小炉子也像灭了。炕上并不是那样暖气烘烘的,睡到半夜,智通将被掩得紧紧的,手脚缩成了一团。惜时和了大衣,睡在光光的炕席上,先是脊梁上犹如冷水冰了一般,渐次蔓延到四肢,都有些冷,勉强忍耐着,在炕上翻了两个身,依然闭了眼睡去,但是到了半闭着眼睛要睡过去的时候,身上简直冷得有些抖颤,又把人冷醒了。这没有法子,只得走下炕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身上越冷得厉害,自己就越跑得厉害,跑得屋子里只是噗噗作响。智通被这种声音惊醒,在被里翻了一个身道:“你怎么半夜不睡,起来胡跑?你不睡,别人也不睡吗?”惜时道:“我有什么不睡,但是炕里没有火,我又没有盖的,实在冷得受不了,假使我睡着冻病了,这不也是你的事吗?”
智通被他这利害相关的话说通了,倒有些恻隐之心发现,便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子想不开,屋子里有的是劈柴煤球,你不会把火笼着来吗?”惜时对于笼火这件事在会馆里已经领教过了,白天笼火,已经觉得是筋疲力尽,现在漆黑了的夜间,摸这样,摸那样,这个火如何笼得着?在屋子里将两手插在衣袋里,还是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智通见他不听讲,将头向被里一缩,索性一切置之不理,去呼呼大睡。
这冬日夜长,半夜起来是起来了,可是这天色依然黑沉沉的,窗子里看不到窗子外一些东西。没有法子,只得走出房去,走到大佛殿上,绕了大佛龛,开起跑步来,先跑了三四个圈圈,还不觉得有什么变态,直等跑到上十个圈圈以后,上气喘息着接不了下气,渐渐地身上有些汗透出来,但是五官四肢,依然还是冷着,还是继续地跑,直跑到脚提不动了,热气由手板心、脚板心冒出来,这才摸着佛龛前一个支蒲团的木头架子上坐了。坐到十分钟,遍体暖气直冒,这才感到遍体舒适,就靠了桌子腿,慢慢地睡去。
可是不过睡到一小时以后,两只出了汗的脚板放在地上,首先冷了起来,接着两腿和脊梁也有些发冷,于是站起身来,又绕了佛龛开起跑步来。这样歇了就跑,跑了又歇,自己一个人这样闹到大天亮,直等智通起了床,然后才帮着笼起了火,烧水蒸窝头,把时光混到中午去。吃过了饭,依然又到颐和园门外茶馆子里去听书。
今天来得早一点儿,茶座上还没有什么人,于是先沏了一壶茶,买了一把铁蚕豆慢慢咀嚼着。恰是那孟排长今天也闲着,不一会儿工夫,他也来了,今天见面,比昨日相识得多。孟排长渐渐知道他是个大学生,便笑道:“我有两三个月没有写信回家去了,请你替我写封信,成不成?”惜时道:“这是很容易的事,有什么行不行?有什么话请你说出来,我可以照写。”孟排长笑道:“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了,你替我写了一封吧!”惜时心里想着,一个人不通文墨,就这样不讲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这真也和那镇台大人要老夫子代写三代履历的一样笑话了,不过和他谈两天的话,也很知道他的近况,便笑道:“那也可以,我先替孟排长起张信稿子,写好了,我念给你听,能用,就寄出去,不能用,就重新再写一张,您看好不好?”孟排长随便答应了。就和茶馆要了纸笔墨砚放到桌上来,惜时对于写这种家常信当然优为之,一面和他谈话,一面写信,把信写完了,便念给他听道:
双亲大人膝下:
上次奉禀而后,有三个月没向家里寄信了,这实在因为公事忙,而且不得便人写信的缘故。上两个月,奉令调防到万寿山守卫,并不天天上大操,清闲得多,只是两个多月才发一次饷。儿在外面,除了剃头、洗衣、买茶叶烟卷之外,又要结交朋友,钱不够花,所以没有往家里寄钱,所幸儿身体康健,比在家还好,望大人可以不必挂念。听说今岁年收很好,儿甚放心。现在年冬岁毕,望大人保重!过年以后,二弟还照前一样,好好做生意,不必三心二意。儿投军几年有什么好处?当差事不容易。可叮嘱二弟,不必出门,在乡一家团聚,岂不比儿这样终年不归的好吗?今因年底已到,特写此信回家,向二老拜年。其余家中之事,二老自会料理,用不着儿多说了。
敬叩
年安
儿占鳌拜上
惜时把这封信念完了。孟排长拍着手跳了起来道:“你这人有状元之才,将来一定要发达,我心眼里的话,口里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写得这样清清楚楚?你不要懂些奇门遁甲,会算命占课吧!”这茶馆子里还有几个喝茶的人,曾听到惜时把信念了,这时孟排长一嚷,大家围了拢来,都争着要信看。孟排长向大家道:“咱们听书,那些封侯拜相的人,不都是以前很落难的吗?这位黄先生你别看现在倒霉,将来是难说的。”这茶馆子里最出风头的就是孟排长,孟排长这样抬举黄先生,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捧起黄先生来,当天孟排长高兴极了,听过书之后,就拉着惜时到隔壁二荤铺里,大吃大喝一顿。
这个时候,正是过年的日子,弟兄们都免不了要写信回家,于是他这一排人都来托惜时写信,有钱的请他吃一餐,没有钱的,惜时就和人家这样白写。只有一个礼拜的工夫,这万寿山街上,就没有人不知道穿洋装的写信先生。惜时认识大兵多了,辗转介绍,连西苑的兵士都有找他写信的。他得了大兵的帮助,就终日不回延寿寺去吃那窝头,而且夜夜地住在街上的小客店里,也不回庙去睡,从此成了个随遇而安的野人。虽是“饱暖”两个字,依然没有凭据,但是以目前而论,也不至于因两餐一宿发生多大的困难。自己索性把这个身子,看着无挂无碍的东西,终日和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在一处厮混着,糊里糊涂,就到了过年的时候,好在所认的朋友也都是做客在外的,大家不过年,也少引起一些感慨。万寿山附近并没有多少人家,过年的爆竹也放得不是那样厉害。
这天下午,孟排长约了他在小街上大酒大肉吃了一餐,晚上就在小茶铺里和几个拉长途车子的人力车夫,赌了一晚小输赢的麻雀牌,然后就睡了。直至上午十一点醒来,心想既是住在延寿寺里,那个智通和尚多少可算一个屋子主人,自己应当去和他贺贺年。于是穿了大衣,匆匆地就回延寿寺来。往日这庙门总是闭得铁紧,要进去,要敲很久的门,今天这庙门却是半掩着的,用手推进门去,走到大佛殿上,远远就喊着道:“老师父恭喜恭喜!给您拜年了。”不料后殿声音寂然,却没有一点儿答复的声音,心里想着昨天大除夕,应该和老和尚买些豆腐白菜回来,自己快活过年没有理会他,也难怪他生气了。心里这样想着,口里依旧叫着恭喜,及至走到屋子里去,事出意外,却吓了一跳。这样一来,让他在悲苦的境遇里又增加一番悲苦了。欲知此系何事,容在下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