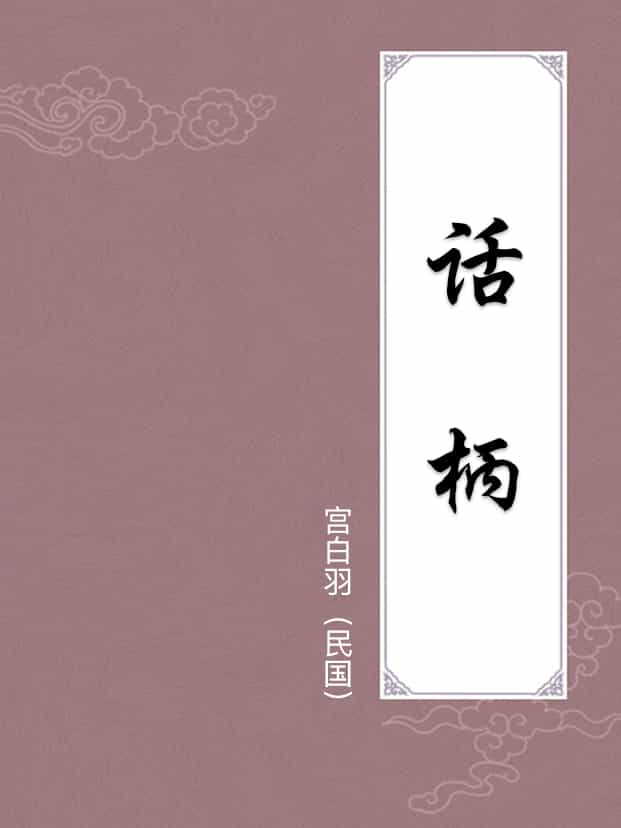民国纪元年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于“马厂誓师”的马厂。
祖父讳得平,大约是老秀才,在故乡东阿作县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门。祖母生前常夸说:“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不信,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这是真的。甚么大官呢?据说:“不是吏部天官,就是当朝首相”;在甚么时候呢?说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据说嫁过来时,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奁田。为甚么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独生女,很娇生,已逾及笄,择婿过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妯娌娌……人多受气,吃苦。后来东床选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虽中资,但是光棍鬼,无公无婆,无兄无弟,进门就当家。而且还有一样好处,俗语说:“大女婿吃馒头,小女婿吃拳头”,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于是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为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气很大,比有婆婆还难伺候。听二伯父说,祖父患背疽时,曾经打过祖母,又不许动,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
我们也算是“先前阔”的,不幸,先祖父遗失了库银,又遇上黄灾,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拖着三个小孩,(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彼时父亲年只三岁)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赔偿库银后,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苦斗,挣扎,把三子抚养成人。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岁时,祖母还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严肃,但很爱孙儿——我就跟着祖母睡,曾经一泡尿,把祖母浇了起来;却有点偏心眼,爱儿子不疼媳妇;爱孙儿不疼孙女。当我大妹诞生时,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又添了一个丫头子!”这“又”字只是表示不满,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
××××
我的父亲讳文彩,字协臣,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母亲李氏,比父亲小着十六岁。父亲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入民国后希望当团长,而结果都没有如愿;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便殁于复辟之役的转年,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
大伯父讳文修,二伯父讳文兴。大伯父管我最严,常常罚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有一次我拿斧头斫那掉下来的春联,被大伯父看见,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然后画一个圈,教我跪着。母亲很心疼的在内院叫,我哭声答应,不敢起来。
大伯父大声说:“斧子劈福字,你这罪孽!”忽然绝处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一把先将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捲”了一顿。大伯父干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爷”!
大伯父的故事太多,好苛礼,好咬文,有一种癖好;喜欢磕头,顶香,给人画符。
二伯父又不同,好玩鸟,好养马,好购买成药,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确切记得,有两回很出了笑话。人家找他要痢疾药,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人问他:“做几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轻重,说:“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赶来,看了看坊单,才阻住了。
不特此也,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说是主治某症,他真个就信。我父亲犯痔疮了,二伯父掏换一个妙方来,是“车辄土,加生石灰,浇高米醋,薰患处愈。”
我父亲皱眉说:“我明天试吧!”对众人说:“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怎么好!”
又有一次,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给我的吃乳的侄儿,治好了某病。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把这药吃下去,死了!
过了些日子,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病了,他又逼着吃,又死了。最后大嫂嫂另一个小孩病了,他又催吃这个药。——结果没吃,气的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
母亲告诉我: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前十年没剩下钱,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大伯父之子)给消耗净了的;我们是始终同居,直到我父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