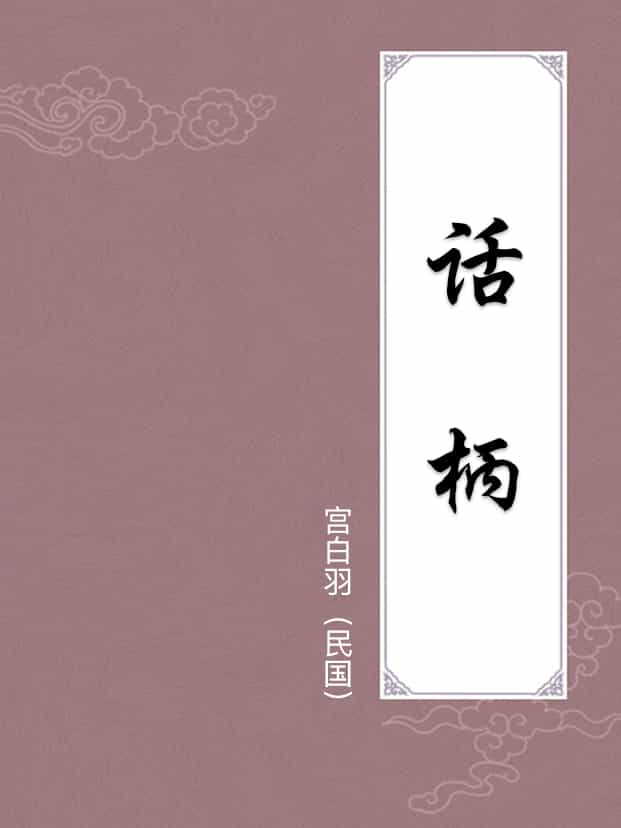在北京十年苦挣。我遇见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见了热情的援手。而热情的援手,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民十七以前,我历次的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邮员、税吏,并曾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官,仍不能解决人生第一难题。军队里欠薪,我于是“谋事无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版、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我的环境却越来越困顿,人也越加糊涂了;多疑善妒,动辄得咎,对人抱着敌意。我颓唐、我忿激,我还得挣扎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穷途的刺激,格外加增了我的乖僻。
终于,在民十七年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因为在十一天中,宣传了八回换局长,受不了乍得患失的恐惧频频袭击,我就不顾一切,支了六块大洋,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只身来到天津,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