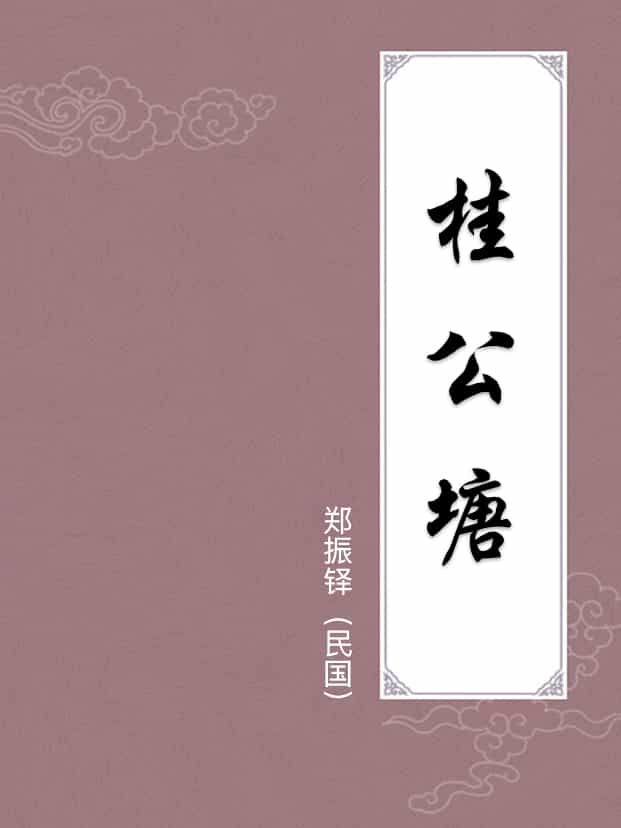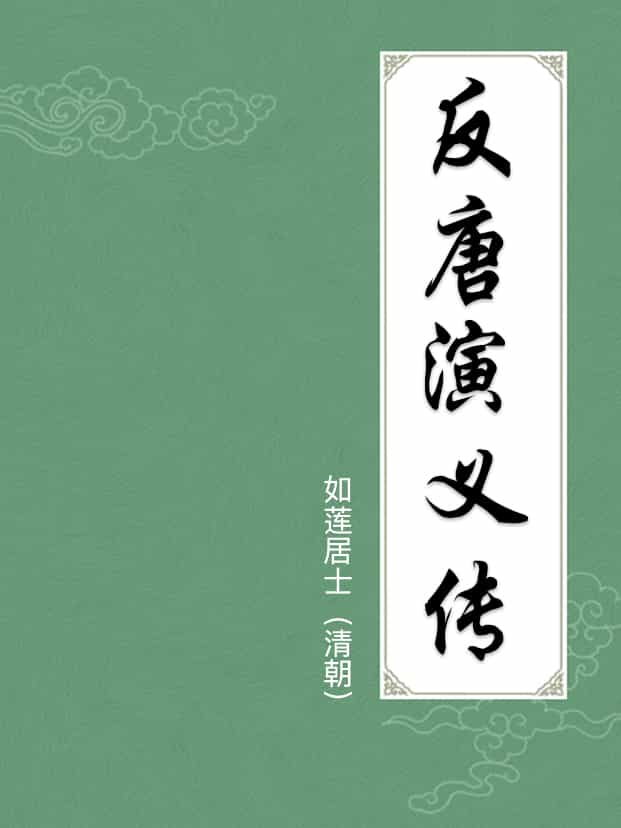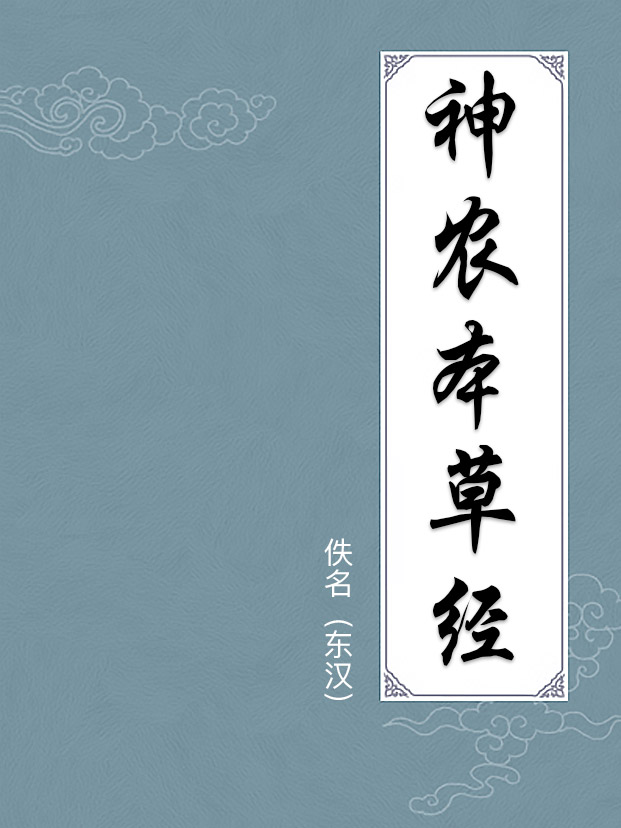有点兒懊丧。这打着民族复兴的大旗的义师,果眞是这样的残暴无人理么?眞的专和讀書人作对么?
說是崇拜天主,那也沒有什么。毁烧庙宇,打倒佛道,原也未可厚非。
要仅是崇信邪敎的草寇,怕不能那么快的便得到天下的响应,便吸收得住人心罢。
民族复兴的运动的主持者,必定会和平常的流寇規模不同的。
难得其眞相。
紳士們的口,是一味兒的传布着恐怖与侮蔑之辞。
黃公俊仿佛听到一位紳士在玩味着洪秀全檄文里的数語:“夫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故胡虏之世仇,在所必报,共奋义怒,歼此丑夷,恢复旧疆,不留余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恶之正。”还搖头摆脑的說他頗合于古文义法。
他覚得这便是一道光明,他所久待的光明。写了这样堂堂正正的檄文,决不会是什么草寇。
紳士們的奔走、呼号、要求編練乡勇,以抵抗这民族复兴的运动,其实,打开天窗說亮話,只是要保护他們那一阶級的自身的利益而已。
他也想大声疾呼的劝乡民不要上紳士的当,自己人去打自己人。
他想站立在通衢口上,叫道:“他們是仁义之师呢,不必恐慌。紳士們在欺騙你們,要你們去死,去为了保护他們的利益而死。犯不上!更不該的是,反替我們的压迫者,我們的世仇去作战?諸位难道竟不知道我們这二百年来所受的是什么样子的痛苦!那旗营,摆在这里,便是一个显例。諸位都是身經的……难道……”手搖揮着,几成了眞实的在演說的姿势。
但他不能对一个人說;空自郁悶、兴奋、疑虑、沸騰着热血。渴想做点什么,但他和洪軍之間,找不到一点連絡的綫索。
后街上住的陈麻皮,那无賴,向来公俊頗賞識其豪爽的,突然的不見了。紛紛藉藉的传說,說是他已投向洪軍了,要做向导。
接連的,卖肉的王屠、挑水的胡阿二,也都失踪了。凡是市井上的泼皮們,頗有肃清之槪。
据說,官厅也正貼出煌煌的告示在捕捉他們。东門里的曹狗子不知的被县衙門的隶役捉去,打得好苦,还上了夹棍,也招不出什么来。但第二天清早,便糊里糊塗的綁出去杀了。西門的伍二、刘七也都同样的做了牺牲者。
虽沒有嫌疑,而平日和官衙里結上了些冤仇的,都有危险。聪明点的都躱藏了起来。
公俊左邻的王老头兒,是卖豆腐浆的,他有个兒子,阿虎,也是地方上著名的泼皮,这几天藏着不出去。但老在不平的駡。
“他媽的!有我們穷人翻身的时候!”他捏紧了拳头,在击桌。公俊恰恰踱进了他的門限,王老头兒的兒子阿虎連忙縮住了口,站起来招呼,仿佛当他是另一种人,那紳士的一行列里的人。
他預警着有什么危险和不幸。
但公俊客气的和他点头,随坐了下来。
“虎哥,有什么消息?”
阿虎有点心慌,連忙道:“我不知道,老沒有出过門。”
“如果来了,不是和老百姓們有些好处么?”
“…………”阿虎慌得涨紅了脸。
“对过烧餅鋪的顧子龙,不是去投了他們么?还有陈麻皮。听說去的人不少呢。”
“我……不知……道,黃先生!老沒有出門。”声音有点发抖。
公俊恳摯的說道:“我不是来向你探听什么的,我不是他們那一批紳士中的一个。我是同情于这个杀韃子的运动的,我們是等候得那么久了……那么久了!”头微向上仰,在幻梦似的近于独語,眼睛里有点泪珠在轉动。
阿虎覚得有点詫异,細細的在打量他。
瘦削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双眼,脸上是一副那末坚定的、赴义的、恳摯的表情。
做了十多年的邻里,他沒有明白过这位讀書人。他总以为讀書人,田主,总不会和他們粗人是一类。为什么他突然的也說起那种話来呢?
“沒有一个人可告訴,郁悶得太久了……祖父,父亲……他們只要在世看見,听到这兴复祖国的呼号呀……該多么高兴!阿虎哥,不要見外,我也不怕你,我知道你是說一是一的好汉子。咱們是一道的,唉,阿虎哥。那一批紳士們,吃得胖胖的,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利益,猪狗般的匍伏在韃子們的面前,过一天是一天的,……但太久了,太久了,过的是二百多年了!还不該翻个身!”
于是他憤憤的第一次把他的心敞开給别人看,第一次把他的家庭的血写的历史說給别人听,他还描状着明季的那可怕的残杀的痛苦。
阿虎不曾听見过这些話。他是一个有血气的少年,正和其他无数的长沙的少年們一样,他是嫉視着那些駐防的韃子兵的;他被劳苦的生活所压迫,連从容吐一口气的工失都沒有。他父亲一年到头的忙着,天沒有亮就起来,挑了担,到豆腐店里,批了豆腐浆去轉卖。长街短巷,喚破了喉嚨,只够两口子的温飽。阿虎,虽是独子,却很早的便不能不謀自立。空有一身的膂力,其初是做挑水夫,間也做轎夫,替紳士們作馬牛,在街上飞快的跑。为了他脾气坏,不大逊順,連这工作都不长久。沒有一个紳士的家,願意雇他的。只好流落了,什么短工都做。有一頓沒一頓的。沒了时,只好向他年老的父亲家里去坐吃。父亲叹了一口气,沒說什么。母亲整日的放长了脸,尖了嘴。阿虎什么都明白,但是为了飢餓,沒法。他憋着一肚子的怨气。难道穷人們便永远沒有翻身的时候了?他也在等候着,为了自己的切身的衣食問題。
一把野火从金田烧了起来。說是杀韃子,又說是杀貪官汚吏,杀紳士。这对了阿虎的劲兒,他喜欢得跳了起来。
“也有我們穷人翻身的时候了!”
他第一便想搶曾乡紳的家,那暴发的紳士,假仁假义的,好不可恶!韃子营也該踏个平。十次抬轎經过,总有九次被辱,被駡。有一次抬着新娘的轎,旗籍浪子們包围了来,非要他們把轎子放下,讓他們掀开密包的轎帘,看看新嫁娘的模样兒不可。阿虎的血往上冲,便想发作。但四个轎夫,除了他,誰肯吃眼前亏。便只好把怨气往回咽去下。他气得一天不曾吃飯。
报怨的时候終于到了!該把他們踏个平!穷人們該翻个身!
他只是模模糊糊的認得这革命运动的意义,他幷不明白什么过去的事。只知道:这是切身的問題,对于自己有利益的。这已足够鼓动他的勇气了。
太平軍,这三字对他有点亲切。該放下了一切,去投向他們。陈麻皮們已在蠢蠢欲动了。
还有什么可牵挂的?父母年紀已老,但誰也管不了誰,他們自己会掙吃的。他去了,反少了一口吃閑飯的。光棍的一身,乡里所嫉視的泼皮,还不掙点面子給他們看看!
他想来,这冒险的从軍是值得做的。这是他,他們,报怨,翻身的最好的机会。
他仿佛記得小时候听人說过什么,“将相本无种,男兒当自强”的話,他很受感动。
他下了个决心,便去找陈麻皮。麻皮家里已有些不伶不俐的少年們在那里,窃窃紛紛的在議論着。
“正想找你去呢,你来得刚巧!”麻皮道。
“麻皮哥,該做点事才对呢,外头风声紧啦。”阿虎道。
麻皮笑了,俯在他的耳旁,低低的說道:“阿虎哥,有我呢。洪王那边已經派人来了。大軍不日就到,要我們做內应。不过,要小心,别漏出风声,听說防得很严紧。”
阿虎走出麻皮的門时,一身的輕松,飘飘的象生了双翼,飞在云中,走路有点浮。过分的兴奋与快乐。
但不知怎样的,第二天,这消息便被泄漏了。麻皮逃得不知去向,他的屋也被封了。捉了几个人,都杀了。
連絡綫完全的断絕,阿虎不敢走出家門一步。
天天在郁悶和危险中过生活,想逃,却沒有路費。
黃公俊的不意的降临,却开发了他一条生路。听見了許多未之前聞的故事和見解,更坚定了他跟从太平軍的决心。他从不曾想到,讀書人之間,也会对于这叛乱同情的。
“但,黃先生,不瞞您老說,我也是向着那边的。太平王有过人来說,……不是您老,我肯供出这杀头的事么?……可惜,这消息不知被那个天杀的去通知衙門里人。陈麻皮逃了,不知去向。……現在只好躱在家里等死!”說着,有点暗然。
“怕什么,阿虎哥!要走,还不容易。明天,我也要走,雇了你們抬轎,不是一同出了城么?”
阿虎又看見前面的一道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