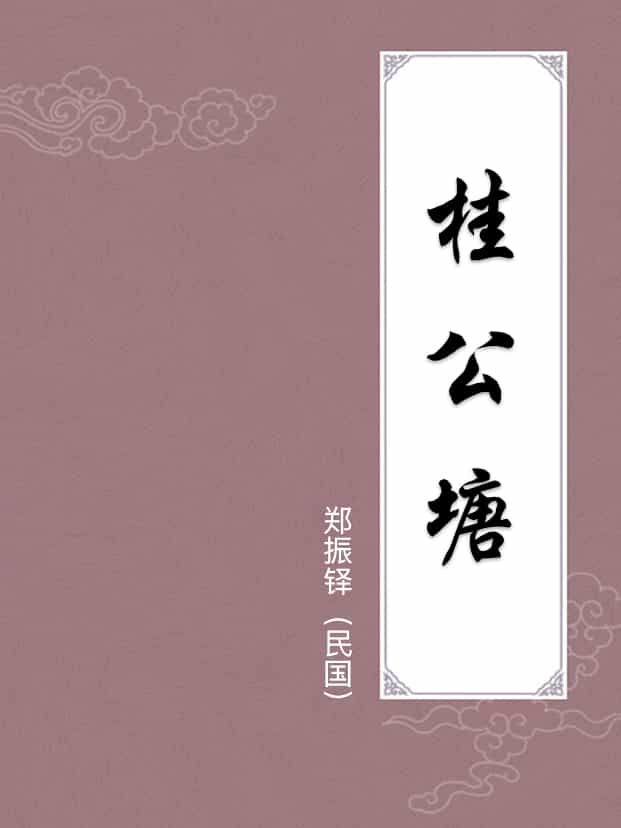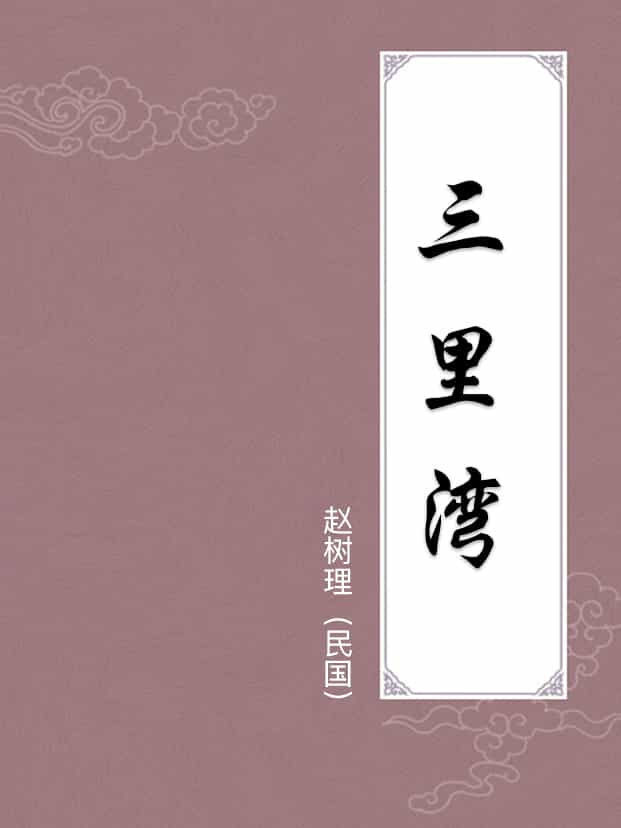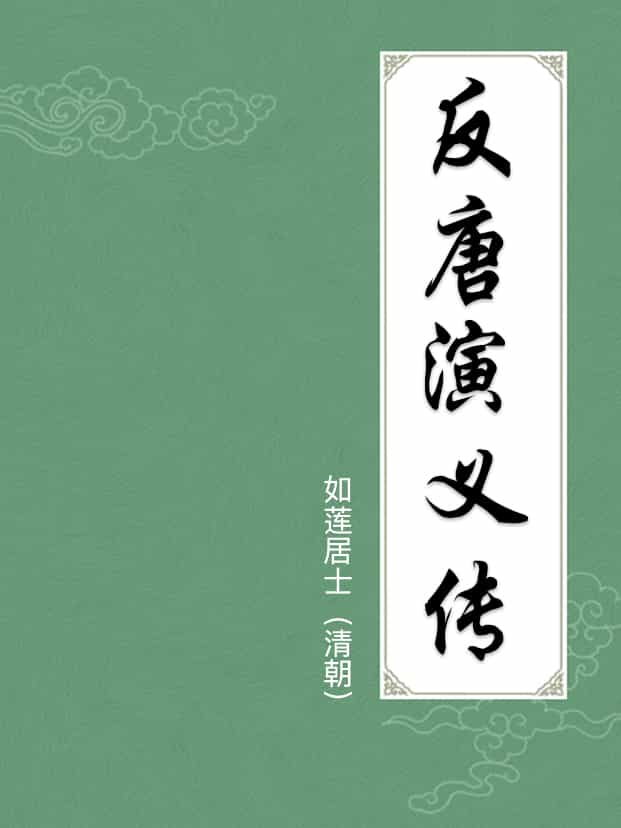闖出了鬼魅横行的长沙城。黃公俊和他的从者王阿虎,都感到痛快、高兴。打发了别一个轎夫回城之后(阿虎假装腿痛,說走不了;轎子另雇一个人抬进去的),他們站在城外的土山上。
茫茫的荒郊,乱冢不平的突起于地面。野草已显得有点焦黃色,远树如哨兵般的零落的站着。
远远的长沙城,长蛇似的被籠罩在将午的太阳光中。城中的高塔,孤寂的聳在天空。几縷白云,懶懶的馳过塔尖旁。
靜寂、荒凉、严肃。
公俊半晌不語,头微側着,若有所思。
“黃先生,到底向那里走呢?”
公俊从默思里醒过来。
茫茫的荒原,他們向那里去呢?长沙城是闖出来了,但要向南去么?迎着太平軍的来路而去么?还是等候在这里?
“但你和他們别了的时候,有沒有通知你接头的地方,阿虎哥?”
若从梦中醒来,阿虎失声說:“該死,該死,我簡直閙得昏了!”用拳敲打自己的头,“麻皮說过的,城里是他家,現在自然是被破获了,沒法想;城外,說是周家店,找周老三,那胖胖的老板。”
“得先去找他才有办法。”
周家店在南門外三里的一个鎮上,是向南去的过往必由之路,他們便向南門走。
几只燕子斜飞的掠过他們的头上,太阳光暖洋洋的晒着,已沒有盛夏的威力了。
过了一道河。河水被太阳射得金光閃爍,若千万金色的魚鱗在閃动。
远远的河面上,有帆影出現,但象剪貼在天边的蓝紙上似的,不动一步,洁白巧致得可爱。
陈麻皮恰在这店里。他見阿虎导了一位穿长衫的人来,吓得一跳。
“你該認得我,陈哥。”公俊笑着說。
“阿呀,我說是誰呢?是黃先生!快請进来,快請进来!您老怎样会和阿虎哥走在一道了?”
公俊笑了笑。“如今是走在一道了。”
麻皮,那好汉,有点惶惑。他是尊重公俊的,看他沒有一点讀書人的架子,能够了解粗人穷人的心情,也輕財好施。但他以为,讀書人总归是走在他們自己那条道上的,和自己是不同的,永不曾想到他是会在这一边的。而且,太平軍的来人,吳子揮,也再三的对他說道:“凡讀書人都是妖,他們都是在滿妖的一边的,得仔細的提防着。”他在城里时,打听得曾氏正在招練乡勇,預备和太平軍打,这更坚了“凡讀書人都是妖”的信念。
难道黃公俊是和阿虎偶然的同道走着的么?他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阿虎也太粗心,怎么把他引上門来?
但阿虎朗朗的說道:“麻皮哥,快活,快活!黃先生与我們是一道兒了!”
麻皮还有些糊塗。
“不用疑心。我明白你們都当我是外人,但我能够剖出心来給你們看,我是在太平軍的一边的!”
于是他便滔滔的說着自己的故事和意念,麻皮且听且点头。
他喜欢得跳了起来,忘了形,双手握着公俊的瘦小的手,搖撼着,叫道:“我的爷,这真是想不到的!唉!早不說个明白!要是您老早点和我們說个明白,城里的事也不会糟到这样。如今是城里的人个个都奔散了,一时集不攏,还有給妖賊斫了的。”
“讀書人也不見得便都卖身給妖,听說,太平軍見了讀書人便杀,有这事么?”
“沒有的話!不过太平王見得讀書人靠不住,吩咐多多提防着罢了。”
“掘墓烧祠堂的事呢?”
“那也是說謊。烧庙打佛象是有的,太平王是天的兒子呢。他信的是天父、天兄,我們也信的是。不該拜泥菩薩。您老沒看見太平王的檄文吧。”他便赶快的到了后房,取了一张告論出来。
“喏,喏,这便是太平王的詔告,上面都写的有,我也不大懂。”
公俊明白这是劝人来归的詔告,写得异常的沉痛,切实,感人。讀到:“慨自明季凌夷,滿虏肆逆,乘衅窃入中国,盜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奋义勇,驅逐出境,扫清羶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臣僕,”覚得句句都是他所要說的。“遂亦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坏我倫常;削发剃鬚,汚我尧、舜、禹、湯之貌,卖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这几句,更打动了他的心。
他的怀疑整个的冰释,那批紳士們所流布的恐怖和侮蔑是无根的,是卑鄙得可怜的。
还不該去做太平軍的一个馬前走卒,伸一伸久郁的悶气么?他們是正合于他理想的一个革命。
虽然天父、天兄,講道理、說敎义的那一套,显得火辣辣的和他的习慣相去太远。但他相信,那是小节道。他也幷不是什么頑固的孔敎徒,这牺牲是幷不大。民族革命的过度的刺激和兴奋使他丧失了所有的故我。
“呵,梦境的实現,江山的恢复,汉代衣冠的复見!”公俊头顱微仰着天,自語的說道。
“太平王的詔論,不說得很明白么,您老?”麻皮担心的問。
“感动极了!讀了这而不动心的,‘非人也!’”
“城里也散发了不少呢!不知别的乡紳老爷們有看見的沒有?”
“怎么沒有,我还听見他們在吟誦着呢。不过,說实話,我們該做点事。听說曾乡紳在招收乡勇,編練民团呢。說是抵抗太平軍。得想法子叫老百姓們别上当才好。”
“我也听得这风声了,”麻皮道。“有法子叫老百姓們不去沒有?”
“这只有两个法子,第一,是太平軍急速的开来,給他个不及准备;第二,是向老百姓們鼓动,拒絕加进去,要他們投太平軍。”
“但太平軍还远得很呢,”麻皮低声道,“大軍集合在南路的有好几十万,一时恐怕来不了。”
“那末,老百姓們怎么样呢?”
麻皮叹了口气,“只顧眼前,他們只要保得自家生命財产平安。說練团保乡,他們是踊跃的;說投太平軍,他們便說是造反要灭族,便不高兴干。”
公俊暗然的,无話可說。
“也不是沒有对他們說太平軍的好处,妖軍的作恶害人。他們只是懶得动弹。幷且,妖探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会被逮了去。曹狗子、刘七、伍二都是派出去說給老百姓們听的,話还不曾說得明白,就被逮了去斫了。”
公俊住在湖南好几代了,自己的气質也有点湖南化,他最明白湖南人。
湖南人是勇敢的,固执的。他們不动的时候,是如泰山般的稳固,春日西湖般的平靜,一旦被触怒了时,便要象海啸似的,波翻浪涌,一动而不可止。他們是守旧的,又是最維新的,是頑固的,又是最前进的;有了信仰的时候,就死抱住了信仰不放。
他們是最勇敢的先鋒,也是最好的信徒,最忠实的跟从者。但被欺騙了去时,象曾氏用甘言蜜語,保护桑梓,反抗掘墓烧庙的一套話,去欺騙他們的时候,他們却也会眞心的相信那一套話,而甘願为其利用。
而那批乡紳們,为了传統的势力,在乡村里是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誘惑力的。难保忠厚、固执、短見、勇敢的农民們不被他們拉了去,利用了去。
可忧虑之点便在此。
公俊看出了前途的暗淡。
难道眞的再要演一套吳三桂式的自己兄弟們打自己兄弟們的把戏,而給敌人們以坐收漁翁之利的机会么?
把农民們爭取过来。但这是可能的么?
他們的力量是这么薄弱。
“还是設法到太平軍里去报告这事罢。”
公俊点点头,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