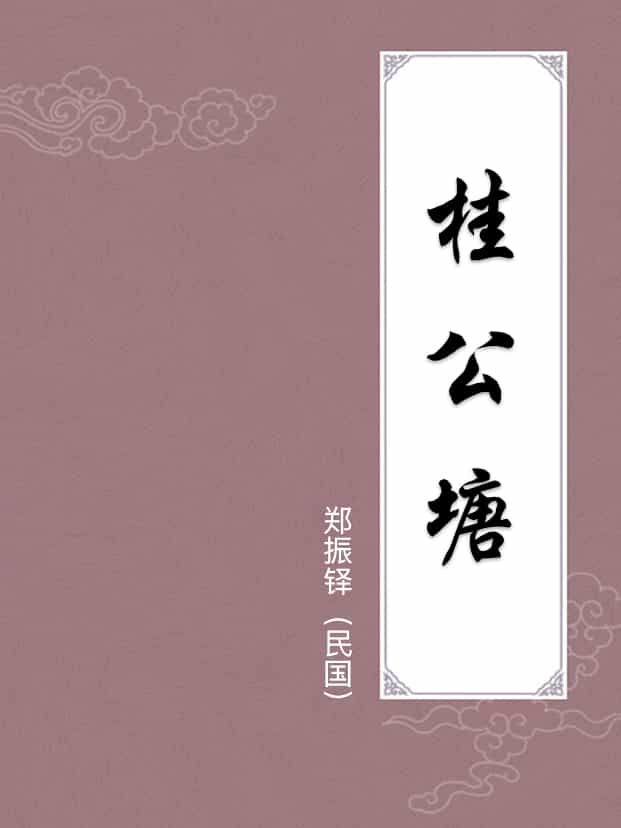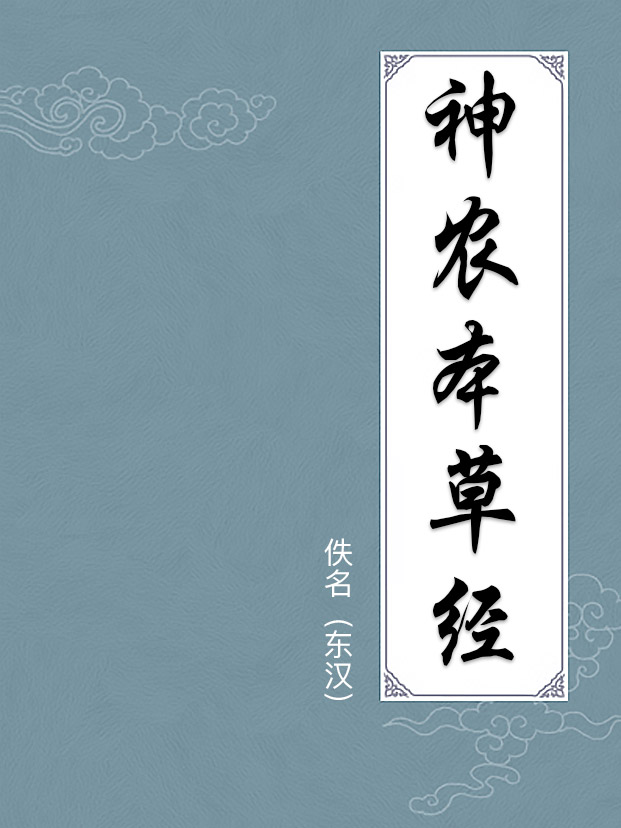太平軍給黃公俊以很好的印象,同时也給他以很大的刺激。象久处在暗室的人,突然的見到了盛夏正午的太阳光,有些头眩脑暈,反而一时看不見一物。
滿目的金光,滿目的錦綉,滿目的和妖軍完全不同的装束,这是嶄新的气象与人物!
天王的朝会的演講与祷告,給公俊以极大的感动。他不是一个任何宗敎的信徒,他具有中国讀書人所特有的鄙夷宗敎的气味兒。和尚們、道士們都只是吃飯的名目,以宗敎的名色来混飯、来做买卖的。但他第一次見到有眞正的宗敎热忱的集会了,被感动得张口結舌,說不出話来。
他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这僻远的金田村的一位敎主,能够招致了那末多的信徒,成就了不很小的事业的原因。这决不是偶然的僥幸。
他全心全意的,以滿腔的热誠,参加于这个民族复兴的运动。以他的忠恳与坚定的認識,以他的耐劳与热烈的情感,不久便博得天王、翼王們的信任。
但湖南南部的战爭总是持久下去,长沙城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太平軍不久便放弃了占領湖南的計划,越过了长沙城而一举攻下了武昌。
这震撼了整个国!民众們如水的赴壑似的来归降,声势一天盛似一天。
太平軍浩浩蕩蕩的由水陆而东下,占領了安庆、江苏、浙江、福建。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而同时,曾国藩、罗澤南輩編練乡勇的計划却也成了功。
如黃公俊之所虑的,忠厚、勇敢的湖南人果然被許多好听而有誘惑性的名辞,鼓动了他們的热情 。
曾国藩輩初以保乡守土为名,而得到了拥护与成功,便更熾盛了他們的功名心,要想出乡“討賊”。乡勇們不意的得到了过度的荣誉与鼓励,便也覚得抵抗太平軍乃是他們的建立功名的机会,乃是他們的唯一的事业。
一批一批的无辜的清白的农民們便这样的被送出三湘而成就他們自己打自己的兄弟們的功业。
太平軍遇到了这么强悍而新兴的生力軍是絕对沒有料到的事。滿洲兵和一般妖軍都是那么样脆薄,一击便粉碎。这时却碰到最强固的“敌人”了——而这“敌人”其实却是兄弟。
武昌被夺去,安庆被夺去了之后,天王召开了一次会議,专門討論湘軍的問題。黃公俊为了是湘人,熟悉湘事,也被召参加。
这时候,太平軍吸引了过多的复杂的分子,初出发时的人物,不是陣亡,便成了名王大将,安富尊荣;而新加入的,沒有主义,沒有認識,只是为了功名富貴,强盜、土棍,乃至妖軍里的腐敗分子和貪汚的官吏們也都成了太平軍中的主要的一部分人物,銳气和声誉在大减。
黃公俊看出了这腐化的傾向,很痛心,然而这是不可抗的趋势。宗敎的热忱也漸减,每天的朝会,只是敷衍的情态,他沒有法子进言。
外面的局势是一天天的坏,生龙活虎般的湘軍是逐步的卷逼了来。
怎样对付湘軍的問題,成了太平天国的焦虑的中心。
无結果,无办法的討論,尽管延长下去。
“和湘軍之間,有沒有妥协的可能呢?”翼王道。
“怕不会有的罢?这战爭成了湘軍們的光荣与夸傲之資。要不狠狠的給他們以打击,是不会有結果的。”北王道。
“但生力軍是从三湘的农民們之間不断的輸送出来的呢。帮妖軍来和我軍作战,成了他們的唯一的事业,近来幷且还成了妖軍的主力了呢。曾氏是那样的把握着湘軍的全权,有举足輕重之势。”天王蹙額的說道。
“曾氏成了湘人信仰的中心,有办法使他放弃了帮妖的策划而和我軍联盟么?——至少是不立在对抗的地位。”翼王道。
北王的眼光扫射过会堂一周。
“咱們这里湘人也不少呢,有法子找到連絡的綫索沒有?”他說。
翼王把眼光停在黃公俊的身上。
“至少这自己兄弟們之間的残杀,必得立刻停止。”
停了一会,他又道:“必得立刻停止,无論用什么条件。”
大众都点头。
“誰去向曾氏致和議的条件呢?”北王道。
翼王的眼光,又停在黃公俊的身上。
公俊也明白,除了他,也沒有第二人可去。但这使命实在太艰巨了,他知道决不会有什么結果。湘人是那样的固执而頑强,絕对不能突然轉变过来的。
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他却不怕冒任何的艰苦和牺牲,明知是死路一条,却总比停着不走好。
“我,为了天王和天国的前途,願意冒这趟险。我最痛心的是自己兄弟們帮助了敌人在和自己的兄弟們战斗、相斫!曾氏乃是旧邻里,他的脾气,我知道的,不易說动。姑且以性命作为孤注去試試。万一能够用热情来感化他呢?……不过条件是怎样?”
这又是一个困难的焦点。
經了許久的討論,結果是,只要停止了自己兄弟們之間的战爭,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認,甚至曾軍可以独立,占据几省,不受天国的管束,不信天敎。但必須不打自己人,不帮助妖軍。天国的一方面,还可以尽力的接济他。只要同盟幷諒解便足够了。先打倒了滿妖,其余的賬,尽有日子清算。
公俊便带了这寬大的条件而去。
那一天,灰色的重霧弥漫了天空,惨白、厌悶、无聊、不快,太阳光被遮罩得半綫不見。
渡过了长江,方才有一絲的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