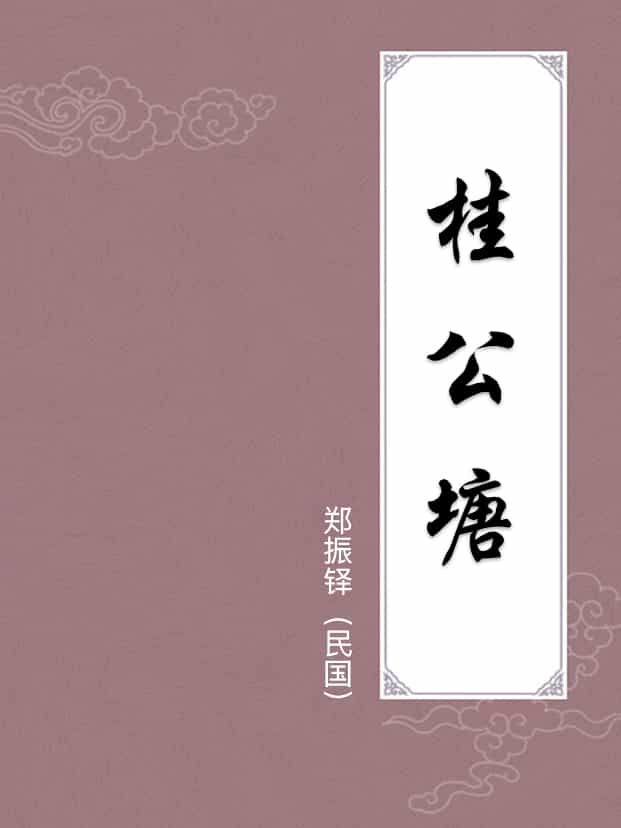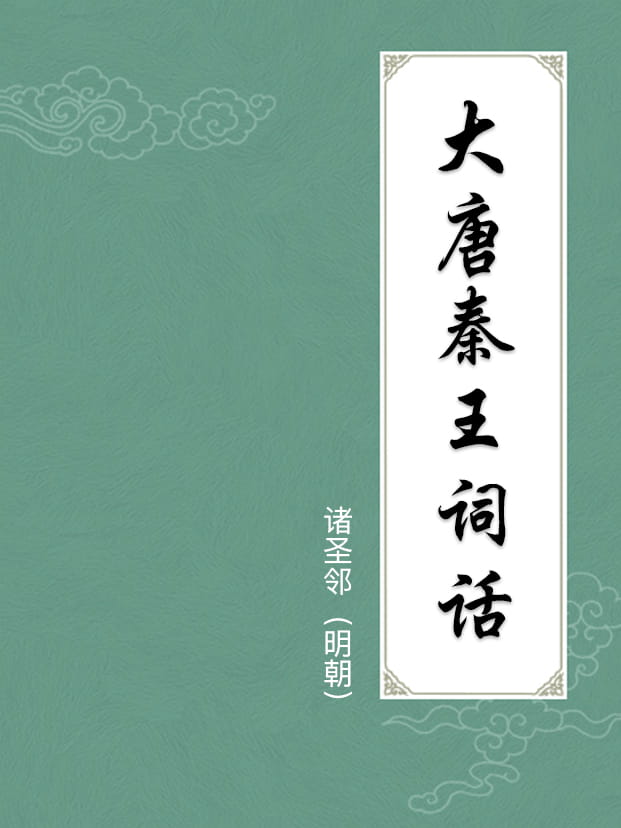太平軍的軍势,江河日下的衰頹下来。北王被杀,翼王則西走入川,只有东南的半壁江山,勉强的掙扎着。南京的围,急切不能解。江苏、浙江各地的战爭也都居于不是有利的地位。上海那个小城,为欧洲人貿易之中心的,竟屡攻不下。
黃公俊感到异常灰心、失望。难道轟轟烈烈的民族复兴运动便这样的消沉、破灭、分崩下去么?
为什么天王起来得那么快,而正在发展的頂点,却反而又很快的表現衰征呢?
这很明白:太平軍的兴起,不单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且也是一种經济斗爭的运动。他們的最早的借以号召的檄文,便是这样的高叫道:
“天下貪官,甚于强盜;衙門酷吏,无异虎狼。即以錢粮一事而論,近加数倍。”
在农民們忍受着高压力而无可逃避的时候,这样的口号是最足以驅他們走上革命之路的。历来的革命或起义,多半是从吃大户,求免税开始的。太平軍以这样的声势崛起于金田之后,沿途收集着无量数的逃租避税的良民和妒視大姓富户的各地方的泼皮們。軍势自然是一天天浩大。但当战爭日久,領兵者都成了腸肥脑滿的富翁的时候,又为了軍需,而不得不横征暴斂的时候,当許多新的大姓富户出現于各地,择人以噬的时候,农民們却不得不移其爱戴之心而表示出厌恶与反抗了。
公俊彻底了解这种情形,但他有什么方法去挽回这頹运呢?他的最早的同伴們,王阿虎早已陣亡了,陈麻皮、胡阿二輩都成了高級軍官,养尊处优,儼然是新兴的富豪,而凶暴則有过于从前的乡紳和貪官酷吏。
公俊有什么办法去拯救他們呢?“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即使說服了一二人乃至数十百人,有救于大局么?
他失意的只在叹气。几次的想决然舍去,作着“披发入山,不問世事”的消极的自私的梦。
但不忍便把这半途而废,前功全弃的革命运动抛在脑后。他覚得自己不該那么自私。虽看出了命运的巨爪已經向他們伸出最后的把捉的姿势,却还不能不作最后的掙扎。
最有希望而握着实权的忠王李秀成,是比較可靠的。他还不曾染上太平軍将士們的一般恶习。他也和公俊一样,已看出了这頹运的将监,这全局的不可幸免的崩潰,但为了良心和責任的驅使,却也不得不勉力和运命在作战。
公俊在朝中設法被遣調出去,加入忠王的幕中。忠王很信任他。
而不久,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这决定太平軍的最后的命运。
由了李鴻章的策动,清廷想利用英国的軍官編練新式的洋枪队来平乱。
这消息給太平軍以极大的冲动。
“該和妖軍爭这强有力的外援才对。”一个两个的幕客,都这样的向忠王献計。
“且許他們以什么优越的条件吧。他們之意在通商,我們如果答应了开辟若干渡口为商埠以及其他条件,他們必将舍妖而就我的。何况北方正在构衅呢!他們决不会甘心給妖利用的。”
忠王躊躇得很久,他和公俊在詳細的策划着。
“一时固然可以成立一部有力的劲旅,且还可以充分的得到英、法新式枪弹的接济,但流弊是极多的,不可不防。”公俊說道。
“我也防到这一点。洋将是驕横之极的,他們无恶不作;且还每每对我軍的行动横加干涉,使人不能忍受。法将白齐文的反复与驕縱,我軍已是深受其害的了,”忠王道。
“所以,这生力軍如果不善用之,恐怕还要貽祸于无穷。”
“如果利用了他們,即使成了功,还不是前門驅虎,后門进狼么?而通商和种种优越的条件——不知他們将开列出多少的苛刻的条件来呢?——的承認,也明白的等于卖国。我們正攻击滿妖的出卖民族利益,我們还該去仿效他么?”
“只要站在公平的貿易和正式的雇兵的編制条件上,这事未始是不可考虑的。”
“但这是可能的么?昨日有密探来报告:滿妖已經允許了洋敎官以許多优待的条件;他們可以独立成为一軍,不受任何上級主帅的指揮,他們是只听洋敎官的命令与指揮的。”
“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不是破坏了軍令的統一么?而况还有通商等等的政治的条件附带着!”
“恐怕这其間必有其他作用。密探报告說:洋敎官的接受清妖的聘任,是曾經得到其本国政府的允許的。”
“必有什么阴謀在里面!”公俊叫道。
忠王道:“所以,我們不能出卖民族的利益,以博得一时的胜利。这事且擱下吧。好在他們的力量也还不大,不过几营人。即使战斗力不坏,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这里議論未定的时候,那边已在开始編練常胜軍了。这常胜軍不久便显出很高的效力来。在英人戈登将軍的指揮之下,他們解了上海之围。随即攻破了苏州,使太平軍受到了极大的損失。
想不到,这常胜軍会給他們以那么大的威胁。旧式的刀枪遇到了从欧洲輸入的火器,只好丧气的被压伏。
几次的大敗,太平軍在江南的声威扫地以尽。軍心更为动搖。南京的围困更无法可解。
天王的噩耗突然的传来,传說是服毒而死。
快逼近了黃昏的頹景,到处是灰暗、凄凉。
无可挽回的頹运。
公俊仿佛看見了运命的巨爪在向他伸出;那可怕的鉄的巨爪,近了,更近了;就要向下攫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