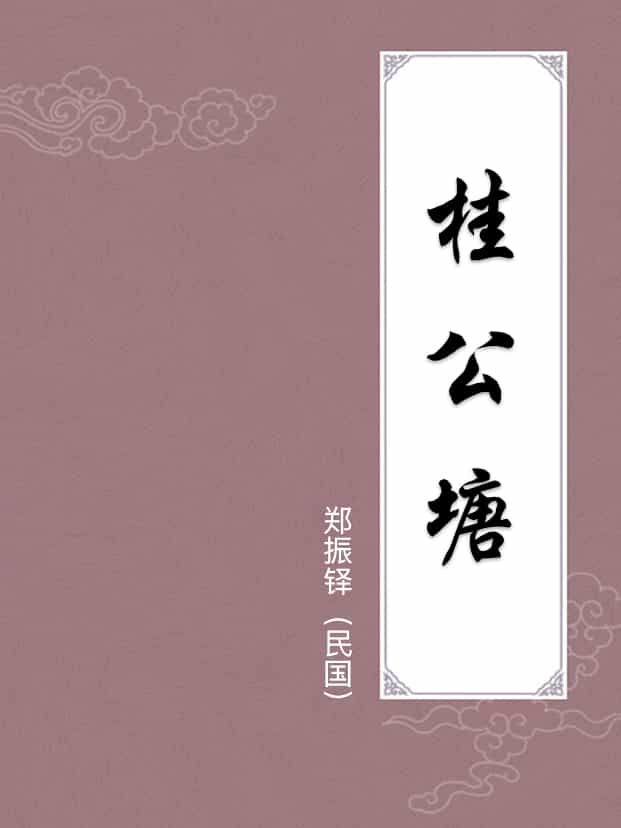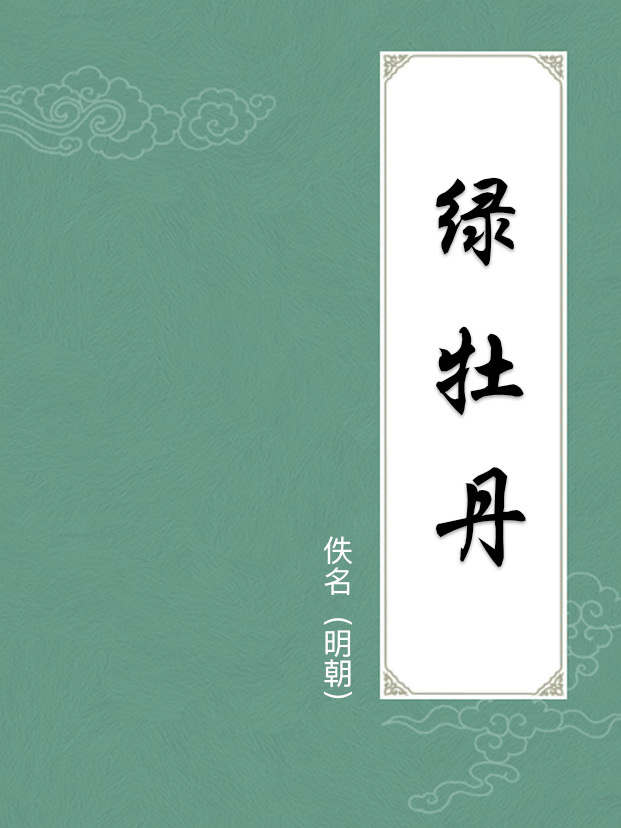侯朝宗冒他父亲之名的信发出了,但同时,黃得功的那支兵馬也被調到江防。淮防完全空虛了。史可法异常着急,再沒有得力的軍队可以填补,深怕清兵得了这个消息,乘虛扑了来。
而这时,西兵已經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顧之忧,已是不成問題。
馬、阮們心上落下了一大块石头。南都里几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綫希望的人,又都灰了心。
秦淮河边的人們,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娱乐着。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态复萌,横征暴斂,报复冤仇,享受着这小朝廷的大臣們的最高权威。过一天,算一天。一点不担心什么。
但,象黃河决了口似的,沒等到黃得功的回防,清廷的鉄騎,已經澎湃奔騰,疾馳南下。史可法和黃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揚州附近布了防。
經不起略重的一击,黃得功第一战便死于陣上,揚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杀。
这噩耗传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陣极大的騒乱。城內,每天家家户户都在紛紛攘攘,搬东移西,象一桶的泥鰍似的在絞乱着。已經有不逞的无賴子們在动乱,声言要抄劫奸臣恶官們的家产,烧毁他們的房屋。
阮府、馬府的門上,不时,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照墙上貼沒头揭帖,說是定于某日来烧房,或是說,某日要来搶掠。
終日有兵队在那里防守,但兵士們的本身便是动乱分子里的一部分。紀律和秩序,漸漸的維持不住。
一夕数惊,說是清兵已經水陆幷进,沿江而来。官府貼了安民的大布告,禁止迁居。但搬走的,逃到乡下去的,仍旧一天天的多起来,連城門口都被堵塞。
什么样的謠言都有,几乎一天之內,总有十几种不同的說法,可惊的又可喜的,时而恐慌,时而暫为寬怀。有的說,某处勤王兵已經到了。有的說,許定国原是詐降的,現在已經反正,幷杀得清兵鼠窜北逃了。有的說,因了神兵助陣,某某义軍大破北兵于某处。……但立刻,这一切喜訊便都被証明为伪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来,无人可抵挡。竟不設防,也竟无可調去設防的兵馬。他們如入无人之地。劝降的檄文,雪片似的飞来,人心更为之搖动。
“看这情形,在北軍沒到之前,城內会有一場大劫呢。泼皮們是那样的騒动。”大鋮担心的說。
士英苦着脸,悄悄的道,“刚从宫里出来,皇上有迁都之意,可还說不定向那里迁。”
“可不是,向那里迁呢?”
“总以逃出这座危城为第一着,他們都在料理行装。”
大鋮还不想搬动。北兵入了城,他总以为自己是沒有什么危险的。
“我們怎么办呢?随駕?留守?”士英向大鋮眨眨眼。他是想借口随駕而溜回家乡去的。
“留守为上。我們还有不少兵,听說,江南的义軍,风起云涌似的出来了,也尽够坚守一时。”大鋮好象不明白他的意思似的說道。
士英走向他身旁,悄悄的道:“你,不知道么?我的兵是根本靠不住的。这两天,他們已經混入泼皮队里去了。逃难人的箱籠被劫的已經不少。还有公然白昼入民房打劫的。誰都不敢过問。我不能維持这都城的治安。……但北兵还不来……就在这几天,我們得小心……刚才当差的来說,有人在貼揭帖,說要聚众烧我們的宅子。南京住不下去了,还以早走为是。”
“难道几天工夫都沒法維特么?”
“沒有办法。可虑的是,泼皮們竟勾結了队伍要大干。”
大鋮也有点惊慌起来,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留居的計划根本上动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