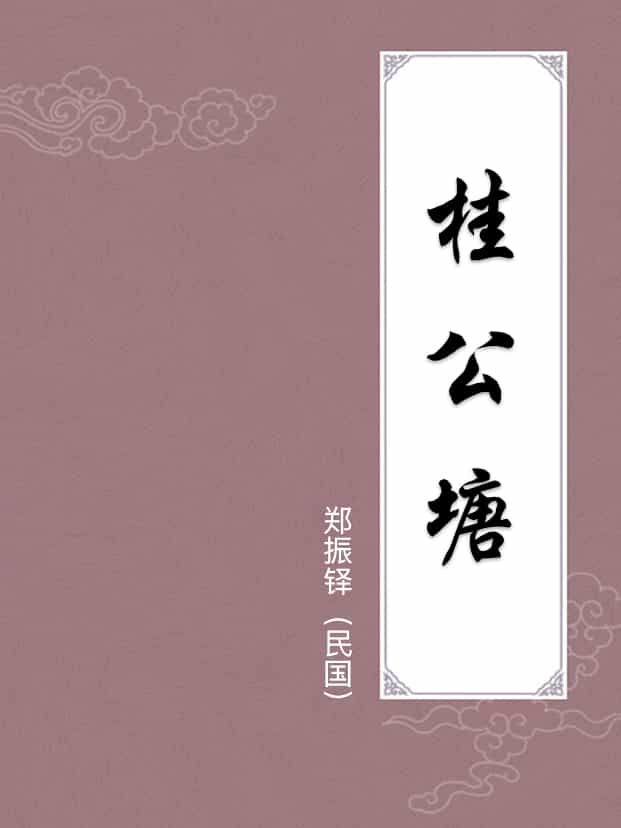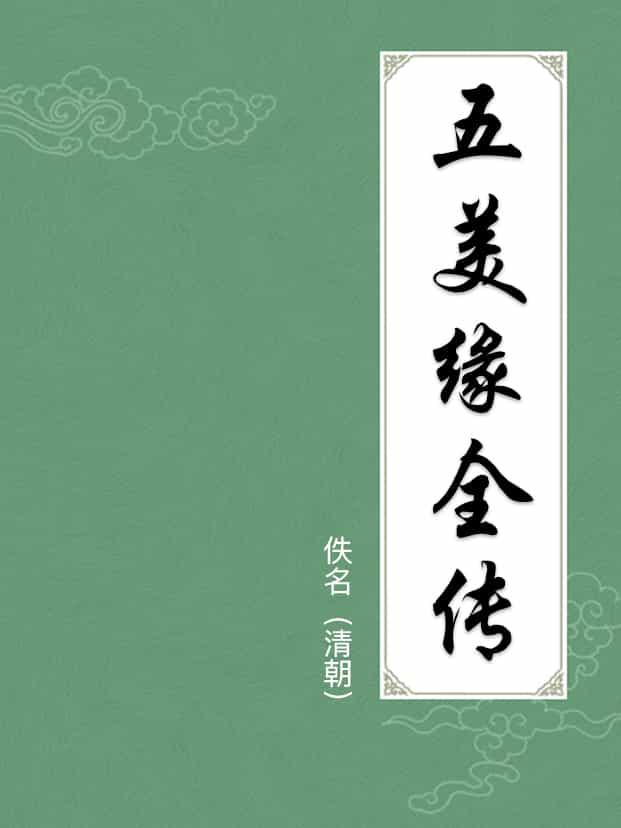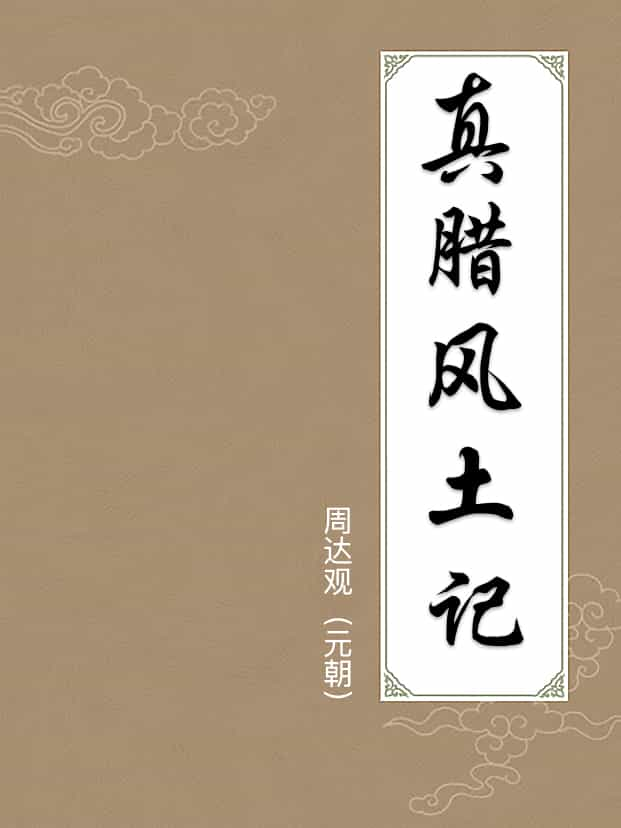大鋮回了家,抱琴哭丧着脸,給他一张揭帖。
“遍街貼着呢,我們的照壁上也有一张。說不定那一天会出事。您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坊卒管什么事的!讓这些泼皮們这样胡閙!”大鋮装着威风,厉声道。
“沒用,劝阻不了他們。五爷去阻止了他們一会,吃了一下老大的拳头,吓得連忙逃回家。”
“不会撕下的么,沒用的东西!”
“撕不凈,遍街都是。早上刚从照壁撕下一张。鬼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一张貼上去了。”
大鋮心头有点冷;胸膛里有点发空。他只在書斋里低头的走,很艰难的挪动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門上的老当差,阮伍,所謂五爷的,气呼呼的走进来叫道,“皇上的鑾駕已經出城門去了!”
“什么!”大鋮吃惊的抬头。“他們走了?”
“是的,馬府那边也搬得一空了。小的刚才碰見他們那边的馬升,他押着好几十車行李說,馬爷騎着馬,在前面走呢。”
他走前几步,低声的說:“禀老爷,得早早打主意。城里已經沒了主。刚才在大街上碰見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泼皮,有我們的仇人王福在里面,仿佛是会齐商量什么似的,我只听見‘褲襠子阮’的一句。王福見了我,向他們眨眨眼,便都不声不响了。有点不妙,老爷。难道眞应了揭帖上的話?”
大鋮不說什么,只揮一揮手。阮伍退了出来。刚走到門口。
“站住,有話告訴你。”
阮伍連忙垂手站住了。
“叫他們后边准备車輛。多預备些車輛。”
阮伍諾諾連声的走去。
大鋮是一心的忙乱,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旁,“你看这書斋里有什么該收拾收拾的?”
“書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时归着不好。”
“快些动手,叫携書他們来帮你。”
“嗻!但是沒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書斋里实在太乱了,可带走的东西太多,不知怎样的拣选才好。
一大批他所爱的曲本,只好先抛弃下,那不是什么难得的。但宋版書和精鈔的本子是都要随身带走的。还有他自己的写作,未刻成的,那几箱子的宋元的字画,那些宋窑,汉玉,周鼎,古鏡,沒有一样是舍弃得下的。他費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沒有一盆肯放下。但怎么能带着走呢?箱子备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装滿書了。
“有的东西,不会用毡子布匹来包装么?蠢才!”
但实在一时收拾不了;什么都是丢不下的,但能够随身携带的实在太少了。收了这件,舍不下那件,选得这物,舍弃不掉那物。忙乱了半天,还是一团糟。从前搜括的时候,只嫌其少,現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么时候到呢?”他忘形的問道。
“听說,沿途搜杀黃軍,还得三五天才能进城,但安民告示已經有了。”抱琴道:“那上面还牵連爷,您老人家的事呢。”他无心的說。
“什么!”大鋮的身子冷了半截。“怎么說的?”圓睜了双眼,狼狽得象被綁出去处刑似的。
“說是什么罪,小的不大清楚。只听人說北兵是来打倒奸賊,解民倒悬的。倒有人想着要迎接他們哩!”
大鋮軟瘫在一张太师椅上垂头不語。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爭的牺牲品了。众矢之的,万恶所归。沒法辯解,不能剖释。最后的一条路,也被塞絕。
逃,匿姓隐名的逃到深山穷谷,只有这条路可走了。还須快。一迟疑,便要脱不得身。
掙扎起身子,精神奋发得多,匆匆向內宅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