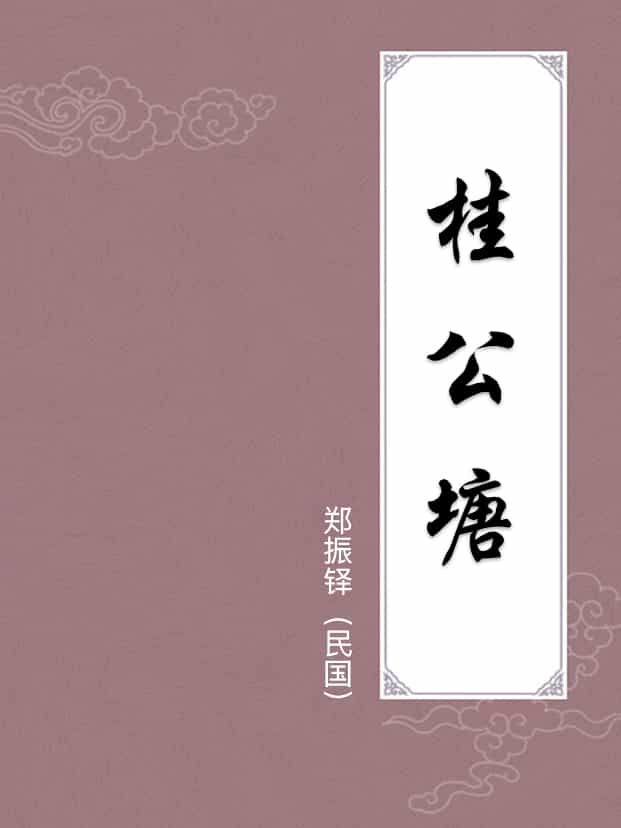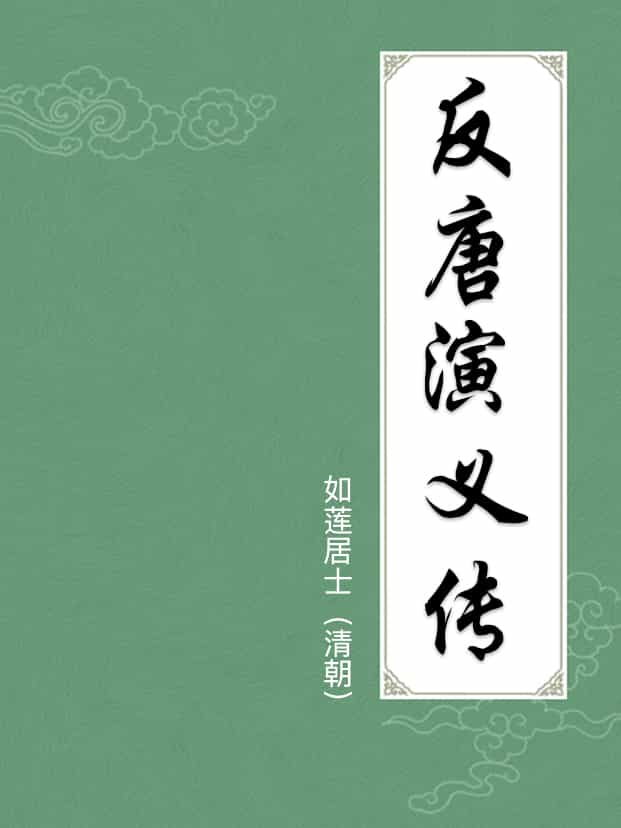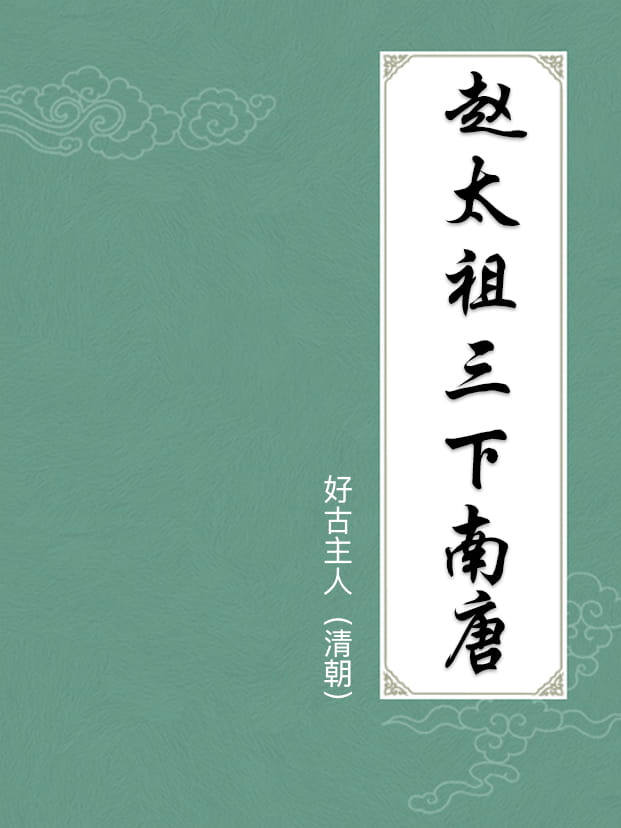“究竟这事怎么办法呢?杀了防河的大将,罪名不小。如果不重重惩治,怎么好整飭軍紀?”馬士英打着官腔道。
馬府的大客厅里,地上鋪着美丽夺目的厚毡,向南的窗户都打开了,讓太阳光晒进来。几个幕客和阮大鋮坐在那里,身子都半浸在朝阳的金光里。
“这事必得严办,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将軍的沉冤。”一个幕客道。
“实在,将官們在外面閙得太不成体統了;中央的軍令竟有些行不动。必得趁这回大加整飭一番。”
“我也是这个意思,”士英道,“不过操之过急,許定国也許便要叛变。听說他已經和北廷有些联絡了。”
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来。
沉默了好久。图案似的窗外树影,很清晰的射在厚地毡上,地毡上原有的花紋都被攪乱。
“如果出兵去討伐他呢,有誰可以派遣?有了妥人,也就可使他兼負防河的大責。”士英道。
“这責任太大了,非老先生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現負着拱卫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輕身北上呢?必得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宿将去才好。”一个幕客道。
“史閣部怎样呢?”士英道。
“他現駐在揚州,总督两淮諸将,論理是可以請他北上的。但去年六月間,高杰和黃得功、刘良佐諸将爭夺揚州,演出怪剧,他身为主帅,竟一筹莫展,現在又怎能当此大任呢?况且,黃、刘輩也未必肯舍弃安乐的揚州,向貧苦的北地,”大鋮侃侃而談起来。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請他移师东向?”一位新来的不知南都政局的幕客說。
大鋮和士英交換了一个疑惧的眼色。原来左良玉这个名字,在他們心上是个很大的威胁。紛紛藉藉的传言,說是王之明就是故太子,現被馬、阮所囚,左良玉有举兵向江南肃清君側之說。这半个月来,他們两人正在苦思焦虑,要設法消弭这西部的大患,如今这話正触动他們的心病。
但立刻,大鋮便几乎带着呵責口气,大声說道,“这更不可能!左良玉狼子野心,举止不可測度。他拥众至五十万,流賊归降的居其多敎,中央軍令,他往往置之不理。外边的謠言,不正在說他要就食江南么?这一个調遣令,却正給他一个移师东向的口实!”
“着呀!”士英点头道,“左良玉是万不可遣动的。何况闖逆犹熾,张献忠虽蟄伏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这一支重兵,是决然不能从武汉移調开去的。”
沉默的空气又弥漫了全厅。
这問題是意外的严重。
“圓海,你必定有十全之策,何妨說出来呢?”士英隔了一会,向大鋮提示說。
大鋮低了头,在看地毡上树影的摆动,外面正吹过一陣不小的春风。
理了理頷下的大浓鬍,他徐徐說道:“論理呢?这事必得秉公严办一下,方可使悍将驕兵知有朝廷法度。但时势如此,虽有圣人,也决不能一下挽回这积重难返的結习。而况急則生变,徒然使北廷有所借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許定国,不放他北走。必須用种种方法羈縻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赶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撫慰他,一面赶快下詔安撫他的軍心,迟了必然生变!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也顧不得什么威信,什么綱紀了。”
“但他仇杀高杰的事怎么辯解呢?”士英道。
“那也不难。高杰驕悍不法,为众所知。他久已孤立无援,决不会有人为他报复的。我們只消小施詭計,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說高杰克扣軍餉,士卒嘩变,他不幸为部下所杀,还亏得許定国撫輯其众,未生大变。就不妨借此奖賞他一番,一面虛张声势,說要出重賞以求刺杀高某的賊人,借此掩飾外人耳目。这样,定国必定感激恩帅,为我所用了。”
“此計大妙!此計大妙!”士英微笑点头称贊道,仿佛一天的愁云便从此消散凈尽一般。“究竟圓海是成竹在胸,眞不愧智囊之目!”說着一只肥胖紅潤的大手,連連撫拍大鋮的肩膀。
大鋮覚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当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还是托恩帅的鴻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