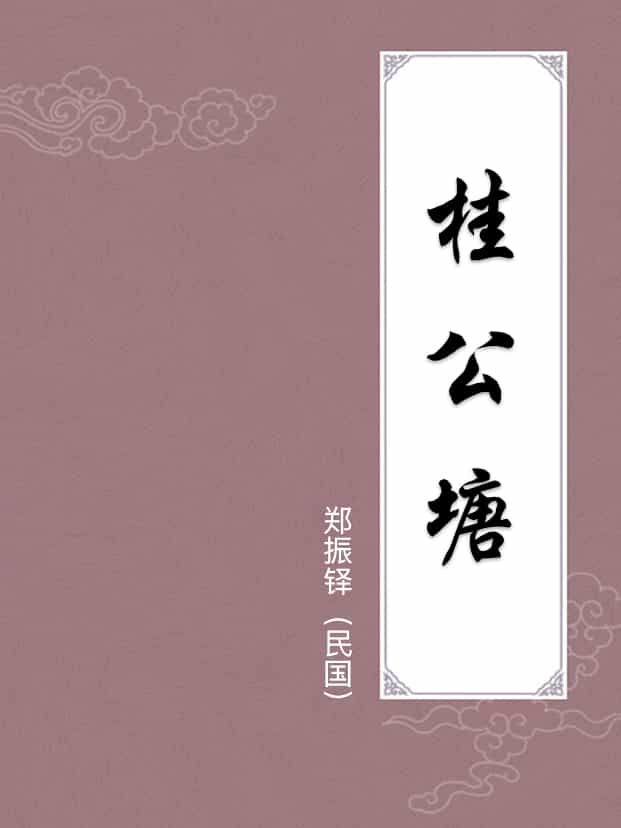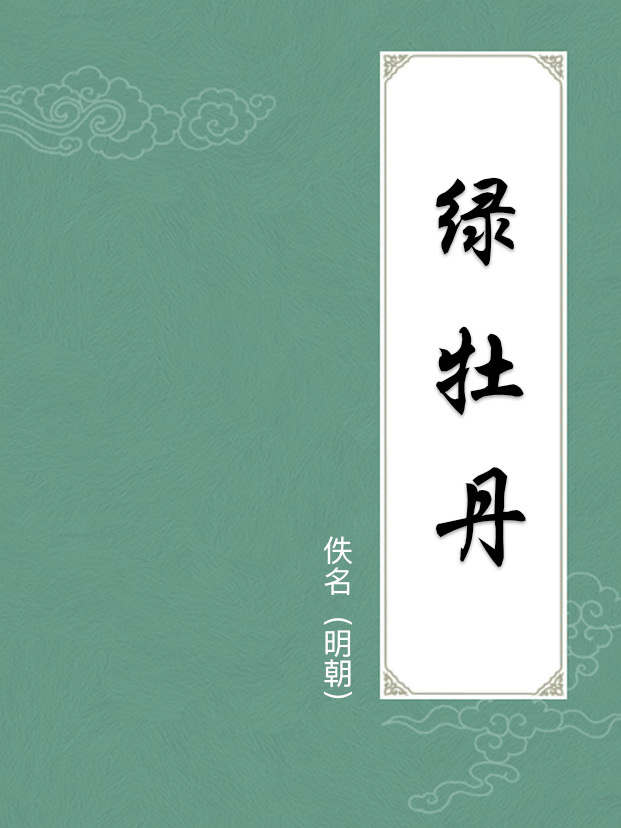“您家大人在家么?”一陣急促的烏靴声在天井旁游廊里踏响着。
“在書斋里呢,楊大人!”書童抱琴說道。
大鋮从自足的得意的迷惘里醒了轉来。
“哈,哈,哈,我正說着龙友今天怎么还不来,你便应声而来;巧极,巧极,請进,請进。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随时准备好了的笑声,宏亮的脱口而出。
但一看楊文驄的气急敗坏的神色,却把他的高兴当头打回去,象一陣雹雨把滿树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时局有点不妙!您听見什么风声么,圓老?”文驄张皇失措的說道。
大鋮的心脏象从腔膛里跳出,跑进了冰水里一样,一陣的凉麻。
“出了什么事,龙友?出了什么事?我一点还不知道呢。”他有点气促的說。
文驄坐了下来,鎮定了他自己。太阳光带进了的桃花的紅影,正射在他金絲綉圓鶴的白緞袍上。
“时局是糟透了!”他叹息道,“我輩眞不知死所!难道再要演一次被发左衽的惨剧么?我是打定了主意的。圓老,您有什么救国的方略?——”
大鋮着急道:“到底是什么事呢,龙友?时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說“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稳做下去的吧”的話,为了新参預了朝廷大計,不象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閑評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体态来,这句放肆的无忌憚的話,已到了口边,便又縮了回去。
“恐怕这小朝廷有些不稳呢,”龙友哑声的說道。
“难道兵部方面得到什么特别危急的情报么?”
龙友点点头。
大鋮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击了一記。
“大事不可为矣!我們也該拿出点主张来。”
“到底是什么事呢?快說出来吧。等会兒再商量。”大鋮有点不能忍耐。
“十万火急的軍报說,——我刚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經差人飞报馬公了——中原方面要有个大变,大变!唉,唉,”龙友有点激昂起来,清癯的脸庞,显得更瘦削了,“将軍們实在太不可靠了,他們平日高官厚祿,养尊处优,一旦有了事,就一个也不可靠,都只顧自家利益,辜負朝廷,耽誤国事。唉,唉,武将如此,我輩文臣眞是不知死所了!”
“难道高杰又出了什么花样么?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难道竟献河給北廷了么?”大鋮有点惊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还鎮定。
“不,高杰死了!一世梟雄,落得这般的下場!”
“是怎样死的呢?”大鋮定了心,反覚得有点舒暢,象拔去一堆碍道的荆棘。高杰是党于史可法的,南都的主事者們对于他都有三分的忌憚。
“是被許定国杀的,”龙友道。“高杰一到了开、洛,自負是宿将,就目中无人起来,要想把許定国的軍队夺过去,給他自己带,定国却暗地里和北兵勾結好,表面上对高杰恭順无比,却把他騙到一个宴会里,下手将他和几个重要将官都杀了。高杰的部下,散去的一半,归降許定国的一半。如今听說定国已拜表北廷,請兵渡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圓老,您想这局面怎么补救呢?这时候还有誰能够阻挡?先帝信任的宿将,只存左良玉和黃得功了。得功部下貪恋揚州的繁华,怎肯北上御敌?良玉是拥众数十万,当武、汉四战之区,独力防闖,又怎能东向开、洛出发?”
大鋮慢条斯理的撫弄着他頷下的大把浓鬍,沉吟未語,心里已大为安定,沒有刚才那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势还不至全然无望。許定国和北廷那边,都可以設法疏解。我們正遣左懋第到北廷去修好,还可以用緩兵之計。先安內患,将来再和强邻算賬,也不为迟。至于对許定国,只可加以撫慰,万不可操切从事。該极力怀柔他,不使他为北廷所用。这我有个成算在……”
書童抱琴闖了进来,說道:“爷,馬府的許大爷要見,現在門外等。”
龙友就站了起来,說:“小弟告辞,先走一步。”
大鋮送了他出去。一陣风来,吹落无数桃花瓣,点綴得遍地艳紅。衬着碧綠的蒼苔砌草,越显得凄楚可怜。詩人的龙友,向来是最关怀花开花落的,今天却熟視无睹的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