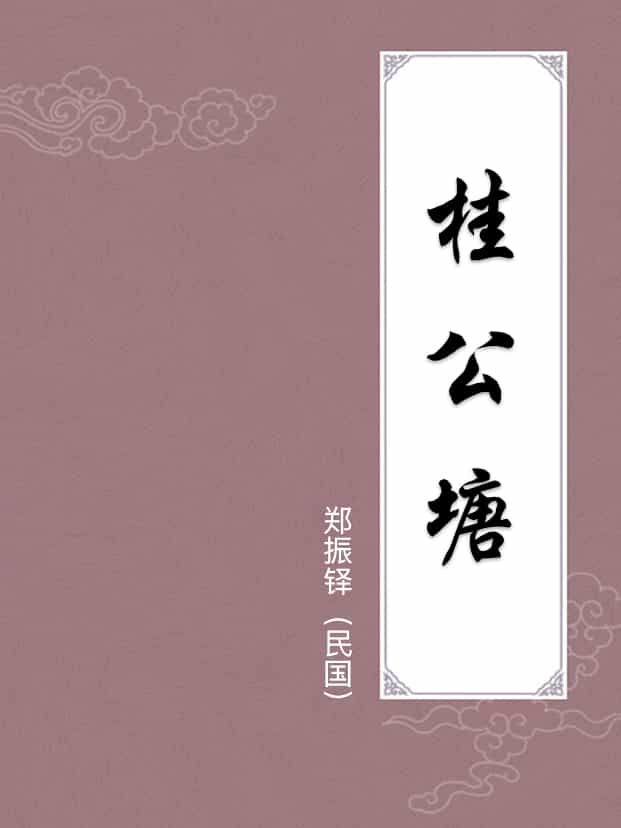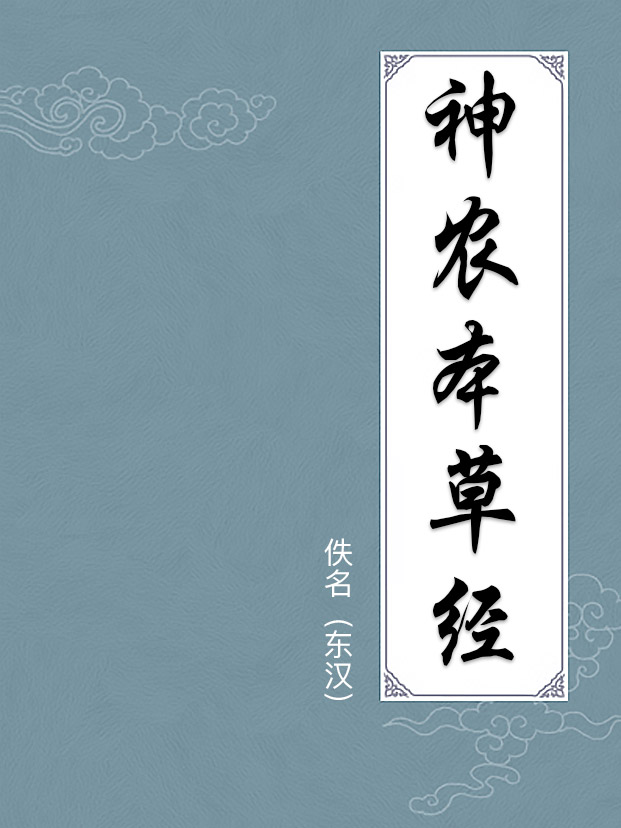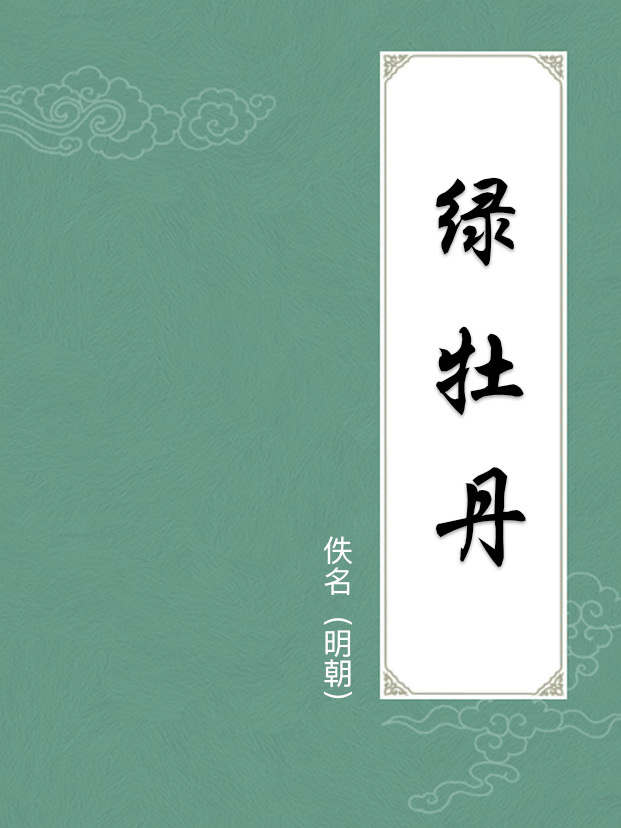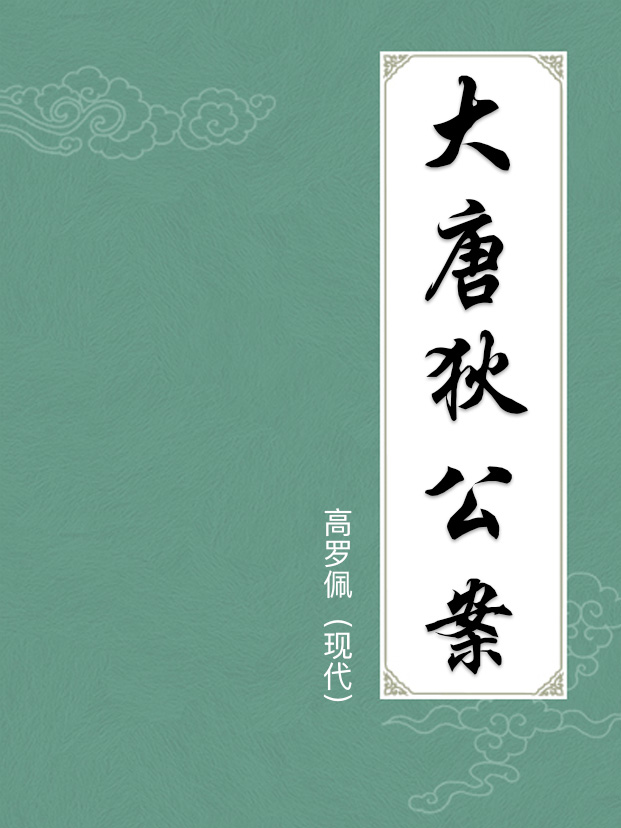那一夜把什么事都准备好了。吳渊去預备好船只,桅上挂着三盞紅灯,一盞綠灯为号。第二天黃昏时便在船上等候,人一到齐,便开船。
杜滸和余元庆預备第二天一清早便再去約妥那領路的老头兒,带便的先踏一踏路。
一切都有了把握。文天祥整夜的眼灼灼的巴望着天快亮,不能入睡。杜滸也兴奋得閉不上眼。少年的金应,沒有什么顧虑,他头脑最单純,他最乐覌,一倒下头便酣睡,如雷的鼾声,均匀的一声声的响着。
邻家第一只早鷄的长啼,便惊动了杜滸;他一夜只是朦朦朧朧的憩息着。
天祥在大床上轉側着。
“丞相还不曾睡么?”杜滸輕声的說道。
“怎么能够睡得着。”
金应們的鼾声还在間歇而均匀的作响。鷄声又繼續的高啼几响。較夜間还冷的早寒,使杜滸把薄被更裹紧了些。
但天祥已坐起在床。东方的天空刚有些魚肚白,夜云还不曾散。但不一会兒,整个天空便都泛成了浅白色,而东方却为曙光所染紅。
鷄啼得更热閙。
杜滸也起身来。余元庆被惊动,也跳了起来。
那整个的清晨,各忙着应做的事。
但瓜州那边的北軍大营,却派了人来說,限于正午以前渡江。脱逃的計划,几乎全盘为之推翻。
又有一个差官来传說,賈余庆、刘岊們都已經渡江了。只有吳坚因身体不爽,还住在临河的一家客邸里,动弹不得。文天祥乘机便对差官說,他要和吳丞相在明天一早渡江,此时来不及,且不便走路。
那位獰恶的差官,王千户,勉强的答应了在第二天走;但便住在那家店里监护得寸步不离。
天祥暗地里着急非凡,只好虛与敷衍,曲意逢迎。在那永远不見笑容的丑恶的狠脸上,也微有一絲的喜色。杜滸更傾身的和他結納,斥資买酒,終日痛飲。那店主人也加入哄閙着喝酒。到了傍晚,他們都沉醉了,王千户不顧一切的,伏在桌上便熟睡。店主人也归房憩息。
余元庆引路,和杜滸同去約那老头兒来,但那老头兒也已轟飲大醉,舌根兒有些短,說話都不清楚。杜滸十分的着急,勉强的拉了他走。那老妇人看情形可疑,便叨叨絮絮的发話道:“鬼鬼祟祟的图謀着什么事!我知道你們的根柢,不要牵累到我們的老头兒。你們再不走,我便要到哨所去告发了!”
想不到的恐吓与阻碍。杜滸連忙从身边取出一块銀子,也不計多少,塞在那老妇人的手上,說道:“沒有什么要紧的事,請你放心。我們說几句話便回的。这銀子是昨天吳头目答应了給他的,你先收了下来。”
白灿灿的銀光收斂了那老妇人的凶焰。
老头兒到了鼓兒巷,大家用浓茶灌他几大碗,他方才有些清醒。
“現在便走了么?”杜滸道。
“且慢着,要等到深夜,这巷口有一棚韃子兵駐扎着,要等他們熟睡了方可走动。出了这巷口,便都是僻冷的小弄,不会逢到巡哨的了。”老头子說道。
王千户还伏在桌上熟睡,发着吼吼的鼾声,牛鳴似的。
誰都不敢去惊动他。他一醒,大事便去,連他的一轉側,一伸足,都要令人吓得一跳。二十多支眼光都凝注在他身上。
一刻如一年的挨过去!听着打二更,打三更。个个人的心头都打鼓似的在动蕩,惶惑的提心吊胆着。
“該是走的时候了,”老头兒輕声道,站了起来,在前引路。杜滸小心在意的把街門开了,十几个人魚貫而出。天上布滿了白云,只有几粒星光。不敢点灯籠,只得摸索而前,盲人似的。
街上是死寂的沉靜,連狗吠之声也沒有。他們放輕了足步,偷兒般的,心肝仿佛便提悬在口里。蓬蓬的心脏的鼓动声,个个人自己都听得見。
老头兒回轉头来,搖搖手。这是巷口了。一所破屋在路旁站着,敞开着大門,仿佛张大了嘴要吞下过客。門內縱縱橫橫的睡着二十多个韃子兵。鼾声如雷的响,在这深夜里,在逃亡者听来,更覚得可怖。
在屋前,却又縱縱橫橫的系住十多匹悍恶的坐馬,明显的是为了挡路用的。一行人走近了,馬群便扰动起来,鼻子里嘶嘶的噴吐着气,鉄蹄不住的踏地,声音怪响的。
一行人都覚得灵魂兒已經飘飘蕩蕩的飞在上空,身无所主,只有默祷着天神的护佑。他們进退两难的站在这縱横挡道的馬匹之前,沒有办法。
亏得余元庆是調馴馬匹的慣手,金应也懂得这一行。他們俩战战兢兢的先去馴服那十多匹的悍馬,一匹匹的牵过一旁,讓出一条大路来,惊累得一头的冷汗,費了两刻以上的时間,方才完事。
他們过了这一关,仿佛死里逃生,簡直比鬼門关还难闖。沒有一个人不是遍体的冷汗湿衣。文丞相輕輕的喟了一口气。
罗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灯火半闌珊;
梦回跳出鉄門限,世上一重人鬼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