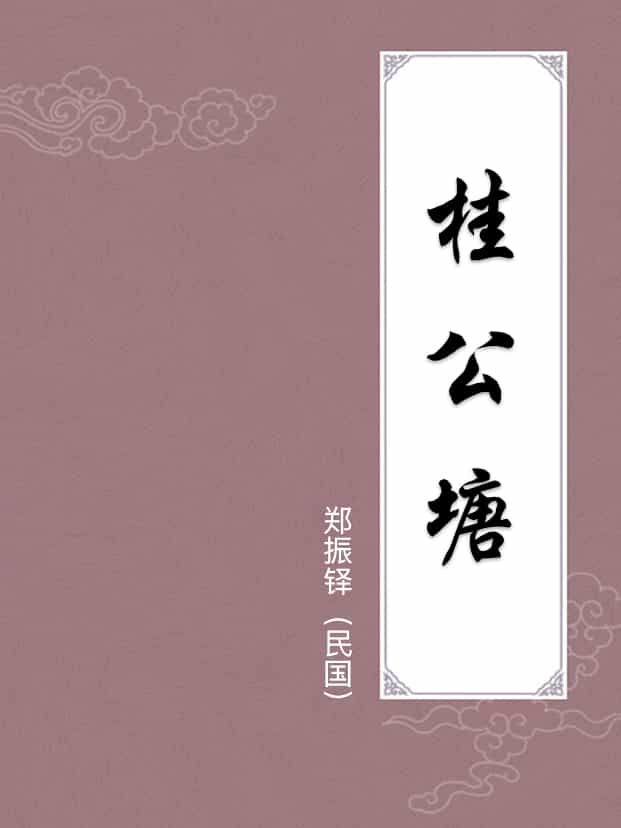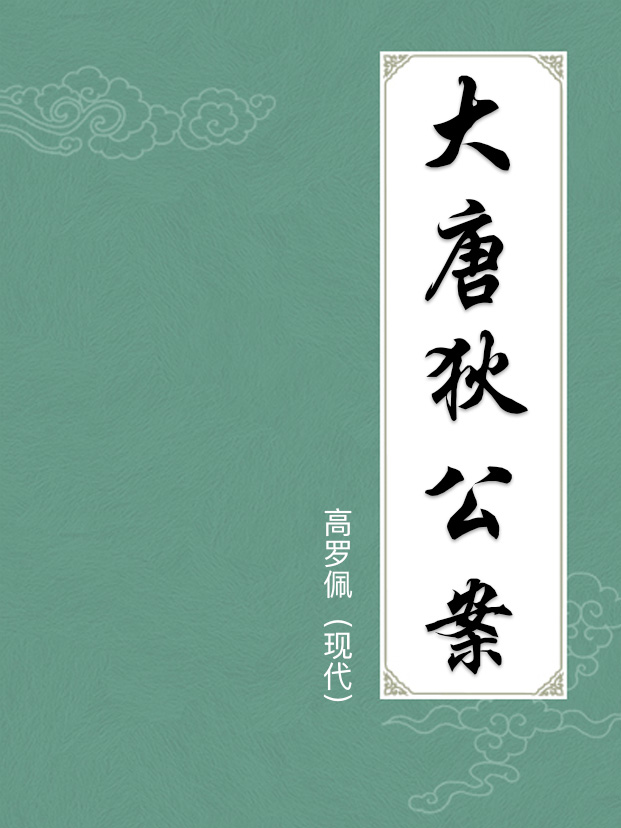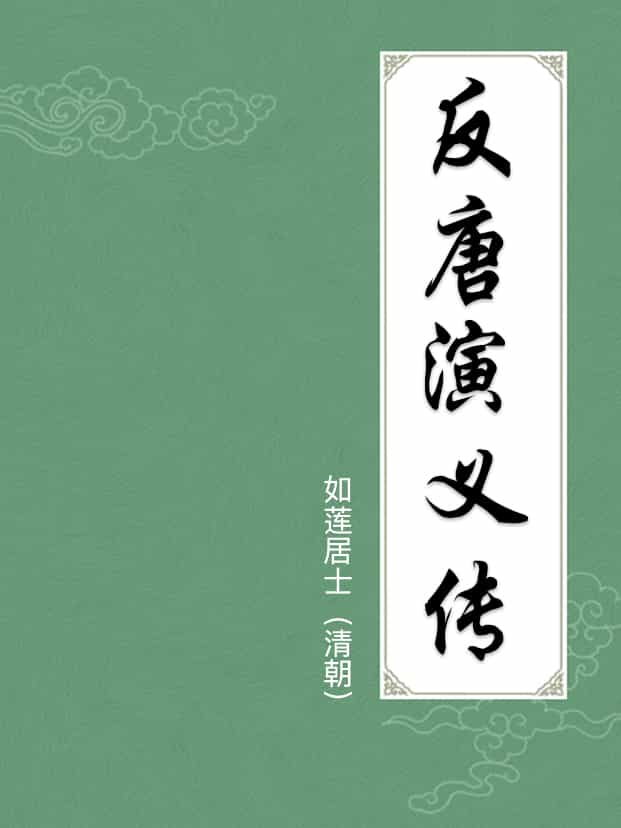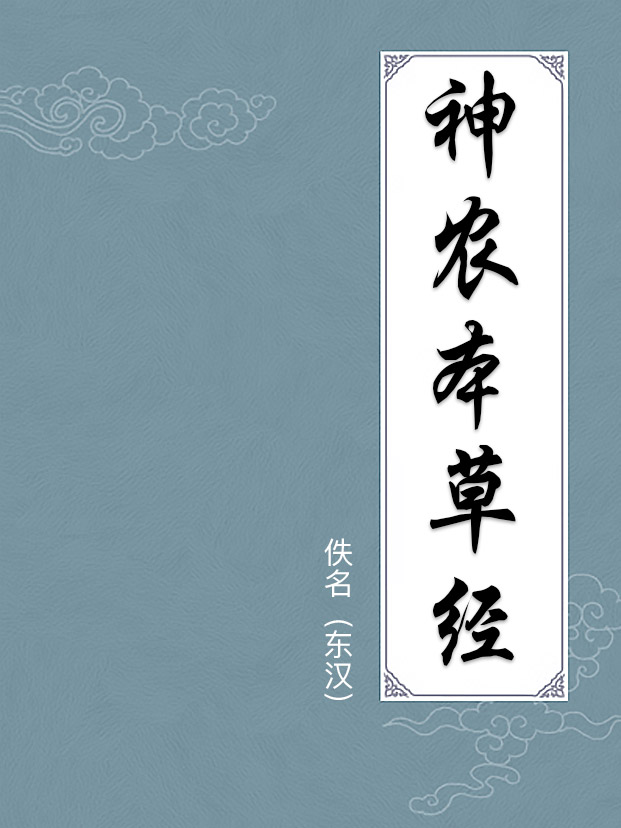余元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訪問他的旧相識吳渊,那位管那只北船的头目。吳渊热烈的欢迎他。
“难得您在这个时候光临。伙計,去打些酒来,买些什么下酒的菜蔬,我們得暢快的談談。”
“不必太費心了,只是說几句便走。”余元庆道。但也不拦阻伙計的出去。
“連年来很得意罢,吳哥。”余元庆从远处淡淡的說起。
吳渊叹了一口气:“不必提了,余哥;活着做亡国奴做随了降将軍而降伏的小卒,有什么意思!想不到鮑老爷那末輕輕易易的便开了城門迎降,牵累得我們都做了不忠不义之徒,臭名传万世!还不如战死了好!最难堪的是,得听韃子們的呼叱。那批深目高鼻,滿脸是毛的回回們更凶暴得可怕。他們也是亡国奴,可是把受到的韃子們的气都泄在我們的身上。余哥,不瞞您說,您老是大忠臣文丞相的亲人,也不怕您泄漏什么,只要有恢复的机会,我是湯便湯里去,火便火里去,决无反悔!总比活着受罪好!我是受够了韃子們回回們的气了!一刀一枪的拚个你死我活,好痛快!”
吳渊說得憤激,气冲冲的仿佛手里便执着一根丈八长矛,在跃跃欲試的要冲鋒陷陣。他的眼眦都睜得要裂开,那样凶狠狠的威棱,是从心底发出的勇敢与郁憤!“可是咱們失去这为国效力的机会!”說时,犹深有遺憾。
余元庆知道他是一位同心的人,故意的叹口气,劝道:“如今是局势全非了;皇帝已經上表献地,且还頒下詔書,諭令天下州郡納款投誠。我輩小人,徒有一身勇力,能干得什么事!只怕是做定了亡国奴了!”
吳渊憤懣的叫道:“余哥,話不是这么說!姓赵的皇帝投了降,难道我們中国人便都随他做了亡国奴!不,不,余哥,我的身虽在北,我的心永远是南向的。我委屈的姑和韃子們周旋,只盼望有那末一天,有那末一个人,肯出来为国家尽力,替南人們爭一口气,我就死也瞑目!”說到这里,他的目眶都紅了,勉强忍住了泪;說下去:
“余哥,别人我也不說,象文丞相,难道便眞的甘心自己送入虎口么?我看,一到了北廷,是决不会讓他再归来的。”
余元庆再也忍不住了,热切的感情的捉住了吳渊的手掌,紧握不放,說道:
“吳哥,我們南人們得爭一口气!我也再不能瞞住您不說了!文丞相却正是为此事苦心焦虑。他何尝願意北去,他是被劫持着同走的。在途中,几次的要逃出,都不能如願。如今是最好的一个逃脫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失,再北行便要希望断絕。我此来,正要和吳哥商量这事。难得吳哥有这忠肝义胆!吳哥,您还沒有見到象文丞相那末忠貞和藹的人呢,眞是令人从之死而无怨。朝里的大臣們要个个都和他一样,国事何至糟到这个地步呢?还有相从的同伴們象杜架閣、金路分們也都是說一是一的好汉們,可以共患难,同死生的。吳哥,說句出于肺腑的話,要不,我为何肯舍弃了安乐的生涯而甘冒那末可怕的艰危与险厄呢?临来的时候,文丞相亲口对我說过:吳哥如果肯載渡他逃出了北軍的掌握,他願給吳哥以承宣使,幷賜白銀千两。”
“这算什么呢?救出了自己国里的一位大臣,难道还希冀什么官爵和賞金!快别提这話了。余哥,您还不明白我的心么?”他指着心胸,“我恨不剖出給您看!”
“不是那末說,吳哥,”余元庆說,“我不能不传达文丞相的話,丞相也只是尽他的一分心而已。丞相建得大功业,恢复得国家朝廷,我們相随的人,可得的岂仅止此!且又何尝希冀这劳什子的官和財!我們死时,得做大宋鬼,得眠歇在一片清白的土地上,便已心滿意足了。不过,丞相旣是这末說,吳哥也何必固拒?”
吳渊道:“余哥呀,我們干罢,您且引我去看看丞相;我为祖国的人出力,便死也无怨!至于什么官賜,且不必提;提了倒見外,使我痛心!我不是那样的人!”
余元庆不敢再說下去。那位伙計恰才回来,手里提了一葫蘆的酒,一包荷叶包着的食物,放在桌上。
“不喝了罢,余哥,咱們走!”吳渊道。
街上,巡哨的尖兵,提鑼击柝,不断的走过。但吳渊有腰牌,得能通行无阻。
“好严厉的巡查!”余元庆吐舌說道。
“整街整巷的都是巡哨,三个人以上的結伴同行,便要受更严厉的盘查。”
余元庆心下暗地着急:“怎样能通过那些哨兵的防綫而出走呢,即使有了船。”
“一起了更,巡哨們便都出来了;都是我們南人,只是头目是韃子兵或色目兵。只有他們凶狠,自己人究竟好說話。我这里地理也不大熟悉,不知道有冷僻点的路可到江边的沒有?”
“且先去踏路看,”余元庆道。“有了船,在江边,走不出哨綫,也沒有用处。”
他們轉了几个弯,街头巷口,几乎沒有一处无哨兵在盘查阻难的。
这把吳渊和余元庆难住了。他們站在一个較冷僻的所在,面对面的覌望着,一毫办法也沒有。
前面一所傾斜的茅屋里,隐約的露出了灯光。吳渊恍若有悟的,拉了余元庆的手便走:“住在这屋里的是一个老軍校,他是一个地理鬼,鎮江的全城的街巷曲折,都烂熟在他的心上。得向他探問。可是,他是一个醉鬼,穷得发了慌,可非錢不行。”
“那容易办,”余元庆道。
一个老妇出来开了門,那老头兒还在灯下独酌。見了吳渊,連忙站了起来,行了礼,短舌头的說道:“吳头目夜巡到这里,小老兒别无可敬,只有这酒,請暖暖冷气。”說时,便要去斟。吳渊連忙止住了他,拉他到門外,說道:“借一步說話。”
給門外的夜风一吹,这老头兒才有些清醒。吳渊問道:“你知道从鼓兒巷到江边,有冷僻的道兒沒有?”
老头兒道:“除了我,問别人也不知。由鼓兒巷轉了几个弯,——一时也說不清走那几条小巷,——便是荒凉的所在。从此落荒东走,便可到江岸。可是得由我引道。别人不会認得。”
吳渊低声的說道:“这話你可不能对第二个人提,提了当心你的老命!我有一場小財运奉送給你,你得小心在意。明兒,也許后兒的夜晚,有几位客人們要从鼓兒巷到江边来。不想惊动人,要挑冷巷走,由你領路,到了江边,給你十两白銀。你要是把这話說泄漏了,可得小心,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兒!”
老头兒带笑的說道:“小老兒不敢,小老兒不敢!”
他們約定了第二天下午再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