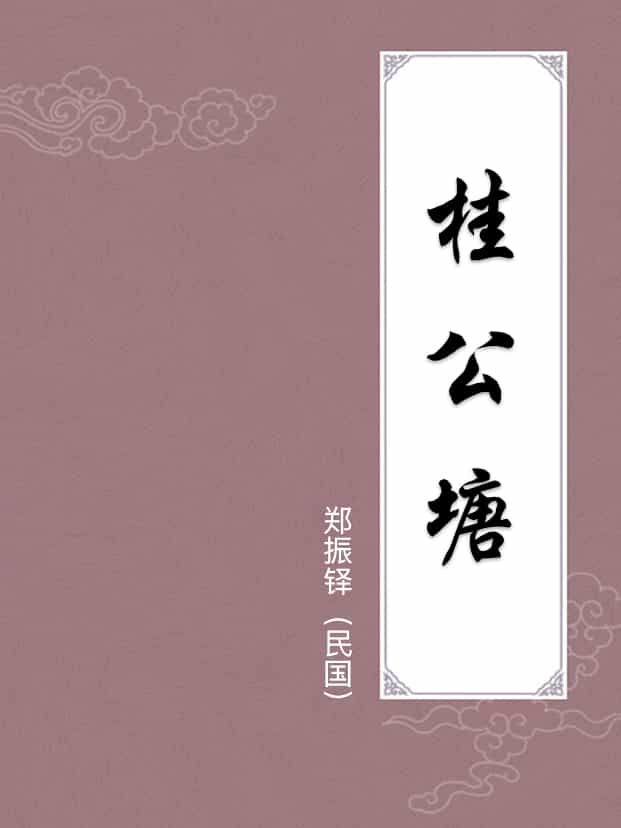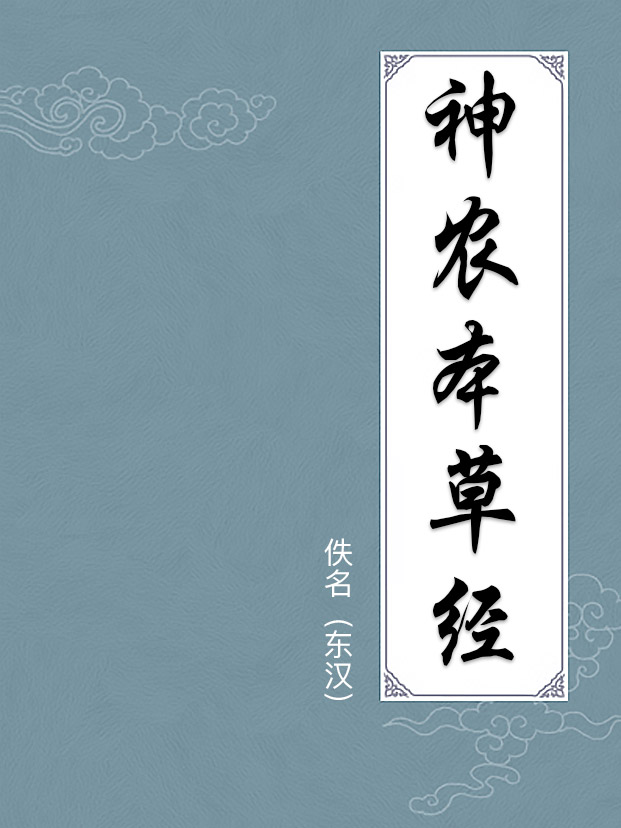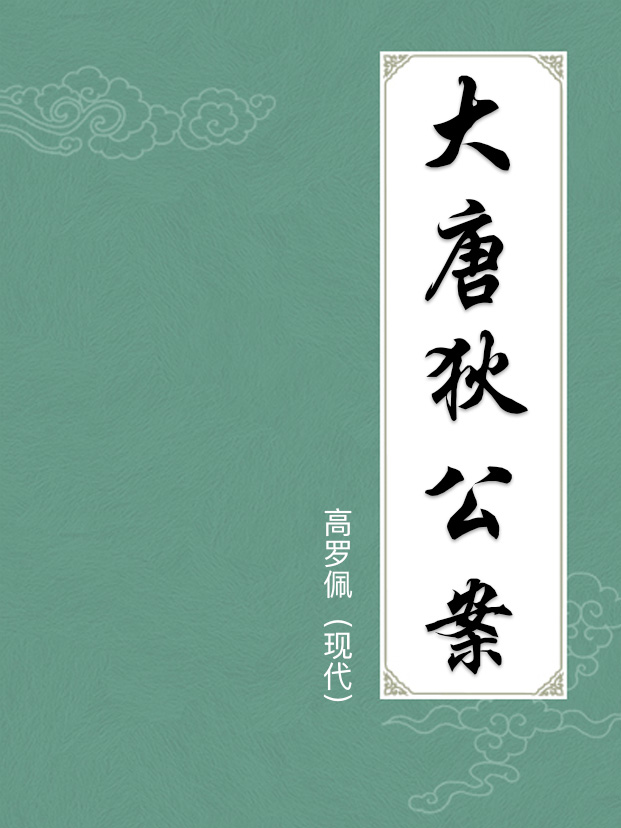那一夜,仍宿在岸上。有留远亭,北酋們設酒于亭上,請祈請諸使列坐宴飲。亭前燃起了一堆火。他們还忘不了在沙漠里住蒙古包的习慣。賈余庆在飲酒中間,装疯作傻,詆駡南朝人物无所不至,用以献媚于鉄木兒。那大酋只是吃吃的笑。
更荒唐的是刘岊,說尽了平常人不忍出口的秽亵的話;只是想佞媚取容。諸酋把他当作了笑具。个个人在取笑他,以他为开玩笑的鵠的。他嘻嘻的笑着,恬然不以为耻。
天祥掉轉了头,不忍看。呂文煥悄悄的对天祥道:
“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为南人羞!”
他幷不答理文煥。半閉目的在养神,杂碎的笑語,充耳不聞,笑語也擲不到他的一个角隅来。
突然的一个哄堂的大笑。站在身边的杜滸頓足道:“太該死了!太該死了!假如有地縫可鑽,我眞要鑽下去了。”
天祥张开了眼。不知从什么地方携来了一个乡妇,丑得可怕,但和北人甚习,恐怕是被擄来已久。北酋們命这乡妇踞坐在刘岊的身上,刘岊居然和她調戏。
一个貴酋指揮道:“怎么不抱抱这位老先生呢?”
乡妇眞的双手抱住了他,咬唇为戏。刘岊还笑嘻嘻的随順着。連吳坚也覚得难堪。
天祥且悲且憤的站了起来,踏着坚定的足步而去。吳坚、家鉉翁、賈余庆也起而告辞。
远远的还听見亭上有連續的笑声,不知这活剧要进行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