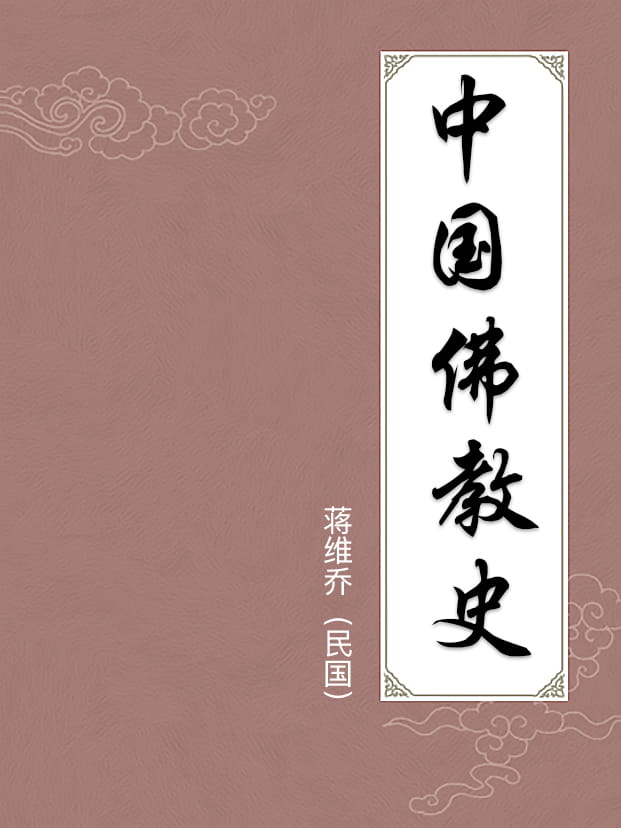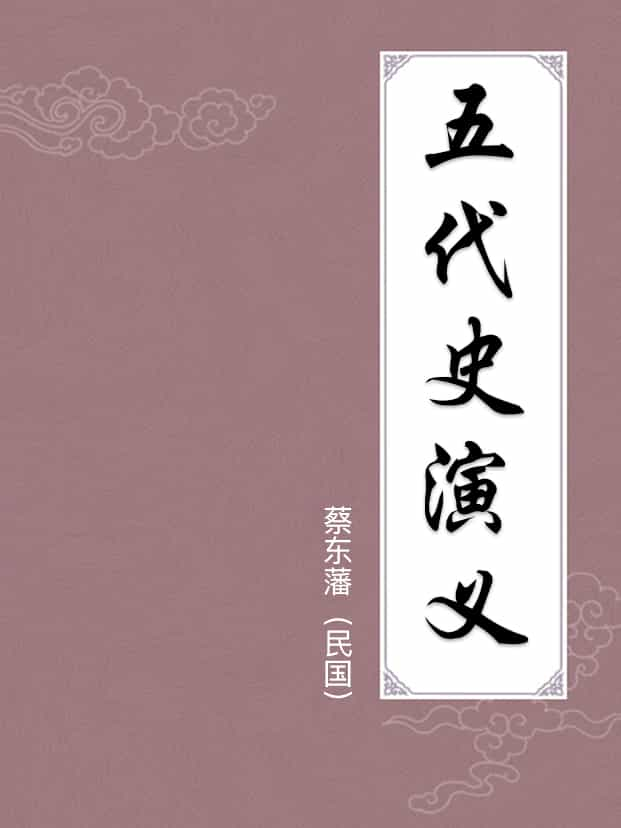天台宗自天台、章安二代而后,气势不扬,传智威(法华)、慧威(天宫)、玄朗(左溪)三代,其间凡百年,自章安贞观六年入寂,以迄玄宗末年。天台宗颇衰微。及玄朗之弟子荆溪尊者(即湛然亦称妙乐大师)出,宗风为之一振,著作等身,天台遗风,大为显扬;盖在肃宗、代宗时也。
湛然,晋陵荆溪之儒家子也。年二十,入左溪玄朗之门,三十二岁始出家。据《佛祖统纪》所载:湛然“谓门弟子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静以观其复,动以应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著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遂慨然以天台再兴自任。
当时禅宗盛行,一方对于其不双传教观,单偏于观法,称教外别传,为轻视智慧,加以非难,斥为暗禅;一方排玄奘所传之法相权教,辟一乘之幽旨。及华严之清凉大师,大为华严吐气时,又取对抗华严之态度。盖荆溪著述甚多,皆恪遵天台之遗旨,发挥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之玄理,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今将荆溪著述之重要者列下:
《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
《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四十卷
《止观大意》一卷
《维摩广疏记》六卷
《始终心要》一卷
《三观义》一卷
《方等补阙仪》一卷
《法华文句记》三十卷
《摩诃止观义例》二卷
《维摩略疏》十卷
《金刚论》一卷
《摩诃止观搜要记》十卷
《法华补助仪》一卷
《五百问论》三卷
此外有《涅槃后分疏》(一卷)、《观心弥经记》(一卷)、《授菩萨戒文》(一卷)、《止观文句》(一卷)、《华严骨目》(一卷)诸书,今不存。尚有《维摩略疏记》(三卷),又再治章安《涅槃经疏》十五卷《文句》、《止观》之科各六卷。
荆溪大师,为天台重要之人;但天台大师创始,荆溪祖述,故其地位,当在天台大师之次。同时华严宗之清凉大师出,大振宗风,荆溪因与之对抗,遂加入天台宗从来所无之分子。如清凉盛引《起信论》,供说明华严教义之用;荆溪亦引《起信论》,借以解释天台一念三千之理。其应用缘起的《起信论》之最著者,即《金刚》是也。《金刚》明涅槃佛性之义,其说无情有性之理曰:
子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故万法之称,宁隔于纤尘;真如之体,何专于彼我。是则无有无波之水,未有不湿之波;在湿讵间于混澄,为波自分于清浊。虽有清有浊,而一性无殊。纵造正造依,依理终无异辙;若许随缘不变,后云无情有无,岂非自语相违耶?故知果地依正融通,并依众生理本故也。此乃事理相对以说,若唯从理,只可云水本无波,必不得云波中无水;如迷东为西,只可云东处无西,终不得云西处无东。若唯从迷说,则波无水名,西失东称。情性合譬,思之可知;无情有无,例之可见。
此说可视为结论之文:即取《起信论》之真如不变、随缘二方面之说,以论无情物之有佛性与否者。若依不变随缘之理,得以常住之真如,与变化无极之差别万法为一体,则一纤尘,亦不得谓为非万法。然则以真如在我为有,在彼为无,决无是理。例取《起信论》水波之譬,水与波为一体,波有清浊之别,而其湿性则断然无别。更就事理别论之:随理而言,真如本体之上,元无情与非情之别;反之随迷情而说,则有情与非情,区别历然,于非情则疑为无佛性。故从理则水原无波;从迷则波无水名,唯见万波相起伏而已。以上为其论旨大要。
(兹所言“子应知”云云,及“子信无情无佛性者”云云,子者,暗指华严之学者而言。)
观以上论调,足知荆溪之用《起信论》,盖为对敌论者便宜上而设。此为《起信论》适用于天台宗之始,然其与后世天台宗之影响,殊不少也。
(荆溪之前,天台大师之《小止观》,及《观音别行玄义》中,虽有引用《起信论》之处,但不甚重要。)
华严之清凉大师澄观,与荆溪虽属同时,以其年考之,则澄观为其后辈。盖荆溪以德宗建中三年入寂,年七十二岁,澄观年才四十六岁也。澄观殁于宪宗元和年间,寿七十岁。此可谓为唐代佛教振兴之最后期也。
(但此殁年及年寿,系据《高僧传三集》。在《佛祖统记》、《佛祖通载》、《编年通论》所载,则澄观殁为文宗开成三年,寿百有二岁。)
据《高僧传三集》所载:澄观于“乾元中,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本州依昙一隶习南山律,诣金陵玄壁法师传关河《三论》。《三论》之盛于江表,观之力也。大历中,就瓦棺寺传《起信》、《涅槃》;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却复天竺诜法师门,温习《华严》大经。七年,往剡溪,从成都慧量法师,覆寻《三论》。十年,就苏州,从湛然法师,习天台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又谒牛头山忠师、径山钦师、洛阳无名师,咨决南宗禅法;复见慧云禅师,了北宗玄理”。律则南山、相部,禅则南北二宗,其他《三论》、天台、《起信》、《涅槃》,无不通晓。又曰:“解从上智,性自天然。”实非虚誉也。又曰:“习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至于篇颂笔语书踪,一皆博综。多能之性,自天纵之。”由此观之,其博习多才可知矣。至其本宗华严,则受自钱塘天竺寺之法诜。所著四百余卷,兹举其重要者列下:
《华严经疏》六十卷
《华严经疏演义钞》三十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一卷
《大华严经略策》一卷
《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一卷
《三圣圆融观门》一卷
《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
《华严法界玄镜》二卷
《华严经纲要》三卷
《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一卷
《华严心要》一卷
《华严玄谈》九卷
此外尚著有《法华》、《楞伽》、《中观论》等疏。清凉亦如贤首之参与《八十华严》之翻译,曾列般若三藏《四十华严》译场。般若三藏,梵名般剌若,华言智慧,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游学中天竺、南天竺,以德宗建中四年来华。贞元十一年,乌荼国今阿利萨地方王献《华严经》,此当前译《六十》、《八十》两经之《给孤独园会》之《入法界品》;《华严》全部梵本,凡六夹十万偈。《八十华严》为第二夹终。此《四十华严》为第三夹,凡一万六千七百偈。见《贞元释教录》。般若三藏奉诏翻译,宣梵文;天官寺广济为译语;西明寺圆照充笔受之任;保寿寺智柔、智通回缀;正觉寺道弘、章敬寺鉴灵润文;大觉寺道章证义;千礼寺大道证禅义;千福寺灵邃及清凉为之详定。
般若三藏所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十卷,乃般若三藏与景净所合译者。景净者,大秦寺僧,即来华传景教(耶稣教)之人也。初般若来华,遇其亲戚罗好心,好心大喜,请译经。般若不明华语及波斯语;景净不知梵文,亦不解佛教;自难成完全之译本。译成,献于朝廷,德宗见其不全,不许流行,命就西明寺重译:般若三藏宣释梵本;沙门利言译语;圆照(西明寺)笔受;道液、良秀、圆照(庄严寺)并润文;应真、超悟、道岸、空,并同证义。佛耶二教之僧,共译佛经,堪发一噱。今举《贞元录》之文于下:其文曰:“好心既信重三宝,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娴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濬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辞疎。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天人攸仰,四众知归。”又曰:“就西明寺,重更翻译讫,闻奏。”按文中弥尸诃教,即耶稣教。弥尸诃原文为Messiah。
华严宗自法藏灭后,以迄澄观,凡六七十年间,除慧苑背师说立异议外,无可观者,实为华严之暗黑时代。澄观在华严宗之位置,与荆溪之在天台相似。其以一宗再兴,祖述师说为己任,二人亦相似。唯澄观于振兴本宗之外,兼排慧苑之异义,力复法藏本旨,颇受当时禅宗之影响。终至其弟子宗密,倡为教禅一致论。其意虽谋发挥法藏之说,而与法藏本旨大异矣。
慧苑之《刊定记》谓澄观五教,不过在天台之四教中,加以顿教而已。其言曰:
此五,大都影响天台,唯加顿教令别尔。然以天台呼小乘三藏教,名谬滥故,直目名小乘教;通教但被初根,故名初教;别教被于熟机,故名终教;圆教之名依旧也。
其意以为小乘、大乘始教、终教、圆教,与天台之三藏教、大乘通教、别教、圆教相同,法藏不过加顿教为五教,此举殊乏意义。何则?法藏之顿教,乃指口不得言心不得虑之绝对真理,实是理而非教;不可与能说之教小、始、终、圆,视同一律。若亦得谓之教,则大乘佛教之极致,皆不得不谓为顿教。此慧苑所以不满于五教,而别立四种教之判释也。(四种教,载在第十三章之二。)
慧苑与其师法藏意见相歧之处,以四种教之判释,及两重十玄缘起说,为最重要。澄观斥为异论,而回复法藏之说,以示绝对之理为顿教,非常神妙。成立五教之判释,至于天台四教与法藏五教相同之处,澄观亦与慧苑同其意见。其相异之处,惟在立顿教与否之点耳。澄观《华严玄谈》曰:“若全同天台,何以别立?有少异故,所以加之?天台四教,皆有绝言;四教分之,故不立顿。贤首意云:天台四教绝言,并令亡诠会旨;今欲顿诠言绝之理,别为一类之机。”其所主张,以为华严之五教,大体同天台之四教,所以于天台外为此说者,因天台不别说顿教,而法藏则为一类离念之机而说之也。至澄观即以禅宗当此顿教,故以五教为合理。实际上顿教今尚流行也。证观对于两重十玄之意见,若欲详叙,恐近烦琐,今略之。
法藏所言顿教为何?应略加说明。盖当法藏时代,尚未置禅宗于眼中,故禅为顿教,未及考虑。及澄观标出禅为顿教,华严与禅,始相接近。澄观论同、别二教,以配五教。兹示之于下:
此以禅宗为同教一乘之极致;反之则降天台宗为终教之位置,即为对抗荆溪所唱之天台也。
加之澄观仿天台亦唱性恶不断之说。性恶不断说,虽为天台之特色,然善恶之体非二:一方见为善,则他方见为恶;虽佛亦非能断性恶,阐提亦非失性善。澄观借天台立说:乃据《起信论》之平等差别一而二二而一之性相融会论,谓真如与万法,真妄合一;故一方见之为真,他方见之为妄,真妄二者,根本相同;离真无妄,故真不可断,则妄亦无尽。此即《六十华严经》所谓“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八十华严经》所谓“应如佛与心,体性皆无尽”是也。证观参照此《六十》、《八十》两译之文,合而详言之。可谓为“心佛与众生,体性皆无尽”也。谓心佛众生之体性无尽,则如来亦可谓为性恶不断也。于是澄观一方扬禅以抑天台,一方又用天台之理,以与天台对抗。
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本为示阿赖耶缘起说一派之论,因与玄奘所传之说违异,故法藏大师,却称扬《起信论》以对抗玄奘。谓玄奘所传之说,仅大乘始教,说真如与万法一体不离之关系,未为彻底;而《起信论》论平等差别一体不二,大乘教之真理,至是始尽其底蕴,故以之为大乘终教,而置于玄奘所传法相宗之上。盖法藏虽以华严自立,而三论宗或真谛宗,凡可为玄奘法相宗对抗之武器者,皆助势力,而置之法相宗之上,以期压抑法相宗;而以华严居最高位置,以示自己之立足地位。故法藏著《起信论义记》,全与著三论宗之《十二门宗致义记》,用意相同,凡以为对抗法相宗之具耳。法藏著《义记》以前,虽有注《起信论》者,但法藏注解,备极周详,使前此不为人所重之《起信论》,促起学者之研究。至荆溪澄观时代,澄观更盛用之,以性相融会差别平等不二一体之说,为性恶不断论之一依据。终更扬法藏所判大乘终教之《起信论》,使侪于圆教之列,遂为证明教禅一致之根据。至宗密而达乎其极。荆溪则用《起信论》以说明自家之教义。于是《起信论》位置,在佛教教义史上,大为重要;但此与《起信论》自身之教义无关也。
澄观之弟子宗密,本传菏泽禅,后乃随澄观学《华严》。著述甚多,比于澄观,更进一步,而唱禅与华严一致之说,于其所著中,发挥尽致。其专说禅教一致论者,《禅源诸诠集》是也。今将其著述之重要者,列之于下:
《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
《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二卷
《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九卷
《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
《四分律疏》五卷
《盂兰盆经疏》二卷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疏》十二卷
《华严心要注》一卷
《钞悬谈》二卷
《高僧传三集》载其著书“凡二百许卷,图六面”,今多不传。
今由《禅源诸诠集》以述其禅教一致论之要旨,盖宗密立禅,区分三种,(此三种禅,已述于禅宗项下。)而谓与之相应之教,亦有三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宗密之唱禅教一致也,以《起信论》为根本;取《起信论》众生心、迷悟、染净、世间出世间之法,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说,而谓禅宗目的,亦在显心;教之目的,亦在一心;其说盖悉本诸澄观者也。
世传华严五祖:以杜顺和尚为初祖,华云和尚(智俨)为二祖,贤首国师为三祖,澄观国师为四祖;圭峰(宗密)大师即五祖也。自华云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太宗以至文宗,咸赐封号焉。
华严宗自宗密以后,继承其绪者,比诸天台宗,著名之人较少;天台则荆溪以后,有道邃、行满诸师。日本之传教大师,即受教于道邃、行满,实为日本天台宗之始。未几,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此所谓三武法难之一也。
兹就唐武宗会昌法难略述之,以示唐代佛教之归结,并言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唐初佛教,已臻隆盛,但道教受朝廷保护尤笃。且太宗以降,领土扩张,远通异域,外国诸教,向未传入中国者,如景教、耶稣教之一派。伊斯兰教、波斯祆教(火教)、末尼教等,皆相继而入,称为新宗教。当是时,本国儒教,深入人心,自无待言;道教见异教纷至沓来,常以该教为产自中土,时与外来佛教争衡;加之唐帝李姓,谓老子为其先祖,故累代极护道教。终唐之世二百余年间,二教冲突,未之或息。
高祖武德四年,道士太史令傅奕,上书十一条,论寺塔僧尼之多,为国家害,请灭省之。又著《高识传》,详列古来排斥佛教诸人,自武德之初,迄贞观十四年,凡二十余年间,极力排佛者,皆认为道教之功臣。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论者续出:高祖时,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辅翼傅奕,从事排佛。太宗贞观十一年,洛阳道士与僧侣辩论结果,道士奏之天子,天子下诏,改儒佛道三教席次,凡有仪式,道士、女道士列于僧尼之前。贞观二十一年,至命玄奘三藏,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集五通观,译《老子》为梵语,以弘西域。
当是时,护持佛教与道士抗辩者,以慧净、法琳、智实三人,为最著名。傅奕上书十一条时,朝廷召僧徒诘问,法琳进而辩之。高祖不仅欲限制僧尼,兼欲淘汰道士等,傅奕不为屈,频传其说于民间。法琳遂著《破邪论》(二卷)驳奕,门下李师政著《内德论》;同时绵州振音寺之明(传不明),对于傅奕,亦著《决破》八条,奏之朝廷;迨其后李仲卿、刘进喜等之《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出,法琳遂著《辩正论》(八卷)。高祖武德八年,国学行释奠礼时,论三宗三座,定席次为老、孔、释,故慧净与李仲卿以下之道士等大论战,终使闭口而退。太宗下席次之诏敕时,智实与法常、慧净、法琳等,随驾上表谏之,谕以背命者处罪。智实独进言,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命还俗,处以流罪。贞观十四年,道士泰世英奏,法琳之《辩正论》为诽谤朝廷,至有捕琳推勘之谕。因琳之辩解,能称帝意,故减罪配益州,琳遂终于蜀地。其他二教争论尚多,兹略之。
唐累代尊敬老子。睿宗且以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冠(女道士),自是皇女始有入道者。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原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崇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像,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瑰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人主亭毒之意。”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后百余年,韩退之著《原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微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及武宗会昌五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宪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唯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会昌元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士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有谏帝者,赵归真更招罗浮山邓元超入都,互相结纳,以厚其势。当时宰相李德裕亦助之。遂应道士之请,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武宗诏曰:“其天下所拆寺,还俗僧尼,收充税户。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五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凡六万区。”由此观之,此举在当时备极纷扰,诚非细故也。
当是时,非独禁佛教也,景教、祆教、末尼教、伊斯兰教等,亦被其厄。景教为耶稣教一派,西历五世纪顷,希利亚之涅槃司特儿始行之。此人唱基督非神子说,故为一般耶稣教徒所排斥;在四百三十一年小亚细亚耶匪耶司之宗教会议被捕,流于阿儿美尼亚;其书悉被焚弃。但此教行于西亚细亚地方,渐经波斯来中国。在中国始传此教者为阿罗本(西亚细亚人),贞观九年来长安,迎于宫中译经。京都造大秦寺,各州建景教寺以弘其教。拜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其后有景净等僧。景教流传中国之次第,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之“景”,碑文曰:“功用照彰,强称景教。”盖谓有照暗黑之功用曰景也。祆教为波斯之昨罗阿司特所开之拜火教。太宗贞观五年,何禄传入长安。当高祖时,长安已有建祆神祠之说。唐设祆正、祆祝之官,其盛可知矣。末尼教,亦波斯宗教,乃末尼(一作摩尼)氏所开,以祆教为本,而调和佛耶二教者。则天延载元年,拂多诞传入中国。回教为穆罕默德所开伊斯兰教,来中国年代不明,似在贞观前后。经会昌之难,诸教皆潜,惟回教复行。
武宗十九年崩,宣宗立,废破佛令。时值唐之末叶,宦官擅权,任意废立天子;加以牛李之争,朝廷纷扰不止;李德裕、牛僧孺、争拥政树党,互相轧轹,谓之牛李之争。且藩镇骄横,不肯用命。经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唐遂亡于朱全忠。经五代之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历五十余年,至后周世宗时,又下破佛令。显德二年,禁止私自出家;废寺院之无敕额者三万百三、十六所,存二千七百寺。民间之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此即世称三武一宗之厄之一宗也。五代诸帝中,周世宗较有力,领土较大;其他各地,为群雄所割据;故此厄仅其一部分耳。至如南方之吴越王,累代奉佛颇厚,其域内佛教甚盛。
吴越王始自钱镠,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赐玉册金印,称吴越王。传钱瓘、钱佐、钱倧、钱俶,累代相承。钱俶之时,值赵宋之兴,终归于宋。吴越王领土之内,有天台山者,历史上有名之大寺也。当吴越王建国时,适值天台十四祖清竦时代,镠加以保护。俶尤崇佛,值天台羲寂时代;俶子钱惟怡,与义通同时;此二人者,与佛教关系颇深。吴越王与天台之关系,俟后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