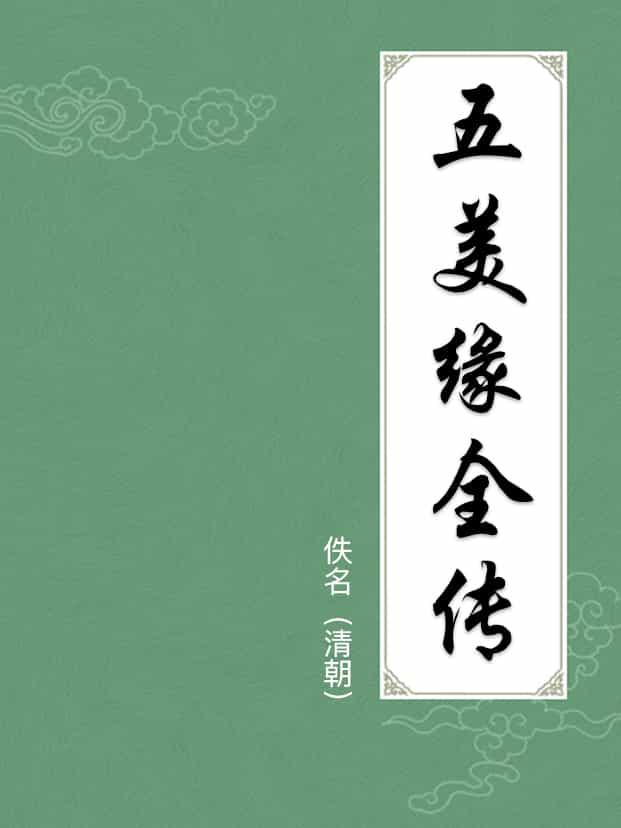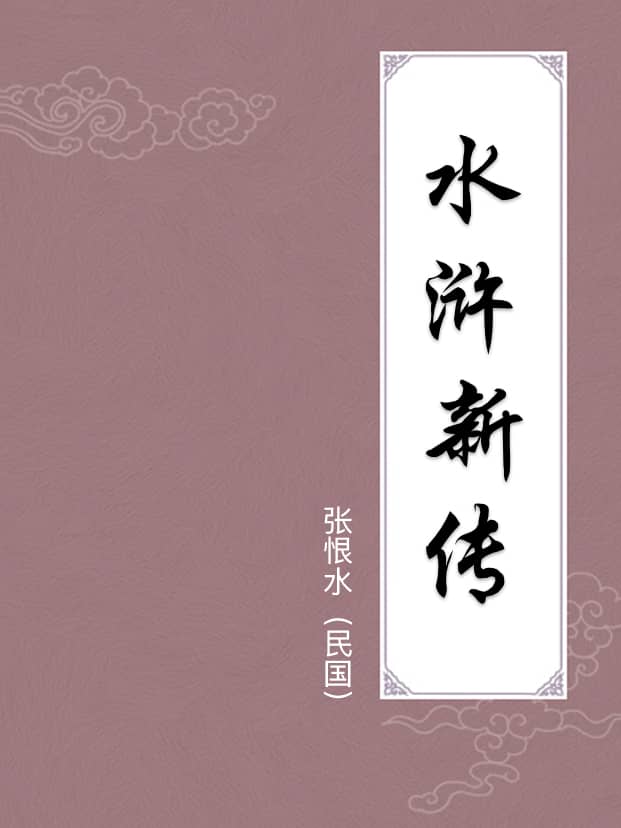诗曰:
婚姻大事非偶然,自有月光暗底牵。
夫唱妇随偕到老,来年寿富又双全。
话说皮奉山叫声:“妈妈,快快打烧酒来我喝!”张妈妈说:“已叫干儿子上街打酒去了,买豆腐干子。”再言大小伙买完,一直来家交把妈妈,站在块不走:“妈妈,我要个钱买巴巴吃!”张妈妈把强氏与她吃的果子把了些,大小伙他欢喜得很,咙时咙嚉耐跳了去了。
再言妈妈开柜,拿酒杯与五爷吃酒。不料五爷眼尖,看见了一盘大鲫鱼,端了出来,搭搭酒。豆腐干子热热,取壶斟酒。妈妈看他,说:“五爷,你从此以后不要找我了,只当你女儿死的了!”五爷说:“我今日吃了你的酒,从此一笔勾销,窝账再不窝你了!”妈妈心内说:“今日强氏嘱托事,我看此人正合她语。”妈妈开口说话:
“老爹,你就不想日子过么?”
“我的妈妈,怎么不想好日子!我时运不好,局就坏了,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想到我不如死了干净!”妈妈说:“五老爷,你可曾娶过亲?我投有,哪一个又还同我做亲?”妈妈又开言说:“你今年尊庚了?”五爷说:“我今曰二十四岁。”
“你今住在哪块?”
“妈妈,我住在土地庙子里藏身。我皮五癞子是六个妈子带大了的。父亲在日,到庙里求神许愿做好事,修桥铺路,修积我这一个献世宝下来。寻了一个吃乳的妈子,她的年纪轻,夫妻又好,两下台不得分开来,带家去了;后又寻个贴乳的妈子,哪晓得贴乳妈子又有了孕了,辞了家去;又寻了一个半乳的妈子,那半乳的妈子老了,家去;又寻一个干带的妈子,那干带的妈子又要下乡种田;又寻一个抱我的妈子,她抱不动;又寻一个抚我的妈子,过了一年,她又去了。”
闲话休提,再官妈妈说:“五老爹,我代你做个媒吧!”五爷说:“妈妈,是哪一家姑娘,代我做媒?说起来你已该晓得,就是孙大理姑娘,名叫孝姑。…妈妈你说起孙老爹,我认得他,他是我个偌大的恩人,还未报他。我想起当初,讹了一个开绸店小官,他回去告诉他家大人,即刻把我送到捕衙里。把我叫到上面问了一声:‘皮五癞子,你又来了么?’叫取头号板子,六寸厚的板子。”站班的恨我,狠狠说:‘伙,今日与你个糖心的吃吃!’若是吃食糖心倒好了,原来是块头号重板子。孙老爹看见叫:兄弟们,公门好修行,你们换个空壳子与他吃吃罢。‘站班的依了老爹,换了轻的。老爷叫打四十板,哀求打了一板。后来叫又打十板,我浑身打得不疼,如扑灭一般。我一个飞脚腿跳出来。可怜孙老爹是个好人,把两把银子与我,说:“老五,你把银子拿了去,做一个生意。’我拿他银子就走,到叉鸡王二家,一输输了个千干净净。妈妈,你说别人家还犹可,你说孙老爹家,妈妈,天下人不要,独独要看上我皮五癞子不妨?还是我人品好?言谈好?家道好?人色好?就是妈你说这种话,看中我哪一件好,不妨耶?你要论品格,极了顶了;若论本人,是我皮五痴子尖几脑儿赛儿,特等之中特特等。也罢!你既代我做媒,还有两句话交代在前:是要叫我养她,是万万不能。天晴各吃各,天阴她还要贴我一顿。奶奶你代我说得妥,你打一斤代我道喜;要是说不妥,你打一斤代我探脑。”张妈妈说:“五爷,你今日且回府,过两天来讨信吧!”
到了次日下午后,张妈妈无事,就到孙奶奶那边走走。不一刻工夫,已到孙府。
用手敲门,奶奶问:“是哪个?”妈妈答应:“是我!”奶奶将门开了,二人进内。奶奶问:“代找的人在哪一块?”“奶奶,人是找到一个。当日开过当铺,两个果子行。”奶奶未曾听完,说:“你还是人,还是鬼么?”“奶奶你不要着急,等我说完了。如今就穷了千干净净,衣不终身,食不充口。家内烟火全无,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身一个,住在土地庙里了。”奶奶听毕,回嗔作喜:“此人正合我意!”奶奶又拜托:“就是此人很好!”于是,二人话毕,张妈妈回自己家来。
到了次日,天还未亮,起来烧烧香,开了门,哪晓得皮五爷还未亮,他就站在门口。他为何不敲门?他虽穷,心里也还明白。他说道:“张妈妈是个半边人,寡妇家,我清早敲门进去,不便。只得站在门口等她开门。”妈妈烧过香,开了门,看见皮五爷,说道:“你早呀?”五爷说:“也不早了!”进来望奶奶说:“你代我说的亲、做的媒如何?”奶奶说:“媒是倒有九分了。你家住房也在一所,你如今住在土地庙里,如何娶得亲?你可有床么?娶她在哪里睡觉哩?奶奶,我房子也有,床也有,被也有,褥子也有,枕头也有,各色皆有!”张妈妈说:“告诉我听,房子在哪里?床在哪里?被褥在哪里?说与我听一听。”五爷说:“妈妈。”你听着:“房子不消说得,土地庙内;床么,我把土地公公、土地奶奶搬搬家,让我们,不是床有了?被褥,你听着,等那晚间,新娘进门,我早起到城门口,同乡下人拿两个稻草下来,不是被褥也有?枕头更容易,拿两块城砖,这个如何?”
“叫斯人到土地庙,稻草铺内,是何话说!必须要寻一所房子,买一张床、做一床紫花布被、绿布褥子,还要买个四脚盆。”奶奶问:“五老爹,你可要添东西”“奶奶呀,你是个什么人!我要有钱添东西,奶奶,我不去赌钱,娶什么亲?我不是呆子,你老人家想想看。”奶奶说:“五爷,我有几两银子借与你,我同你去寻一间房子要紧。”五爷就同了张妈妈带了银子,锁了门户,到了街上寻房子。五爷说:“奶奶,要看看人色何如?奶奶,不是我皮五癞子说大话,开口是我皮五癞子一个人,哪一个大胆穷得过我皮五癫子?站起来是我皮五癞子,竖起来还是皮五癞子,睡下去还是皮五癞子,把我就癞得千干净净!”
不谈五爷癞大口,再讲张妈妈同他一路谈心,顺步而走。走到了东门城脚根,走了几家门口,见有一家贴着:“七十三闲房子把人住。”奶奶认不得,上写着:“黄门姚氏七十三岁,领黄衣的。”妈妈说:“怪不得上面忒黄些!”张妈妈又走过了几家,看见那门口有一位奶奶,坐在板凳上,端了一盆衣服在块洗的,旁边有一间空房子。张妈妈说:“问了声奶奶,这间壁房子可租与人?”奶奶说:“是租的。”妈妈说:
“拜托!带我看一看!”奶奶说:“等我喊人去,带你老人家看房子。”奶奶喊了一声:
“细小伙老子,有人看房子哩!”倪三正同人打天九,听见喊有人看房子,打挫了牌包子,一直跑了家来,看见老太,彼此通名通姓,妈妈说:“里面房子是尊府?”倪三说:“敝友徐老二的,待我喊他一声。”说:“张奶奶,我家敝友的房子干干净净,又不安水。如今我这个敝友,系他家父置下来的,如今这敝房又租别人。敝房是千干净净,连一点水也没有。”随即喊了徐二过来,讲了房租,二两八钱一年房租,彼此言定,永无异说。徐二问多早晚成交,择了好日,张妈妈说:“改日不如撞日好,就是今日吧!”不知成交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