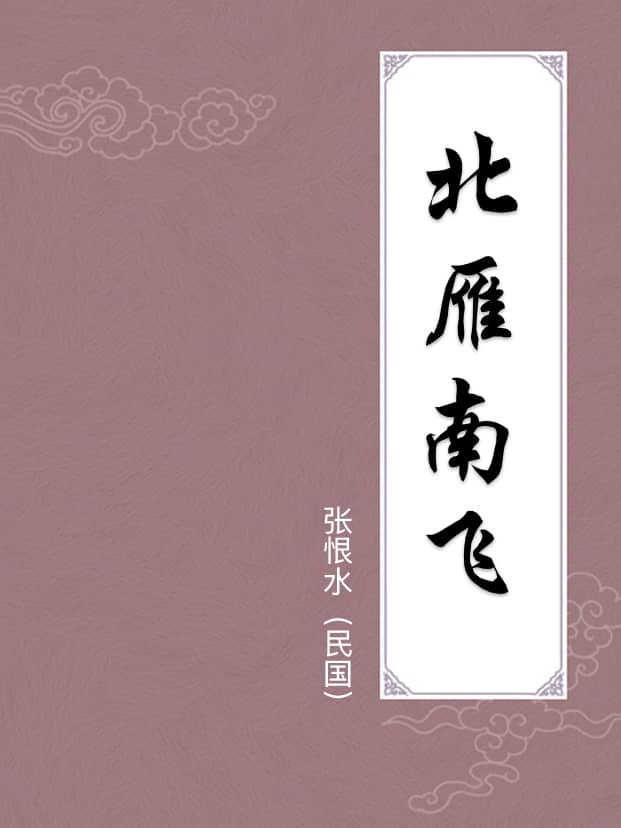话说谭绍闻回家,次日无事。到了第三日,王中在门首,只见一个粗蠢大汉,面目带着村气,衣服却又乔样,后头跟着一个年幼小童,手拿着不新不旧的红帖,写着不端不正的字样,递于王中。王中一看,上面写着“年家眷弟茅拔茹拜。”上下打量,是个古董混帐人。又细看跟的人,脖项尚有粉痕,手尖带着指箍,分明是个唱旦的。方猜就是个供戏的。便答应道:
“家主失候,有罪。往乡里照料庄农,收拾房屋去了。回来我说就是。”那人道:“几时走的?”王中道:“去了四五天。”那人道:“这就出奇了!前日还在林宅同席,如何会走了四五天?分明是主子大了,眼中没人。依我说,我还看不见这样主户哩。你这管家,也就大的很,就是你主子不在家,也该让我到家中坐坐,吃你一杯茶,留下帖子,好不省事的要紧。像我们每日在外边闯,也不信这样人家会作践人。我就到客厅中闲坐坐,怕甚的!”
一面说着,早已上门台到院里了。进的前院,这绍闻正在客厅檐下坐着,口中打啸,引画眉儿叫。茅拔茹道:“好大的主子!明明在家,却叫家人说往乡里去了七八天。九娃儿,把帖子交了,咱走罢。这就算咱拜了客。”九娃道:“帖子家人收了。”茅拔茹道:“既是收了,还讨回来。”扭回头来就走。绍闻道:“这是那里话?”茅拔茹道:“你没在家,出门七八天,我跟谁说话哩?”绍闻一把扯住道:“这是啥话?”茅拔茹道。”啥话不啥话,你问你门上二爷。”绍闻一灵百透的人,便说道:“想是底下人不认的,错说了话。千万休怪,我赔礼就是。”慌忙作下揖去,茅拔茹搀住,说道:“不消,不消。我坐坐就是。”
一同到了厢房,也不为礼。绍闻一片声叫看茶。茅拔茹道:
“还吃茶么?”绍闻道:“啥话些!”茅拔茹道:“我前日席上,看见尊驾像是个好朋友,所以今日来拜。不料门上二爷,硬说你出门七八天。我小弟在家,也是乡宦旧家,家下小价,没有像这样敢得罪人的。”绍闻明知是王中,便说道:“小价该死,我一定处治他。”双庆儿送上茶来,绍闻奉过茶,茅拔茹道:“九娃,与谭爷磕头。那人咱也不与他一般见识。”九娃走上前来,磕下头去,说道:“少爷好呀。”绍闻一手搀起,那九娃就站在绍闻跟前,等着接茶盅,绍闻见温存光景,便吩咐双庆儿:“你放下茶盘,到后边摆几个粗碟儿。连德喜也叫的来。”
说犹未完,夏逢若已进门来,未说先笑道:“好呀!好呀!”
茅拔茹立起身来道:“少时便去奉拜,如今不为礼罢。”逢若道:“岂敢。”一同坐下。双庆摆上碟儿,德喜提着酒注儿斟酒。茅拔茹也不推辞,逢若也不谦让,便吃起酒来。酒未数巡,茅拔茹使叫九娃唱曲子。九娃顿起娇喉,唱了两牌子小曲,逢若哼哼的接着腔儿,用箸敲着碟子,却也合板眼。九娃唱完,说道:“唱的不好,爷们笑话。”夏逢若道:“间《集贤宾》第四句,再挑高着些,第六句,少一个弯儿。”九娃道:“记下就是。”逢若道:“我也递你一盅酒儿。”九娃星眼看着茅拔茹说道:“我不会吃。”茅拔茹道:“既是夏爷赏你,你吃了罢”九娃方才接住吃了。又唱了两三二个曲子。--若是将这些牙酸肉麻的情况,写的穷形极状,未免蹈小说家窠臼。
日将午时,早已一桌美馔上来。茅拔茹道:“初次奉拜,那有讨扰之理?”绍闻道:“便饭不堪敬客。”逢若道:“既是通家相与,也彼此不用客气。”九娃儿也站在一旁吃饭。吃完了,茅拔茹要起身,说道:“今日天晚,明日去拜夏兄。”夏逢若急忙接口道:“我两个明日即去答拜。既是好朋友,何在到我家即算拜,不到我家不算拜么?我两个明日去奉看就是。”茅拔茹道:“这才是四海通家的话。我明日就在小店恭候。”夏逢若问九娃道:“那座店里?”九娃道:“同喜店。”逢若道:。是戴君实家,是也不是?”九娃道:“正是。”绍闻还留吃酒,茅拔茹道:“戏上事忙。头盔铺里邓相公说,今日下午商量添几件东西哩。我去罢。”一同出了厢房,恰遇王中从大门进来,茅拔茹笑道:“说你出门七八天,就是这位大爷。”绍闻道:“这是河北茅爷,认着。”王中一声也没言语,站在门旁,让客与家主出去。一拱而别。
逢若又进来,要再吃一杯茶,订明日回拜的话。”又夸了一会九娃,着实有眼色。又说:“明日回拜,那里有戏子,我衣服不新鲜,脸上不好看。也还得二两赏银,一时手乏。还得帮凑帮凑。”绍闻道:“你休高声,我今晚给你运用。明日你只用早来约我同去,就都停当了。”逢若道:“你衣服太短,我穿着不像。”绍闻道:“有长的你穿就是。我实不瞒你,先父还有一领蓝缎宽袍儿,你穿的了。你明日只要看那个王中不在门首,你进来。不是我怕他,他是先父的家人。我通不好意思怎么他。”夏逢若道:“这是贤弟的孝道。王中粗人,那里得知。”绍闻道。”这话休叫盛大哥知道。”逢若道:“休看我多嘴,正经有关系的话儿,却会烂在肚里。”日夕时去了。晚间,绍闻替逢若料理衣服,赏银。
到了次日早晨,逢若瞅着王中不在门首,进的厢房。绍闻出来相见,说道。那书柜里是昨晚拿出来的衣裳,你趁没人先穿上。”又拿出七八两银子,说道:“这是我在账房要的。一言难尽,多亏王中极早睡了,说他身上不好哩,才要出这七八两银子。这个够赏戏子么?”逢若换了衣服,说道:“到也可体。只是时常来借,却不便宜,不如就放在我家,我却不要你的。老伯的衣服,我断不敢不敬重。至于赏戏子们,若要说这是称准的一两二两,便小家子气了;只可在瓶口捻出一个锞子、两个锞子,赏他们,这才大方哩。”
一时早饭上来。吃完,叫双庆儿讨了两个拜帖,不用阎相公写,逢若在厢房自写,也写了“年家眷弟”的派头。绍闻却是素花柬,跟着两个小厮。逢若道:“这两个他都认的,显的我是借的人。只叫一个跟去。你与我再安排一个人,就是粗笨些也可。”绍闻因叫邓祥算上一个。二人出的大门,德喜、邓祥在后,一直向同喜店来。
到了店口,戴君实看见,与夏逢若作了揖,与谭绍闻也作了揖,说道:“二位回拜客来了?茅爷今早,叫当槽的在如意新馆定下一桌酒席,说午时要待客哩。戏已安排就了。”逢若道:“只怕别的还有客。”话犹未完,茅拔茹在上房看见店门是谭夏二位与店主说话,早已不待传帖,跑将出来,说道:“候的久了。”于是连店主一同让进去。
二人方欲行礼,茅拔茹搀住,说道:“论起来,我还该与二位磕头哩。我家里家叔不在了,昨晚有信来,真正活气死我。
二位坐下,我说。”店主叫当槽的送上茶来。‘九娃斟茶,奉毕,绍闻脸皮渐厚,便对九娃道:“昨日有慢你。”九娃笑了一笑。夏逢若道:“谭贤弟成了款了。”只见茅拔茹把膝上拍了一下,说道:“咳!你说气人不气人,家叔竟是死了!”逢若道:“什么陡症?如何得知?”茅拔茹道:“昨晚送的信来,说起来恨人之极。我小弟在家,也算一家人家,国初时,祖上也做过大官。只为小弟自幼好弄锣鼓,后来就有江湖班投奔。小弟叫他伺候堂戏,一些规矩也是不知道,倒惹的亲朋们出像。我一怒之间,着人去苏州聘了两位教师,出招帖,招了些孩子,拣了又拣,拣出一二十个。这昆腔比不得粗戏,整串二年多,才出的场,腔口还不得稳、我今实不相瞒,上年我卖了两顷多地,亲自上南京置买衣裳,费了一千四五百两,还欠下五百多账。
连脸子、鬼皮、头盔、把子,打了八个箱、四个筒,运到家里。
谁想小地方,写不出价钱来。况且人家不大热合这昆班。我想省城是个热闹繁华地方,衙门里少不了正经班子,所以连人带箱运在省城。连昨日林宅,共唱了三个戏,还不够箱的脚钱。
谁知道我家叔老人家,偏偏的会死起来。我来时,家叔病原沉重,原说不叫我来。我想在家一干人空空盘绞,也是难事,因此硬来了。如今果然不在了。我待说不回去,他一是我个胞叔,不说在舍弟脸上不好看--舍弟他还小哩,也不知道啥,怕亲朋们也谈驳我。”--逢若插口道:“是哩。”--“我待说回去,这一班子人,怎么安插?我明日就要起身,赶上大后日封柩罢。真真的活闷怅死了人!”
九娃上来问:“开锣罢?”茅拔茹道:“这还问我么?”一声锣鼓,早已在院里棚下,唱了两三出散戏。如意馆抬上席来,茅拔茹赏抬盒人五十文钱,又吩咐九娃道:“您煞了戏罢,去附近铺子里吃了饭,早回来开戏敬客。”因又说道:“这可像个样子么?况且这宗花消,我走后如何支撑得住。”夏逢若便向绍闻道:“我们备一顿饭钱。”便向绣瓶口掏出一个锞儿,绍闻掏出四个锞儿。夏逢若道:“班上的,这是我两个送你们一顿粗饭。”老生道:“不敢讨赏。”逢若道:“见笑,免人意儿罢。”茅拔茹道:“不该费心,叫他们通过来磕头谢赏。缝若又叫道:“九娃儿,我与谭爷替你做件衣裳,你自去拣你心爱的买罢。”逢若一个锞儿,绍闻两个锞儿,九娃收了,磕头又谢。茅拔茹道:“他们吃饭。你就在这里伺候罢。”九娃道:
“知道。”于是德喜儿、邓祥摆开席面,谭。夏二人首座,店主、茅拔茹打横。九娃斟酒。
饮酒中间,店主道:“茅爷,你通不吃一盅儿?令叔老大爷去世,想是大数该尽,也不用过为伤心。”茅拔茹道:“倒也不在这些。只是如今这一伙子人,主人家,你承许下,我就不作难了。”戴君实道:“我是赁的这座店,不过替买看吃罢了。茅爷你撇下,我实实摆布不来。”逢若道:“茅兄是愁没房子么?”茅拔茹道:“一来没房子,二来没人招驾。”逢若道:“谭贤弟有一攒院子,在宅子后,可以住得下,我就替你招驾,何如?”绍闻未及回言,茅拔茹早已离座三揖,道:“箱钱就是谭兄哩,长分子就是夏兄哩。就是吃三五石粮饭,用十数串莱薪钱,我回来算账。我若有一点儿撒赖,再过不的老爷河。”戴君实道:“茅爷何用赌咒。通是好朋友,何在这些。”
逢若向绍闻道:-就是这样了,你看行也不行?”绍闻千不合万不合,答道:“你看该怎的,就怎的。”茅拔茹哈哈大笑道:
“明早就起箱去。爽快我有一句话,一发说了罢。九娃过来,你就拜了谭爷做个干儿子罢。”绍闻这一惊不小,方欲回言,九娃早已磕了四个头,起来靠住绍闻站着。店主起来作揖,说与谭绍闻道喜,绍闻嚣的耳朵稍都是红的。逢若指定九娃道:
“好孩子,有福!有福!”
须臾,戏子吃饭回来,又开了戏。不叫九娃出角。把残席赏了德喜、邓祥。当槽的速去如意馆取五六盘小卖,叫九娃吃了。唱完几出戏,家中宋禄套车来接。茅拔茹打点起身,不肯再留。一同出了店门,九娃小心用意搀住绍闻上车。逢若早已超乘而上。说了一声“扰!”车儿飞也似跑了。到分路之时,逢若下车而去。
绍闻到了家里,心里只是乱跳,又不敢向人说。只推有酒,蒙住头就睡。
到了次日,未曾起来,早已八个箱,四个筒,枪刀号头,堆满了碧草轩。原来东方日出时,蔡湘方才起来,开了园门,一轰儿抬的抬,搬的搬,不多时,一院子都是戏子。把一个蔡湘竟是看呆了,只像梦里一般。这一个戏娃子弄花草,那一个戏娃子摸笔砚,只听掌班的喝道:“休要多手。等谭戏主出来,你们要摆齐磕头,休要失了规矩。”九娃道:“我是不磕头的。”
蔡湘定省一大会,方才往宅下飞报军情。咳!
子弟切莫学世路,才说周旋便浊污;
依依父兄师长前,此外那许多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