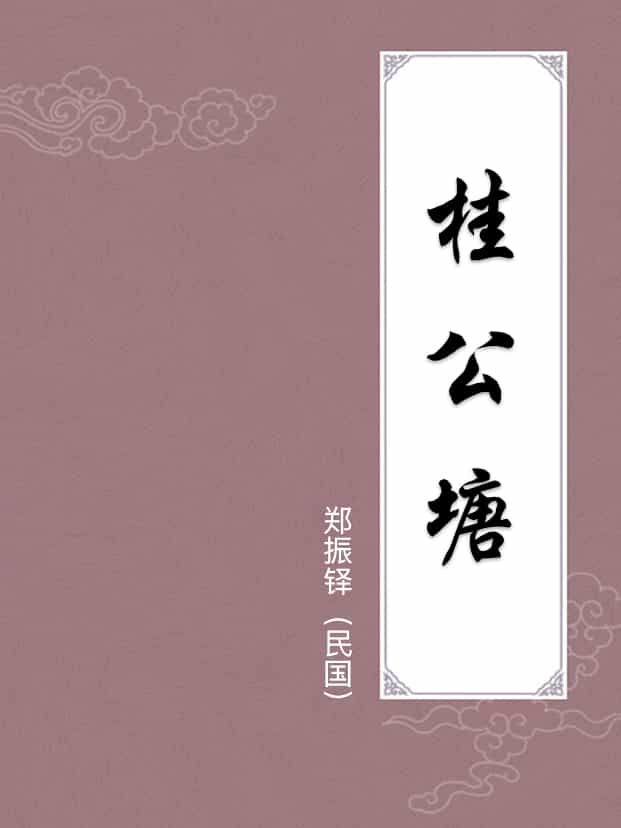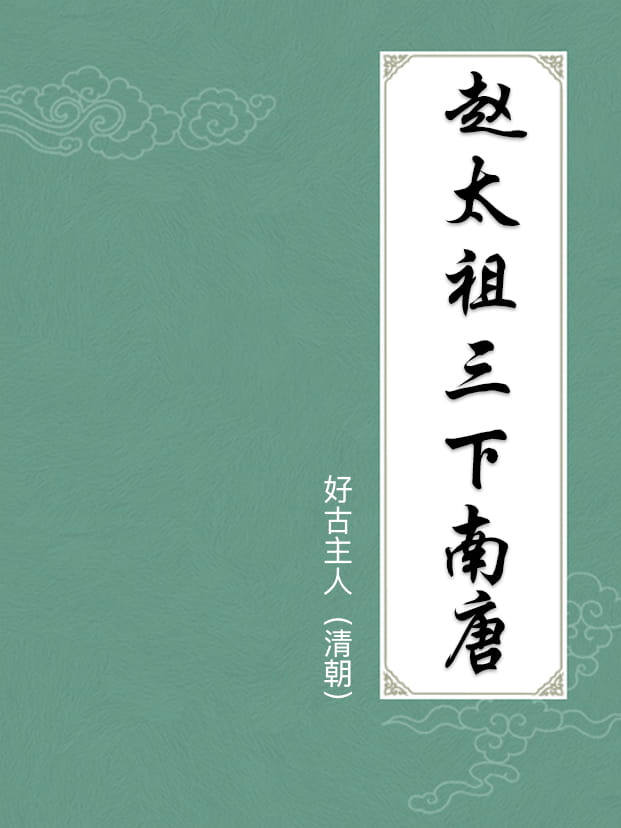整整的走了一天,都是羊腸鳥道,有时簡直沒有路迹可循。那一带沒有山居的人,也沒有茅舍小庙,有銀子买不到东西充飢,大家餓了一天。金应那小伙子,飢餓得要叫喚起来,但忍住了千万的怨恨,不說什么。
天祥走得喘不过气来,扶在余元庆的身上,勉强的前进。有几次,实在走不动,便象倒了似的,坐在荒草上,一时起不来。休息了好一会,方才再得移动。
到了一个山谷里。夜色不知什么时候已經爬在天上,鐮刀似的新月纖秀的挂在东方。
“过了这山谷,便近高邮了,是一条大道。只怕山頂上有哨兵。我們得格外小心。别开口,足步走得輕些,最好躱在岩边树隙里走。”余元庆悄声的說道。
“前面是桂公塘,有个土围,我認得。原是一个大牛栏,如今栏內大約不会有牛匹了。到那里憩息一夜,养好了足力,絕早便走。除此可隐蔽的以外,四望都是空曠之所,万不能住下。有几户山民,不知还住在屋里否?但我們万不可去叩門,韃子兵也許会隐藏在那里。”余元庆又道,在这条路上,他是一个向导,一个統帅,他的話几乎便是命令。
他們暫时占領了这土围。金应們不一会便都睡着了;只有天祥和杜滸是警醒着。风露漸凉起来,只有加厚衣在身,紧紧的裹住。夜天的星光,彼此在熠熠的守望着,正象他們的不睡。
新月已經西沉,烏云又已被风所驅走。繁星的夜天,依然是說不出的凄美动人。
文丞相和杜滸都仰头向天,好久好久的不言不动。
仿佛已經过了三更天的光景。山道上,远远的传来嘈嘈杂杂的馬蹄声。
杜滸警覚的站了起来:“不是馬蹄声么?”
“这时候难道有哨騎出来?”
“不止数十百騎,那声响是嘈杂而宏大。”
余元庆也被惊醒过来。“是什么声响?”
“决然是馬队走过。馬蹄踏在山道上的声响。仿佛更近了些。但願不經过这土围!”
余元庆凄然的說道:“只有这一条大道!”
杜滸有些心肺蕩动,“这一次是要遭到最后的劫运了!”他自己想道。
騎兵队愈走愈近。宏大而急速的馬的蹄声,听得很清晰。金应們也都醒了来,面面相覷,个个人都惊吓得沒有人色。
上下排的牙齿,似在相战;膝头盖也有些軟瘫而抖动。只有天祥和杜滸还鎮定。
天祥又探握着他的小匕首,預备在袖口里。
馬蹄声近了,更近了;嘶嘶叱叱的馬匹的噴气声也听得到。馬上的騎士們的偶发的簡語,也明晰可聞。大家都站了起来,以背負土墙而立,仿佛想要鑽陷入墙里一样。
就在土墙外面走过。一騎,二騎……数十数百騎,陆續的过去。仿佛就在面前經过,只隔了一座墙。土墙有些震撼,足下的地,也似应和着外面的馬蹄的践踏而响动着。
总有两刻鐘还沒有走完。
难堪的恐怖的时間!
“这土围里是什么呢?”明白的听見一个騎兵在說。
“下馬去探探看罢!”另一个說。
“这一次是完結了!”杜滸絕望的在心底叫道,全身血液似都冷結住了。
“沒有什么,臭得很,快过去罢,左右不过是馬栏、牛栏。”又一个說。馬蹄得得,很快的过去了。
总有三千騎走过。騎兵們腰上挂的箭筒,喀嗦喀嗦的作响;連这也历落的传入土围之內的他們的耳中。
当最后的一騎走过了时,人人都自賀更生。
馬蹄声又漸远漸逝了,山間寂寂如恒。
不知从那里,随风透过来一声鷄啼。
天色有些泛白,星光暗淡了下来。彼此的手脸有些辨得出。
“趁这五更天,我們走罢。”余元庆道。
有的人腿足还是軟軟的。
闖过了山口,幸沒遇見哨兵。
山底下是一片大平原,稻田里刚插下秧苗,新碧得可爱。
太阳从东方升起。和藹的金光正迎面射在他們的身上脸上。有一股新的活力輸入肢体。
山背后还是黝黑的,但前面是一片的金光。
英雄未肯死前休,风起云飞不自由!
杀我混同江外去,岂无曹翰守幽州!
——文天祥:《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