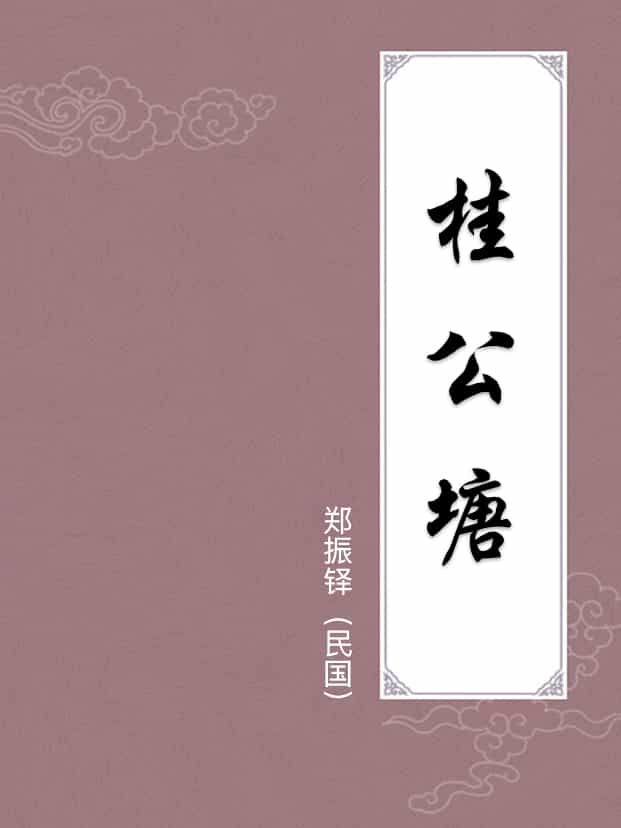天地虽寬靡所容!长淮誰是主人翁?
江南父老还相念,只欠一帆东海风。
——文天祥:《旅怀》
他們是十二个。杜滸,那精悍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負似的,不择地的坐了下去。刚坐下,立刻跳了起来,叫道:
“慢着!地上太潮湿。”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淤湿了。
疲倦得快要瘫化了的几个人,听了这叫声,勉强的掙扎的站着,背靠在土墙上。
一地的湿泥,还杂着一堆堆的牛粪,狗粪。这土围至少有十丈見方,本是一个牛栏。在这兵荒馬乱的时候,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們牵去了呢,还是已經逃避到深山里去,这里只剩下空空的一个大牛栏。湿泥里吐射出很浓厚的腥騷气。周遭的粪堆,那臭恶的气味,更陣陣的扑鼻而来。他們站定了时,在靜寂清鮮的夜間的空气里,这气味兒益发重,益发难聞,随了一陣陣的晚风直冲扑而来。个个人都要呕吐似的,长袖的袖口連忙紧掩了鼻孔。
“今夜就歇在这土围里?”杜滸无可奈何的問道。
“这周围的几十里內,不会有一个比这个土围更机密隐秘的地方。我們以快些走离这危险的地带为上策,怎么敢到民家里去叩門呢?冷不防那宅里住的是韃子兵呢。”那作为向导的本地人余元庆又仔細的叮囑道。
十丈見方的一个土围上面,沒有任何的蔽盖。天色蓝得可爱。晶亮的小星点兒,此明彼灭的似在打着灯語。苗条的一弯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围靜悄悄的,偶然在很远的东方,有几声犬吠,其声凄惨的象在哭。
露天的憇息是这几天便过慣了的,倒沒有什么。天气是那末好。沒有一点下雨的征兆。季春的气候,夜間是不凉不暖。睡在沒有蔽盖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气,就从立足的地面蒸騰上来,更有那一陣陣的难堪的粪臭气浓烈的夹杂在空中,熏冲得人站立不住。
“在这个齷齪的地方,丞相怎么能睡呢?”杜滸躊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書生,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穿着蓝布衣褲,腰系布条,足登草鞋。虽在流离顛沛之中,他的高华的气度,渊雅的局量,还不曾改变。他忧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脸,好几天不曾洗了,但还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际聚集了几条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虑。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还勉强的站立着。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足底板是又痠痛,又湿热;过多的汗水把袜子都浸得湿了,有点怪难受的苦楚。但他不說什么,他能够吃苦。他已經历过千辛万苦;他还准备着要經历千百倍于此的苦楚。
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凉颸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在痠痛。
“我們怎么好呢?这个地方沒法睡,总得想个法子。至少,丞相得憇息一下!”杜滸热心地焦急着說道。
文丞相不說什么,依然昂首向天。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領略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詩句呢!”年輕的金应悄悄的对邻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說。
“我們得想个法子!”杜滸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
向导的余元庆說道:“沒有别的法子,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凈土出来再說。”
“那末,大家就动手打扫,”杜滸立刻下命令似的說。
他首先寻到一条树枝,枝头綠叶紛披的,当作了扫帚,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秽土。
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
“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脸上了!”
“小心点,我的衣服被你的树枝扫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浆呢。”
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在責駡,然而一团的高兴,几乎把刚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記了。他們孩子們似的在打閙。
不知扫折了多少树枝,落下了多少的綠叶,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显得干凈些。
“就是这样了罢,”杜滸叹了一口气,放下了他的打扫的工作,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个侍从,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鋪在地上。
“丞相也該息息了,”他怜惜的說道。
“諸位都坐下了罢,”文丞相藹然和气的招呼道。
陆陆續續的都围住了文丞相而坐下。他們是十二个。
年輕的金应道:“我覚得有点冷,該生个火才好。”
“刚才走得热了,倒不覚什么。現在坐定了下来,倒眞覚得有些冷抖抖的了。”杜滸道。
“得生个火,我去找干树枝去。”好动的金应說着,便跳了起来。
向导,那个瘦削的終年象有深忧似的余元庆,立刻也跳起身来,挡住了金应的去路,严峻的說道:“你干什么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誰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韃子兵呢?生火招他們来么?”
金应一肚子的高兴,橫被打断了,咕嘟着嘴,自言自語道:“老是韃子兵韃子兵的吓唬人!老子一个打得他媽的十个!”然而他終于仍然坐了下去。
“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来巡邏的么?到正午便都归了队,夜間是不会来的。”杜滸自己寬慰的說道。
“那也說不定。这里离瓜州揚子桥不远,大軍营在那边,时时有征調,总得格外小心些好。”余元庆的瘦削見骨的脸上露出深謀远虑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眼睛还是望着夜天。
鐮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东边的天上略显得阴暗。有些烏云在聚集。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块,横亘在那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現的。
晚风漸漸的大了起来。土围外的树林在簌簌的微語,在凄楚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