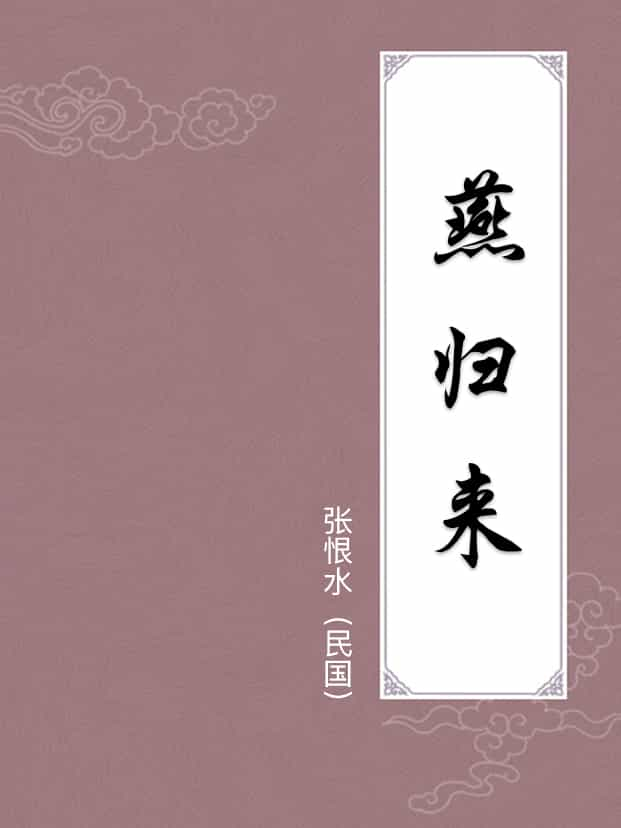说到了婚姻问题,谁也觉得是带点神秘性的事情,从没有痛痛快快一口说出来的;尤其是女孩子们,她们无论如何,总得把这事含蓄着说,好像不含蓄着说,就有点不切题似的。燕秋虽是爽快一流的女子,然而究竟年纪轻一点,所以灿英那样好的女友,只管追问着她,也不肯一口就说出来。灿英呢,虽晓得她必定有了一个人,到底猜不出这人是谁。现在见她说到口边,又把这话忍了回去。就跳了脚道:你真要急死我了!肯说就告诉我,真不肯说呢,我也不能非刑拷打逼出你的口供。你老是这样装腔作势作什么?
燕秋这时就握住灿英的手,正色道:真的,我不骗你,人选我是没有决定,纵然有人和我同行,我也必定到了西北以后,得了长时期的考察再说。现在你要我告诉一个人,我糊里糊涂指上一个人骗骗你,那倒不要紧。可是把这话传出去了,将来发生了误会,那岂不是一件笑话。
灿英点点头道:得!你有理,我不问你这些话了。你说还有重要的事情要重托我呢,你就说吧,究竟还有什么事要重托我?
燕秋又昂着头想了一想,还是抿嘴笑着摇了两摇头。灿英跳起来道:这真是急惊风遇到慢郎中,你什么话,我也不要问了。现在我们解决别的问题,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一块儿吃午饭去,就算是我和你饯行了。这还有什么可以推诿的吗?
燕秋道:哎!老大姐!你不能谅解我?
灿英道:我谅解你呀,我不谅解你,还能请你去吃饭吗?
说着,就把搭在椅子背上的雨衣,拿到了手里来。燕秋道:还下雨呢,就在旅馆里叫些东西吃,不省事得多吗?
灿英道:那怎样的叫我请你呢?
燕秋说着话,可还坐在椅子上呢。灿英走过来,搀住她一只手,不问她同意不同意,口里连说着走走走!燕秋笑着站了起来,拍着她的肩膀道:你我的感情,确乎不错,将来我到西北去了,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灿英鼻子一耸道:哼!我倒是不会变心的,就怕你将来有了对手方,可就把我们摔在脑后了。
燕秋索兴伏在她肩上,向她耳朵边问道:难道你就不找对手方的吗?将来你有了对手方,又把什么态度来对付我呢?
灿英答复得很妙,微笑道:你就往后瞧吧。
燕秋笑道:好!凭你这一句话,我也得去叨扰你这一餐饭。
说着话,换了皮鞋,就同灿英一路下楼。
到了旅馆门口时,马路上的雨正下得大。那屋檐下垂下来的檐溜,如牵着长绳子一般,不容人钻了出去。燕秋站在门里,笑道:你看,这样大的雨,哪里叫车子去?就是有车子,恐怕他也要大大的敲一笔竹杠吧!
灿英道:我穿着雨衣呢,不要紧,让我到门外叫去。
燕秋道:不要胡闹了,让茶房去叫吧。
两人正在这里拉扯着。只见一个穿西服的人,外罩雨衣,头戴雨帽,两手插在雨衣袋里,跳了进门来,口里叫道:好大的雨。
他说着话,取下头上的帽子,连连的摔了两下,摔下两条水线,有一条直洒到灿英脸上来。她红了脸,正待发作两句呢。那男子也就发觉了身后站着有人,立刻扭转身来,鞠着躬满脸堆下笑来道:对不住!对不住!
当他口里说话时,他已看得清楚,就是来追求的杨燕秋。灿英也看清楚了,这就是像电影皇帝运动家石耐劳。燕秋笑道:这样大雨,石先生由哪里而来?
他笑道:特意到这里来看看密斯杨的。不,杨女士讨厌人家叫密斯的。
说着又向她道:请替我介绍介绍,这位女士是…………
燕秋挽了灿英的手道:她是我极好的同学,李灿英女士。李!这是大名鼎鼎的运动家、足球健将、田径赛…………
石耐劳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刚才进门,冒昧得很,胡乱洒水,洒了李女士一身水吧?
灿英看到他以后,早把洒上几滴水点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笑道:没关系。我身上不还穿了雨衣吗?
石耐劳道:这样大雨,二位女士,要到哪里去?
燕秋道:李女士要请我出去吃饭呢。门口雨大,外面又没有车子,我们正在这里想法子。
石耐劳道:不成问题,我身上有雨衣,我到这里都来了,出门叫车子还不行吗?
说着话,他已走出了大门去。灿英向燕秋低声地笑道:这样大雨,他都来了。
燕秋没有作声,微微的一笑。
不多一会儿,石耐劳果然领着人力车来了,笑道:我真是冒失,也没有问二位到哪里去,就把车子叫来了。
灿英道:就是这条马路上的今雨楼。石先生若是不嫌弃的话,一块儿去坐坐。
石耐劳道:好的。二位请先上车吧,我随后就到。
说着,他弯腰代拉了车把,将人力车子拉过了滴水檐下,好让二位小姐上车,躲过那水溜去。这二位女士,不是傻子,石先生这番体贴之意,自是很明白。二人坐上了车子,自各有一种感想。到了酒馆里以后,找了一个单间。因为雨天,除了两人,此外并没有顾客,所以整个馆子,都是静悄悄的,正好谈话。燕秋和灿英抱住一只桌子角坐着,灿英手摸了燕秋的手,微笑道:杨!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对手方就是这位石先生吧?
燕秋正色道:你不要胡说。这句话我绝对不能承认。
灿英见她说得如此的肯定,倒有些奇怪。纵然说石耐劳是对手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她有些气急的样子?望了她的脸色,也正想把这句话追着向下问,却听到茶房吆喝一声五号的,接着有一阵皮鞋声;咚咚咚的走上了楼来。灿英心里明白,立刻停止了话不说。
门帘子一掀,石耐劳满脸是笑容,走了进来了。他两手拿着两把花,向前一鞠躬,笑道:在路上遇到一个卖鲜花的,我看到这把玫瑰开得实在是好看,就买了两把,送给二位,在雨天解个闷吧。
他说话时,心里可就想着:李小姐乃是今天初次见面,总算是极生的朋友,应当先疏而后亲。于是把左手上捏住的花,右手先分过一把来,递给了灿英,然后很随便的把左手这把花交给了燕秋。燕秋果然如他心里所想象的,彼此是很熟的朋友,不拘形迹。可是灿英拿了花在手上,立刻凑在鼻子上嗅着,由花上放出一道喜色的眼光,把这位像电影皇帝的运动家全身都笼罩着。然后笑道:石先生!谢谢你啦。
同时,她心里想着:对一个老朋友,何必要送什么鲜花?分明他买这花是送给我的。至于给燕秋一把花,那不过是陪笔罢了。不见他将花交给她的时候,是很随便的样子吗?燕秋笑道:这个样子,我们坐了车来,石先生倒是在雨地里走了来的了?
耐劳脱着雨衣,手上提着抖了两抖,笑道:有这个,不要紧。
他说着,正要向钩子上去挂起来,同时就发现了衣钩上还有一件女子雨衣,这正是新朋友李女士的。说这话,倒好像说人家穿了雨衣,还要坐车。于是又跟了解释着道,这也只有我们好运动的人,有这样走路的瘾。其实这样大的雨,穿了雨衣,也是不济事。二位是非坐车子不可,街上的水深着啦!
说着话,拖了凳子在下方坐着奉陪。桌上已是放下了一把茶壶,四只茶杯。灿英斟了一杯茶,隔了桌面,双手递到耐劳面前来。他站起来道:怎么要李女士倒茶呢?不敢当!不敢当!
灿英笑道:这个小约会,是我的主人;我倒茶敬客,不是应当的吗?哟,说起来,我更不对,石先生是客,怎好坐下方呢?
耐劳穿的是西服,空了两只手在外面,他就互相搓了巴掌,表示出那踌躇的样子来,便笑道:若是这样的客气,我就不好奉陪了。
燕秋也向灿英笑道:你怎么这样些客套?坐下吧。
灿英觉得怎么这样些五个字里面,有点醋味,也就只好笑着,向耐劳道:从此大家不客气了,就请石先生开菜单子吧!
耐劳搓着手向燕秋道:我好开菜单子的吗?我不过是一位陪客罢了。
燕秋笑道:主人请你写,你就写;也许你不写,就不成其为陪客了。
石耐劳对于灿英的托付,那就不好怎样的违抗,再加上燕秋这一番言语,他更是推诿不得,这就笑道:我又不知道二位喜欢吃什么,怎样的下笔呢?
灿英笑道:这可怪了。难道杨女士喜欢吃什么东西,石先生不知道吗?
耐劳笑道:可不是!就是不知道。
他说着话,就到旁边茶几上,搬过了笔墨纸张,要来开菜单子。他这个印象给于灿英是非常的深刻。因为打这里起,灿英知道耐劳和燕秋的交情,并不怎样的深密。要不然,哪有燕秋喜欢吃什么东西,他都会不知道呢?在这种情形之下,这餐饭,大家都吃得很快活。
吃完了,恰好天气已经开晴了。于是三个人顺着马路边的人行路,一同走回旅馆去。到了旅馆门口的时候,燕秋想起来了:石耐劳必是来答复自己那句问话,可以到西北去的。其实他不答复也知道他决定会到西北去;因为他是在四个男友之中,首先表示愿意去的。不过自己已经说明了,非到一定的限期,事前不许答复。在男子面前,第一次订的信条,必须遵守着;要不然,自己就不能树立威信,如何能够约束人家呢?于是就向石耐劳笑道:还是请你明天来一趟吧。
这样一句无头无尾的话,灿英自然是莫名其妙。不过耐劳听着,就明白是拒绝自己提早回答的意思,自己也就不敢过于讨好。点着头答应道:好的。明天会了!
灿英站住了,踌躇一会子,笑道:天快出太阳了,我身上还穿着雨衣,那也是笑话。我不到旅馆去了,我们也改天见吧。
燕秋倒也以为她这话是对的,便笑着道:你一定要走,我也不强留你。改一天,我来邀你出去玩玩,和南京各处的名胜告别,因为以后相逢,就不知是哪年哪月的。
灿英道:好的,通电话来约定吧。
燕秋一面说着话,一面走着路,就走进旅馆去了。
灿英见石耐劳还站在前面,就笑道:密斯脱石!你搭公共汽车吗?
石耐劳笑道:不,我喜欢走路,我走了回去。
灿英已是走了过来,笑道:运动家总是令人钦佩的,第一就是精神好。
耐劳笑道:这也是各人的嗜好不同。
说着话,两人竟是并排走起来了。灿英道:对于石先生,我是久仰得很了。在运动会场上,我是看见过好几回的,现在居然认识了。
说着,将手上拿着的花举了一举道:还多谢你这个呢。
耐劳道:这太不成礼物了。不过表示一点敬意。
灿英望着他抿嘴微笑了一笑。耐劳道:今天叨扰了李女士在先,我觉得很有点冒昧,明日若是天晴,我来奉请;请李女士先指定一个地点,我也不约定多人,就请杨女士一个人作陪。
灿英笑道:虽然密斯脱石觉得非还礼不可,这也可以。但是何必这样的急?
耐劳道:固然是不必急,但是不久的时候,恐怕我要离开南京了,我想提前来请一请。
灿英听到,本来就想跟着问一句,离开南京到哪里去呢?转念一想,这何须问得,自然是到西北去。于是就点了两点头道:哦!原来如此。
两人只管说话,不觉就走到了街的尽头。灿英问道:我向右走了,密斯脱石呢?
耐劳恰是不曾加以考虑。便向左指着,说是走这边。灿英道:那么,再见吧。电话号码,就是你名片上的那个吗?
耐劳连说是的,于是二人告别。
耐劳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因为学校寄宿舍组织得很完全,他就住在寄宿舍里。他在这两天,也不知神经起了什么变化,只觉起坐不安,就不想上课,本来某个学校里产生一位运动员,至少是有十个荒疏功课的学生。石耐劳本人就是运动健将,根本上就不许有读书的工夫。学校当局,因为他是一位有名的运动员,给本校增加许多荣誉,就是他的成绩不好,勉强也算他及了格。因为如此,所以石耐劳虽是学地质的,他对于地质却是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自从昨天一口答应了燕秋,送她到西北去;以为抢了一个先,可以让燕秋明白,是对她最诚恳的一个;只要她有了好感,别人不见得有什么把握,自然也不愿千里迢迢去撞这个木钟。所以今天冒雨,还要到旅馆里去撞一下。不想无意之中,又遇到了一位李小姐;她虽没有燕秋那种健康之美,可是她另有一种流露在外的聪明,很讨人的欢喜。回家的时候,她伴着走了那样一大截路,也许是有心的。好在自己是要离开南京的人,不然,也许会引起一幕三角恋爱的趣事呢,他心里在无限的幻想之中,又加上了一重幻想,更是不想上课。回到寄宿舍里,就睡在被褥上,和了皮鞋,将两只腿架在铁床的栏干上面,只管这样的望了天花板出神,忘了一切。有时也拿一本书过来,两手捧着看;但是看不到三行,把书就放在胸脯上,又出神去了。虽是这出神的当中,大部分是关于杨燕秋的;然而小部分也不免关于李灿英的。他有了这样一种态度,于是在这日晚上,就得了灿英一个电话说:杨女士快要走了,在南京玩一天是一天,打算明天请她去游后湖。石先生不是说要请客吗,我想也不必。我请你吃了一顿饭,一天之后,就要回答吃一顿饭。现在樱桃上市了,那里有许多卖樱桃的,你就到后湖请我们吃顿樱桃吧。来不来呢?
耐劳只有感到请人吃樱桃不足以言还礼,自是连连的答应了来;同时还约定了,是明日下午一点钟。耐劳也就想着明天下午七点钟,是答复燕秋限期的时候了。我明天自下午一点钟起,就陪伴着她,无论是谁,若竞争答复得最早,这一着棋,那是不能更胜于我的了。他有他的思想,他也就有他的计划,自然他也有他的成绩。
到了次日,恰好是个大晴天;正午的太阳,尤其暖烘烘的。耐劳有件白府绸的翻领衬衫,备而未用,今天特意穿了起来。皮鞋当然是擦得雪亮,西服也换了一套浅灰色的。打开箱子,将家里汇来的用款,就分了一半揣在身上,然后坐了车子,直到玄武湖去。倒底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这样好的美景良辰,不肯辜负的人很多。因之一出城来,便是沿途停着各种车辆。不过这里的风景,倒并不因人多,就失去了它秀丽的气象。大雨之后,湖水涨得满满的,差不多和岸一般的平;只看那岸沿上的绿草,浸在水里面,这就有一种诗情画意。太阳照着这荡漾生光的湖水,人的眼光,似乎就另有一种变化,自然的精神就振兴起来。对湖的锺山,格外的绿了,两三高低不平的峰,斜立在湖的东南角上;于是一堆巍巍的苍绿影子,上齐着白云,下抵平白水。在水里的倒影子,还隐隐约约的看得出来,随着水浪,有些晃动。由山下向北走,恰好围了湖,是些小山冈子。靠山靠水,有几家茅屋在树影子里,半显半藏着,那简直是画图了。他一面赏鉴着湖光山色,一面向五洲公园里来。那青草地上,还是湿黏黏的。东一丛西一丛的竹子林里,也都抽着四五尺高的新笋子,表示出那雨后的情形来。可是那稍微干燥一些的地方,摆好了茶座,就是整群的人,在那里围绕着;其余那些树棵竹林子外的人行路,全是牵连不断的男女游人,乱哄哄的,没有个片段。石耐劳只和灿英约好了,在五洲公园里会面,究竟在什么地方等候,可没有确定。于是只好忙了这双眼睛,四处张望着;忙了这两条腿,在人缝里钻。
约莫有一小时之久,才听到身后有人轻轻的叫了一声密斯脱石,看时,正是李灿英。耐劳虽然满肚皮不耐烦,到了这时,却也不由得笑起来了。灿英道:我在进公园的路口上等着,以为你来了一定可以碰到的。不想你倒先进来了,白等了许久。密斯杨来了吗?
耐劳道:没有看到呀。没有和密斯李同来吗?
灿英道:我以为你一定会打电话通知她的,所以我没有去约会她。既然你没有给她电话,她哪里会知道?
耐劳心想这话就不符了;不是你和她约好了,才来通知我的吗?怎么你两人还没有接洽过呢?不过彼此还是初交,不便怎样的追问,只作罢了。灿英见他沉吟的样子,笑道:也许她会来的,我们先找个地方坐着谈谈吧。
男女同在一处,女子倒先约会着男子去谈话,这哪里有拒绝之理?自然笑嘻嘻的就答应着好好。顺着路转了两个弯,就到了一丛竹子边,离了水边不远的地方。那里正空着一张露椅,于是耐劳先掏出手绢来,拂了两拂椅子上的浮土,鞠着躬请灿英坐下。她坐下来,耐劳不敢冒昧的就跟着坐下来,站在椅子边,故意昂了头四面去看着,免得露出那踌躇的样子来。灿英这就看出他为难的样子来了,用手连连拍了凳子几下,便笑道:干嘛站着?坐下呀!
石耐劳回头看看,这才含着笑容坐了下来。他将头上的帽子取了下来,放在大腿上;但是刚放下,觉得不妥,又拿起来向头上戴着。灿英虽是和他并排坐着的,可是转过了眼睛珠子来,向他身上偷着睃了两下,看到他那手足无所措的样子,心里头已经索然了。这就搭讪着笑道:这后湖的天然风景,山是真山,湖是真湖,那是很好的。只可惜这里的人工建筑,不但没有伟大精神,而且简陋得一点艺术意味也没有。同这个湖和这个山,实在不相衬。
耐劳道:这是建都没有几年的关系,将来这公园当然要伟大起来。不过向远处看看,山光水色,也就值得留恋的了。
灿英笑道:密斯脱石快要到西北去,这就另有一番眼界了。
耐劳很惊讶的猛然掉转身来,向她问道:这件事我并没有决定,密斯李怎么会知道的呢?
灿英抿嘴微笑着。耐劳道:真的,走与不走,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呢。
灿英笑道:为什么倒没有决定呢?
她说着这话,可就回转身来向耐劳望着。耐劳低了头望着地上,同时用皮鞋尖在地上涂抹着字。在这一刹那,灿英很快的看了一眼她的手表,已经达到了三点半钟了,她不由暗中点了点头,便笑道:我很有划船的兴趣,不知密斯脱石喜不喜欢这个?
耐劳笑道: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的。密斯李有这个兴致,我们马上就去。
随着这个声音,灿英也就站立起来,自然的,随着这以后便是划船到湖心里去了。
一小时随着一小时的过去,他们是很快活,这也是南京的风景,有胜于西北千倍万倍。所以石耐劳只管贪着在湖里玩,却忘记答复燕秋的话,自有那一定的钟点;虽然不许在限期以前答复,可是也没有规定在限期以后答复。大概石耐劳是忽略了这一点,竞是安心在玄武湖里划船了。
那太平酒店里的杨燕秋,自到这天下午一点钟以后,就没有出门,料着那四位男友,今天七点钟前后,都会到旅馆里来。经过这一度肯定,迟则一个星期,快则三五天,就要动身了。在这个时候,不妨从从容容的,把事情来预先布置一下。她如此的想着,所以心里非常镇静。只等那几个侍卫来报到,那第一个报到的人当然可以决定,必是石耐劳,因为昨日那样大雨,距限期又是那样早,他还跑到旅馆里来,今天他会性子更急,也许下午三四点钟,他就来了。殊不料她所揣想的完全不对。到了下午七点钟,第一个却是伍健生来了;第二个是高一虹;费昌年虽来得最晚,却也没有过七点十分。自然,他们见了燕秋,都说决定了和她同路到西北去。燕秋心里,觉得石耐劳身体健康,彼此的感情似乎也比较的深一点,假使大家同路到西北去的话,少不得请他作一个队长。现在别人都来了,偏是他落后,以后倒不能太信任他了。她心里如此的想着,表面上却是很镇定的招呼来报到的这三个人,饮茶闲话。伍健生看了一看手表,就笑道:当杨女士给我们限期的时候,只说不能早过一定的时间,至于晚过一定的时间,大概是可以的;要不然各人的钟表,不能对得一秒不差,来着恰恰碰到那个时间,可是不容易。
高一虹笑道:我想,也不宜于太晚了吧!
燕秋一听他们的话音,就知道是对石耐劳而发;虽然想到他必定有了什么特别的原因,阻碍着不能来,可是表面上决不肯公然袒护他。就微笑道:虽然晚过一定的时间,没有规定多久,可是也不能太久了。因为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动身,哪个日子走,都得预定好了;若是加入的人太晚了,要变动我们整个的计划,那只好是拒绝了。
费昌年点点头道:我们有这些个人上路,也算是个法团吧。一个法团,应当有个大家遵守的规例,无论什么人,也不许违法。
燕秋道:这话很赞成,我一个女子,和四个青年男子要同走这样长的路程,也很希望有个约束大家的东西。等到石先生来了,我们就可以来先讨论这件事。
大家听她的话,总也不能因为石耐劳到得稍晚,就把他取消;那也只好暂时说些闲话,一切问题,都等了他来再谈。不过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来到这里的,在设想了两天一夜之久,各人少不得有些话说。现在忽然把这件事搁起来不谈,一时倒感到无话可说;然而当了女子之面,大家板起面孔来坐着,那也是要不得的。因之费昌年首先向身边的高一虹兜搭着说话,笑道:昨天那么大雨,想不到今日这样大晴。
这话因无聊而发问,又在想不到三个字里,把别人代答的话,也代答复了。这倒叫高一虹没什么可说的。他是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旁边一张茶几,上面叠了几张报,他就手摸了报,问道:你每日看的是那几份报呢?
他两个人这种谈话,已够无聊的。伍健生靠了桌子斜坐着,却拿了一匣火柴,在两手心里来回的颠换着。
燕秋看在眼里,再看手表,时间已经延迟到了九点。便皱了眉道:这可奇怪,石先生为什么不来?纵然他不到西北去了,也该给我们一个回信。现在我们不必等他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就可以提出来讨论。我们决定了,他来了也不能推翻。谁教他缺席的呢!
这三个人都有这种感觉,石耐劳和燕秋比较的是接近一点,现在他不遵守时间,正好借了这个机会,来给他一个打击。都一致赞成燕秋的提议,立刻讨论起程的事宜来。由九点钟讨论到十二点钟,大致都议妥了:自明天起,加紧准备。第三天的晚上,就坐北上车到徐州转陇海路西行。燕秋昼夜望回西北去,现在如愿以偿,自然十分高兴。虽然所希望最亲切的石耐劳,不曾到来,也就不怎样的介意了。不过她心里想着:到了第二日早上,石耐劳一定有个回信的。然而她这层预想,又是不曾料定。到了正午十一点钟,茶房送进一封快信来,下款正是石耐劳的名字。燕秋拿着信在手上,颠了两颠,她心里可就想着,他必定是有了什么障碍,来不及当面报告我,所以就写快信来说,内容一定是报告他不能亲来的苦衷,就由书面来答应我一定到西北去。她心里头这样想着,随手就来拆信。然而信的内容,又是第三次又出于她意料之外了。那信上说:
燕秋女士惠鉴:请你原谅我,我不得已而失信了。昨天下午两点钟,接到家里一封电报,说是家中有急事,叫我赶快回南通去。我家里双亲年老,得了这种电报,不由得心里不慌乱,所以我立刻就动身,来不及告辞。假如没有什么事,我一定赶回南京来。纵然女士已经渡江北上了,我也可以赶上去的。方寸已乱,有言不尽,谅之谅之。即祝努力!
石耐劳上
燕秋将信看了两遍,心想:这就难怪了,人家有电报叫了回去的。她不但对于这个电报没有什么疑问,而且还对伍健生等说:自己就是回西北去找家庭的,别人因了家庭暂时不能同行,那当然是可原谅了。
其余三位男友,见石耐劳已落选了,各人也是心里暗喜,不觉又添上一分精神。
到了第三日,是大家出发的日子,事前约好了,就在旅馆里齐集。因为燕秋说了,西北人民都过的是刻苦生活,这回大家前去,都要用朴素些的服装。要不然,不但这样长的路程,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一路引着人家来注意看着,自己也怪难为情的。大家听了她的话,三个男友都换上了青布短衣,黄斜纹短裤,连皮鞋也不穿,只换了布底球鞋。这只有高一虹不同,多加上了一副圆框眼镜了,也许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是学文学的了。燕秋为感谢他们起见,今天中午又备了一顿上等菜饭,请他们在旅馆里饱餐一顿。当吃饭的时候,四人共围了一张四方桌子坐定,四只玻璃杯子,斟满了深红色的葡萄酒。燕秋可就按住了桌沿,先站起来了。她穿了一件短袖子粗布短褂子,隐约在衣纹里透出她那丰润的肌肉来。她的美发,在脑后方面,虽然还有些弯曲波纹来,然而也就修剪得很短了。她抬起了那嫩藕似的手臂,举起那酒杯来,向在座的三位男友道:三位先生!蒙你们很大的牺牲,陪我到西北去,我这一分感激,也无从可以说起。这一顿饭,就算我先向各位道谢。第二呢,以后我们一路走着,当然是每日每餐,都要甘苦共尝。这一顿饭,也可以说是我们合作吃饭的开始,借了这杯酒,预祝我们前途顺利,大家干了吧!
她说毕,举起了杯子来,先就一口喝了个干净;其余三个人,看到这种样子,也就突然地站起来,谁也不谈什么话,举着杯子全都喝干了。燕秋笑道:许多要送行的朋友,我都支使着他们到浦口车站上去了。这点用意,就是为着我们要吃这顿痛快的饭,请吧!
她说着话,坐下去,首先扶起筷子来。她那杯酒抢着喝了下去,热气上冲,立刻两个红晕印到双颊上。只看她那双眼珠活动着,自然是很快活了。这三位青年,自然也是以燕秋的态度为转移,大家都带上了笑容吃饭。燕秋笑道:今天今时,在出发的地方吃饭,四个人围着了一张方桌,吃得很痛快。可不知道我们最后合作的一餐,是在什么地方,又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情形。
对于情感问题,高一虹是最好讨论的,这又是他一个发挥的机会了。便笑道:所以古人登山览胜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发生了无限的感慨。离开了南京,杨女士总也算是离开了第二故乡,这一番感慨的话,那是应当有的。
费昌年和伍健生都腻厌他谈文学,不由得皱了眉,健生道:吃完了饭,我们就和杨女士收拾行李吧。外面雨还下得很大,不如早点上车站去。泥滑滑的匆匆忙忙过江,恐怕有些不便。
燕秋站起身来,开了窗户看看,不想一阵冷风,拥进细雨烟子,直飞到吃饭的桌上来。那黄色绸子的窗幔,被风吹着,只在屋顶下胡乱飞舞。同时就看到一个穿雨衣的人,帽子戴得很低,在对过马路上,有向这里偷看的意思。因窗子开着,他就走了。燕秋也来不及考量,连忙将窗户关闭笑道:这雨虽不大,来势可凶得很。
费昌年道:若不是事先宣布了,我们今天可以不走了。
燕秋正色道:那又不然,若是这一点斜风细雨,我们就要害怕;到了西北去,困难还正多,那如何前进?走!我就来收拾行李。
她说着把胸脯子一挺,就回房去收拾一切。本来也就收拾齐备的了,经她一提倡,这三位男友,都打起精神来,不到半小时,四个人的行李,都已运上了汽车。到这时,虽然有些留恋南京的意味,也不能不走了。他们另坐了一辆汽车,跟随着行李车到了渡口,呵!好一派风雨江景,只看江的东西两头,都让阴云重重的罩着,好像面前的大江是由阴云里面钻了出来,依然还流进阴云里面去。望对江浦口镇,那些新式建筑,如车站货仓之类,都大半让阴云笼罩住了。高一虹向那边指着道:再过三小时,我们就到那云雨之中去了。
燕秋笑笑,没有作声。
车子到了轮渡边,大家又少不得一阵纷乱,拥上轮渡码头去,远远就看到李灿英在码头船中间东张西望。燕秋直走到身边,她还不理会,燕秋将她衣服一扯道:你找谁呀?
灿英哟了一声,抓住她的手道:哟!你改成了一身布衣服。猛然间,倒看不出来了。
说时,看她身后三个同学,都穿了布衣服,就点点头微笑。燕秋挽了她的手,一同走上轮渡,因道:天气这样坏,为什么在码头上等我?
灿英道:我得了电话,知道你们快要来了,所以在这里等你。
燕秋道:谁打电话给你?
灿英顿了一下道:一个不相干的人。
说着挽了燕秋向船边走,笑道:到这里看看江景吧。西北哪有这个呢!
这时,那细雨如漫天漫地的烟雾一样,江面上稍微远一些的船只,就迷糊着看不见。江水扑了船边,拍打有声,江心里的水,时常翻着白花的浪头子。燕秋不觉失声道:好一幅江景!
灿英低声道:你不久还是回来吧。你舍得江南;和你同去的几个人,可舍不得江南呢!
燕秋笑道:我说了吧,那个像电影皇帝的人,不在我同行之内吧!可惜我没有机会,不然倒要和你作进一步的介绍呢。你不是很崇拜他吗?
灿英脸色红着,却说不出来,正是汽笛呜呜一声,轮渡要开,于是拉着她道:江心里冷,进舱去吧。
于是这个问题,也就始终含糊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