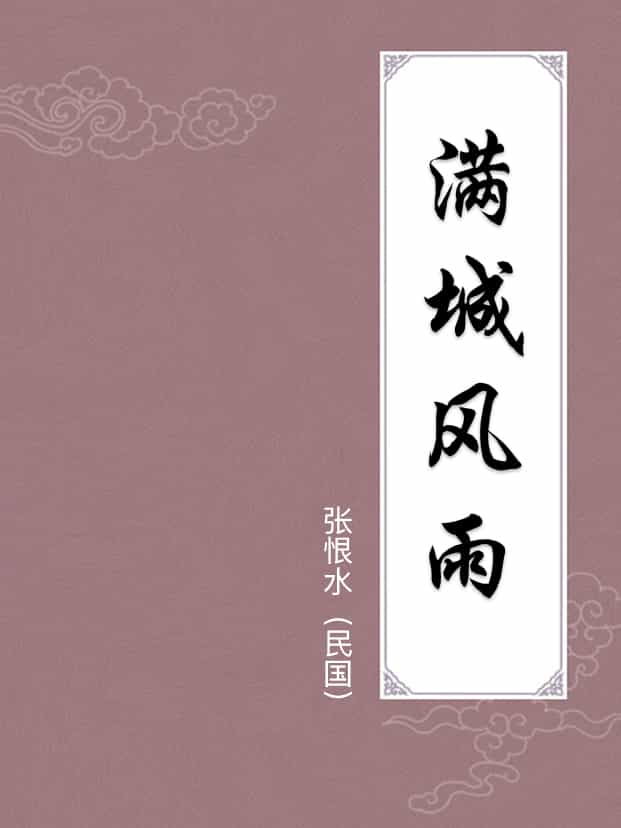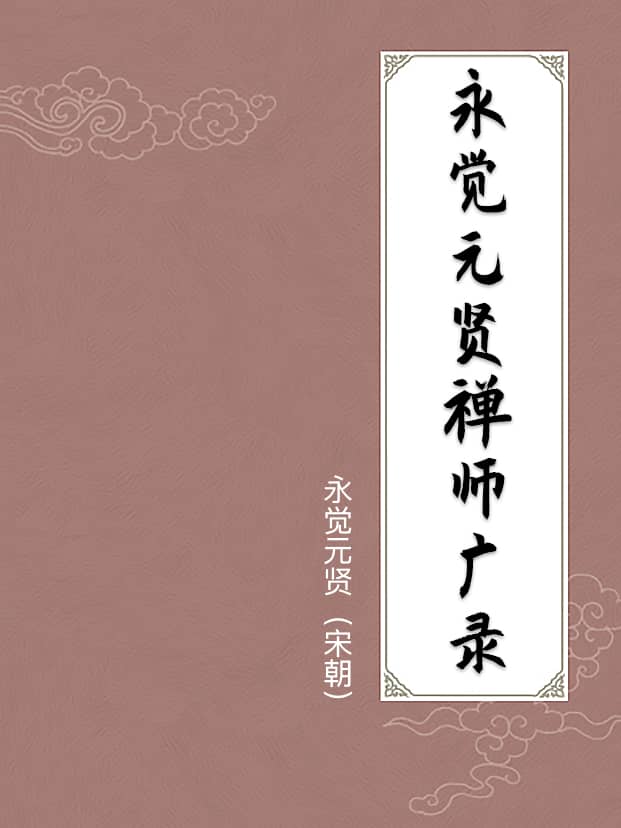却说伯坚正以收拾屋子下榻迎宾,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又很像交斗的样子,心里不免又添了一种疑阵。及至仔细听来,自己又为之失笑,原来是这巷子里的米坊在连夜用砻子磨稻,这种声音正是磨稻磨出来的声音。自己向来也不怕事,为什么今天处处疑神疑鬼?未免太胆小了。这样想着,就把晚上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当作幻想,不再去惊疑了,空屋子也不去再照耀,就坦然地睡觉了。
到了次日起来,刚一起床,只见李发笑了进来,拍手道:“没事了!街上已经照常有人走路,铺子也依旧做生意,这样看来我们昨日是虚惊了一场。
仲实也在窗外喊道:“怎么样?不是一点事没有吗?昨天看龙船看得好好的,那样把人拖回来,现在让我们好笑了。
伯坚对于他们这些话都不曾听到耳里,匆匆忙忙地洗过脸,连茶也不曾喝就走出大门,一直奔二叔子约的家来。一走到天井里,就听到子约在骂人,他道:“明知道大兵是不经过这穷州苦县的,我们自己着什么惊?好好地送三十六块钱给县太爷。我昨天该死!该大着胆子说让县里派人来抓我,我也不出钱。抗到今日,这钱就不守住了吗!
伯坚一听这话又是叔叔在痛财,便在天井里先咳嗽了两声。子约伸着头由窗子上冒出来望了望道:“伯坚吗?昨天晚上回去对你母亲说了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二位舅母,说是你母亲要接她们过去作客,他们都预备了。你打算接她们去过多少时候?
伯坚笑道:“只要二位舅母不嫌简慢,就多住些时。若是住不惯,当然也不敢强留。
子约听他如此说,就对他招了招手,让他到屋子里去,因低着声音道:“你千万不要说这种客气的话,在外面逃难的人保得住性命,就是千万之幸,有什么住不惯。再说你袁大舅家,向来也就过着苦日子,到我们这里来作客,至少也胜过他们家里生活。所以我就依照着你大舅的意思,饮食是家常的,不肯铺张。我就对你袁大舅说,亲戚就应该这样诚实招待,像家里人一样。就是将来我们有一天逃到你府上去的时候,我也只要你府上给我粗茶淡饭吃。袁大舅连点头说不错,你就照着我的话办,若是不然,你只管肥鸡大肉招待亲戚,这一笔账可不要写在我身上,我是不记你的情的。
伯坚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我既是自来接客去,只要客过得下去,粗茶淡饭也罢,肥鸡大肉也罢,我就老老实实说是请客完了,也不记袁大舅的账,也不记二叔的账。不怕二叔讲生意经,请客总是蚀本的事,因为请了客,客决不能照钱还给你,至多双倍三倍回礼而已。可吃的吃了,可玩地玩了,总是消耗的。若要不蚀本,最好不请客。
子约红了脸道:“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不过怕浪费了,逃难的亲戚过意不去。若是我不愿请客来,为什么你袁大舅一家人,不走东不走西,老老实实就到我家来呢?
伯坚本想再说两句,又怕二叔的脾气发了躁,真会不让二位舅母和表妹去,那就全盘计划都失败了。便笑道:“我也是说笑话,谁不知道二叔这番体恤亲戚的意思。我就是把二位舅母接去了,总也望宾主两方都过得去。因为总想二位舅母多住一些时候,若是待她们太好了,我怕她们不肯长住,倒反为不美了。
最后这一句话,子约听了倒很是适意,禁不住笑了起来道:“你这一句话,我倒是极端赞成。只要二位舅母愿意在你那里住,我也决不勉强去接了她回来的,这个你放心吧。
伯坚笑道:“这一层我倒是放心的。
于是跑进上房,在天井里就喊道:“两位舅母,我母亲打发我来接你过去住几天。
只说了一句,淑珍手上拿了一把带柄的长梳子梳着她的头发,一掀房门帘子伸出半截身子来。伯坚道:“表妹,请你也去,我母亲最想念你呢。
大舅母田氏在房里答道:“我们是刚刚起床。大先生来得真早,请在外面坐吧。淑珍,好在你不怕人,就陪表哥坐一会吧。
珍淑笑着出来道:“自从我到省里进了几个学校而后,大家就说我不怕人。其实这是他们自画供状,说自己怕人。女子也是一个人,为什么就应该怕人呢?我真有些不懂了。
伯坚笑道:“像表妹这样,在女学生里面已经是道学先生了,再要怕人,那恐怕要成了落伍的村学究了。
淑珍抿嘴一笑,回头又看了看内房,才道:“你以为我的思想不落伍吗?
伯坚笑道:“我觉得你这种态度倒为适中。
淑珍笑道:“适中是骑墙的变名,有什么好?你看我这衣服料子是时兴的,样子还脱不了家乡风味,这也不能不算是骑墙了。你看我穿这衣服到府上去,令慈喜欢不喜欢?
伯坚道:“穿衣服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问人家喜欢不喜欢?而且家母纵然爱管闲事,也不会管到客人的衣服上去。
淑珍道:“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做客的人总要得主人喜欢为是。况且……
这且字接不下去了,说着先笑了一笑,然后才接着道:“我在这边穿着,姑母就说了我好几回,说我是时髦姑娘了。那边伯母恐怕比我姑母还要守旧些。
……只说到这里,淑珍又微笑了一笑。伯坚道:“你放心。我母亲虽然学佛,是很慈祥的,对于我们,就是有什么话教训,也慢慢地说。
淑珍笑道:“表兄这话有点不合逻辑,伯母对于你们弟兄们的态度,怎能拿来对于亲戚作比?
伯坚一想,这话也是。顿了一顿,一想这话又默认不得,怕她更会起什么误会,便道:“怎么不合逻辑?这话很合逻辑的。你想,我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子都很好的,对于别人更是会好了。你若不信,可以去问我二婶,一定可以证实我这话。
淑珍笑道:“论逻辑,我是没有错的。因为儿子是自己生的,当然可以待他好些。至于亲戚,就疏一层了。
说到这里,淑珍的父亲袁学海,嘴里衔了一枝雪茄由后面出来了,那一股子冲人的烟臭,比他人还要先走过好几尺。原来学海是西平县一位讲维新的绅士,一切习惯都模仿省城中上等社会的样子。他看到省城里人不少抽雪茄的,因之也抽雪茄。但是这西平县交通比较的阻塞,物质文明可万万赶不上省城,他要抽雪茄只能买到十二个铜板一枝的粗烟。不要提气味不好闻,那颜色也就漆黑,远望去,倒好像他嘴里衔了一截圆墨。西平县抽雪茄的人不多,就有抽的也是这一路货色,所以并没有人说他抽烟不好。他到了亲戚家里,要表示他时髦,这雪茄更是刻不去口。他倒很喜欢伯坚,因为他是大学生,是个崭新人物。伯坚又不高谈学理,只是将就着他的程度说话,他极为合口胃。一听他在和淑珍说话,把他那件旧蓝纺绸长衫套在身上,背了两手慢慢踱了出来。一见伯坚,便笑道:“你们高谈逻辑,这个我也知道。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辞达而已矣
。伯坚知道他的主张,凡是西洋过来的东西,总是中国古来就有的,便笑了一笑。学海道:“你二叔除了做生意、存多少货、能赚多少利而外,别的是一切不管,这样时局严重的时候,连报也不订一份看看。我日前在报上看到,省里要办航空邮政,若是飞机由我们那里经过的话,当天可以看省里的日报了。西洋人的机器之学真是厉害,其实吾华固自有之。
说着将身子微微摆了一摆。伯坚一想,别的中国有罢了,找遍了四库各书,也没有飞机两个字的出典,这就不敢附和了。袁学海看他那种犹豫的情形,知道他是不相信的,便道:“墨子造木鸢,这个典我想你是知道的。这木鸢与飞机有什么分别?我想比飞机还活动些也未可定哩!
伯坚不料他找出飞机的典竟在二千年上,有凭有理,还有什么可驳的?含笑点头称是也就算了,便将话扯开道:“大舅,我今天一早来是奉有一点使命的,家母让我来请两位舅母,到舍下去住几天。
说着眼光转向了淑珍,然后又回转头来,对袁学海道:“大舅,表妹也可以去玩几天,家母很惦记她的。
淑珍听了这话,便低了头坐着,只管把脚悬起来前后摇撼着。那样子似乎甚是闲适,一点什么事都没有放在心里一样,但是眼光却斜着向她父亲射来,看她父亲是怎样地回答。袁学海道:“她当然是跟她两个母亲去。就是你不请她,她也未必在这里坐得住。
淑珍听了这话,倒噗嗤地一声笑了。
伯坚见大舅已经都答应了,这事就不成问题。因笑道:“我就先回去一步,好吩咐家里筹备欢迎的盛典
。说着,高声向屋子里叫着两声舅母务必要来,然后笑嘻嘻地出门去。刚走到大门口,却听到身后有脚步响,回头看时,淑珍来了。因笑着轻轻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吩咐吗?
淑珍笑道:“你太客气了,我怎么敢吩咐你呢。我不过有件事要求你罢了。
伯坚道:“你太客气了,你对我怎么说上要求二字呢。
淑珍笑道:“这倒好,我和你客气一句,马上就回我一句。
说着,站住了脚。用手理着头上的短发,向着伯坚微笑。伯坚道:“你‘要求’什么?就是要求我在门口站上一会子吗?
淑珍笑道:“不相干的一句话,我不说也罢。
伯坚道:“既是程度够用‘要求’两个字,这事一定不小,我希望你不客气说出来。
淑珍笑道:“这事是……总而言之是用不上‘客气’二字来形容的。
伯坚道:“那更好了,你说吧,什么事呢
?淑珍望着微笑,停了一停,才道:“我是说,到了府上以后希望你不要像在我姑丈家里一样。
伯坚道:“当然我是主人了,自然要客气一点的。
淑珍道:“错了,错了,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我到府上去了,你不要无事找着我说话。
这个“话
字一出口。马上一抽身就跑回上房去了。
伯坚望着她的后影痛快已极,不由得哈哈大笑。走上大街,见各家铺子都开了门,已是照常做生意。昨日县知事唐履本酷爱和平的布告,已经撕掉了一只角,旁边另贴了一张新布告。布告上说:
照得联合军兴,意在伐罪吊民。义旗高处一举,旬日连克数城。业于本月念日,大军行抵西平。本邑通省要道,原为水陆必经。义军前后过境,自当一律欢迎。所有攻克各处,义声早有所闻,都道秋毫无犯,所至鸡犬不惊。现接前方来电,大军不日抵城。统告绅商各界,准备盛大欢迎。切勿造谣生事,商务照常经营。特此预先布告,商民其各凛遵。
年月日安乐县知事唐履本
伯坚一看,心里也笑起来,昨日还说守土有责,今日就欢迎大军进城了。不过这样也好,县里不必打仗,大家只欢迎一阵就把这场虚惊揭了过去。我这也就可以安心去办我的事,不必一心牵两头了。一路想着到了家里,脸上兀自还有笑容。曾太太问道:“什么事你这样的好笑?我知道你到二叔家里去过,又是笑二叔守财奴了。
伯坚倒不料母亲会看出脸上的笑容来,就随便说了一句县知事的布告贴得颠倒可怪,含糊着答应过去了。于是马上告诉李发,找了本巷里面两个帮闲工的将三间空屋打扫干净;一面又拿出钱来,叫李发上街采办食物。自己还怕想得不周到,又去问她母亲还有些什么事要筹备。曾太太笑道:“你向来不愿管这些琐碎事情,不料你和两个舅母这样有缘。你自己舅父也来过,我不曾看过你这样殷勤招待。
伯坚笑道:“自己母舅住在本城,常常可以见面,当然用不着怎样客气。袁家母舅是老远避难来的,自然要招待得不同一点。
曾太太道:“你既是这样说,怎么把袁家大舅倒去了不请过来哩?
这一句话真把伯坚问倒了。便笑道:“大舅是个新书呆子,又带些官气,我怕请了来你老人家不大对劲,所以我没有请过来住。其实他倒不客气的,不请也会来啊。
曾太太觉得他说的话也有理,就不问了。
伯坚忙了一上午,一切的事情都办清楚了,这就只静等着客来。自己本来想去催请,又怕太着了痕迹,装着散步的样子,曾溜到大门外去了两次,向巷子口上两边望望看看来没有来。然而整整等到吃过午饭,何曾见三位客来!自己究竟按捺不住,又缓缓踱到巷子口来。刚刚走上大街,忽然一阵劈劈啪啪之声响了起来。在这样草木皆兵的时候,忽然听到这种声音,当然足够大吃一惊,但是虽有这种声音,街上的人都是行所无事地照样作生意买卖。这不能算是有军事了。正在这里犹豫,却见附近的店铺里都用竹竿子挑着一挂爆竹站在门口,有人手上拿了香火只等着燃放。那远处的爆竹声正也接连不断,由远而近缓缓传来。伯坚身边,是家小豆腐店,豆腐店的老板约莫有六七十岁,一嘴苍白的短胡楂子,现出那萎靡不振的样子来,手上也提了一挂短短的二百数的小爆竹,燃了一根香,站在店门台阶上。伯坚认得他的,便问道:“王老板,街上家家放爆竹,这是什么意思?
王老板四方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年月,不用讲理了。这是县警察局传下来的谕,说是联合军的第一师长进城,经过的大街上都要挂旗放爆竹。而且吩咐每家不许放短爆竹,越长越好。因为由军队过来起到军队过完了止,爆竹的声音不许断,哪个地方爆竹声音断了,回头就和哪家店铺算账。我是左右前后有几家大字号抬住了,和他们讲了一份人情,我点一挂双百子应应景儿也就算了。
伯坚心里有事,一切都未曾注意。这时才抬头一看,果然一条街上家家都高挂了国旗,有两家商店,还另外用大红纸写着欢迎联合军的大标语,临时贴在墙上。在这个当儿,街的那头爆竹响起来了,爆竹越响越紧,跟着军鼓军号之声也由那头送了过来。伯坚要看看这一份热闹,就不曾走,只站在巷口上看。一会儿左右前后的爆竹,一齐响了过来,那军队已随着军鼓军号走了过来。伯坚看时,那些兵士都是四个一排,便步走着。这个热天,那身上的灰色布制服白的是汗霜,黑的是粘土,不白不黑带着黄色的却是浮尘。兵士们的帽子也和衣服的颜色一样,在头上歪戴着,在歪的一边,还在帽子里夹着一块灰色布巾垂下挡住了半边脸,大概那是遮太阳的作用。前头的兵士身上都背了一根枪,也绕着两排子弹,枪是歪背着,连身上的制服,也一齐歪了过来。中间些的士兵也有制服,可是没有枪,各人身上背着一把大砍刀,最末一段的,有的灰色褂子便服裤子;有的灰色裤子便服褂子,有的灰色褂子、裤子都没有,只戴着一顶帽子。穿便服的倒舒服,将胸前的纽扣一齐敞了开来,枪自然是没有,刀也没有,这三种人一组,梯梯踏踏走了过去。后面又是三种人一组,在每组的前头,有人挺着一面大旗子,上书某团某营,知道这是一营人了。一营过去又继续着一营,人数大概也真是不少,不过驮着枪的兵士仅仅只有三分之一,真打起仗来倒不知道这不拿枪的兵却是怎样去应付。看那些兵时,他们倒很高兴,一面说笑,一面向前走。好在这一条街上的爆竹堆起来燃放,除爆竹声音以外别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他们在马路上走着,敞开来说话,并没有哪个听见。伯坚先是看那些兵士的全身,这时好奇心重,不觉看到他们的脚上去。在他们的脚上一看,又发现奇观了,有的穿了布鞋子,有的赤脚着了草鞋,有的还穿着布鞋子。走的时候,你上我下,那一路参差不齐的脚,看着也很有个意思。一直让这些兵士走完了,最后倒也有几匹马,一步一点头缓缓在后面跟着。有匹高大的马上坐着一个黑胖的军官,却也雄赳赳地左顾右盼。等着这军官过去了,最后面就是些长袍马褂,本县县城里各法团领袖。看到这里,已是无可再看了,正待抽身要走,人丛中走出一个人来一把将伯坚拖着,笑道:“好极了,我们这里面正差着一个学界的代表。
伯坚看时,乃是本县县农会会长何士干。因道:“哪里差着一个学界代表?说的是欢迎团体里面吗?我还有许多私事,恕我不能奉陪。
何士干道:“这个你谈什么奉陪不奉陪!又不是哪个人的私事,你若不陪,这话传出去了,人家可要说你对公益的事太不热心。你在本城也有财产,也有家族,就能说那句话吗?
说着,也不容他再分说拉了就跑。伯坚笑道。“我去就是了,大街上这么些个人,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
何士干笑道:“只要你肯去,我又何必拉?
说着,向伯坚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不过就是少穿一件马褂,好在要走舍下经过的,我可以和家里通知一声,叫他们拿一件马褂送到师长行馆里去,然后穿着我们一齐进去。
他们在一处走路的,也有本县商会长在内,他本是昨日到西平去劳军,在路上遇到这支吊民伐罪的军队的。这商会会长夏体仁,是个大肉胖子,他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外套着黑芝麻纱的大马褂,头上的汗珠子真有豌豆大小,一颗赶着一颗由头上乱流下来。他左手拿了一条大手巾,不住地在脸上扑汗,右手拿了自己的帽子当做扇子,只管在胸前乱扇。他一回头看见伯坚来了,就向他点着头道:“欢迎,欢迎。昨天我在屈狗桥遇到这位霍仁敏师长,把我们这番慰劳的意思一说,他就欢喜极了,当时就留着我在一处吃饭,他再三地说他的军队纪律很好的,这次到了我们县里,不过是经过而已,只要我们对于差事敷衍得过去,保可平安无事。我想只要能平安无事,我们在招待上就客气一点这也无所谓,你看怎么样?
伯坚哪有功夫驳他们这些话,也就唯唯点头答应,一路说着话不知不觉到了师长外馆。这安乐县是个平常的县分,哪有大地方给师长作外馆?只有县里的文庙和庙旁附设的小学随时可以借用。本来这里唐知事一接到师长必来的消息,已经派人告诉这里的小学校校长立刻停课,把学校各处房屋一齐腾出来。这个小学校校长,是一个科举出身的人才,抱着那鸟兽不可与同群的态度,早就先愿躲开,自己只吩咐了办事人腾房子,他已不知所之了。这时霍仁敏到了小学里下马,立刻派了四名卫兵在大门口站看守卫。县里十几名代表原是附骥尾一同进去的,霍师长传下命令,他要换衣服,请各位在外面稍候,不必先进去。于是大家也就只好在大门口走檐下立着候等。原来大家想着,换一换衣服要不了多少时候,不料等了又等,那位霍师长还不曾传见。这些法团的代表,费了一番力量把人欢迎进来,总应该说几句话才可以回家,若是不辞而别,到外面去说起来,既然是没有面子,而且也怕霍师长要见怪。因此大家依然在走檐下静等。别人还罢了,惟有伯坚是加倍地焦急:“今天把两个舅母和表妹好容易请动了,偏是客到门自己又不在家,不知道家里怎样安顿这三位客。若是把表妹安顿在母亲一处住,那阿弥陀佛的声音一定会把表妹腻死,甚至为了这事引起表妹的疑问,也在不可知之列,真就铸成大错了。
心里想着,自己背了两只手就只管在走檐下来回地走着。夏体仁手上捏着揩汗的那条手绢,已经成为水洗的一样了,他还是不住地揩着,望了伯坚苦笑道:“曾先生,你不要急,不多大一会儿师长就会传见的。
伯坚道:“对不住,我要先走一步了。我本不是代表,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何必跟在一处作陪客?
夏体仁连摇着手说不行,何士干更走上前两手一伸,拦住了他的去路,笑道:“不久霍师长就会见我们的,你和他谈两句也不坏。你当过代表,见过一个带上万军队的师长,这很有面子,将来你就是在学生会说话,也比较的有力量些。
伯坚听了这话,恨不得手起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转身一想,原是自己不好,明知道这班东西做不出好事来的,为什么随便地来当代表?于是也不去驳何士干的话,只当是迎着风吹过,特意走到天井中间去。一看大门外,站着几个凶焰逼人的卫队,也不敢一人乱闯,怕引出是非来。其他的人,为了是见师长来的,自然也不敢走。由日中一直等到太阳落山,大门外又是震天动地的一阵爆竹响,接上就有许多民伕一人一挑两人一抬,搬着许多东西向里面而去。伯坚看那挑抬的东西,有的是酒,有的是肉,约莫二三十挑抬。夏体仁用帽子当了扇子在胸前连连扇了几扇,身子一摆,表现出他那种得意的样子来。因笑着向伯坚道:“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是我们各法团办的一点酒肉,慰劳霍师长卫队的,也无非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意。我想霍师长念着交情的话,必定要把我们叫进去多谢两句。那末,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就可以说几句话了。
何上干道:“其实霍师长本人倒很谦逊,和我们见过一回面,居然就像很熟的朋友样,就是不送礼、不劳军,我们这样爆竹喧天欢迎他,他也很应当谢我们的。
伯坚正想着,他们也不过和姓霍的见了一面,何以交情就深到这样?既是成了朋友了,霍师长就该让这些代表见面了。这时,有一个马弁雄赳赳地由里面出来问道:“哪些人是当代表见师长的?
夏体仁两手捧了帽子向着那马弁拱了拱手道:“兄弟是这县里的商会会长。师长在哪里接见我们。
那马弁且不答应他的话,对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微笑道:“哦,你是商会会长?
夏体仁又抱着帽子拱了手,笑嘻嘻地道:“是兄弟,是兄弟。
那马弁突然将脸一变,喝道:“你是商会会长,你办的好事!你挑来的肉一大半是臭的,酒也不大好,好像掺了水的。师长说,你们简直胡闹!不念你们是这县里的绅士,还有差事交给你们办,那就要把你们押起来。师长在洗脚,没有工夫见你们,有什么要对你们说时,自然会传见。滚吧!
这一下子,不但夏体仁下不了台,就是跟着他来当代表的人都羞得无地自容,面面相觑,作声不得。那县知事唐履本,这时也长衫马褂,由里面走出来向夏体仁微微点了一点头道:“这件事,你交给哪个承手办的?实在不大高明。幸而师长是个宽怀大量的人,要不然……
说着摆了几摆头,好像说出来就骇人听闻似的。伯坚虽然觉得他们可恶,然而自己是急于要回家的人,趁了这个机会正好还家,也不待夏体仁再说什么,便道:“这很好,我们也急于要回家去呢。
掉转身子一个人先走了。
一路走回家的时候,街上又变了一个样子,三三两两满街都是兵,家家铺子里也都是兵。看看那些店里的伙计,一个个满脸堆笑来,口里不绝声地叫老总。再看店门前悬的欢迎旗子,门口柱上贴的欢迎标语,一茬茬都在那里,这也就不容商人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且这些兵脸上都带着一层蛮横的样子,碰了他就是祸,因此远远地就离开着他们,一路都不敢正眼看他们一眼。一直到了自己巷子口方才向前望着,只见那王老板豆腐店里,也站着三个兵在那里纠缠。王老板又发了那老毛病,只管将左手在右手背上擦痒,一个兵骂道:“你换不换?你若不换,把你这老杂种的豆腐架子给你拆了,你妈的!
王老板比着两只光拳头连作了两个揖道:“三位老总,你要吃豆腐干随便就拿了去,我们这小店哪里能作换银钱的生意。
一个兵砰的一声,跟着一条矮凳向旁边一滚,那个兵骂道:“我不看你上几岁年纪,我一脚踢你妈的回老家去!哪个管你开银钱店不开银钱店!老子身上的军用票用不开来,要你兑换两张。也不算什么,你说你家里没有现钱,你能让老子搜一搜吗?
两个兵都骂了王老板一阵了,旁边还有一个兵。伸手一摸豆腐榨上的一根长梁,向着王老板瞪了大眼睛,那样子似乎就要动手。伯坚在一边看到,一想王老头子若再强顶,马上就要吃亏。只得连忙跑上前叫道:“王老板,你这人也太执拗,几位老总和你换点零钱用,你就换给他好了。
一面说着向前走,一面在那三个大兵后面挤眼睛,又道:“你若是店里没有零钱,我这里给你先垫上也不要紧。
那几个兵翻了眼睛向他望着,本有些不满意,然而他说是来垫钱的,也就不便怎样为难他,都等着看他怎样发落。伯坚道:“哪位老总要换钱呢?
一个兵道:“我们都换!
于是一人拿出一张一元的军用票来,伯坚接过一看,这种军用票不但没有经手用过,而且也没有听见说过。原来就是一张白纸,很简单地四周印了些花纹,花纹正中两面旗子交叉掩护着一尊大炮,炮两边印着两个圈圈,各套着一元两个大字,炮头上一条横格,框着联合军军用票六个字,就凭这个,军队到哪里,就用到哪里。人家怎敢花?伯坚正自看着,一个兵道:“你看什么!这票子还有假吗?我们都是拿性命换来的钱,我们在满街大铺子里都买了东西,哪个敢说不要!你这小豆腐店,我们没有什么可买的,一个人只要你换一块零钱用你还有什么不愿意?
伯坚道:“我这里有三块现洋,和三位老总掉一掉,行不行?零钱可没有。
三个兵听了这话,彼此望着一笑,虽然眼锋之中还露着凶焰,然而那两腮上已不是先前那样铁板制的一般了。一个兵道:“他奶奶的,有现洋还怕换不出零钱来吗?你拿来我们就走。
伯坚见街上的兵正不断地走来走去,连忙掏了三块钱交给三个兵,他们笑嘻嘻地走了。伯坚道:“王老板,你今天还打算做什么生意,赶快上店门吧!横竖太阳是落山了,你也不在乎多做一两个钟头的生意。
王老板听了,还自犹豫,早见附近店家已有几处上门了,于是也跟着上了门。伯坚也没有提那三块钱,揣着军用票回家了。
一进大门就连叫几声李发,李发一出来。便问道:“客都来了吗?屋子都安排好了没有?
李发道:“你不问的袁家舅太太吗?二老爷那边现在闹得一塌糊涂了,她们哪有闲功夫来作客!
伯坚道:“那边闹什么?我二叔和二婶又吵闹起来了吗?
李发道:“那倒不是,我听说今天满街都是大兵买东西,二老爷杂货铺里今天下午这大半天没有断过人,卖出去了七八百块钱东西。
伯坚微笑道:“好生意。
李发道:“好生意?要了命了!这些大兵买东西一律都是军用票,买了东西不算,拿一张五块的给你,买一块钱货,还要你找四块现钱给他。起初店里伙计们不敢不找,后来大兵来得多了,这样钱物两蚀的事如何受得起?同街商店一商量宁可把东西相送也不找钱。店里总算热闹了一下午,可不算做生意,只是办了一下午的兵差。
伯坚不等他说完,连忙将他衣服一扯,早听见大门口有人叫着“老板
。李发回头看时,是两个穿了灰色褂子没有穿灰色裤的兵。伯坚怕李发不会说话,就迎上前陪笑道:“二位老总,我们是住家的,不是店。
一个兵沉吟着道:“哦,这不是店。
又一个兵却横着眼道:“管他是店不是店,难道说米也没有吗?你是这里什么人?
说时向他瞪着黄色的眼睛,右手里拿了一根破烂的断皮带,叠成了一个长卷,在左手心里打着消遣。伯坚心想:“要说没有米,无此情理,要说有米,他一定有一种要求。
正自犹豫着,另一个兵就在身上掏出一张一元的军用票来,微笑道:“不管多少钱一升,请你通融两三升米给我,钱有多,你找一些铜板给我。
伯坚心里倒吃了一颗定心丸,充其量也不过是三升米而已。便拱了一拱手,笑道:“老总,你太客气,二三升米还要什么钱?四海之内都是朋友,这不算什么。李发,你把我们米缸里的米打三升来。
说着,回头向李发丢了一个眼色让他快去,于是又向兵笑着道:“二位用什么装米?
那个黄眼睛的兵道:“你为什么不要钱?你以为八大爷不讲理,白吃百姓的吗?
这一个兵也笑道:“不要钱那可不好,我们又没有交情。
伯坚道:“我刚才说了,四海之内皆是朋友。我已经说了奉送,决不能反悔,若要反悔,我这人太不够朋友了。二位没有什么公事,请到家里喝一杯茶去。
两个兵原只有一个兵板着脸,伯坚既这样的客气,那个板着脸的兵也就不好意思再板脸,只在手心上打着皮带。一会儿李发用木盆盛了三升米放在地上,那个黄眼睛的兵道:“好吧,既是相送,这个木盆索兴送给我们,要不然我们不能把三升米用手捧了回去。
伯坚心想,这两位瘟神早早送出去的好,那一只木盆也用不着爱惜了。便道:“小事小事,老总随便拿去就是了。
这两个兵无眼可挑,一个捧着木盆,一个唱了小调子,就同着走了。李发这一会子乖觉了,连忙关上了大门,因道:“就是这一台戏。你想我们二老爹的店里,今天闹一下午,那要吃多大的亏!二老爹听了这个信,先跑到店里看了一阵,既是心痛又没有法子,一生气就跑了回家去躺在账房里发哼。但是在家里哼着又不放心,二次又跑到店里去。在这店里看着,还是那种兵来兵去的情形,心痛不过,就晕过去了。在店里好容易把他救醒过来,那买卖又十分热闹,再让他看见不得了,大家就用一张藤椅子把二老爹抬了回去。我也是得了这信,跑去看的。你想,这个时候舅太太好意思过来吗。
伯坚想了一肚子的心事,以为进门就要开始来搬演,不料完全属于幻想,懊丧极了。这一天当了半天的代表,浑身是汗气,因之在家里洗了个澡,匆匆忙忙换了干净衣服,就打算到子约家里去。这时仲实由外面回来,特意到伯坚书房里来笑道:“代表当得痛快吗?我早就得着商会送来的消息了。这个样子,你还要到二叔那里去吗?淑珍表姐有一封信叫我带来,大概是请你不要去了。
他说着便在衣服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含笑交给了伯坚。伯坚只看那信封上的笔迹秀润,就知道是淑珍写的。便道:“不用看了,大概是说她今天不得来的意思。
仲实道:“我只知道替她带来而已,内容她是说些什么,我是不过问的。
说毕一笑而去。伯坚先掩上了门,然后才拆开信来看,那信道:
伯坚:
听说你今天被人拉着当代表去了。你今天原是要当代表,不过是打算招待一个极不平凡的人,可不是要招待那声威赫赫的要人哪。当你作代表的时候,一定是想到贵客临门,不知如何招待?怕怠慢了来宾。及至回得家来,不见有客,一定是大失所望的了。其实我们本打算来,后来听说满街是兵,接上姑丈又为钱急病了,我们不能不在这里侍候着,等他身体恢复。写信的时候,他已经能走路,能说话了,大概与健康无甚关系。我猜你是要来看令叔的,现在既然很平安,兵荒马乱,天色已晚,你可以不必出来。据商家说,这生意到了明天更不能做了,一定罢市不下店门,风潮恐怕更要闹大。我们并不拘什么形式,希望你明天也不要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伏维珍重。 淑珍
伯坚看了这封信就犹豫起来,还是去呢还是不去呢?不过今天晚上,街上的兵,纵然停止了,秩序上也会发生问题,好在自己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去和淑珍说,这就恭敬不如从命,今天晚上不要去吧。仲实一个在窗子外,忽然自言自语道:“天下人都是高脚烛台,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今天晚上明明街上有问题的,还有人要打算出去。
伯坚从屋子里笑了出来道:“哪个要出去?你在这里说我吗?
仲实望了他微笑道:“我看你那样子就很想出去,我要拦阻你,又怕你不高兴,所以自说一声。我以为侄子对于叔叔,倒不在乎这种形式上的恭敬,不去二叔也能原谅你至于表姐呢,好在有信给你了,当然不在乎你去不去的。
伯坚只笑着说一声“你胡说
,也就无可再说的了。其实仲实都这样解释清楚了,自己还要装着糊涂,也不好意思。在这晚依旧忍耐着一晚,到了次日一早起来,李发便道:“大先生,你今天不要上街了,满街的商家都关了门罢市,兵在街上抓夫。
伯坚道:“罢市我早知道了,在街上抓夫,还不至于吧?
李发道:“怎么不是!隔壁的张裁缝就被抓去了。他父亲看见要上去讲情,索兴把他父亲也抓去了,张裁缝的老婆正在家里哭哩。
伯坚听了这话,心上又加了一层烦闷。挨到吃了早饭,曾子约家里一个跛脚伙夫满头是汗捶着门跑了进来,敞着纽扣掀起一片衣襟,在头上不住地揩着,一进门便问道:“大先生,二先生哩?这事情可弄坏了!
伯坚一听这口音,心里就是一跳,由书房里跑出来道:“什么事?二老爷病不好吗?
伙夫道:“不是,我们隔壁那幢空房子让兵占了,有些兵简直从墙头上跳过来要柴要米,家里一些女眷都躲在柴房里,不敢出头。我是一个残疾,走出来也不怕拉夫,所以特意叫我来报个信。大先生不是当了代表吗,请大先生和他们官长去交涉一下,叫他们的大兵不要爬墙。
仲实在屋子里答道:“哪个人长了两个头,敢叫这些兵守规矩!这只有去找那个唐知事,叫他把兵差派好了,他们自然不用得爬墙。
伯坚背了两手,把一只脚在地上乱点着默然地低头想了许久,便道:“交涉虽然是无益,我总得去看一回,至少也要把女眷换一个安全的地方。
便问伙夫:“街上情形怎样?
伙夫道:“街上像过年一样,没有一家开门的,也没有人走路。我只走了一小截街,都是从小巷子里转过来的。
伯坚一顿脚道:“我决计去看看。仲实你在家里不要出去,母亲问起来,你就说我睡了。
他于是穿了一件夏布长衫,更换上一双白帆布皮鞋,故意装出一个读书学生样子来,纵然是让大兵碰得了,知道是个文弱书生,也决不会为难,因此放着胆子就跟了跛脚伙夫走出门来。
伙夫因为刚才由小巷里走来,并未曾遇到什么人,现在由这里回去自然是不要紧的。伯坚不以为意,伙夫也不以为意,两个人放开了脚步走。刚刚是转过自己家门口一截小巷,要进一个大巷街,对面来了七八个大兵,后面有穿长衣的,有穿短衣的,还有打赤膊的,有一大批人跟着他们走。伯坚一见,便知道这事不妙,连忙向后一缩。但是伯坚看见他们,他们也看到了伯坚,早跑过来了两个兵,当头一个麻子喝道:“他奶奶的,往哪里跑。
伯坚看他们背上都背了枪,腰上都挂了刺刀,若要逃走反为不妙,便停住了脚。麻子道:“走!跟我们当夫子去!你妈的,倒舒服,穿了这样白的皮鞋。
伯坚听他出口便伤人父母,恨不得伸手就给他一个巴掌,无如后面又跟上来四个兵,每人都托着枪在肩上,他拿下来就能放,如何敢和他抵抗,只得陪着笑道:“老总,我是个学生,一点力气没有,怎么能挑动?
麻子后面一个黑矮子兵,反过枪就用枪托在伯坚肩上横扫过来,伯坚将身子一闪,那一枪托便扫在跛子伙夫腰上,跛子哎哟一声,人就向地上一蹲。伯坚摇着手道:“不要打,不要打,我陪你去就是了。
那矮兵眼睛一斜,放出一阵狞笑来,骂道:“你奶奶的!我怕你不去!不去,我一下就送你归天。王老三,这小子他说是学生,把他绑在先生们一起吧。
那个王老三过来了,是个瘦而长的人,穿了一套宽大的军衣,人像一个木头衣架子一样,走起来浑身晃荡晃荡。他背上背了一把大砍刀,左手拿了一根鞭子,右手牵了一根粗索头,他一走过来,后面有七八个穿长衣的人跟着上,原来都是在这一根索子上犹如穿鱼腮一般拴了右胳膊。王老三走过来,将那鞭子向脑后衣领里横插了去,然后照样将伯坚右臂绑了。麻子用脚连踢了伙夫屁股两下,骂道:“你跟我站起来!你妈的不中用,一枪托就躺下了。
伙夫见那矮兵倒拿着枪,大有再打二下之意,两手扶了墙慢慢地站了起来。矮兵骂道:“你装死吗?那容易,老子赏你一刺刀。
麻子一摇手笑道:“不要把他弄死,我们还差人呢,回头到家里去交不了数。
矮兵听他这样说,横瞪了伙夫一眼,道:“便宜了你这小子。
伙夫哪里还敢俄延,死命地挣扎着站立定了,于是又有一个兵上前,将伙夫拴在另一串人上。麻子喝一声“走
,大家穿了巷子走去。原来这天满城的人都知道兵士在闯祸,都不敢出来,走了几条巷子只遇到一个上野毛厕的人,就在厕所门外拴了。及至走到大街上,家家商店关得铁紧,不见一个人影子,碰到了人,便是大兵和拉的夫。走了两条街,麻子喝道:“老子在街上放一把火,看你们这些杂种出来不出来!
矮子笑道:“怪不怪?我昨天到今天,满城找遍了,不看见一个女的,难道说都跑了?
王老三道:“班长,今天晚上,我们交了差,出来找找花姑娘吧。他妈的,两个月了没有捞着女人一根毛。
麻子笑道:“捞着一根毛又怎么样?给你妈的剔牙齿。我倒是饿得厉害,想肉吃,回头同找去。
王老三道:“不要提吃肉了,我昨天亲眼见的,这县商会里,挑了好几挑子肉送到师部里去,那是给卫队吃的,我们连骨头也没有。他祖奶奶的,我要遇见了那个商会会长,我要他交出老婆陪老子玩。
麻子笑道:“你这个色鬼,三句离不开娘们。
王老三道:“班长,你忘了在十里亭那件事吗?一个五十岁的,你还当了美人一样留着哩。
于是一群兵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旁若无人地在街上走着,把那些粗鄙又猥亵的言语充量地说着。伯坚听在耳里,心想:“这就是吊民伐罪的军队,救国救民的男儿?未免有点笑话了。可是全县城的商家,曾放了爆竹欢迎他们进城的,纵然受了他们的侮辱,又去怪谁!
心里正自这样想着,由冷巷里穿过去经过一道矮墙,墙里有一片操场,七八个穿学生制服的人围在一架秋千下谈话。麻子一见,便喊道:“你们看,这里不是人?一齐都绑上!有了这一批,我们就可以交差了。
只这一句话,早有三个兵背了枪就跳过墙去。操场上的学生见大兵来了,不知道什么事,就向屋里跑。三个兵早端了枪做出瞄准的样子,喝道:“不许动!哪个打算逃走,我就是一枪了!
那几个学生一看形势不妙,只得站住。那矮子又拿了一根绳子,向墙里一跳,连话也不和人说,就用索子绑起他们的手臂来。学生见前面三个端枪的兵,枪还不曾放下,已是吓呆了。有两个胆大些的,等到矮子兵上来绑手才问道:“我们在自己学堂操场上,犯了什么事?
矮子兵一伸手拍拍两下,一个人脸上打了一个耳刮子,骂道:“你妈的!老子要绑你,管你在什么地方!你不是瞎子,不看见墙外绑了那些人?我们是拉伕么!儿子们,你跟着我来,你要多一句嘴,老子舍不得花枪子,不打你,用刺刀扎你!
说着。牵了一个索头在前面走,一大串学生都只好忍着气跟着爬了墙出来。麻子一伸大拇指笑道:“你是好的,把这些狗养的打得比小羊还驯。
矮子道:“他们敢不驯吗?老子能要他的命!
伯坚自己被绑,都还罢了,见他们爬过墙去拉夫,欺人太甚,不由得心里心血沸腾。这些学生都是本城中学的青年,没有过十八岁的,文弱极了,让他们去当伕子,如何担任得起?一面随着几个兵走,一面就默想着要怎样脱他们于难。一路行来,已经到了县城隍庙,大兵将他们几串人一齐拴在戏台下柱子上,有二十几马匹和他们同等待遇,也拴在柱子上。地上除了马的草料而外,马屎成堆,马尿像沟水一般的四面流着。那一串学生,恰是拴着站在马尿里,伯坚所站所幸还是干地。然而太毒烈的太阳正在当头猛晒,受是受不了,躲又躲不开,只好将没有被绑的左手打开手上的扇子在头上遮住。看这庙里时,由大殿以至十八间地狱都躺满了兵士,院子中间太阳里面,却是些拉来的百姓,约莫有一二百人,荫凉地方站了拿枪的兵,在那里监视着。靠西边廊厅下,用砖砌了一路地灶,连乱柴和稻草向灶里乱塞,烟薰了半边天。那些碎草和碎柴遍地皆是,加上烧饭的冷热水就地浇泼,好好的石板地,糟得像阴沟一般。东边廊庑下乱哄哄的,全是起行坐卧的兵,伯坚看到心想:“凭这些东西,就能横行一时鱼肉人民,中国人民除了当兵的而外,真是一群驯羊了。
当他这样想着,不觉冷笑了一声。他这一笑不打紧,却听得有人喊道:“这个杂种,进来以后就是四处乱望,大概是间谍,拿去砍了!
伯坚一听,心里猛然一惊,也不免自危起来。
正是:
青天白日群魔舞,虎日孤身怎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