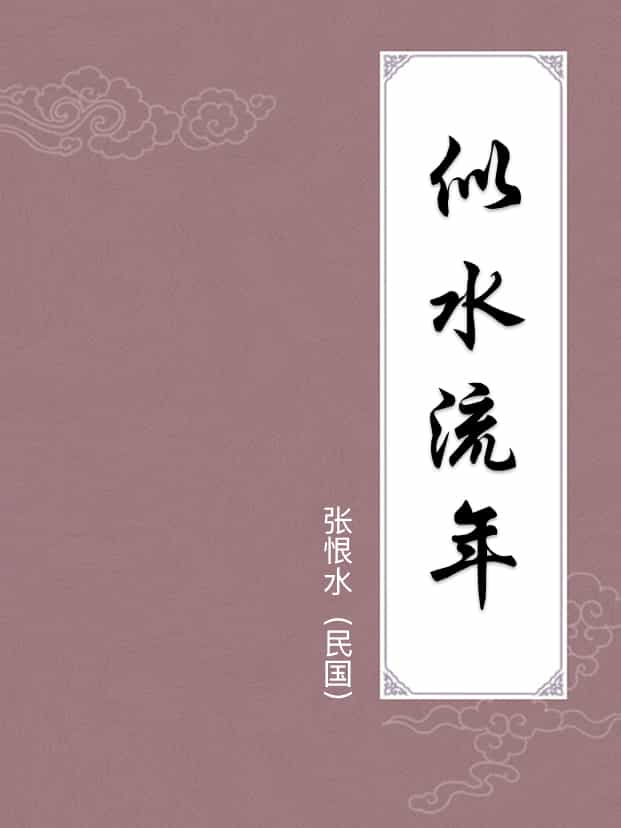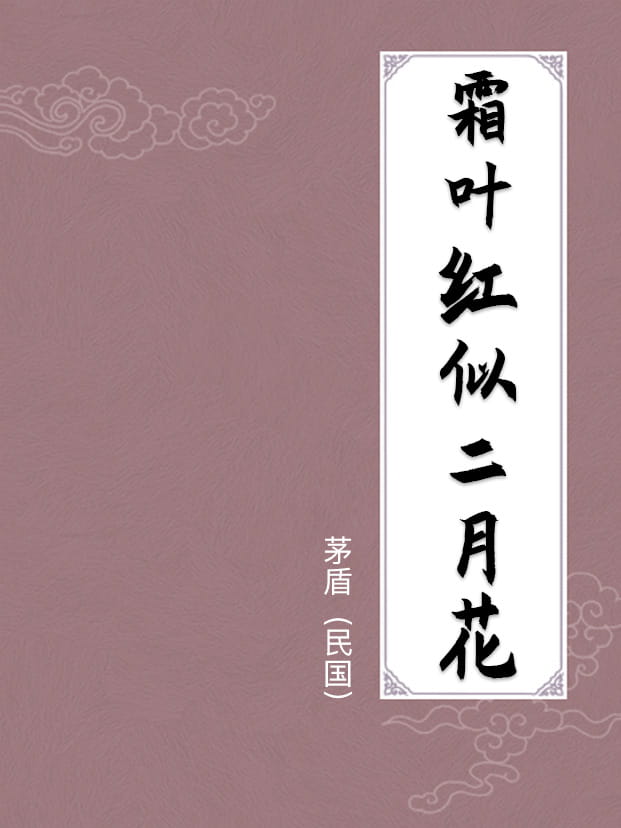这段事情现在应从马威从李子荣那里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师。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伊牧师顺着牛津大街往东走,虽然六十多了,他走得还是飞快。
从太阳一出来直到半夜,牛津大街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这条大街上的铺子,除了几个卖烟卷儿的,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的。她们走到这条街上,无论有什么急事,是不会在一分钟里往前挪两步的。铺子里摆着的花红柳绿的帽子,皮鞋,小手套,小提箱儿……都有一种特别的吸力,把她们的眼睛,身体,和灵魂一齐吸住。伊牧师的宗教上的尊严到了这条街上至少要减去百分之九十九:往前迈一大步,那支高而碍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伞上不可;往回一煞步,大皮鞋的底儿(他永远不安橡皮底儿)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脚指头上; 伸手一掏手巾,胳臂肘儿准放在妇人提着的小竹筐儿里,……。每次他由这条街走过,至少回家要换一件汗衫,两条手巾。至于“对不起”,“没留神”这路的话,起码总说百八十个的。
好容易挤过了牛津圈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了声“谢谢上帝!”脚底下更加了劲,一直往东走。汗珠子好象雪化了似的从雪白的鬓角儿往下流。
伊牧师虽然六十多岁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头发不多,可是全白了。没留胡子,腮上刮得晶亮;要是脸上没有褶儿,简直的象两块茶青色的磁砖。两只大眼睛,歇歇松松的安着一对小黄眼珠儿。眼睛上面挂着两条肉棱儿,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棱儿上也长过眉毛。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对小眼镜,因为鼻子过高的原故,眼镜和眼睛的距离足有二寸来的;所以从眼镜框儿上边看东西,比从眼镜中间看方便多了。嘴唇儿很薄,而且嘴犄角往下垂着一点。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可是平常见了人,他是非常的和蔼;传教师是非有两副面孔办不了事的。
到了博物院街,他往左拐了去。穿过陶灵吞大院,进了戈登胡同。
这一带胡同住着不少中国学生。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中国城有这样的好名誉,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的。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气。鸡贩子养鸡不见得他准爱鸡,英国人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又何尝是爱中国人呢。
戈登胡同门牌三十五号是温都寡妇的房子。房子不很大,三层小楼,一共不过七八间房。门外拦着一排绿栅栏。三层白石的台阶,刷得一钉点儿土也没有。一个小红漆门,门上的钢环子擦得晶光。一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客厅后面是一间小饭厅。从这间小饭厅绕过去,由楼梯下去,还有三间小房子。楼上只有三间屋子,临街一间,后面两间。
伊牧师离着这个小红门还老远,就把帽子摘下来了。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正了正领带,觉得身上一点缺点没有了,才轻轻的上了台阶。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才拿着音乐家在钢琴上试音的那个轻巧劲儿,在门环上敲了两三下。
一串细碎的脚步儿从楼上跑下来,跟着,门儿稍微开开一个缝儿,温都太太的脸露出一半儿来。
“伊牧师!近来好?”她把门开大了一点,伸出小白手,在伊牧师的手上轻轻的挨了一挨。
伊牧师随着她进去,把帽子和大氅挂在过道儿的衣架上,然后同她进了客厅。
小客厅里收拾得真叫干净爽利,连挂画的小铜钉子都象含着笑。屋子当中铺着一块长方儿的绿毯子,毯子上放着两个不十分大的卧椅。靠着窗户摆着一只小茶几,茶几上一个小三彩中国磁瓶,插着两朵小白玫瑰花。茶几两旁是两把橡木椅子,镶着绿绒的椅垫儿。里手的山墙前面摆着一架小钢琴,琴盖儿上放着两三张照像片儿。琴的前边放着一支小油漆凳儿。凳儿上卧着个白胖白胖的小狮子狗,见伊牧师进来,慌着忙着跳下来,摇头摆尾的在老牧师的腿中间乱蹦。顺着屋门的墙上挂着张油画,两旁配着一对小磁碟子。画儿底下一个小书架子,摆着些本诗集小说什么的。
温都寡妇坐在钢琴前面的小凳儿上,小白狗跳在她怀里,歪着头儿逗伊牧师。
伊牧师坐在卧椅上,把眼镜往上推了一推,开始夸奖小白狗。夸奖了好大半天,才慢慢的说到:
“温都太太,楼上的屋子还闲着吗?”
“可不是吗。”她一手抱着狗,一手把烟碟儿递给伊牧师。
“还想租人吗?”他一面装烟一面问。
“有合适的人才敢租。”她拿着尺寸这么回答。
“有两位朋友,急于找房。我确知道他们很可靠。”他从眼镜框儿上面瞅了她一眼,把“确”字说得特别的清楚有劲。他停顿了一会儿,把声音放低了些;鼻子周围还画出个要笑的圈儿,“两个中国人——”说到“中国”两个字,他的声音差不多将将儿的能叫她听见:“两个极老实的中国人。”
“中国人?”温都寡妇整着脸说。
“极老实的中国人!”他又重了一句,又偷偷的看了她一眼。
“对不——”
“我担保!有什么错儿朝我说!”他没等温都太太说完,赶紧把话接过来:“我实在没地方给他们找房去,温都太太,你得成全成全我!他们是父子爷儿俩,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看上帝的面上,你得——”伊牧师故意不再往下说,看看“看上帝的面上”到底发生什么效力不发。
“可是——”温都太太好象一点没把上帝搁在心上,脸上挂着一千多个不耐烦的样子。
伊牧师又没等她说完就插嘴:
“那怕多要他们一点房租呢!看他们不对路,撵他们搬家,我也就不再——”他觉得往下要说的话似乎和《圣经》的体裁不大相合,于是吸了一口烟,连烟带话一齐咽下去了。
“伊牧师!”温都太太站起来说:“你知道我的脾气:这条街的人们靠着租外国人发财的不少,差不多只剩我这一处,宁可少赚钱,不租外国人!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以自傲的!你为什么不到别处给他们找找房呢?”
“谁说没找呢!”伊牧师露着很为难的样子说:“陶灵吞大院,高威胡同,都挨着门问到了,房子全不合适。我就是看你的楼上三间小屋子正好,正够他们住的:两间作他们的卧房,一间作书房,多么好!”
“可是,牧师!”她从兜儿里掏出小手绢擦了擦嘴,其实满没有擦的必要:“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
“中国人不——”他正想说:“中国人不吃老鼠,”继而一想,这么一说是分明给她个小钉子碰,房子还能租到手吗?于是连忙改嘴:“我自然嘱咐他们别吃老鼠!温都太太,我也不耽误你的工夫了;这么说吧:租给他们一个礼拜,看他们不好,叫他们搬家。房租呢,你说多少是多少。旅馆他们住不起,不三不四的人家呢,我又不肯叫两个中国人跟他们打交道。咱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咱们总得受点屈,成全成全他们爷儿两个!”
温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的长毛,半天没言语。心里一个劲儿颠算: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想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又怕把伊牧师僵在那里,只好顺口支应着:
“他们也不抽鸦片?”
“不!不!”伊牧师连三并四的说。
她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把她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所得来的中国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问完了,心里又后悔了:这么问,岂不是明明的表示已经有意把房租给他们吗?
“谢谢你!温都太太!”伊牧师笑着说:“就这么办了!四镑十五个先令一个礼拜,管早晚饭!”
“不准他们用我的澡盆!”
“对!我告诉他们,出去洗澡。”
伊牧师说完,连小狗儿也没顾得再逗一逗,抓起帽子大氅就跑。跑到街上,找了个清静地方才低声的说:
“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