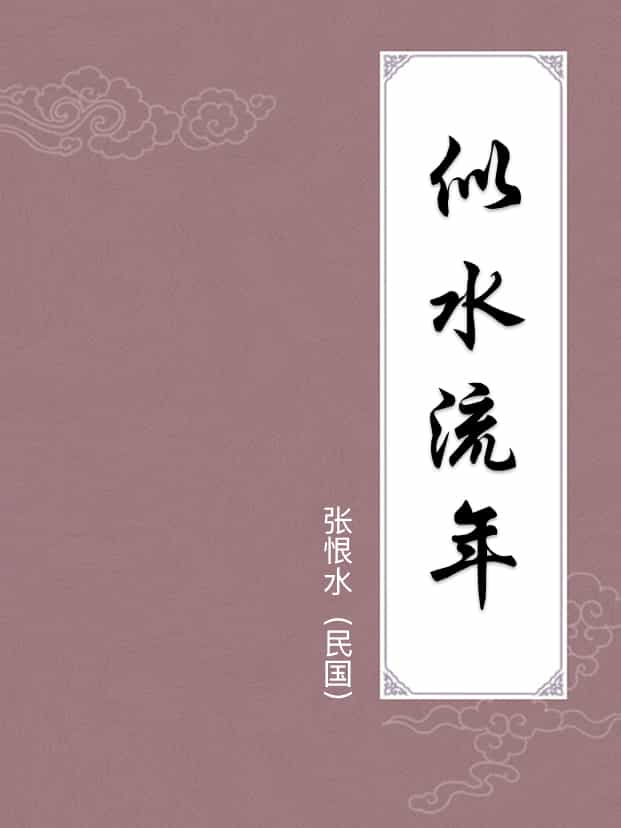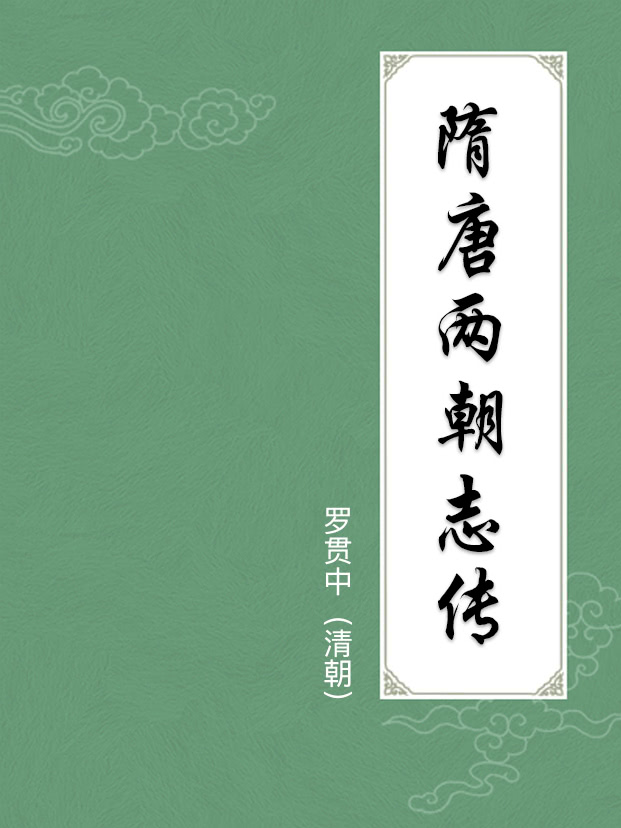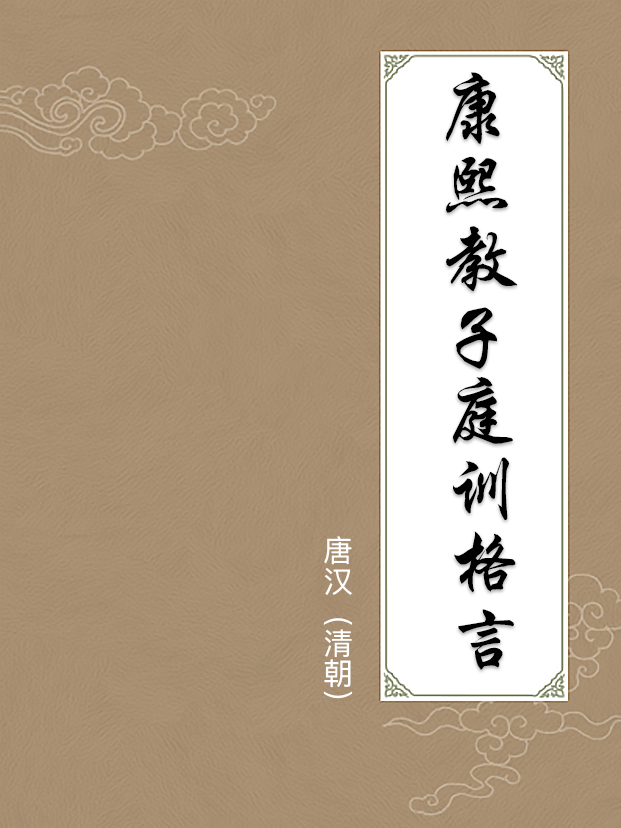却说惜时和行素只管讨论月亮,讨论得彼此有些意见不同起来,惜时却有些失望,看她的意思,赞成嫦娥碧海青天夜夜心,竟是愿意守独身主义的了。女子守独身主义,虽然是口头禅,然而对于交情浓厚、有了婚姻希望的,不应该这样表示,若是这样地表示,那简直就是拒绝婚姻的要求了。这样想着,惜时觉得是万分地兴味索然,站在行素身后,默然无语。
行素回转身来笑道:“你又在想什么呢?”惜时笑道:“我没有想什么?”行素道:“说着话,你突然不作声了,分明是有所感动,怎样说没有想什么呢?”惜时道:“我想是在想一件事,但是想入非非,不在本身问题以内了。我想男女婚配,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现在的女子都喜欢说守独身主义,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如此!若照这样说,天下的女子都守独身主义,这人种岂不要绝灭了。”行素道:“你何以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惜时顿了一顿,又笑了一笑,才道:“刚才你说嫦娥的生活好,可以站在一边看别人离别与团圆,那么,谁又该做离别与团圆给别人看的?”行素这才想起自己一句闲话,惜时多了心了,因笑道:“你这人真是到处多心!无论听到什么话,都有研究的价值了。”说完了这一句,行素连忙走开,就由柏树林子里走上了大路,踏着月色,一步一步地数着脚儿走一般。
惜时听她的口音,好像表示说:刚才是一句闲话,她的志愿并非如此。正要说两句,无奈她又走开了。于是也跟了走过来,在她身后笑道:“不错!我听话是很用心的,说话也是很用心的,不过我这个用心是特殊的,对于一个人如此而已罢了!设若你答的话也很用心的话,那就你有什么意思,只要微露出一点子来,我就知道了。反之,你若是随便地答复,那就很会引起我的误会的。设若你对于我论月亮一点,你用心答复的话,你却是怎样地说呢?”行素在前面慢慢地走,对于他所说的话,就像没有听到一样,只管抬着头看天上的月亮,惜时因她不说,这话也就不好向下追问,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我很恨我这一张嘴笨!有话也不会说。”行素这才答道:“你还不会说话,那天下就没有会说话的人了。一句很平常的话,我看你常是绕了极大的圈子说出来,而且说出来时,也很微妙的。”惜时笑道:“你这样地了解我说话的法子,何以又答非所问呢!”说着这话,已经由人迹稀少的地方走到人市繁密的地方来。而行素走的脚步很快,似乎全副精神都注意在走路上。惜时所说的话,又不能答复了。
走了一截路,行素就在路上的电灯下看了一看手表,故意失惊道:“说着话,不料就到了八点多钟,我要走了,我如晚些回去,对我们亲戚必要声明在先的。”说完了,又是很快地向前走。惜时好容易三弯九转地说着话,有点儿讨行素口风的机会了,不料她更是机灵,一点儿机会也不给人,故意随处闪避,使人话说不进去,只急得口里又吸气,又微微叹气。行素在前面走着,只急于要出公园回家去。
惜时眼望着她匆匆地走出大门,却没有法子再吐出胸中一个要吐的字。行素雇好了人力车,两足登上车去,笑着道了一声:“再见!”车子拉起,如飞地走了。惜时在门口呆站了一阵,也就回公寓去。他心里想着,在今日这种形势之下,她虽不能完全容纳我的要求,似乎也不明白拒绝,不过糊涂着说话,给我一个无结果。直言之,是没有到那种答复的程度而已。我想只要自己肯努力,绝没有不成功的。现在第一步,还是努力去增加彼此的友谊,将友谊增加到了一百度的时候,这爱情自然会随着增加,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懈怠的。至于她呢?据现在她的情形看起来,并不曾有个对手方,男子方面,友谊最厚的就只有我,当然我是婚姻第一候补者,我除了自己努力而外,还要设法,不让第二个候补的人产生才是道理。他这样地想着,便有些进步的计划。
恰是他在这晚,有计划进行的时候,邱九思和铁求新、卓新民回家很早,一见他屋子里灯放亮着,邱、铁二人口里咀嚼着口香糖,邱九思左手托了一小包五香瓜子,右手一粒一粒地钳着,只管向口里抛着,咯的一声,吐出瓜子壳来,接上又是一粒抛了进去。三个人那种逍遥自在的样子,笑嘻嘻地踱进了惜时的屋子,惜时笑道:“你们今天是茶围打完了呢,还是还没有出发?这样早就回来了。”邱九思笑道:“全不对!今天花光了,没有子儿了。前天发的快信,回家要钱去了,至早还要半个月才能到,这就得憋上半个月,真受不了。还是你好,进行恋爱,有钱固然是好,暂时无钱,也不受什么影响。”惜时笑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样说着,真有些侮辱女性。”邱九思道:“不管侮辱女性不侮辱女性,但是你能说和女朋友谈恋爱,可以不花钱吗?”
铁求新将口里的口香糖吐在手上,用指头抡成了一个小球,大拇指按着中指一弹,啪的一声,弹在棚顶上,笑道:“那位女士到我们公寓里也来过好几次了,我没眼福,始终没有看到是什么样子。”邱九思道:“你一提这话,我倒想起来了,老黄太岂有此理!早说了给我们介绍的,可事到如今,还没有实行。现在,你自己要确定一个日子!不然,你简直对不住我们这些朋友,我非罚你不可。”铁求新道:“还有一件事,你对不住朋友。我听到茶房说,三宝来过一趟,和他秘密地办了交涉,并没有告诉我们。”惜时红了脸道:“那是什么话?我要有什么坏心眼,不会找她去,何必……”
邱九思摇着手道:“不要紧!不要紧!她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秘密也好,公开也好,我管得着吗?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就是要你介绍女朋友和我们会面,别的我们不管。”惜时想了一想,才笑道:“关于这一层,我绝无成见,只是人家乐意不乐意,不得而知。你得让我先去征求了她的同意,再来答复,否则我答应了,她不答应,是徒然让我失信而已,那又何必?”邱九思道:“这话果然说得有理,不过在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你故意推诿的。”惜时道:“请你们给予我三天的限期!在三天之内,我总可以疏通成功。”卓新民口里衔着一片口香糖,有半片还垂在外面,就笑道:“这是当然可以的!最好是你请一次客,把你那女朋友的女朋友,再请上几个,于是乎也给我们一个求恋的机会。”他说话时,靠了惜时的书桌,脚一点,人竟坐在书桌子一个犄角上。
惜时看到他们这种浪漫的样子,实在有些不高兴,为着拘于面子,又不便怎样说得,就笑道:“你们也太高兴了,回公寓以后,自己的屋子都不曾进去,就在我这里闹起来,这不要说是穷,若是不穷的话,应该怎样办?非闹着把这屋子拆去不可了。”邱九思笑道:“别闹了!用功的先生有点儿讨厌我们了,我们走吧!”说着,大家哈哈一阵笑,拥出了房去。卓新民由桌子上跳下来,未免过于急速一点儿,把桌子摇撼着,一水孟子墨水倒泼了有一大半在外面,桌面上立刻画了一个墨水蜘蛛。他一回头说了一个英文单词“梭累”,笑着跑了。惜时望了这些人的后影子,不免连摇了两下头。这样一来,把他心里所拟的计划更坚决地要施行了。
次日上课以后,照例和行素同到小馆子里去吃饭,因对她道:“公寓里简直不能住了!不但里面声音庞杂,无法念书,而且几个朋友都是浪漫人物,让他们搅扰不堪,我还是搬到寄宿舍里来,躲开他们的好。”行素笑道:“我极赞成!省了走路的工夫,也可以多看一点儿书。”惜时笑道:“虽然是如此说,但是……”说着,就望了行素一望,行素道:“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惜时道:“怎么没有?我希望你也跟着搬到寄宿舍来,相距很近,有什么事商量,也很便当。”行素笑道:“别胡扯了!我们除了上课,还有什么事要商量,而且还要搬到就近来商量,未免笑话了。”惜时也笑道:“虽然没有什么商量,但我很愿意搬到一处来,至少的成绩,也可以增加些我们见面的机会,我的话实是说出来了,你看怎么样?若是不肯搬来的话……”说着便一笑,行素连忙问道:“不肯搬来便怎么样?”说时,嘴角掀动着,向了惜时微笑。惜时一时说不出理由来,便道:“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不过是加倍地失望罢了。”行素道:“我搬到寄宿舍里来,或者不搬到寄宿舍里来,这也是极小的一件事,我看你还是搬来的好。老实说,你那公寓里我也就不大愿去。”惜时只听她这口音,已经知道她的意思如何了,便笑着跳了起来道:“我今天看好房子,今天就搬,明天看好房子,明天就搬。”
他于是在吃过饭之后,首先就到邻近女寄宿舍的一个寄宿舍里去找房子。那里舍监说:“这里的屋子都是上一学期的学生就在这里住下的,开学以前已经就满满的了,现在哪里有呢?”惜时听说,颓然而返。因为自己知道离女寄宿舍远些的那个寄宿舍就空了三分之一的屋子。这边的设备还不如那边齐全,当然也是很空的,不料是适得其反。当时低了头走出那寄宿舍,无意思极了。
忽然后边有人道:“你要是找个好读书的地方,我倒是有个地方可以介绍。”惜时回头看时,是这边寄宿舍里的一个校役。因摇了一摇头道:“我不找公寓。”校役笑道:“绝对不是公寓,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就在这寄宿舍东边一点儿。正对了女生寄宿舍,你去看看,不赁也不要紧。”说着,他用手向一个洋式门面一指,惜时以为路既不远,跟了他去看看也好。
到了门口,一看墙上已经贴了一张红纸分租帖,上面写着有洋式楼面五间,电灯、电话、自来水共用。只这一看,便觉得用途过于浩繁,便无租赁之意,那校役一敲门,有房东出来了。听说是看房的,自让他们进去。惜时一看这房子,有两进已是有两家人家,只有旁边这个跨院,另盖着上下五间一字楼面,下层是房东自己用的,空了这楼面租人。惜时更是不愿和住家的人家在一处,便不打算上楼再看了。正在这犹豫的时候,那楼下房子门一开,却有两个学生装束的女子出来,只一闪,便闪到旁边屋子里去了。心想这倒不单调!可以多认识女朋友了。自己虽然不曾将这两个女子看得清楚,然而就那身材上看去,都不过是十七八岁,决计不错。
那校役在廊子外楼梯上点头,让他上楼,这就不肯再考量,自上楼来。到了楼上屋子里一看,却也收拾得干净,再出来在楼栏杆伏着,向外一看,这不得不惊为洋洋大观了。原来这里看去,不偏不倚,正看到女生寄宿舍第一个院子。那些女生进进出出,都离不开这里。若在栏杆上伏着一望,比赏鉴什么美术还要有趣了。到了这里,禁不住问了一声:“要多少钱一个月?”房东说:“楼房照规矩应租三块钱一间,加上电灯、电话、自来水,共要二十四块钱。你先生既是一个人,电灯和水都节省些,减租二十块钱吧!”
惜时想着,光是住房子,每月就花二十块钱!一个学生,未免耗费点儿了。他又犹豫着不能答复。那正院子里,却有个白胖的女郎向这边叫着:“密斯童!我姐姐请你过去玩哩!”于是这楼下的两位女郎答应了一声,翩若惊鸿地过去了。惜时看得清楚,便问房东道:“二十元不能再少吗?”房东道:“二十元不但不能少,还要你马上就付定钱。不然,也许下午就租出去了。我们租给你,就是因为你只一个人。”惜时现在不容犹豫了,马上掏出五块钱来,付了定钱。这一下子,觉得事情办得很痛快!只是家具少一点儿,五间房至少要空三间。这也不去管他,好在这一所大楼只有自己一个人住着,设若请朋友在这楼上谈话,那比在公寓里要强十倍了。
当日很高兴,回公寓去把行李收拾,算清账目,趁着邱九思他们不在家,便搬了过来。收拾行李的时候,点了一点箱子里的存款,还有四百多元,这足够新居布置的。因之索性花了一百多元,到了家具铺里置下了一些床凳桌椅,同时还买了些影印的书画。五个屋子,一间睡觉,一间看书,一间会客,忙了三天,布置妥当,在屋子里自己一看,也觉很妥了。
原来的意思,只要布置好了,就想引了行素来看一看这屋子,然后要她搬到女生寄宿舍去,自己的计划便成功了。但是到了第二天,自己这种主张就有点儿摇动。原来这楼下住的两位密斯童,不过是中等人才,尚无所谓。那正院里有个密斯高,就是那白胖女郎的姐姐,却太美了,她和对面寄宿舍的女生似乎有不少的朋友,时常来往。惜时第二日下午从外面回来,正好她在门口,她穿了一件黑绒的旗袍,配着水红的绸里,已经是颜色调和了,加上她是个丰秀的女子,那旗袍短小的袖子,露出两只粉团般手臂,可爱煞人。然而她的脸,正不是那样肥,恰是圆圆的、白白的,加上两块血晕,好看得如苹果一般。她的头发梳得溜光,只卷着发梢那一小截,配着白嫩的脖子,尤其妩媚。
他一看,似乎觉得比天天看熟了的白行素动人得多。而她因为加了一个孤身的院邻,一人住着五间屋子,这个学生也太挥霍一点儿,不免对于他多注意两眼。她这种注意,完全是出于好奇心,当然没有其他的作用。这一下子,可引起了惜时一股热情,莫非她对我有意了?由此下去,这情局更可以打开了。这样好的机会千万不可失去,也不要让这位密斯高看出了行藏。那个密斯白,暂时只要请她不要来,若是来了,她疑心我心有专属,就不会接着向我进行爱情了。女子们的嫉妒心是最大的,漫说我和白行素是形影很密切的,就是不密切,一个孤身的男子家里,有一个孤身的女子不断地往来,这一种关系还要问吗?因之,自这日起,在学校里遇到了行素,绝口不提搬家的事。
行素心里想着,这是我的不对了。他屡次试探着我的口气,我总是不即不离,最后他要搬家,希望我跟着一齐搬,我又给他大碰钉子。把他一头高兴完全压了下去,他怎样不恼!他之不肯提到搬家,一半固然是怕碰钉子,一半也是觉着屡次迁就,总得不到一个答复,这也未免太过于无味。这样说,完全是自己的不对,不能怪惜时的了。于是在下了课之后,故意迟迟不走,在课堂外等他出来,对他微笑道:“每次都是你提议一路去玩,我成了一个附议的,今天我也还你一个礼,我来提议,请你,不知道你可能赏光?”惜时的心目中现时虽另有所属,然而一见行素的面,也不知什么缘故,又不忍对她十分淡漠,依然放出以前殷勤的样子来,便笑道:“这实在是难得的事了!无论是什么地方,我一定奉陪。”
行素见他已欢喜了,不能再让他有什么失望之处,于是先约了他去看电影。看过电影之后,又请他吃晚饭。然而惜时和她谈话,说来说去,总不提到搬家的一件事。
到吃完了饭,惜时要分别回家了,行素才提到了搬家的事,便笑道:“你迁居以后,大概是很忙!怎么还没有让我去参观一下。今天已搬了三四天了,大概总已布置妥当,可以让我去看看吗?”惜时笑道:“我原是打算裱糊好了,东西安置齐了,然后再来请你。你既是要去,我很是欢迎,不过已经黑夜了,又要你绕这远的路,我心里很不过意。”
行素本来奇怪着他迁居以后何以不让自己前去,现在听他说的话又近于敷衍,这就不知道惜时有什么用意藏于其内了,勉强笑道:“晚上去拜贺新居,果然是有点儿不恭敬!等你布置好了,通知我一个信,我再来拜访吧!”
惜时见她说不去了,显系有些不满意。自己和行素向来是形影不离的人,今天忽然表示疏远起来,使她不明白自己的用意,心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当时听了行素的话,简直无可答复。望了行素,只是微笑,说不出所以然来。
行素道:“你的新居既是还要布置,你就回新居布置去吧!我过两天再去奉看吧!”惜时已是有话在先,说布置未曾就绪,这时人家不去,一定要人家去,有点儿前言不符后语,而且自己的屋子实在也布置好了,若一定要她去,更见得自己是撒谎,只得答道:“明后天一定请你过去!你什么时候搬呢?”行素道:“我吗?再说吧!”说着,便是一笑。她说了这句,不再提了,竟是告辞而去。惜时快快地回家,当晚很有些不安。
到了次日,恰好是个礼拜日,惜时偶然推开这楼后的窗子,这一下,不由他不惊奇一万分!原来同居那位密斯高的书房,恰好转了一个弯,倒转在这窗户的后面,她正开了窗子,吸收着新鲜空气,昂了头看看天上一样什么东西,出足了神。那一张可喜的面孔,不啻是整个儿送给楼上人来看。
惜时手扶了一扇窗子,也就一声不响,静静地赏鉴,不知如何受了一口冷风,情不自禁地却连打了两个喷嚏。对面的密斯高转过脸来一望,才知道有人偷看她。于是瞪了一眼,砰的一声将窗子关了。惜时只看到她关窗子,却没有看到她瞪眼,她虽关了窗子,只以为她是害臊,却不知道她是生气。因之对了窗外,还是呆呆地望着。站了许久,一点儿声息没有,也就算了。
他心里望着:这位密斯高,体格真是好,合了新美人的美的条件。设若她也会跳舞,露出那滚圆的手胳膊与大腿,那真可以令人销魂的了!加上她是那样对我注意,我一定可以认识她,进而为朋友的。本来自己很无聊的,拿了一本闲书,如此想着,就看不下去,就端了一张方凳子,也坐到窗边来。自己的脸一般地对着天空,装出那照样呼吸新鲜空气以及别有所思的神气。其实他的心却照在楼下对面那间书房,看她还有再来的机会。
过了一会儿,却听到楼下有一阵洞箫声,这不必猜,吹得这样悠扬婉转,一定是密斯高吹的。今天是星期日,她为什么不出去,莫不是为了我?她既为了我不出去,那么,这洞箫当然是故意吹给我听的。我这次不是完全虚想,因为我每次见着她,她都是这样对于我注意的。有时走过去,还回转头来望我呢!岂能说是无动于衷?我若是全副精神去应付她,她岂能不像白行素一样,和我要好吗?我这一所房子,挑得实在是太好了!打开后窗,可以看见女性,打开前窗,也可以看见女性。接近女性的机会是这样地多,总不难找着几个女友。
他一人想入非非地坐在窗子下,静等着那密斯高再出来。不料她的行动惜时竟没有猜着,已经换了衣服走到前院打电话了。他们这电话装在前面一个过堂里,大家共用的。这过堂恰在楼下的隔壁,打电话正可以听见。只听得密斯高道:“是密斯丁吗?今天天气很好,上公园去吧!有好些个同学去了呢!”
惜时听到,突然引起了注意。心想:她打电话,又是故意让我知道的吧!不然,何以这样大的声音呢!他自己觉得十分聪明地猜着了,连忙换了一套漂亮些的西服,头发上也刷了一些凡士林,加梳了一会儿。接着洗了一把冷水脸,在脸上搽了一层雪花膏。修饰好了,对着镜子照了两次。然后找了一条花绸手绢,向左边上口袋里一塞,提出手绢两只角,大有一只花蝴蝶其势翼然欲飞的样子。各样都预备好了,带上房门,正要下楼,但是在他踏下去两层楼梯之时,低头一看自己穿的皮鞋还未曾擦油,于是重新开了房门,涂上鞋油,找了一块布,使劲擦了一顿,将脚左右歪着仔细看了一看,见是十分光亮,这才放了心,带上门匆匆忙忙就下了楼。看到一辆干净的人力车,赶快说了一句“公园”,也不讲多少价钱,坐了车,就让车夫拉着走。
及至到了公园门口,丢了车钱就向里走,然而这时他倒自己不知所可了。密斯高只说是到公园里,究竟到公园里什么地方来,却是不知道。公园里地方很大,既不是一步便能相见,只好一人慢慢去寻找,好在她来了,不能点一个卯就走。到处留心,总也会把她们见着。这样想了,于是先顺着大路转了一个圈圈,大圈子转完了,又随着小道乱钻了一阵。然而自己的理想究竟不易成为事实。
转了许久,依然不能看到她,自己心里暗骂了一声惭愧!我这人未免太傻了,就她电话里一句邀朋友的话,我就追了来,知道她的朋友在电话里是否答应了她这个约会?设若她朋友不会答应,她自然也不会来的,那么,我这一趟算是空跑了。仔细一想,我这人真有几分冒失!于是顺脚所之,不觉踏到了一个菊花圃里,背了两手,顺着太阳地里列好的菊花盆景,一行一行地向前看去。这菊花最后一部分,有一架紫藤花,这时已是秋深,藤上的叶子只稀稀地留有一部分,让秋风吹着,微微发出响声,那半黄半红的颜色,带着这一点儿瑟瑟之音,这种寂凉的秋意,自然让人深深地感受着。
惜时偶然走近了一步,只见紫藤架下翩然有两个人影子一闪,接上还有微微的歌声传出,这分明是有女子在里面。自己若是直接上前的话,恐怕现出轻薄相来,要碰那女子的钉子。于是绕了半个大圈,老远地抄到紫藤架后面去。这一下子,却令惜时十二分地出于意料以外,原来那里果然有两个女子,她们都披了夹的斗篷,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米色,背着阳光,却在那里舞蹈。那轻质的斗篷,她们更用手胳膊鼓舞起来,真似两只蝴蝶,在花底下飘来飘去,这种好看的姿势,已经令人不得不注意。及至她们一抬头,看着她们的面孔时,原来一个是同院的密斯高,一个就是考学校的时候,踩了她一脚的那个可认为绝美的女子。自己一个旧倾倒和一个新倾倒的,陡然一时同见着,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遇。因之远远地站着,倒愣住了。
她们原以为这地方是没有人到的,一时高兴舞了起来,现在密斯高猛然一抬头,看到老远一个西服少年在那里站着,立刻停止了。那个漂亮女子也看见了,笑着向那花架子里一闪,也藏起来了。密斯高认得是同院的黄姓学生。想起在家里,他在楼上偷看的那回事,不由得远远地瞪了惜时一眼。
惜时一想:也许人家嫌来得冒昧,有点儿煞风景!这就不如闪开为妙。于是将两手插在衣袋里,只当是看花,慢慢地走了过去,由这里行步走上了大道,低头走着,心想:这真巧了,原来那个女子,是和密斯高认识的,她们既是朋友,少不得她也要到密斯高家里去拜访的,那么,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倒先知道我在这里了。这样一来,我不愁没有法子和她认识。心里想到这里,有些扬扬自得。
忽然在身边发现一种哧哧的笑声,抬头一看,她们正也由对面挽手而来,两人都把斗篷搭在手臂上,脸上微微地发着红晕,她们舞得香汗津津了。笑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同考场的女子。她一笑之后,见惜时望了她,连忙伏在密斯高的肩上,轻轻一推道:“走吧!”说完了这两个字,一阵脂粉香在空气里荡漾着。这种香气,虽不知道是哪一位女士所流传下来的,然而绝不出此两人。只在这香气芳馥之间,似乎她们并不是绝不可侵犯的。密斯高是同居的,不难慢慢看出她的为人。至于另一个女郎,她为人就极其和蔼。记得同考那一次,踩了她一脚,自己十分抱歉,她不但不见怪,反笑嘻嘻地说不要紧,这种人大概是长于交际的,只要有一点儿机会和她接近,彼此就可以成为朋友的。心里这样想着,不免低了头,只管向前走,走到了哪里,自己也并不知道。
忽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倒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却是同班学生余超人。他先笑道:“怎么你也是一个人逛公园,密斯白没有来吗?”惜时和同班的学生原还没有熟识,也不便去反问他一句,为什么要连带着密斯白?既不便说话,也就一笑而已。余超人笑道:“刚才我们的培大之花过去了!你看见没有?”惜时道:“哪个是培大之花?我不知道。”余超人笑道:“这是因为有了爱人,不注意校中男女问题的缘故。这几天,我们学校里,大家正起哄选举校花。昨天下午揭晓了,就是刚才过去的米锦华当了选。”惜时笑道:“你还是和我白说了。哪个是米锦华,我也不知道。”
余超人笑道:“你这人真枉说是培本大学的学生了!连密斯米都不认识!刚才过去的,有一个穿米色夹斗篷、烫头发的女士,你看见了没有?”惜时道:“哦!就是大家传说的米女士,果然不错!”余超人道:“你这个‘哦’字,大有惊讶之意,是何缘故?”惜时笑道:“说起来,我是有些惭愧!原来这次考进本校的时候,我和她同场,我不小心踏了她一脚,我当时很不过意,她倒先和我表示不要紧,因为这样,我对于她的印象很深!但是很奇怪,她既是我们的同学,何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
余超人道:“她是学音乐的,在分院上课,不是学校里有什么集会,她不上这边来的。可是现在她天天要到这边来了,我们学校里快要举行十周年纪念大会,女士们自然是首先所需要来点缀的。听说她除了团体音乐而外,还选了新剧和跳舞,这一回风头,她真要出了一个够了。”惜时道:“到纪念大会只有上十天了。这种筹备那如何来得及?”余超人道:“老生们已经练习半年了,还有什么不成?这次新戏里,就是破格加入这样一个新生,我们就看本校校花大显身手吧!你看,她又来了。”他低着声用手碰了惜时的肩膀,让他向前看,惜时向对面看去,果见米锦华来了。
这次她没有和密斯高同行,却是一人独步。惜时和余超人本站在人行路中间,看到米锦华来了,不约而同地向路边一闪,米锦华认识这两个青年,都是同学,以为人家和她谦让行礼,这也是同学的一种礼貌,未能置之不理,因之也就和他二人微笑着一点头。先时惜时感觉到在空气里荡漾的脂粉香,现在又闻到了,目视她姗姗而去。行走远了,香气犹自在空气里。
余超人也是抱有同感,先笑道:“我以为女子身上的东西,无论哪一部分都带些引诱的力量!尤其是这种香味,由鼻孔直钻到人的心眼里去,可惜我不是新生,我要是新生,为了精神上得着安慰起见,我要改入音乐系了。”他这本是一句笑话,惜时听了,心里倒是一动。心想他不能加入音乐系,我可能加入音乐系,虽然音乐学好了将来也不过当一个音乐教员,此外并无出路,然而自己家中有的是产业,并不靠着自己挣钱。本来音乐系的女生不少,真个如余超人说的话,有女子调剂情况,精神上可以得着无限的安慰。
在这几分钟之间,他读书的志向立刻就变换了。和余超人在公园里兜了一个圈子,便先回寓所。一上楼,就在后窗子里向后院里张望了一下,看看密斯高回来了没有。见那屋子窗户依然是双扉紧闭,这才收了心。又转念到音乐系的学生都是爱漂亮的。要打算和女生们接近,非有两套漂亮的西装不可。自己穿的一套西装是在省城里做的,样子不大好,而且料子也不高明,现在应该做两套新西装,料子也要最上等的,大概要一百六七十元方才够用。现在箱子里所有的钱,做衣服是够了,做过衣服之后,却怕不够零用钱。那么,还是写信回家去,让家里赶快寄几百块钱来,不要等钱快用光了再去要,那就有些来不及了。
心里一有了这个念头,马上就写了一封挂号信回家,信上无非说的是北京生活程度高,冬天又快来了,应该预备一点儿皮衣服,请父亲早早寄钱来;在寄钱的这几行字上,画了两道密圈。这封信写完了,自己觉得办了一件正常事。今天星期日,发挂号信的时间已过,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寄,自己还怕把这件事会忘了,又在星期一的日历上,注上了三个字,乃是“发家信”。把这一行字注明了,才放心将信放到抽屉里去。这一天晚上,似乎加倍地感到焦急,为着要安慰自己起见,就一人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自己计划着:看了电影回来,是十一点多钟,就可以睡觉。一觉醒来,便是次日早上,发完了信,就赶到学校里,去和教务长商量,将自己调到音乐系,只要他答应了,明天我就交学费,立刻在音乐系肄业。
他如此地算着,似乎是很容易,事更凑巧,当他在影院入座之时,偏偏那位培大之花和了几个女同学坐在前一排。惜时不必看她的脸色,只她那一件米色斗篷就十分认识。因之,将座位挪近一点儿,正靠着她后面。这一坐下来,首先所感到的便是那阵脂粉香气。记得在公园花下,人去香留,为之神往。现在彼此又遇着了,而且可以静着一处,为长时间地享受。若是和她成为朋友,这就更可享受不尽了。他只管把这香气来赏鉴着,银幕上的电影,倒成了似乎看到,似乎不看到,至于什么情节,更无所知。
半场电影完了,到了休息时间,满场的人都纷乱着,前排的人偶然一回头,看到了惜时,似乎有点儿认识,望了他一眼,惜时脸上虽不能有什么表示,心里十分欢喜,足见她已经是对我注意了,她脑子里有了我的印象,那么,我的计划更不会白费了。他想到此时,由虚无缥缈的观念一变而为乐观的事实,自是二十分高兴。也不知如何电影映完了,米锦华和那一班引人视线的人物都离开了座位,在人丛里挤着,惜时只迟一步,没有赶上,就分手了。他正有点儿懊悔不能跟到门口,听她雇车到哪里,但是偶然一低头,却看到一样东西,又引起他的兴致来了。要知此是何物,下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