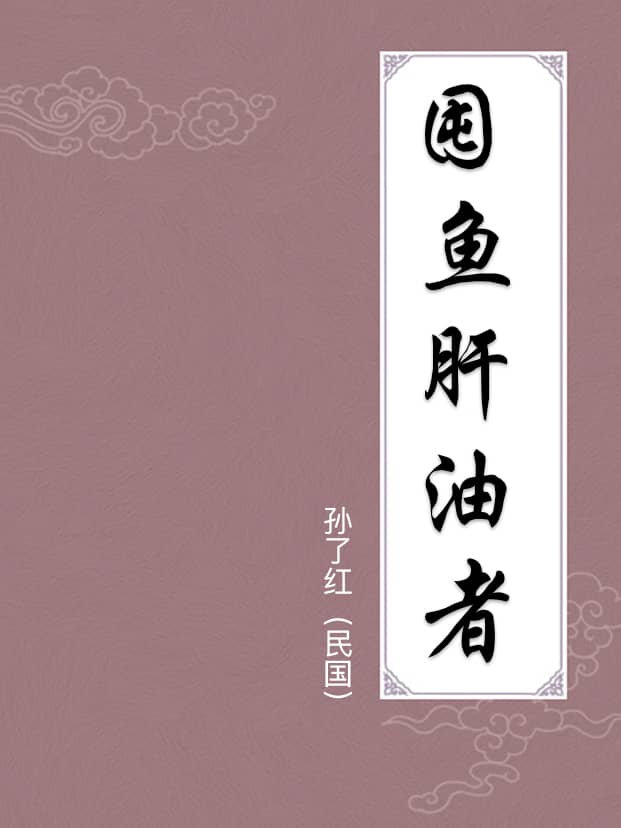据说是这样:一个素不害病的人,不害病则已,一旦害病,要比一般人更重。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是否有理。
而这一次,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却遭遇到了类如上述的事情。
这个故事中的主角,连名带姓,叫做余慰堂。
这里并不说他真的害什么病,而是记着他所遭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主角,一生所走的路,都是平坦顺利的路,从来不曾遇到一件事情,可以称为奇事。然而这一次,他竟遇到一件事情,比任何人所遇到的奇事还要奇。
你们曾在古书上,看到过那些借尸还魂之类的故事吗?
那些不很可信的故事,大半含着一些骇人的意味。根据传说:有些人在某种情形之下,自己的灵魂竟会走进另外一个躯壳而演出许多骇人听闻的奇事!这样的事,听听似乎不足凭信。然而,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他竟有这种经历。虽说那件事的背后,另有一种内幕,可是,单就开场时的情景而论,那已尽够加上神秘恐怖之类的字样了!
以下,就是我们的主角在某一夕中,他所亲身遭遇到的怪事件。
再看下去一二页,连你,也要感到非常奇怪了!
故事揭幕的时候,我们的主角,他正独自一个,在一条马路上面摇摇晃晃地走着。
那时候,他像喝醉了酒;他像在腾云驾雾;他又像坐着一叶孤舟,漂泊到了惊涛骇浪中。
奇怪的是,他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他不知道,他将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眼前他的身子,是在什么地点?他更不知道,凭什么理由,他要把他自己,带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点来?
总之,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而且,所做的梦,还是一个并不十分清楚的梦。如果这时候,有人向他注视,那一定可以看出:他的发直的眼光,不像一个平常人的眼光;他的走路的姿态,也分明带着一种梦游病的姿态。
那条马路好像很幽静;路边的行人道,平坦而宽阔。可是,在他疲软的脚下,却并不发生平坦的感觉。他像一个幼孩,在一张装着强度弹簧的长椅上面学走路。
记着,这故事的发生,是在时代开始动荡的时节。都市之夜不同于以前的情调。时代的晦暗,正自钻进每一个街角;街角的晦暗,也正自钻进每一颗人心。于是,在这一种晦暗的背景之下,却使我们这个晦暗的故事,更增加了一重晦暗的色彩。
天际有些稀疏的星;路上有些稀疏的人;街面有些稀疏的灯。路灯从道旁一排外国梧桐的树阴中,把惨淡的光线挤进来,却在平坦的行人道上,画了一些漆黑的剪影。
这时,我们的主角,就在这种黑沉沉的树影之下,拖着他的梦游的步子,像一个魅影那样,在扶墙摸壁地走过来。
劈面吹来一些风,微微的风把他已失去的记忆,恍恍惚惚唤起了一点。
不!比较妥当该这样说:被这微风一吹,让他恍恍惚惚,记起了一点梦中经过的片段。
他恍惚记起:不久以前,他好像曾从一辆汽车中走下来。至于那辆汽车是白牌?是黑牌?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这些,他竟完全不知道。
他又恍惚记起:在汽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曾经搀扶着他走了几步路。
至于那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这些,他也完全记忆不起。
如果那辆汽车正是自己的,那末,现在自己那辆汽车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那个搀扶自己的人,是个熟人,那末,现在那个人为什么把自己抛在这个地点呢?
以上的问题,他很想从头到底思索一下,但是,他竟绝对无从思索。稍微想一想,他觉得他的脑内,就像斧劈一样的痛。他还觉得他的耳边,一阵阵,像泼翻了一片海水那样在发响。
远处有些汽车的喇叭声在随风送过来。
听到汽车的喇叭,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汽车;因为想起了汽车,紧接使他想起:自己在这路上孤零零地走,到底他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四面看看,路灯是那样的暗。树影横在地下,显着一种可怕的幽悄。身前身后,“秃!秃!秃!”有些稀零的脚步声,送到耳边,使他引起异样的感觉。
每一个路人的影子,在他身旁闪过,都像憧憧的鬼影!
他开始觉得有些怕!
有一个意念紧接着害怕的感觉而走进他的脑海:“回去!”
抬眼看到对街正有一辆人力车,他不禁半意识地发喊:“黄包车!”
呼喊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不同于往常;——简直不像自己的声音。
正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忽然送来一个意外的语声:
“喂!不行!坐黄包车太危险!”
那个语声,好像发自他的身旁。但是,反顾身旁,却看不见有什么人。只有数码以外,有两个路人,站在另外一片树影下,悄然在谈话。那两个人,却不像在和自己打招呼。
也许这是错觉吧?他这样想。于是,他继续招呼着对街的车子。一辆空车向他身边奔过来。他刚待移动步子,踏上这辆空车。不料,在他身旁的树影之下,很轻捷地跳出一个人,竟抢先一步不讲价而跨上了那辆人力车。
他眼看第一辆车子很快地消逝。
由于他的嘶哑的呼喊,第二辆空车又从马路的另外一端迎候上来;但是,在那辆车子还没有走近之前,他的背后,另外又有第二个人,在向那个车夫尽力挥着手,意思不让那辆车子拉过来。
他并没有看到背后这个离奇的情形。
时候似乎已经不很早,那条幽悄悄的马路上,车子简直特别少。摇晃晃的身子,在行人道上呆立了片晌,结果,他并没有雇到一辆他所需要的人力车。
事情真的有些可怪,在这一个离奇的晚上,他不但失落了他的自备汽车,甚至,他连从来不屑一坐的人力车也坐不成。
周遭的情形,越看越像一个迷离的梦境!
而且,单身站在这种黑沉沉的梧桐树下,越看越有点怕!
现在,他似乎已开始发觉,在他身后,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追逼他;至于追逼他的那是什么东西?他却完全说不出来。
无可奈何,他只得重新拖着他的灌铅似的脚步,昏昏然,重新再向梦境一样的路途上走下去。
还好,走过来一点,四周的情形,似乎比较热闹了一点。两旁的店面,间有一些比较明亮的灯光,射进他的眼角。不过从一个不很光明的环境之中转入一个较明朗的地点,那是一种新的刺激。他努力眨眼,眼珠有点发痛。
头脑越弄越昏沉;身子越弄越疲倦;脚步越走越软弱;当前的事情,越弄越糊涂。
昏惘中的唯一的意念,他急于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至于其他的一切,他已绝对没有功夫再去管。
他把失却重心的身子,投入于那个比较光亮的所在。同时他的双手,却已摸在一些冷冰冰的东西上:那是一条擦得很亮的铜梗,一种玻璃窗外的装饰品。看这玻璃窗内,揭起着很漂亮的锦帷。在窗槛上,有些翠绿的植物,浮上他的眼膜。
高处有一条霓虹灯组成的横招牌,一排闪着光的玻璃字,在他昏眩的感觉中,却像卡通片上的五彩人,一个个都在摇晃,一个个都在跳舞。
第一眼中他看到如后一排大小不等的字样:
口力口口非食官
努力定神,他把缭乱的视线缚住了那些跳跃的字体,他方始看清,这是“咖啡馆”几个字。当然,在这三个字上,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字。
啊!这里是一家咖啡馆。他向自己报告。
脚步还只刚刚停下,就有一个很响亮的声气,像从半空飞下来,直飞进了他的耳朵,那个声音说:
“喂!站在这里做什么?进去坐一会不好吗?”
他慌忙掉过头来,看时,只见这家咖啡馆的门口,正有一个西装男子,在挽留另外一个人。呆怔了一下,他意识到那句飞来的话,并不是向他所说。
他不禁抬起迷惘的视线,向这西装男子看了一眼;同时那个西装男子却也有意无意向他回看了一眼。
他让那个意外飞来的建议提醒了他。他想:“好,就到这家咖啡馆里去坐一会。”
他以神经病者踏进疯人院的姿态,他摇晃地向那门口里走来。
一个孩子,穿着整洁的制服,恭敬地替他拉门;却把一种诧异的目光,投上了他的脸。
屋内和屋外,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音乐在响,器皿在发光,座客们在笑语;一些像凤凰那样美丽的女侍应生,穿着一式的服装,在柔和的灯影下,穿花一样在忙碌。
我们的主角余先生,平常,习惯出入于这大都市中的一些最豪华的所在。对于这种略带贵族化的娱乐处所,一向相当熟悉。但是,在他此刻的眼光里,一切的一切,都觉迷离而惝恍;一切一切,都觉缭乱而陌生。他像一个童话中的苦孩子,被推进了一座光怪陆离的魔宫。
他在一个离门不远的座位里面安放下他的身子。坐下去时,几乎碰翻那张轻巧的圆桌。
四周有许多异样的视线,从不同的角度里,陆续投集在他据坐的位子上;可是,他自己却丝毫没有觉察。
有一个女侍应生,蝴蝶那样翩然飞集于他的身前,以一种询问的目光凝注着他,意思问他:“需要什么?”这女子的眼珠睁得很大,好像在看一个银幕上的恐怖剧。
我们的主角,最初踏进这个地点,原意他只需要休息一下。由于这个女子的询问,他方始觉到嘴里干燥得很厉害,好像即刻刚从大沙漠里逃出来。于是,他模模糊糊随口说出了一些饮料的名目。实际,他在说过之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
女侍应生退下以后,他把他的疲惫而又刺促的眼球,茫茫然,看着四周的一切。他看出这一处装饰瑰丽的所在,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广厅。四角列着四支大方柱;柱的周围,镶嵌着晶莹的镜子。他的座位和其中一支方柱,距离得相当近。他的眼光,偶然落到镜面上,只见里面的人影,像是华德狄斯耐笔下的东西,花花绿绿地在旋转。多看一眼,就使他的眼球,格外增加眩晕的感觉。
不行!他赶快把视线收回来。
一大杯流汁,和一盆西点,托在一个银盘里面,送到了他的桌上。那个凤凰似的侍应生,放下了东西,却像逃遁一般,轻捷地旋转身子就走。一面,她还回眸向他偷看了一眼。
那个女子,走向她的一个同伴之前,轻轻说了些什么,立刻就有四条视线,远远投向他的坐处;这四条秀媚的视线之中,都在透露异样的神情。
我们余先生,他,当然不知道。
饮料来了,他惘惘然举起玻璃杯,狂饮了一口。他的手有点发颤,杯子里的流汁在晃荡,一只手不行,他用双手捧住这杯子。
喝了一口冷饮,心里感觉很畅快。因这冷饮的刺激,他的神志,好像清醒了一点。如果不是耳边的声音太嘈杂,他几乎快要找到他的已失去的经过;仿佛,他已屡次将要找到一些什么,但是,仿佛,屡次快要找到什么而一下子却又轻轻滑走了!哎!思想始终那样昏沉,头脑始终那样胀痛,耳边始终像泼翻潮水那样的响。
但虽如此,他终于迷迷糊糊,抓住了一些失去的记忆。
这时候,他的眼光,正自失神地停滞在对座一个啤酒瓶上。突然,有一个意念,轻轻闪进他的脑角;他像在无边黑暗的长空里,看到了一颗星。
他心里在喊:“瓶!”
不错,有一只瓶……有一只瓶……有一只瓶……有一只瓶,怎么样呢?
他苦苦思索下去。他再下意识地擎起那只玻璃杯,猛喝了一口冷饮。
他恍惚记起:在过去的时间中,好像他的手里,曾经拿到过一只什么瓶?……他好像曾在那只瓶里,嗅到过一种什么强烈的气味?……但,他却绝对思索不起,这是一件发生在什么时刻与什么地点的事。
那是梦里的事情吗?他自己迷惘地问。
不!那不像是梦里的事!他自己迷惘地回答。
但是,以后呢?——在捧着那只瓶,和嗅到那种气味之后,以后又怎样呢?
看着对面那只啤酒瓶,他的神思,不觉深入于他所失落的迷离的梦境之中。不料,过去的哑谜,还没有解决,眼前的奇事却已接踵而来。——而且,那些奇事,竟像穿在一根绳子上,简直成串而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他背后,忽然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而不十分严重地,在警戒他说:
“喂!你要留心呀!你——”
第一遍的声音他似乎并没有听到;即使听到他也决不以为这是向他说的话。可是,第二次的语声紧接着又在说:
“喂!听得没有?余先生,你要留心你的危险呀!”
那个突兀的声音,不但近得像是凑在他的耳边所说,而且,语声之中还清清楚楚指出他的姓。
他被那个声音猛然从迷离的思索中唤回。他不等那个声音歇绝,就愕然抬起他的视线。他向近身的一个小圈子里四面找过来,只见:那些桌子上的人,有的在吃,有的在喝,有的在谈笑,有的在把烟圈吐在热烈的空气里。结果,他并没有找到那个喊他“余先生”而向他发言的人。
只有隔座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单身的座客,那个人,距离和他最近。看样子,最有可能向他说出如上的话。但是,看这家伙,一手执刀,一手执叉,正自埋头苦干于他面前的一个餐碟中。工作得这样忙,在神气上也绝对不像开口说过话。何况,自己根本并不认识这个人。
于是他仅仅把困扰的眼色,在隔座这个家伙身上轻轻一掠而过。他只模模糊糊看到那个人,是个阔肩膀的人,年纪并不十分老,穿的是一套深色的西装。——不过,也许他连如上模糊的印象也不曾留下。
其实,如果余先生的脑力能够清醒些,他就可以看出:隔座这个穿西装的家伙,正是即刻在这门口高声说话的人;如果他的脑力再清醒些,他一定还可以记起这个人,也就是从汽车上把他扶下来的人;再,如果他的脑力,能清醒得和平常的人一样,他一定早已觉察:在路上的时候,这个神秘的家伙,一直是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在暗地里追随着他的。
实际上,他从一辆汽车之中,莫名其妙被扶下来。连着,他又莫名其妙,无形被压迫走进这家咖啡馆,其间他只走了绝短的一段路,多说些,也不过六七个门面。——至于他在这个离奇的晚上,究竟已遭遇到了一桩何种的事件?那也只有坐在他隔座的这个家伙——就是从汽车里把他扶下来的那个人——能够解答这个太神秘的问题。
可惜他都不知道。
这时候,他的迷惘的意识,已被那个突兀的语声,从苦思之中拉回来。他无暇再找他的已失落的记忆,而只顾抬起视线,昏乱地,在寻觅那个和他说话的人。
平素,余先生有个习惯:遇到什么疑惑不决,而需要思索的事,他喜欢一面思索,一面把他的脚尖,一起一落,在地上抖动,像是拍板的样子。——在这举目四顾的瞬间,他的脚尖,不知不觉,又在桌子底下颠顿起来。由于脚尖的抖动,他开始觉得他的两只脚,竟是那样的不适意,像被什么东西束缚了起来。无意之中,他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脚。他在他的脚下,找到了些非常可怪的东西;竟使他的两个眼球,立刻起了凝冻的作用!
“皮鞋!”他几乎要出声高喊!
一双皮鞋,那也值得惊异吗?未免太多惊异了!然而不!说出来是自有可惊异的理由:原来,我们的主角,他有一个古怪的性情,他一向最不喜欢穿皮鞋;也可以说,他的一生,从来不曾有过一双任何式样的皮鞋穿上过他的脚;不料,眼前他竟发现自己的脚上,不知如何,竟已换上了一双他所从来不曾穿过的东西。并且,那双皮鞋擦得那样光亮,一望而知这是十分摩登的式样。
看到了那双皮鞋,再把视线沿着皮鞋逐步看上来。哎!事情越发可怪了!
当时,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他的额上,有些汗液在流出来。他把两个眼瞳,扩张得很大,错愕地向四周乱望,他像一头受惊的野兽,在找寻出路。他又像准备向身旁的大众提出如下的问句:
“今天晚上,我——我到底遇见了怎么一回事?”
但是,四周那些浸沉于欢笑中的座客,除了有一两个人,偶然举起诧异的眼光在向他看,谁能知道他的意思呢?
一时他的目光,又本能地飘落到附近那支方柱上。他从镜子里面,呆呆照着他的影子。他不照这镜子还好,一照之后,只觉全身的汗毛,每根都已竖立起来!原来,他在镜子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影子,那个影子,却绝对不是他本人的影子!——他本人的影子不见了!
这里,我们应该把这主角固有的面目,简单介绍一下,方始能让听故事的人,了解这故事的超出乎理性以外的神秘性。
我们的余慰堂先生,在今天以前,他的正确的年龄,已超过五十岁。他是这个镀金大都市中的一个老牌闻人。(平心而论,我们很喜欢谈谈闻人们的故事;甚至,我们有时也喜欢故事造造他们的谣言,因为,多谈闻人们的事情,渐渐地,也许我们自己,也就成为闻人啦。)
他的外貌,是一个典型的旧人物。他的两眼带点小学程度的近视。在他脸上,留着两撇庄严而美观的八字须。他这两撇小须,至少在最近市面上,正像仁丹商标一样风行而有名。就为人家都很尊重他的小须,于是,这小须在他自己眼内,便也格外显得珍贵。尤其他在无事的时候,最喜欢独自拈捻一下,如同一个好古的人士,玩弄一小方汉玉一样。
以上,便是我们这位余先生的一个速写像。
而现在呢,他从那面神秘的镜子之中看出来,他又看到了一些什么情形呢?——说出来真是太觉可怪了!
再说一遍:镜子里的影子,完全不是他!
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太漂亮啦!
一套浅色的西装,剪裁得入时而配身。洁白的衬衫,配上一条鲜艳的领带,一个梅花形的小钻针,扣在这领带上,在闪烁发光。再看头上,一些稀疏而带白星的头发,却已梳得很光亮,看样子是很花费了些美发浆。这个时髦家伙的年岁,看去顶多只有四十岁。最主要的是:镜中人的小白脸,又光又洁,你拿显微镜来照这整个的颜面上面,你也不会找到半根胡子星。
他的最尊贵的八字小须失踪了!
你想,一个素向穿中装而很保守的人物,他在照镜子的时候,竟发现了如上那样一个神秘的影子,你想吧,他将发生如何昏迷错愕的感觉?
总之,镜中人的面貌,在他略带近视的眼光里,轮廓还有点像他,而镜中人的样子,却已经绝对不像是他!
如果说,镜中的影子就是他,他怎么竟会变成这种样子呢?
如果说,镜中的影子并不是他,那末,他自己的影子呢?——他自己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睁大了恐怖的眼球,重新跌进了噩梦的深渊!最初,他还以为这是眼睛的错觉。——因为,在这一个离奇的晚上,他自觉他的神经有点错乱;他疑惑他在过去的时间中,曾经剧烈地喝醉过酒,以致在听觉与视觉上,屡次发生错乱的感觉。
但是他尽力抹抹他的眼眶,尽力再凝视这镜中的迷离的影子:清清楚楚,这是一个穿西装的人!低头看看身上,没有错;用手摸摸身上,也没有错!
一种无可形容的恐怖,霎时布满于全身。这使他立刻想到了以前所听得的那些借尸还魂的故事!他的身子,不自觉地渐渐直立起来,接着,又不自觉地颓然地倒坐下去。最后,他的视线已凝冻在镜子上,他的血液已凝冻在血管里;而他的身子,也联带像一座化石那样,凝冻在他的座位之中,不复再有动作的可能!
至少,这时他的外表的神情,却已接近疯狂的状态。无怪四周的座客,不时举起惊奇的眼色,在飘到他的座位上来。
那些女侍应生,也都纷纷把视线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集中于他的脸上;尤其是最初招待他的那一个,偶尔向他偷看一眼,格外显着害怕的样子。
他这僵化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些东西唤醒他,简直不知道将要维持到怎样长久!可是,在这昏迷错愕的瞬间,那个离奇突兀的语声,紧接又幽幽然像叫魂那样起于他的座后,那个声音清楚地在说:
“喂!余先生,胡思乱想做什么?你的危险来了!还不赶快留意吗?”
这同样的可怕的语声,好像一连说了两遍。在第二遍上,他让危险两字从那面迷离的镜子里把惊魂唤回来。他再度旋转眼光,急剧地寻找这语声的来源。但是,他依旧没有找到。
他只发觉四周有许多人在汹汹然地向他注意。
隔座那个穿深色西装的人,正自低着头,在把一些糖块,用心地调在一杯咖啡里。
扩声机中,在放送一片繁杂的音乐,把满座上的笑语声都盖住了。
一切的事情,都是那样离奇而突兀,仿佛在他昏迷的脑壳里,接连在放焰火,使他越弄越不懂。
今天晚上,到底碰到了什么恶鬼?他这样想。
想念未已,突然,一个更严重的声气,忽又直刺进他的耳朵,那个声音很害怕地在说:
“赶快看门口!”
这最后一次的语声已使他疑惑到那个向他发言的人,就是隔座这个穿深色西装的家伙,但是,他来不及向这家伙加以更多的注意,而已抬眼看到这咖啡馆的门口里,正有一个很可怕的脚色在昂昂然走进来。
走进来的新脚色,是一个魁梧大汉子。如果说,眼前这满咖啡馆中的座客身材都不及新进来的这人那样高大,这话也不算武断。此人头戴一顶黑呢帽,身穿一件深青色的哔叽长袍,两个袖子,连着里面白纺绸短衫的袖口一同不规则地卷起,在他强壮而多毛的臂腕上,右腕露出一个阔带的大手表。此人的面颊上,长着大块的横肉,像是两枚橘子的样子。
他的一双向外突出的眼珠,完全是三角形,好像上帝在安置他这三角怪眼的时候,怕他这双眼珠因过于突出而脱离眼眶,因之,顺便在他眼膜的四周,络上了些粗粗的红筋,让它不至于掉下来。
总之,那个人的相貌,简直凶恶得可怕!
此人走进来时,立即举起他的三角怪眼,在各个座位之上恶狠狠搜索过来。最后,他的视线,却紧张地停留到我们这个主角的位子上。
这时,我们的主角余先生,正因为身旁的警告而惊愕地举眼,一时,他的眼光,恰巧和这大汉的眼光像针锋那样接触了一下;似乎由于心理上的虚怯的关系吧?余先生被这双凶锐的眼睛一看,全身顿时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
他简直不敢向这新进来的长大家伙再多看一眼。但是当他第二眼再偷看时,只见那个大汉,已在距离他四张圆桌的一个座位里面坐下来。双方的面部恰好斜对着。
有一个女侍应生在招呼这个大汉。只见这大汉,正以诡秘的神气,在向那个女侍应生问什么话。女侍应生一面回答,一面在扭转头,不时把眼梢歪到自己这边来。
看样子,他们对于自己,分明正有什么诡秘的谈论。
自从这个大汉进门之后,奇怪,余先生的注意力,似乎全部已被这个家伙所吸住。这时候,他已全部遗忘了过去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之间,竟屡次举眼,偷看这个新的脚色 他每次看到那双红筋满布的怪眼,每次在增加不安的感觉,最后,他简直越看越觉害怕,越看越觉不敢再看。
这情形很奇怪,但是这还不算最奇怪。
最奇怪的是:他这里在向那个大汉密切注意,不料,那个大汉同样地也在向他密切注意;而且,看那大汉的神气,同样地也在露着一种害怕,每逢双方的视线直接碰到时,只见那人的目光,立刻就迅速躲开;总之,在那双可怕的三角怪眼中,分明包有一种无可描画的神情。
他不明白这个新进来的脚色,为什么要把这种阴险可怕的眼光来威胁他?
这个家伙要和自己过不去吗?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此人将以什么方式,和自己过不去呢?
一种新的恐怖只管从那双三角怪眼之中,一阵阵向他这边传送过来;这恐怖引起了他像马蹄那样历乱的思想。
本来,他自从走进这家咖啡馆里,获得了一点短促的休息以后,他的神识,仿佛将要接近清醒的边际。不料,眼前所遇的事情,每件都是那样的突兀,每件都是那样不可解释,这使他的将近清醒的神志,越发堕入了一个较前格外昏乱的境界。
正当这个迷离惝恍的瞬间,他身旁的幽幽的语声却又随之而起,只听那个语声穿过了四座杂乱的音响,而送到他耳边说:
“喂!听到没有?我叫你别乱想啊!”
这语声使他猛然记起那个向他发警告的人,他赶快回头,看着隔座那个穿深色西装的家伙。这一次,他已吃准这话就是此人向他所发。一看此人的眼光,却并不向着自己,而脸上也依然并无说话的表情。但是,细看此人的眼角,却含有一种非常戒备的神气。只见他的两眼,呆望着玻璃桌面,嘴里还在幽幽然地说:
“赶快把你的头旋过去!不要只管看着我!”
这是一种极度严重而带命令意味的声气,像一柄刺刀那样割破了白热的空气而送向他的身边。由于这语气的严重,吓得他慌忙把昏乱的眼光从隔座收回来。他不期然而然,又抬眼偷望对方那个大汉,恰巧看到那个大汉也在抬眼偷看他。四条视线略一接触,他看到那双三角怪眼,却像移转阵地似的躲闪到了别处去。
同时他听到隔座穿西装的那个人,还在用着警告的语气向他说:“喂喂!余先生,别忘记你的身价!你得留心着对面这个恶汉!”
那声音又连着说:“好好保护你自己!——千万不要再向我看!”
以上的语句,虽然并不响亮,但每个字眼夹杂在音乐的繁响之中,都有一种沉重的力量。
不错,他是一个有身价的人。谁都知道,一个有身价的人,很像一枚直立着的鸡蛋;而一枚直摆的鸡蛋,最容易遭遇被碰碎的危险。
这样的意识,他在昏迷错乱之中,当然也还没有忘掉。而现在,他听得隔座那个人,连续向他提出危险的警告,自然,这使他错乱的神经上,越发增加了极度不安的感觉。
一个意念飞速闪进他的脑海:“啊!有危险!还是赶快离开这地点!”
想定主计,他摸摸头,把双手撑在圆桌上,却像酒醉那样站起来,准备举步向门外走。
四周仍有许多异样的眼光,乱箭一样地飞集于他的一身。这些眼光,包括许多座客,女侍应生,身旁那个穿深色西装的怪客,以及对方那个三角眼的大汉。
他的身子刚离座位,不料面前来了一个人,竟自拦住了去路不让他走,使他吃了一惊。
一看,只见方才那个女侍应生,秀媚的眼角带着畏怯在向他问:
“先生,不需要什么了吗?”
他看到这女侍应生的手内,捧着一个腰圆的小银盘,盘里放着一张小纸片。
他呆了呆,方始意识到自己吃了东西,还没有付账。他不禁伸手到衣袋里面,准备掏钱。
在这伸手掏钱的瞬间,一种莫名的恐怖重新又袭进他的心坎:因为他已记起,身上所穿的衣服,已并不是自己固有的衣服。
他不知道在这一套神秘得莫名其妙的衣服里,究竟有没有钱?他姑且伸手到衣袋里去摸索一下。还好,他在右边的衣袋里,摸到了一些纸片,样子可能是钞票。掏出来一看,果然是两叠蓝颜色的花纸。
他把其中较厚的一沓,向那小银盘里一抛。不管三七二十一,摇晃晃地向门口就走。
他完全没有看到那个女侍应生睁大了眼在向他发愣。
穿制服的孩子仍旧用先前那样的眼色看着他,而替他拉开了门。
他的身子从热闹的空气之中再度摇晃进幽悄的街面。
迎面夜风吹来,使他昏乱的脑子,比较更清静了些。
这时街面上已比前更冷静。
他准备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准备回家。看看四周,并没有一辆车子。定定神,他模模糊糊意识到他身子所在的地点,好像是在霞飞路的某一段。他开始懊悔,没有在这咖啡馆里借打一个电话,好让家里放车子来接他。但是,想起了那个大汉的三角怪眼,他并不想再回去。
他姑且向着比较光亮的地方走过来。
他把极度疲弱的身子,再度投入于那些梧桐叶的晦暗的剪影之下。
过去的奇事,一件件在脑内打转。一种莫名的恐怖,一阵阵在刺促他的神经。想来想去,只觉今天晚上的事,完全像是一个梦。然而仔细想想,明明不是梦。既然不是梦,那末,到底已遇见了些什么事情呢?——他依旧无法解答这个谜。
他一面找着车子,一面在树影之下摇晃地向前,一面不知不觉,伸手插进了西装的衣袋。他在方才摸索过的那只衣袋里,又摸到了一些手帕,烟盒,铅笔之类的零物。同时,他在满脑子里搜索过来,却想不出他所穿的,究竟是谁的衣服。
因为摸着右边的衣袋,顺便他把他的左手,再向左边的衣袋里伸进去。他的指尖,碰到了一件坚硬的东西,那是一件金属品的东西;分量似乎相当沉重。
仔细一摸,手指的触觉告诉他:那东西不是别的,却是一支冰冷的手枪!哎呀!衣袋里面,怎么会有这种危险的物品呢?他的胆子一向就很小,并且,他自生手指以来,一生也从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
他怕这支不知来历的手枪,没有关上保险,一不小心会触动触动枪机而闯出祸来。他赶快把手从衣袋里伸出来。
他的心在狂跳!同时他的脚步在加速地向前移动;在他昏乱的意识中,好像是要逃避衣袋里的那支手枪的追袭!
就在这个时候,这静寂的街面上,忽有一串历乱的皮鞋声,直向他的耳边送来。
起先,他还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脚声。因为他还记得他的脚上,已被换上了一双莫名其妙的皮鞋。但是,仔细一听,那种急骤的步子,分明来自他的身后。当时,他不回头去张望倒还好,回头一望,他的灵魂几乎要飞散在这幽暗的树影里!
原来,他从路灯光里看过去,只见二丈路以外,正有三四个人在追随着他。为首的一个,正是那个三角怪眼的大汉。其余的几个,他不及看清是什么人;仿佛觉得内中有着穿短打或是穿西装的人。这使他在万分惊慌之中,陡然想起了咖啡馆里隔座那个怪客的警告;紧接着又有一个念头迅速走进他的惊慌的意识中。
哎呀!一定遇见绑票了!——他这样暗喊。
一面迅速地转念,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不自觉地在向前飞奔。
可是他虽奔得很快,背后的人似乎追得更快,听听脚步声,分明已越追越近。他的一颗心几乎要在腔子里狂跳出来,呼吸也越弄越短促。在这冷汗直冒的瞬间,他想起衣袋里面藏有一支莫名其妙的手枪。虽不知道这支手枪是否实弹?可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他想,何不取出来,吓吓那些追踪他的匪徒,也许可以救一救急。
想念之间,他赶快把手伸进衣袋里,在他伸手摸出手枪的瞬间,他听到那些急骤的脚声,已经接近他的身后。他在万分慌乱之中,准备旋转身子,把枪镇住那些追踪他的人。他的手指刚自钩住扳机而旋转身,不料,就在这个短促的瞬间,他的执枪的手臂,已被人家一把抓住;同时他的手指却在一阵凌痛之中,被人狠命高举了起来。
“呯!”——
一响尖锐的枪声从那支向天的枪管中急骤地发出,而划破了街面上的幽悄的空气!
连下来,他不知道他在那个沸腾的刹那之间,又做出了一些什么动作?他只觉得做梦那样,一双手已被一种铁制的东西铐了起来!
再连下来,他只觉得他已被一小队气势汹汹的家伙,推进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那个宽大的车厢里面一片漆黑,不见一丝光。
在那狭长的车座上,左右各有一人,把他紧挤在中间,连转动一下也不可能。
对面也有两团黑影,惨默地坐在那里,不作一声。车窗上的铁丝网里偶尔漏进一丝光来,闪在这两个黑影的脸上,他不时看到那双三角怪眼,正在向着他狞笑。
他觉得天地在他脑海里疯狂地旋转!
不久,他又完全丧失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