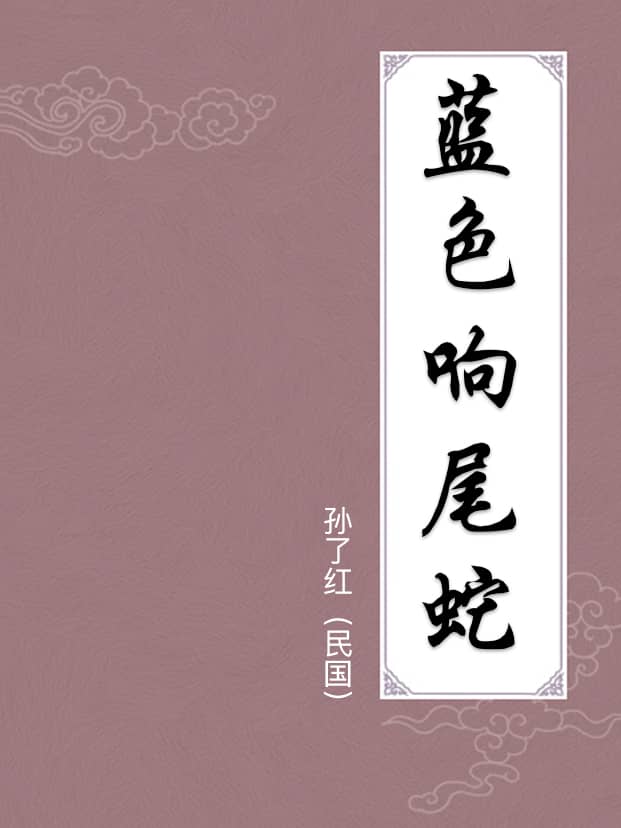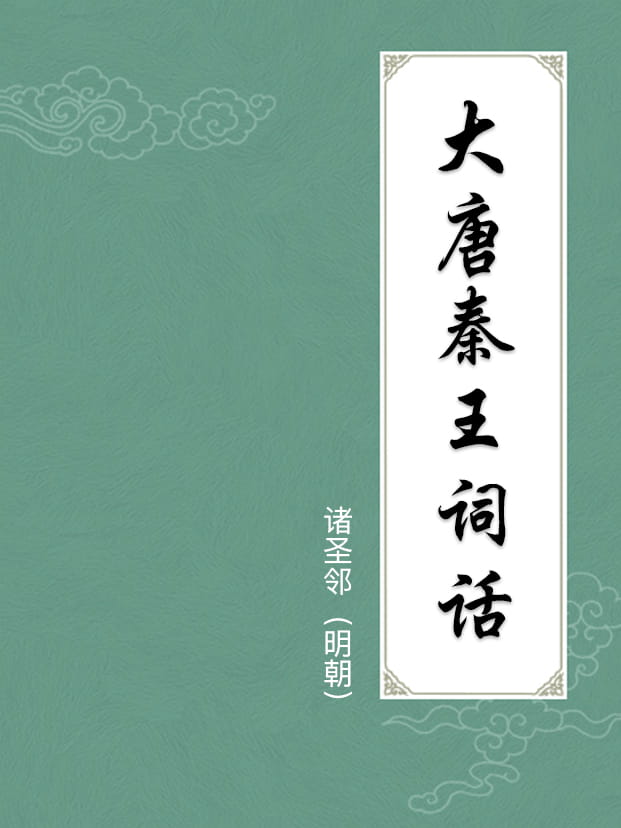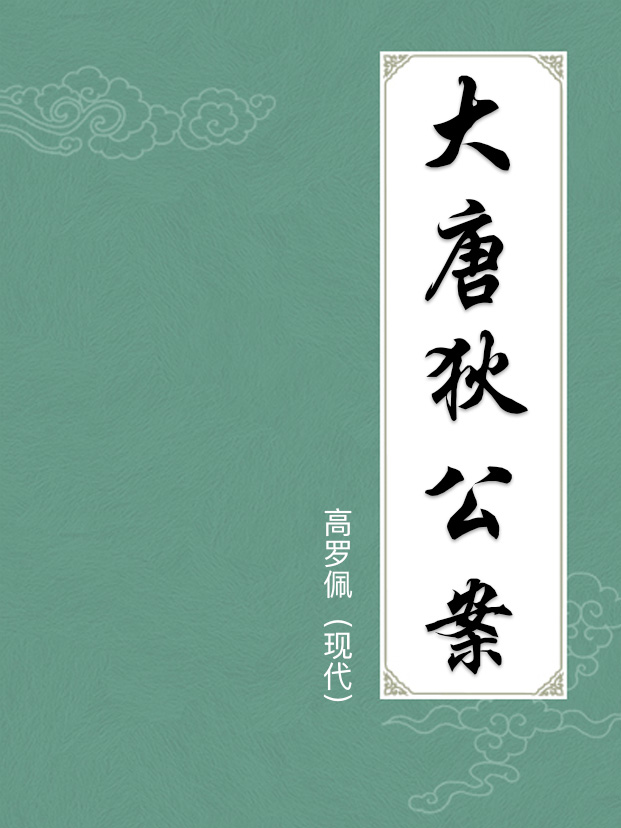那对黑宝石,从酒杯上抬起,凝视在鲁平的脸上。她耸耸肩膀,在冷笑。
忽然,她胸前的蓝色线条又是一阵颤动,格格格格格,她竟扬声大笑起来!
这样的笑,在她,已经并不是第一次。在郁金香,她曾同样地笑过一次,那是在我们这位红领带英雄被剥夺了警务员的假面具的时候,她这笑,笑得非常美,非常媚。就为笑得太美太媚了,听着反而使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鲁平在想,怎么?难道把戏又被拆穿了吗?
他忍不住发窘地问:“你笑什么呀,亲爱的?”
“我笑吗?嗯,亲爱的,”——她也改口称鲁平为亲爱的了,“你,真胆小得可爱,而也愚蠢得可怜!”
“我,我不很懂得你的话。”
“请勿装佯!”对方把双手向纤细的腰肢间一叉,撅着红嘴唇直走到鲁平身前说:“请问,你是不是把这两只杯子换了一个方向?”
这女子会掷出这样一个直接的手榴弹,这,完全出于鲁平之不意。他白瞪着眼,呆住了。至少,在这片瞬之间他是呆住了。
对方带着媚而冷的笑,像一位幼稚园中的女教师,教训着一个吃乳饼的孩子那样向他教训说:“你不敢在我家里抽我的纸烟,为什么?你全不想想,一整听刚开听的纸烟,我可能在每支烟内,加上些迷药之类的东西吗?哎呀,你真胆小得可爱!你太迷信那些侦探小说上的谎话了。”
“嗯……”鲁平的眼珠瞪得像他部下孟兴的眼珠一样圆!他听他的女教师,继续在向他致训:
“还有,你把这两个杯子,换了一个地位,这又是什么意思?请你说说看。”
“……”
“噢,你以为,我在这两只杯子的某一只内,已经加上了些蓝色毒药或者氰化钾了吗?假使我真要玩这种小戏法,我能当场让你看破我的戏法吗!傻孩子,难道,你全不想想吗?”
吗?吗?吗?吗?吗?
鲁平一时竟然无法应付这些俏皮得讨厌的“吗”!
这女子把腰肢一扭,让全身闪出了几股蓝浪。她飘曳着她的伞形的大袖,走回那只桃花心木的圆桌,她说:
“胆小的孩子,请看当场表演吧!”
她把两只杯子一齐拿起来,把右手的酒,倾进左手的杯子,再把左手的酒,倾进右手的杯子,倾得太快,酒液在手指间淋漓。咕嘟,咕嘟,她在两只杯子里各喝了一大口。
她的喝酒的态度非常之豪爽。
然后,她把两杯中之一杯递向鲁平的手内,嘴里说:“现在,你很可以放心了吧?亲爱的!”
鲁平在一种啼笑皆非的羞窘状态之下,接过了那杯酒。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一生将有一次,要在一个女孩子的手里,受到如是的攻击。
叮当,杯子相碰。两个脸同时一仰,两杯酒一饮而尽。
酒,使这个女子增加了风韵;酒,也使鲁平掩饰了窘态。
空气显然变得缓和了。
鲁平放下杯子,夹着纸烟,退坐到那双人沙发上。这女子挈挈衣襟,遮掩住赤裸着的大腿,挨着鲁平坐下。电一样的温暖,流进了鲁平的肩臂,浓香在撩人。她伸手抚弄着鲁平的领带,投射着轻轻的嘲弄:“久闻红领带的大名,像原子弹那样震耳,今日一见面,不过是枚大炮仗而已!嘿,胆量那么细小,怕一个女人,怕一杯酒!”
鲁平突然把身子让开些,恼怒似的说:“小姐,你注意我的领带,是几时开始的?”
“在郁金香里,何必大惊小怪呀?”
鲁平暗暗说:“好,你真厉害!”
这女子又说:“告诉你吧,今天下午,我接到情报,有人在四面打探我昨夜里的踪迹,我就疑心了,但我没有料到就是你——鲁先生。”
“哈!你的情报真灵!”鲁平苦笑。心里在想,看来韩小伟这小鬼头,他的地下工作,做得并不太好呵。
这女子把左腿架上右腿,双手抱住膝盖,嘴唇一撇:“难道,只有你的情报灵?”
鲁平伸出食指碰碰那颗小黑痣,呻吟似的说:“我的美丽的小毒蛇,我佩服你的镇静,机警!”他把那股暖流重新搂过来,欣赏着她的浓香。“亲爱的,你使我越看越爱,甚至,我连你的沟牙管牙也忘掉了!”
这是鲁平的由衷之言,真的,他的确感到了这条蓝色响尾蛇的可爱了!
这女子把她的小黑痣贴住了鲁平的肩尖,嘤嘤然说:“据我记忆所及,你在郁金香门口开始,称我为亲爱的,到现在,已经造成了第三十六次的纪录啦。”
“你的记忆真好,亲爱的!”
“第三十七次。”
“你愿意接受这个称呼吗?亲爱的。”
“三十八!”那对有暖意的黑宝石镶嵌上了鲁平的脸。“我以为这两个字,在一面,决不能随便出口;另一面,也决不能太轻易的就接受。记得,西方的先哲,曾为‘爱’字下过一种定律:爱的唯一原则,决不可加害于对方,好像圣保罗也曾向什么人这么说过的。”
鲁平在惊奇着这个女子的谈吐的不凡。他索性闭上眼,静听她嘤嘤然说下去。
戒备,快要渐渐溶化在那股浓香里!
她继续在说:“假使上述的定律是对的,那么,你既然称我为亲爱的,你就该放下任何加害我的心,对吗?”
“对!”这边依旧闭着眼。
“那么我们绝对应以坦白相见,对吗?”
“对!”
“你说那个陈妙根,是我亲自带人去把他枪杀的,对吗?”
“对呀!”鲁平突然睁开眼,“难道你想说不?”
“嘘,我曾向你说过不吗?”她侧转些脸,在鲁平脸上轻轻吹气,一种芝兰似的气息,在鲁平脸上撩拂。
“老实告诉你,我对这件事,原可以绝不承认。因为我并没有留下多大的痕迹,没有人会无端怀疑到我。”
鲁平在想:“小姐,自说自话!”
她在说下去:“但是,我在郁金香内一看到说这话的人是你,我就不再想抵赖。我知道跟你抵赖不会有好处。”
香槟跑过来了!
世界上的任何人,上至满脸抹上胜利油彩的那些征服者,接收大员;下至一个小扒手,都喜欢香槟;接收大员当然欢迎有人称颂他的廉洁;小扒手当然也欢迎人家说他“有种”。总之,一头白兔也欢迎有人抚抚它的兔子毛。我们这位绅士型的贼,当然也不能例外。
他被灌得非常舒服,但是他还故意地问:“为什么一看见我,就不想抵赖呀?”
“一来……”她只说了两字,却把那对黑宝石,镶嵌上了那条鲜红的领带。然后微微仰脸,意思说是为了这个。她索性把鲁平的领带牵过去,拂拂她自己的脸,也撩撩鲁平的脸。
“还有二来吗?”这边问。
“二来,我一向钦佩你的玩世的态度。”那对黑宝石仿佛浸入在水内,脸,无故地一红。“你知道,钦佩,那是一种情感的开始哩!”
鲁平像在腾云了!但是,他立刻憬然觉悟,在一条小毒蛇之前腾云是不行的。他把身子略略闪开些,真心诚意地说:
“听说,那个陈妙根,是个透顶的坏蛋哩。”
“当然哪!否则,我何必捣碎他!”
“你有必须捣碎他的直接理由吗?”
“当然!”
“我能听听你的故事吗,亲爱的?”
“我得先看看你的牌。”蓝色线条一扭。
“已经让你看过了,不是吗?”
“不!”睫毛一闪,“我要看的是全副。假使你是真的坦白对我,你该让我先听听,你在这个讨厌的故事上,究竟知道了多少?”
“知道得不多。”鲁平谦逊地说。他在想,虽然不多,好在手里多少有几张皇与后,你别以为我是没有牌,偷机!想的时候他把身子坐坐直,整一整领带,换上一支烟,然后开始揭牌。
“亲爱的,你听着。”他喷着烟,“第一点,你跟你的同伴,是在昨夜里十点五十分左右,走进那宅公园路的洋房的,即使我提出的这个时间略有参差,但至多,绝不会相差到十分钟以上!”
他说话的态度,坚决、自信,显出绝无还价之余地。对方颔首,表示“服帖”。
“你带领着两位侍从,连你,一共三个。”
那双妩媚的眼角里透露出一丝轻倩的笑。她说:“噢,连我,三个?好,就算三个吧。”
就算?字眼有问题。鲁平忍不住说:“假使我是发错了牌,亲爱的,请你随时纠正。”
“别太客气,说下去。”
鲁平觉得对方的神气有点不易捉摸,他自己警戒,发言必须留神,否则,会引起她的第三次的格格格格,那有多么窘!
他继续说:“你的两个侍从,其中一个,带着手枪——带的是一支德国出品的Leuger,枪,带枪的那个家伙个子相当高,他姓林。对不对?”
他吃准刚才在郁金香门口跟黑鹏比武的那个工装短发的青年,就是昨夜里的义务刽子手。他听这位黎小姐用日本语称他为“海牙希”,所以知道他是姓林。
这女子居然相当坦白,她又抚弄着鲁平的领带,嘴里说:“名不虚传!”
鲁平在对方的称赞之下得意地说下去:“还有一个,大概就是刚才在郁金香内陪你小坐过一会的青年绅士,穿米色西装的。你说他姓白。他和你的交情很不错。大约他像我一样,喜欢称你为亲爱的,纪录也一定比我高,对吗?”
他的问话显然带着点柠檬酸。
她耸肩:“你看刚才那个穿米色西装的小家伙,线条温柔得像花旦博士一样的,他会参加这种杀人事件吗?喂,大侦探,说话应该郑重点,别信口乱猜,这是一件杀人案子呀!”
她又耸肩,冷笑,神气非常坚决,绝对不像是说假话。鲁平在担心,不要再继之以一阵格格格格格。还好,她只冷笑地说:
“大侦探,请你发表下去罢。”
“那么,”鲁平带着点窘态,反问,“除了那个姓林的家伙以外,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是谁吗?告诉你,根本不止还有一个哩。”
“那么,还有几个是些什么人?”鲁平真窘。
“你问我,我去问谁?”一枚纤指在他脸上一戳,“别让大侦探三个字的招牌发霉罢!”
她怕这位红领带的英雄下不了台,立刻就把一种媚笑冲洗他的窘态。她说:
“别管这些,你自管自说下去罢。”
鲁平带着点恼意说:“你们这一伙,”他不敢再吃定是三个。“在那洋房的楼下,先击倒了两个人,把他们拖进一个小室,关起来。对不对呀?”
“对,说下去。”
“以后,你们闯进了二层楼的憩坐室。那时候,陈妙根已经回来。你,曾在那张方桌对面坐下来,跟这坏蛋,开过一次短促的谈判。这中间,你们曾威胁着他,把一串钥匙交出来,打开了那只保险箱,搬走了些什么东西,连带拿走了那串钥匙,对吗?”
“对,说下去。”
“在谈话中间,你曾敬过这位陈先生以一支绞盘牌。对吗?”
“好极。”红嘴唇又一撇,眼角挂着讥笑,“一个专门以拾香烟屁股为生涯的大侦探,倒是福尔摩斯的嫡传哩!还有呢?”
鲁平带着点无可奈何的恼怒在想,小姐,暂时你别太高兴!拖着红色领带的人,不会带着鼻子上的灰就轻轻放手的!想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位陈妙根先生,在跟你谈判的时候,曾把一叠钞票,横数竖数数过好几遍。对不对呀?”
那对黑宝石突然闪出异光。她像在喃喃地自语:“是的,当时他曾向我借过一张钞票哩。”
“噢,他曾向你借过一张钞票?是关金?美钞?伪币?还是CNC?”鲁平猛喷了一口烟,烟雾中浮漾着得意。
女子格外怀疑了,她知道鲁平的得意不是无故的。
鲁平紧接着问:“你知道这一小叠钞票的用途吗!”
这女子思索了一下而后说:“他把那叠钞票,整理了一下,想差遣着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代他去买一听纸烟。”
鲁平暗暗点头,在想,这是一个欲擒故纵的好办法。想的时候他问:“当时你们怎么样?”
“当然不理他。”
鲁平在想,好极了,你们当然是“当然不理他”,而那位将要进服铁质补品的陈妙根先生,当时所希望的,正是你们的“当然不理他”,然后,他才能把这遗嘱一样的线索,随便留下来,真聪明,聪明之至了!
他对那位已经漏气的陈妙根先生,感到不胜佩服。他又问:“当时你曾注意他的神气吗?”
“他知道死神已经在他头顶上转,他很惊慌,吸纸烟的时候甚至无法燃上火。”这女子在怀疑的状态之下坦白地回答。他想听听鲁平的下文。
这边却在想,好,精彩的表情!他又问:“后来,你曾注意到那叠钞票的下落吗?”
“没有。”
鲁平想,这是应该注意的,而你竟没有!聪明的小毒蛇,凭你聪明,你也上当了!
他微微耸肩,尽量喷烟,暂时不语。
沉默使对方增加怀疑,她的那颗精彩的小黑痣再度贴上了鲁平的肩尖,催促着说:
“咦!为什么不说下去呀?”
鲁平赶紧躲闪着这个纸币的问题,他说:“我手里还有好多张纸牌哩。”
“那么,揭出来。”
“我的最重要的一张牌知道你们发枪的时间,是在十一点二十一分。毫无疑义!”
那双黑眼珠仰射在鲁平脸上,表示无言的钦佩。她实在思索不出,鲁平对这发枪的时间,何以会说得如是准确?她问:
“还有呢?”
“还有,我知道你们在开枪之后,曾在房中逗留过一个短时间,约摸十分钟左右,对吗?”
“嗯,差不多,说下去。”
“你们在这最后逗留的时间中,曾拿走了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大约就是你的照片。对吗?”
这女子冷笑,在想:我的照片是绝不会随便留在外面的,你胡说!但是她问:“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曾拿走一张照片呢?”
“因为玻璃下的照片行列弄乱了。”
“好吧,说下去。”
“我知道在这最后逗留的时间中,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曾把窗帘拉下来。对吗?”
“对,还有?”
“我又知道,最初,你们并不曾准备就在那间屋子里用枪打死他,我猜测得不错吗?”
“歇洛克,请举出理由。”
“因为,你们用的那种Leuger枪,声音太大,你们绝不会傻到连这一层也绝不考虑。对不对呀?”
“亲爱的歇洛克,你的猜测相当聪明。但是,你还缺漏一些小地方,别管这个,你且说下去。”那颗小黑痣在鲁平的肩尖上摩擦。
鲁平在那股浓香中继续说:“以后突然地开枪,那是由于一种意外的机缘所促成,恰巧,那时有几位盟军,在吉普车上乱掷掼炮,这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亲爱的,我猜得对吗?”
他不等对方的回答连着得意地说下去:
“所以,我说,这种内战杀人的机会,正是那几个坐吉普的盟军供给的!”
“你说内战,这是什么意思呀?”黑眼珠中闪出了可怕的光!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跟这陈妙根,原是一伙里的人。”鲁平随口回答。
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条蓝色响尾蛇,在盘旋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