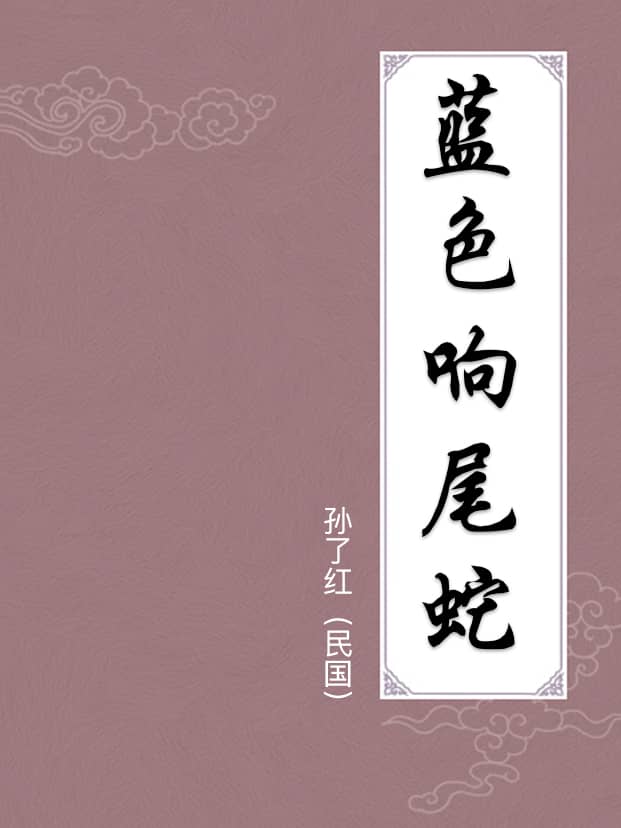第二天,鲁平对于公园路的这一注生意,差不多已不再介怀。一向,他自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人。他对每宗生意,目的只想弄点小开销,而他在这生意上,的确已经弄到了些钱,虽然数目很细小,但是,他绝不会跟那些接收大员一样,具有那样浩大的胃口,一口气,就想把整个的仓库囫囵吞下来。
总之,他对这件事情,认为已经结束了。
不过还有两个小问题,使他感到有点不可解:
第一,昨夜,那个女子是明明有机会向他开枪的,她为什么迟疑着不开枪?
第二,那个女子曾在最后一瞬中,露出一种得意的笑。她为什么笑得如此之得意?
他对这两个问题无法获得适当的解释。
他在他的小小的办公室中抽着纸烟。纸烟雾在飘袅,脑细胞在旋转。
无意之中,他偶然想起了老孟昨天的报告:所谓美金八十万元的大敲诈案。这报告是无稽的,近于捕风捉影。但是,由此却使他想起了那个中国籍的日本间谍黄玛丽。
那个女子是非常神秘的。她有许多离奇的传说,离奇得近乎神话。所谓黄玛丽,并不是个真正的姓名,那不过是一个缩短的绰号而已。她的整个的绰号,乃是“黄色玛泰哈丽”;意思说,这是一个产生于东方的玛泰哈丽,黄色的。
真正的玛泰哈丽,是第一次欧战时的一名德国女间谍。她的神通非常广大;她的大名,曾使整个欧洲的人相顾失色。有一次,她曾运用手段使十四艘的英国潜艇化成十四缕烟!
这时,他忽想起这个玛泰哈丽的原文Mata Hari,译出意思来,那是“清晨的眼睛”。
他的眼珠突然一阵转,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他想起了昨天韩小伟的报告,那位黎亚男小姐,她有许多许多的名字,其中之一个,叫作黎明眸。他所以特别记住这个名字,那是因为,过去有个电影明星,叫作黎明晖。黎明晖与黎明眸,这两个名字很容易使人引起联想。
黎明眸,这个名字相当清丽,译成了白话,那就是“清晨的眼睛”,而这清晨的眼睛,也就是Mata Hari。
他的两眼闪出了异光。
他在想:那么,这位又名黎明眸的黎亚男小姐,跟那黄玛丽,难道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吗?
若说黄玛丽跟这黎亚男就是一个人,不过在年貌上,却还有些疑点,根据传说,那个黄玛丽相当老丑,年龄至少已有三十开外。而这黎亚男,她的年龄,看来至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况且,她是那样的漂亮。
除此以外,从多方面看,这朵漂亮的交际花,跟那个神秘的女间谍,线条的确非常之相像。
他想,假使这两个人真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自己贪图了些小鱼,未免把一尾挺大的大鱼放走了。
该死!昨夜里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怪不得,昨夜那个女子,显出那种得意的笑。
他从座位里跳起来,抛掉烟尾。他像追寻他的失落了的灵魂那样,飞奔到门外,跳进了一辆停在门外的旧式小奥斯汀内。
他决定再到海蓬路二十四号的屋子里来试一次,能不能把已失落的机会,重新找回来?
在车辆的飞驶中,他对那件公园路的血案,构成了另一个较具体的轮廓,他猜测,那个被枪杀的陈妙根,跟那另一坏蛋张槐林,一定是把握住了这女子过去的什么重大秘密,想要大大的敲诈她一下。因之,才会造成前夜的血案。而那张槐林,或许前夜也是那位蓝色死神的名单上之一个。因为一向他跟陈妙根,原是同出同进的。而他之所以能免于一死,那不过是由于一种偶然的侥幸而已。
他觉得他这猜测,至少离事实已不太远。
照这样看来,孟兴的那个报告,所谓美金大敲诈案,或许多少有些来由哩。
汽车以一个相当的速率,到达了海蓬路。他并不把车子直驶到二十四号门口,远远的就煞住了车,跳下车来,锁上了车门。重新燃上一支烟,把它衔在嘴角里。然后,他向那宅洋楼缓缓踱过来。
那条路真冷僻,白天也跟夜晚一样静。抬头一望,这座小洋楼的结构,比之夜晚所见,显得格外精致。从短墙之外望进去,这宅屋子,静寂得像座坟墓,看来里面像是没有人。短墙边上,有两部脚踏车倚靠着,其中之一部,是三枪牌的女式跑车。他匆匆一瞥,没有十分在意。
短墙的小铁门仍旧虚掩。他轻轻推门而入,踏上阶石,伸手按着电铃。
立刻有人出来开门,开门的人,正是昨夜那个小女孩——秀英。
“啊,鲁先生,是你。”女孩的脸上,带着一脸平静的笑。闪开身子,让他走进门去。
这女孩子的神气,使他有点奇怪。
她把鲁平引进了一间寂静的会客室,招呼他坐下来,然后,她说:
“鲁先生,我已等了你半天了。”
“你知道我要来?”他的眼珠亮起来。
女孩点点头。她又说:“鲁先生,昨夜里,你把你的帽子,遗忘在我们这里了。”
她回身走到一个帽架之前,取下那顶呢帽,双手送还了他,然后又说:
“先生,请等一等,还有东西哩。”
这女孩子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中的小仙女,她以一种来无声去绝迹的姿态,轻轻走出室去,而又轻轻走回来。她把两件东西,给了鲁平说:“黎小姐有一封信,一件礼物,嘱我转交给你。”
“一封信?一件礼物?交给我?”鲁平从这女孩子手内接过了一只漂亮的小信封,跟一只蓝色丝绒的小盒,那封信,信面上的字迹非常秀丽,不知为何,他的手在接过这封信时有点发颤。他赶快拆信。
只见信上如是写着——
鲁君:
我知道你一定要来,不一定今天或者明天,我知道,当你再来的时节,你已把某一个哑谜猜破了。
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踏上了遥远的征途。此刻,或许是在轮船上,或许是在火车上,或许是在飞机上。非常抱歉,我不能再像昨夜那样招待你。
昨夜里的某一瞬间,我好像曾经失掉过情感上的控制,由于心理冲突,我曾给予你一种机会。或许你是明白的,或许你还不明白,假使你还不明白,等一等,你会明白的。
凭这一点浅薄的友谊,我要求你,不要再增加我的纠纷。在上海,我的未了的纠纷已经太多了!
昨夜,你忘却劫收我的钻石指环了,为什么?你好像很看重这个指环,让我满足你的贪婪吧。请你收下,作一纪念。愿你永远生长在我的心坎里。
世界是辽阔的,而也是狭隘的。愿我们能获得再见的机会,不论是在天之涯,是在海之角。
祝你的红领带永远鲜明!
×月×日亚男
信上的话,像是昨夜里的蔻莉莎酒,带着相当的甜味,而也带着相当的刺激,这有几分真实呢?
他把这信一气读了三五遍。打开蓝丝绒的小盒,钻石的光华,在他眼前潋滟。
一种寂寞的空虚充塞满了他的心。他不知道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才好。他茫茫然踏出了那间寂寞的会客室,甚至,他全没有觉察,那个小女孩,拿着一方小手帕,站在那个开着的窗口之前,在做什么?
他把那封信,跟那只蓝绒小盒,郑重地揣进了衣袋,茫茫然走出了这宅小洋楼。他戴上了帽子,走向他的小奥斯汀。
刚走了二三十步路,突然,头顶上来了一阵爆炸声,跟前夜差不多,砰!砰!砰!砰!
那顶KNOX牌的帽子,在他头上飞舞起来,跌落在地下。
他赶紧回身,只见一个西装青年,伛着身子骑在一辆脚踏车上,正向相背的方向绝尘而去,眨眨眼,已只剩下了一枚小黑点!
捡起地下的帽子来看,帽子上有两个小枪洞!
他飞奔回来,一看,矮墙上的两部脚踏车,只剩下了一部。那部三枪牌的女式跑车不见了。
啊!她!向他开枪的正是她。只要瞄准略略低下些……嗯,她为什么不把瞄准略略低下些?
在这一霎时间,他的情感,突起了一种无可控制的浪涛。他完全原谅了她的毒囊与管牙;甚至他已经绝无条件地相信了她昨夜里给她自己辩白的话!他感觉到世间的任何东西,不会再比这个女子更可爱!
那颗小黑痣,在他眼前,隐约地在浮漾。
他喘息地奔向他的小奥斯汀。他在起誓,送掉十条命也要把这女子追回来,无论追到天之涯,海之角。
但是,当他喘息地低头开那车门时,突然,一个衰老的面影,映出在车门的玻璃上,这像一大桶雪水,突然浇上了他的头,霎时,使他的勇气,整个丧失无余。
可怜,他们间的距离是太远了!
他怅惘地踏上驾驶座,怅惘地转动着驾驶盘,怅惘地把车子掉转头。
太阳已向西移,在那条寂寞的路上,在那辆寂寞的车上,在那颗寂寞的心上,抹上了淡白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