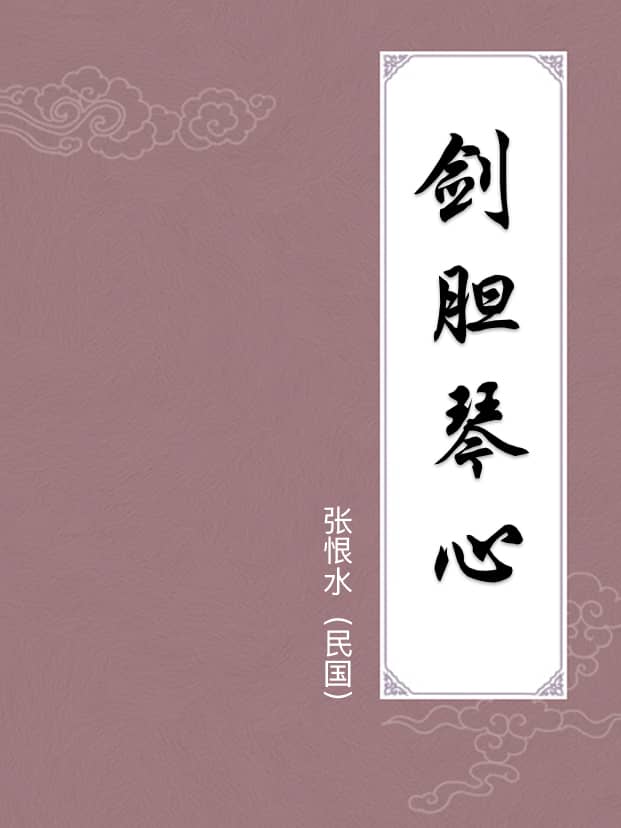他们住在饭店里,李氏父子是一间房,朱怀亮自己是一间房,振华是一间房,振华的房恰好和李氏父子的房对面。这时两位年纪老的人出去了,李云鹤在饭店里闷得慌。这天上午,在书店里买了几套书,便拿了一套,横躺在床上看。看到得意之际,不觉脱了鞋子,架着脚在床上摇曳起来。振华由房里出来倾洗面水,却看到李云鹤架起脚板来,把那双袜底穿出两个大窟窿。一见之下,不由噗嗤一笑。倾水回来,斜靠着门,看李云鹤嘴里念得哼哼有声。脚板还是尽管摇曳着,把那袜底垂下来的一块布,摇得一摆一摆。振华踌躇了一会子,便轻轻的咳嗽两三声。李云鹤一抬头,将书丢下了,便坐将起来。笑道:“大姑娘没有出去?”振华见他已踏了鞋坐起来,这话没来由,又不好说,不觉倒笑了。李云鹤见她这一笑,平空而来,摸不着头脑,也就跟着一笑。振华将牙咬着下嘴唇,勉强忍住了笑。问道:“李先生,你们出门的时候,衣服鞋袜,只洗换不缝补的吗?”李云鹤道:“自然也缝补的,不过不是时候忙得来不及,就是找不着人补,总是模糊过去了。”振华道:“你和我一路出门,不能算找不着人。我虽不能挑花绣朵,但是打个补钉,缝个袜底子,这很容易的事,不见得不会。”李云鹤拱了拱手道:“多谢,以后我要破了衣服,破袜底,我就要烦大姑娘的驾了。”振华笑道:“不必谈以后,目前你就该烦我的驾。”李云鹤听了这话,想起刚才振华一笑大有原因。便笑道:“我衣服哪里破了吗?”说时掉转头,就周身去找伤眼。振华身子向后一缩,缩到门限里。笑道:“不在衣服上,脱了鞋子找一找罢。”说着一扭头,格格笑个不了。
李云鹤大大难为情,连忙走回去,将鞋子脱下来一看,可不是袜底破了两个窟窿吗?这才恍然大悟。因自说道:“朱大姑娘说了半天的话,却是绕了一个大弯子,要给自己补袜子。”于是换了一双干净袜子,却把那破袜拿在手上,要向振华屋子里送。送到门口,一想事情不妙,又退回来了。振华看见笑道:“你拿来我补就是了,客气什么,又要拿回去。”李云鹤站住了脚笑道:“不瞒姑娘说,这袜子是穿得好些日子,忘了换去。现在恐怕有些气味,不便让大姑娘补。”振华笑道:“你这人倒有自知之明,有气味也不要紧,我不会先洗后补吗?你丢在那椅子上罢,让我给你先洗一洗。”李云鹤当真就把袜子丢在椅子上,因道:“我父子二人的性命,都是姑娘救的,你姑娘又这样和我们客气……”说到客气两个字,自己觉得有些不对,这并不是客气。但急忙之间要想找句话来更正,也是来不及。忽然之间,就停顿了。振华笑道:“洗一双袜子罢了,很轻微的事,这也用不着谈些什么报恩报德的话。”李云鹤原未便走进振华的房,只站在门口和她说话,便一手扶了门拴,斜靠了门笑道:“我和姑娘认识这样久,受姑娘教训真是不少。姑娘为人十分痛快,有话便说。我原来那种酸溜溜的秀才气,让姑娘治好了许多。我若是有姑娘这种人常常拿直话来指教我,将来我一变二变,也会变得像姑娘这一样的痛快了。”振华笑道:“那很容易呵,你跟了我爹爹去学艺,我们常常见面,我就可以常对你说痛快话了。但是我这种说话,是得罪人的,你不讨厌我吗?”李云鹤道:“古人说寻师不如访友,有朱老爹这样的老师,又有大姑娘这样一个师妹,还有什么话说?但是也不必一定要跟朱老爹学艺……”他说到这里,也不知应该怎样一转,就这样站住了。
振华见李云鹤不好意思,也不去管。自去舀了一盆水进房来,将他的袜子,洗得干净。然后送到饭店后一个小天井里,放在一条凳上晒。店伙计看见,便道:“大姑娘,已经快没有阳光了,晒在这里,也是不容易干的。到了晚上,投店的客人多,来来往往,也怕碰了人,你了如在屋子里悬着,明天再晒罢。”振华踌躇了一会子,只好把原物带回,走到房门口,一想:自己屋子里,晒上一双男人的袜子,究竟不大好。便站在李云鹤房门口笑道:“李先生,你的袜子我给你洗了。我屋子里不大透风,还是在你自己屋子里晾上,晾干了再拿来,我就可以和你补齐。”李云鹤连忙出来一拱揖笑道:“真是对不住,那样的破袜子,倒要姑娘给我拿去洗。”振华将两个指头,夹住袜子尖上提了。笑道:“咳,你接过去罢,这哪里值得你作上许多揖!”李云鹤仍然道谢不已。振华道:“你这人太罗嗦!”说毕,将袜子一抛,由李云鹤头上抛了过去,直抛到他的枕头上。李云鹤口里还叫多谢,振华只一转身,已不见影子了。李云鹤将袜子在床上拿起,便搭在椅子靠背上。背了手在房里踱着,口里不觉把“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几句诗,唧唧哝哝念将起来。口里念着,踱来踱去,就忘了神。
房门一推,李汉才由外面进来,却和他撞了一个满怀。李汉才道:“趁着无事,正可以在南京城里城外游览名胜,你一个人在房里踱来踱去,又在想什么?”李云鹤多少中了些子曰诗云之毒,却不肯欺瞒他的父亲。但是自己心里所思慕的事,又怎能和他父亲说,也不过一笑而已。因问道:“你老人家去找韩家的,找着没有?”李汉才道:“韩广达这人做事太痛快了。他今天有了钱,今天就走了,连亲戚朋友,都未曾辞行。我们找到他家,他母亲出来见了我们,说已经走远了。”说着,两手一扬,向椅子上坐着一靠道:“这种人难得呵!”李云鹤连忙抢上前,扶住他父亲道:“靠不得!靠不得!”李汉才回头一看,原来椅子背上,放了一双湿袜子,便笑着站起来道:“好好把袜子洗了作什么?”李云鹤道:“不是我自己洗的,是朱大姑娘给我洗的。”李汉才道:“这更不对了,你一双破袜子,怎么好给人家大姑娘去洗?”李云鹤道:“我哪里敢请大姑娘洗,原是大姑娘自己要洗的。”于是就把洗袜子的经过,对他父亲从头至尾一说。李汉才摸着胡子微微笑了一笑,点了点头道:“这姑娘人是很好的。其实她是我们的恩人,我们的恩还没报,我们怎好再去累人?”他一个自言自语的,不觉却在屋子里也踱将起来。
朱怀亮正在屋子外边走过,把他父子二人所说的话都听了,一个人站在天井里,也就不住的掀髯微笑。李汉才一开门出来,见朱怀亮手摸着下颏,抬头望天,便搭讪着问道:“朱老爹又在看天色,打算怎么样?看好了天色,打算回府了吗?”朱怀亮道:“我们这回出门,原没打算过多少日子,现在已经有三个月,天寒地冻,客边实在没有意思。我想回去过年了。”李汉才道:“朱老爹要走,我也是要走的。但不知老人家哪一天走?”朱怀亮道:“明天耽搁一天,后天再耽搁一天,到大后天,我总可以走了吧?”李汉才正要说时,振华姑娘忽然由屋子里跑了出来。笑道:“爹,你决定就是这样走吗?怎么在事前一句也没有告诉我。上次到南京来,什么地方都没有玩到;这次到南京来,又玩不到,那要算白到南京来一趟了。”朱怀亮笑道:“这样冷天,你还想到雨花台,游莫愁湖吗?”振华道:“有什么不能去?在大雪地里,我们还渡过江来哩!”朱怀亮道:“我原是这样说,你若是一定要在南京玩两天,我可以多耽搁些时候。”振华笑道:“你老人家说了要算话,可不要骗我哩!”朱怀亮道:“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也值不得骗你。”.李汉才听了朱怀亮要走的话,站在屋外着急;李云鹤听了这话,站在屋子里着急。但是心里虽然着急,却没有法子挽留得住。现在他父女二人,倒是自己留住自己,这就用不着旁人家去劝驾了。李汉才便对朱怀亮道:“你虽有几天走,我们也就不久要分手了。我想请你今天晚上到酒楼上喝两杯,赏不赏脸呢?”朱怀亮听了李汉才要请他酒楼上喝酒,脸上却露有三分微笑。便道:“这倒是我愿意的。但是我看令郎的酒量就有限,老先生的本领怎样,能和我老朱拚上一二百盅吗?”李汉才道:“今天晚上我请朱老爹一个人喝酒,用不着别人。”朱怀亮笑着点了点头,说是一定去。
到了晚上,李汉才多多带了几两银子,穿好衣衫,便先到朱怀亮屋子里来奉请。朱怀亮本来是愿去,李汉才这样恭请,更是要去了。二人一同上街,刚刚也是灯火上街。等到喝了酒后回来,已经快到三更天了。振华先因为父亲没有回来,还未曾睡。这时父亲一回来,她便走到这边屋子里来伺候条水。一看见她父亲满面通红,颈上却是紫色,露出一根一根的筋纹;鼻子里呼出来的气,老远便是酒味喷人。笑道:“我有半年多,没有看见你老人家这种样子。大概今天的酒,喝得实在不少了。那位李老先生,倒也是个海量,居然把这老酒缸子打倒。”朱怀亮一歪身向床上坐下,下巴颏向上一翘,手理了一理胡子,望着振华先笑了一笑。然后说道:“他量是没有量,今天我让他灌醉了,是有些缘故的。你愿意听这一段缘故吗?”说时,将两只巴掌,自己鼓拍起来,哈哈大笑,点了点头道:“大姑娘,你猜一猜看,老先生为什么好好的请我喝酒呢?他实在有点意思的呢!”振华听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就笑道:“我知道你老人喝酒醉了,夜深了,不要惊动了大众。睡罢!”朱怀亮伸了一个懒腰,哈哈大笑道:“明天说吗?也好。就是明天说罢。”振华让她父亲一人睡下,就不陪他说话。
到了次日,还是坐在房里,就不曾出来。到了吃饭的时候,振华才板着脸一同吃饭。这一路之上,朱李两家,一共五人,都是在一桌吃饭的。平常振华最爱热闹,有说有笑,今天这一餐饭,她可是鸦雀无声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吃过饭,她首先就离席了。饭后,李氏主仆三人,一同出去游览去了。朱怀亮将振华叫到自己屋子里来,笑着先让她坐下,然后笑道:“这一件事,你应该知道的。就是那李先生父子,倒要和我们联亲。”说到这里,朱怀亮就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眼光也正了,望着振华的面孔。振华见父亲这样郑而重之的说话,也就不敢像平常一样调皮,便低了头,静静坐着,听她父亲向下说。朱怀亮道:“我有这一把年纪,你是知道的了。俗言所谓风中之烛,瓦上之霜,知道哪一日死?设若一日不幸,我两脚往那里一伸,只剩下你一个年轻的姑娘,孤苦零丁,你又靠着哪一个人?倒不如趁我没有死之先,把你安顿好了,我才好放心。不过这一件事,不能鲁莽从事,总要看看人家如何,人才如何,是不是可以和我们联亲?论到这李氏父子,第一是为人厚道,的确是个君子;我们这种人家,难道还望荣华富贵的门弟不成?只要是清白人家,良善君子……”那朱怀亮道:“咦?我和你说话,你倒睡着了!”振华倒不是睡着了,她听她父亲说话,置之不理,固然是不好;光听父亲说,翻了两眼望着他,也是不好。所以索性低了头,右手剥着左手的指甲,默然不语。直到朱怀亮问她睡着了没有,她抬起头来笑道:“哪个睡着了呢?”朱怀亮道:“你既没有睡着,我问你的话,你听见没有?”振华道:“我一不是聋子,二又不隔十丈八丈远,怎么听不见?”朱怀亮道:“你既然听见了,那就很好。我说的话,你意思怎么样呢?”振华又无言可答了,低了头,还是剥她的指甲。朱怀亮道:“我也知道,小李先生是个文弱书生,和你有些谈不来。”振华突然站了起来,将脸一转道:“我几时说过这话?”朱怀亮笑道:“你原不曾说这话,我见你有些不大愿意的样子,以为讨厌他是个酸秀才哩!”振华起了一起身子,正想说什么。因见她父亲望着她。把话又忍回去了。朱怀亮道:“平常你是嘴快不过的人,这倒奇了,总不见答应一个字。”振华见她父亲逼得厉害,索性不说了,就起身回她自己房里去。朱怀亮着那样子,似乎可以答应。料到硬作了主,是不要紧的。等了李氏主仆游览回来,故意对他们露出高兴的样子。李汉才见朱老头子满面是笑,也就明白了,也是望着他嘻嘻发出笑容来。朱怀亮道:“你们玩得怎样,有趣吗?”李汉才两手拱着高举过头顶,连道:“很是得意,很是得意。”李云鹤虽然口里不曾说什么,然而也是满脸春风的,只管笑着。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振华说是头痛,要躺一会子,不来吃晚饭。饭后,朱怀亮走到振华屋里去。见她对了一盏孤灯坐着,右腿架在左腿上,两只手十字互交,抱了右腿,只管向灯焰上看着,又望着那墙上的影子。朱怀亮一进来,什么话没有说,她一低头,先就笑着红了脸,一阵羞晕,一直晕到颈脖子上去。朱怀亮道:“你为什么不吃饭?”振华笑道:“我头痛。”朱怀亮道:“胡说,你也能说,也能笑,哪里有什么头痛?这会子你不吃饭,到了半夜,你要是饿了,这饭店里是没有地方去找东西吃。”振华道:“半夜里吃不到,这个时候,总有得吃的。赶快罢,就趁着饭是热的,叫伙计送到房里来吃。”朱怀亮只有一个姑娘,不能不让她恃着几分娇宠,也就由了她,将饭送到屋里来吃。在一边看时,她一口气倒吃了个三大碗。朱怀亮笑道:“你这是有病的人?一吃就是三大碗,若是没有病呢?”振华笑道:“那也是三大碗。”朱怀亮正着脸色说道:“我们和李氏父子共过患难的,也就可说和家人父子差不多,一路相处得很好,现在既然加一层亲戚之谊,更要随便,何必还要这样藏藏躲躲?同住在一家饭店里,总不免彼此见面的。若是这样一躲一闪,见了面更是难为情了,还是大大方方的罢。”振华一顿脚,头一扭道:“我不知道。”
这边屋子里,朱怀亮说得他姑娘杏脸生春;那边屋子里,李汉才老先生,觉得是可以公布的时候了。也就和他令郎李云鹤,把和朱家求亲以及朱老爹慨然答应了的经过,说了一遍。说毕,脸色正了一正道:“像朱老爹这样的人,我们是不能把他当平常人看待的,就是他的姑娘,也可以说是一个女丈夫。我很喜欢她不带平常妇女那种小家子气象,你不要以为她能提刀动仗,不能够治家。”李云鹤虽然是正襟危坐,静静向下听着。李汉才说到这里,他就忍不住笑道:“我何尝说过这种话呢?”李汉才道:“我也知道,你不曾说话。我总觉得心里有点挂虑这层,以为他或者不能治家。只要心里原来明白,那更好了。”李云鹤听父亲的话,不由得只是微笑。李汉才道:“朱老爹也说了,我们一言为定,不要拘那些俗套。大家都在饭店里。突然认起亲戚来,也怕人家疑心,大家还是照平常一样,让我来定个日子,就借夕照寺庙里,你去拜见岳父。我们再放下一点定礼。”李汉才说一句,李云鹤就答了一句是,心里这层欢喜,简直没有法子可以形容。依着他的心事,恨不得跳上两跳,才可以把满心的乐趣发泄出来。当天晚上,也就不解是什么缘故,自己一点儿睡意没有,在床上总是睡不着。只想到将来成了婚,怎样可以和她学些武艺,又教她一些为妇之道。由上半夜里一直想到鸡啼,都不曾睡稳。
正在朦胧之际,却听得朱怀亮屋子里有些响声,连忙爬下来,开了门。朱怀亮屋里已经点了蜡烛,由门缝里放出火光来。他一开房门,李汉才也就醒了。李汉才见李云鹤开门,就问道:“对门朱老爹到这时候还没有睡吗?”李云鹤道:“大概没有睡,他屋子里还点着灯呢。”一句话未了,朱怀亮屋子里的门就开了。朱怀亮轻轻走出来,反手带上了门,便踱到李汉才屋子里。这屋子里,也就亮上烛来了。朱怀亮衣服齐全,果然不像曾睡了的样子,他对李氏父子笑了一笑,点了点头,便递上一张纸条给李云鹤,他又转身回去了。李云鹤拿了纸条,在灯烛下一看,那条上写道:
前二日,有同道二三人,曾在制台衙中,携去寿礼不少。因为长江上游,同道穷兄弟甚多,打算变卖周济也。南京官场追究甚急,捕快四处打探,至今未休。今晚龙岩老师到店中来报告,我辈自江北来,颇易为注目。老汉何惧,只恐连累贤父子耳,因此不曾安睡。通知贤父子,即刻收拾行李,天亮便起程,我父女当相送至城外十里亭,一切在路上再谈。
李云鹤一看,不由心上一阵发热,个个毛孔向外冒热汗。捧了纸条,作声不得。李汉才也不知道什么事,接过字条一看,才明白朱怀亮在南京站不住脚。读书的人比江湖上的朋友,自然要小心一层。朱怀亮说是要走,当然不能停留。连忙收拾行李,捆扎停当。一面叫醒李保,通知店家,结清帐目。这陆道上的客人,起早歇晚,原是常事。所以李汉才父子说是要走,饭店里却也不以为奇,便点了蜡烛和他们结帐。
帐目结完,天色则是黎明,李氏主仆就要上道。朱怀亮胁下夹了一把行路伞,便来送行。振华也起来了,垂了头,跟在她父亲后面,一句声也不作。李汉才心里明白,就不曾谦逊。朱怀亮倒是先说:“李先生,客边聚首一场,我送你一程罢。”李汉才假答道:“这就不敢当了。但是一路之上,我们说说也好,不过……”说到这里,便对振华望了一望,那意思好像说是不敢当。朱怀亮道:“女孩子也让她送一送老伯罢。”振华正想说一句话,说到口头,嘴唇皮动了一动,又笑了一笑。一行五人,也就不再多说,一路走上江南大道。一路之上,李氏父子在前,朱氏父女在后,李保挑了一担行李,走在最后。振华在一挑行李之前,走得却是较别人慢,常常让李保的行李撞着了身后。李保笑道:“大姑娘你是会走路的人,怎么倒走不过我?你走上前去一步罢。”振华回头说道:“你不说自己挑得不好,倒说我路走得慢?”朱怀亮向后退一步道:“你就上前如何?”振华却一扭身笑了。原来朱怀亮的前面,就是李云鹤。朱怀亮不由得将手理了一理胡子笑道:“你怎么也是这样不大方起来?”李云鹤在前面走着,听到心里自是欢喜,不过说不出来罢了。
越走天色越亮,到了十里街一个风雨亭边,大家走进来歇下。朱怀亮先就说道:“这回事,两方都是出其不意,一点不能预备。至于我们的两家婚姻,有言在先,一言为定。我们两边也不必要什么聘礼定礼,随便在身上解下一样东西,就可以了。”李汉才道:“呵哟,那如何行得?未免太不恭敬了。再说云鹤是个书呆子,从来就不象花花公子一样,身上带个什么?这样罢,行李里面,还有一点文房用品。”朱怀亮笑道:“那太累赘了。”说时将手上抱的伞一抽,由里面抽出一柄短剑来,将手托着,交给李云鹤道:“贤侄,这一把剑,是我少年时用的,这几年就交给女孩子了。一来交与贤侄,作一个信物;二来这种东西,也是文雅之物,读书人也可以把来当古玩。请你带着,以壮行色。令尊以为没有随身带的东西,很是为难,我倒看中了两样东西了。”说着,一指李云鹤戴的瓜皮小帽道:“那不是?”李汉才恍然大悟,也就鼓掌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李云鹤这帽子上缀了一块小翠翠牌子,两粒珍珠,东西虽不高贵,倒是真的。李云鹤将帽子取下,把上面缀的两粒珍珠,从从容容摘下。振华在一边侧眼看见,便道:“爹,我看有两粒珠子,就行了。帽子上光秃秃,也不好。”朱怀亮也就连忙说道:“是是,有两粒珠子就行了。那片玉牌子还让它缀在帽子上吧。”李云鹤听说,果然停住了手不去摘下。手掌上托了两粒珠子,就递给朱怀亮。他接过去放在裤袋里,笑道:“很好,这定礼很不俗。”李汉才笑道:“我们这就是亲戚了,云鹤上前拜过岳父。”李云鹤听说,就朝着朱怀亮拜了四拜。朱怀亮含笑弯着腰,将他扶起。李汉才也走过来对朱怀亮作了一揖。振华扶了亭子上一根柱子,却背过脸去,看亭子外的风景。朱怀亮道:“振华也过来见公公。”李汉才连连摇手道:“这是大路上,有人来往,很不合适,不必拜不必拜。”朱怀亮道:“我们两家既成了亲戚,放了定礼,若是孩子们不在当面,自然不相干;孩子们既在当面,那却不能当着不知道。振华过来行礼。”振华还是背立着,头却低了下去。朱怀亮放重了声音道:“怎么样?难道你这大的人,一点礼节都不懂吗?”
振华原是有些不好意思,听了她父亲这话,她可有些不服。就掉转身来,对着李汉才,一低头正要跪下去。李汉才笑得眼睛都合了缝,伸着两手,向前虚虚一拦。口里说:“不必行大礼了,这不是行礼的地方。从权罢!”但是振华已经跪下去了。她真个翩若惊鸿,只一贬眼工夫,又已站立起来,依然掉转身,站到柱子边去了。朱怀亮道:“你看太阳已经出山,不便聚谈,你们走吧。”说时,对着李汉才拱了拱手。李汉才踌躇道:“这回走得太匆忙了,有许多话,还未曾和亲家说。”朱怀亮道:“不用说,我都明白就是了。明年三月十五,百花开放的时候,我准送小女到府上去完婚。其余的话,不会再重似这个。”李汉才拱手道:“好,我们告辞了。亲家自己保重,在南京不必留恋,免得兄弟挂念。”于是将朱怀亮送来的宝剑,插在行李上,携着李云鹤的手,先走下亭子。李保挑了一挑行李,就开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