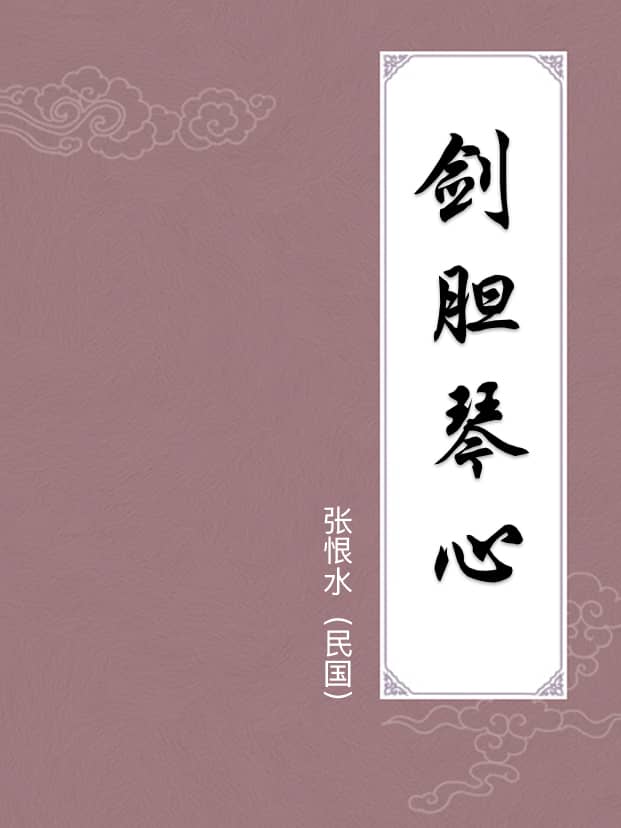全太守将孙道法送出了大门,一路摇着头走回上房。口里只顾念道:“质胜文则野,质胜文则野。”全太太见他是这样走进来,便问道:“又有什么事引动了你?把孔夫子请出来。”全太守就把孙道法刚才的言行,说了一遍。因道:“难道说做武官的人,就可以这样不讲礼节吗?”全太太道:“你可别得罪他呀!这会子,我们全仗他打土匪。打跑了,是我们坐享太平。”全太守道:“你们妇女们只好坐着打鞋底,谈谈张家招女婿,李家聘姑娘,若谈到军国大事……”他正这样说着,只见那位在这里作客的德小姐,站在全太太身边,却是微微一笑。全太守道:“姑娘,你笑什么?我这话说得有点不对吗?”德小姐说道:“我哪敢笑姨父说的不对。但是妇女们不能全是坐着打鞋底,说张家招女婿,李家聘姑娘的。”全太守点了点头道:“是呵,你就是个女学士,我怎么能一笔抹煞呢?”德小姐笑道:“姨父真是喜而供诸案,恶而沉诸渊了。”全太守连连点着头道:“上一句话,爱而加诸膝,轻轻一改,改得很好,改得有身分。”说着话时,将头摆着小圈圈来。全太太道:“你瞧瞧,谈什么你都不得劲儿,一谈到之乎者也,你就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全太守道:“你知道什么,等你懂得这个,恐怕还要读二十年书哩!”说着,笑向书房里去了。全太太笑道:“我没有那长的寿命。就有那长的寿,我为了要懂之乎者也,再读二十年书去,那是个什么算法呀!”德小姐道:“姨妈不提起读书,那也算了,提起了读书,我倒有一桩事要乘便求求姨妈。自从到了这里来,整天的是打听土匪的消息,每日提心吊胆,饭都吃不饱。现在是土匪打跑了,救兵也到了,大概事情可望平息。我一天到晚捧了胳膊坐着,闲得怪难受的。我想请姨妈给我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也好写写字。”全太太道:“一说请孔夫子,你就真请孔夫子了。西右那一带厢房都是空的,我就让当差的给你收拾收拾罢。”德小姐听了,马上带了两个女仆就到西厢去看屋子。
这地方外面是道长廊,对着石阶下的四方院子。这院子里左右排列两棵高出十余丈的大樟树,屋子里一年四季是映着绿色。屋子后开着两扇高高的推窗,窗子外又是绿竹,被风吹着,将绿竹竿子,吹得一时闪过来,一时又闪去。窗子上的绿影子,不住的摇动。德小姐一见,非常的愿意。连道:“这里就好,你们快些给我收拾起来罢。既幽雅,到上房又近,我一天到晚,要坐在这里了。”德小姐高兴得什么似的,只是催仆役们收拾。全太守知道德小姐要收拾书房,他已很高兴,就亲自上前,指点一切。不半天工夫,就收拾妥当了。到了次日,德小姐一早起来,就让女仆泡了一壶好茶送来,自己焚了一炉香,就抽了几本书,坐在临窗的一张桌边来看。越看越有味,只除了吃饭,终日都坐在这书房里来了。有一天,德小姐看了一天的书,到了晚上,还想掌着灯到书房里去。全太太笑道:“你这样大小,还是孩子的脾气,喜欢新鲜味儿。爱看书,慢慢的看吧,别把这一点劲头儿,几天给使完了。”德小姐也觉有点倦意,就不去了。次日到书房里去,却在雪白的窗纸上,发现了一行小字,乃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她忽然心里一动:这一句词却是自己心坎里一句话,何以恰好写在自己的书案边?而且这窗纸是新裱糊的,在这几日之内,都没有看见,分明是昨晚上有人写下的。这上房除了姨父,并没有第二个人懂词章,但是姨父写得一笔好殿体书,这字非常灵动,当然不见得是他写的。既不是他,难道还是前面公事房里幕宾们写的不成?那更不对了,自己纳了一会子闷儿,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于是用墨将那一行字来涂了,也不再去理会了。
这天晚上,她在书房里看书,还看到二更后,出书房门之时,将门带拢,用锁来反锁了。又过了一天,再到书房里来,却见窗纸上,又添了一行字,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一句话。这不由得她不吃一惊了,房门昨晚锁着,今朝是自己开的,决不能有人进来。这一行字,从何而来?难道还有什么幽灵之物,特意来写上这句词,暗射我心里的事不成?她仔细想了一下,实在想不出一个道理。坐着看书时手里捧着书,眼睛却不向着书上,只抬了头四面的观望着出神。正在四处张望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桩可注意的事,就是后墙向着竹丛的那两扇高窗门,却是开的。分明记得昨晚在此看书,因觉得阴凉,就自行端了一个凳子,爬着把窗户关上。现在窗户开了,当然是有人由那里进来,然后在这书案边的窗户纸上,题下那一句词了。记得由四川到汉口的时候,在船上那个姓柴的,曾和我打了两个照面。后来到了南昌,在码头上,又看见过他,莫非他跟到这里,要和姓秦的作昆仑不成?我是名门小姐,现在又住在姨父衙里,非红绡可比。就是那秦学诗,有叔父管住了他,不见得就学了崔生。让姓柴的带到广信来,只是这一句词,除了我和他,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他就是没有来,也是把这事告诉了姓柴的,有话转告我了。最好我是见他一面,当面问他几句。但是我是个深闺弱女,他是个江湖武丈夫,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见他?若是出了什么意外,却怎么办呢?德小姐这样一想,倒反而惊怕起来。既没有心看书,也饮食无味。到了晚上,深怕那个姓柴的来了,反为不美。天色一黑,她就到上房里去,索性一步也不敢到外面来了。
到了次日,天色不好,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德小姐心中有事,不由得更因此添上一层烦闷,吃过午饭,才慢慢走到书房去。可是一到书房门口,心里一阵乱跳,反是站在廊上,不敢走了进去。凝了一凝神,自己暗笑道:我这个人真是疑心生暗鬼了!这白天,又在这上房里,难道那姓柴的还有隐身术,能飞了进来吗?于是咳嗽了两声,又喊了一声女仆倒茶,然后才走进去。进书房之后,首先便注视书案前的窗纸上可有什么,恰似很明显的,那里又添了一行字。不过不是先前那句词了,乃是“若不知,何以涂抹之;既知之,何不回报之”。德小姐看了,愈加惊慌,觉得不理会他,岂不失了机会?而且辜负了人家千里奔波的苦心,要理会他,又不好意思见他,也没有恰当的地方敢见他。可是要永久不见他,他却纠缠不清,每晚都进衙来。若是让人知道了,那还了得!只她这一着急,当日急出一身病来,就发着烧热,睡在床上,不过人却是清醒的。这天下午,雨更连绵了,加着不断的风吹来,将那上房前后左右,一些树木,吹得如海潮一般作响。到了晚上,人声是静寂了,人坐在屋子里听到屋外的风雨斗树声,更是厉害。窗纸上摇着一线淡黄的清油灯光,越显得屋子都要让风雨来撼动,仿佛人在一只破船中一样。
这晚上,全太守晚饭后也是觉着风雨之声闷人,便找了一本古版《易经》,坐在灯下,细细的咀嚼。以为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候,只有古圣人经纬宇宙的大道理,可以镇定身心。正看了几页,忽听到窗外走廊下,一片惊号之声。全太守听到不由着一惊,便问怎么了,怎么了,外面答道:“有……大仙,吓……死我了。”全太守更是惊慌,连连叫着道:“来呀!来呀!”在那个的时候,官吏叫他的仆役,多是无名无姓,就叫“来呀”两个字,代表一切。两个字越叫得急促,越有紧急的事情。全太守如此一闹,早惊动了上房内男女全班仆役,大家拿了灯烛,一阵风似的,就拥到走廊下来。只见厨房里一个打杂夫子,蹲在一个屋角下,脸色白得像纸一般,只管哼着,一语不发。地下倒着一个木提盒子,盒子虽不曾揭开,却是泼了一地汤汁。大家将他扶进屋里去,盘问他时,他说提了一盒东西,走过廊下,有一条黑影一闪。先还以为是眼睛花了,仔细一看,那黑影直窜到我的身边,这才看清楚,是个有手有脚又能飞的大仙。我冒犯了大仙,大仙还踢我一脚,我哎呀一声,亲自看见他由走廊下,跳上樟树上去了。全太守手上拿着一本《易经》,正着颜色道:“攻乎毕端,斯害也已,以后再不许说这种话。有说这种话的,我就要重办。”全太守越骂声音越大,由内室里一直骂到堂屋里来。这些仆役们,虽然怕大仙,比较起来,却是更怕大人。所以全太守一喝,大家都软起来,不敢作声。全太守在堂屋里骂着不算,又由堂屋里骂到走廊下来。随叫唤捕快来,捉拿大仙。
这些捕快,忽然见府大老爷连晚召集问话,料着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大家都战战兢兢捏着一把汗。及至到了府衙,让全太守一说,才知道是府老爷要他们捉大仙。因回答道:“老爷要小的们捉贼捉强盗,小的们拚了命也是要去捉的。现在有了大仙,小的们可是不敢奉命。慢说小的们这种无用的人,就是请了剑仙侠客来,他们也没有那灌口二郎神能耐。”他们说这语时,都不住的转头来向后张望,仿佛就有大仙从屋顶上跑进来一样。全太守道:“胡说,好好的叫你们捉贼,你们倒装神装鬼。有什么妖怪?有什么大仙?你们到那二堂后身去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人的手脚印?有手脚印,那还是大仙,还是贼呢?”捕快们进衙之时,也曾在二堂后查勘了一会儿。那个手脚印,果然像是人印下来的。只是这广信地方从来不曾出这种飞檐走壁的人,突然发现,到哪里去找。要说是现在闹土匪,是由二龙山来的,这二龙山也不过是一班舞刀耍棒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半空里来去。全太守见他们站在花厅中犹豫着,他坐在凳上,突然站了起来。喝道:“你们若是不去捉贼,那就是你们和贼通同一气,将你们重办。现在限你们三天期限,三天之内,若采访不到一点消息,就仔细你们的狗腿!”说毕,将长袖子甩了一两甩,一转身子就回上房去了。
这些仆役们哪里禁得住吓,只得到次日,便把这话传扬出去,说是知府衙门闹狐仙。满衙门的人,到了晚上走路,都不免有戒心。可是为了他们过分的害怕,到处都显着有鬼怪出现。次日的风雨,依然未歇,二堂后有两个打更的,在二更以后,因雨地里不好走,便坐在倒檐下,避着雨打磕睡。刚是要闭眼,就在这倒檐上啪的两声落下两块瓦来,同时又很重的一声,落在地下。两个更夫本把闹大仙的话深深的印在脑子里,现在一惊,睁眼看时,只见一个黑影在阶石下那青苔毡上,连跌了几跌,然后才一窜窜上墙去。再由墙上一翻,才不见了。当他翻动时,墙上落下两块整砖来,将墙里的水溅起来,两个更夫脸上都溅得有了。当那黑影子在面前时,两个人吓得成了两个呆子,只管望着。现在黑影扑过墙去,眼前没有什么了,两个人这才如发了狂一般,大叫救命。衙役齐跑了来,这才知道又是发现大仙。据两个更夫说了,大家便用灯火一照,果然地下有几个滑倒的人手足印子。再看看那面墙上,却也是有人的手印,印在湿青苔上。这一来,大家都证明更夫所说的话不错,更哄传出来。
这个时候,全太守还不曾睡,觉得这事情不能含糊过去,在西花厅传全班捕快问话。捕快们看到府太爷这样雷厉风行的样子,气得是话讲不上去,彼此相看了一会子,相率走出了花厅。又绕到二堂后来,仔细看了一看。那手脚印有几个,印得清清楚楚,果然是人留下来的。便就推了两个人,亮着灯笼火把,上屋去照了一照。在屋上墙上,又发现了好几处脚印,有几处还踏碎几片瓦,若是大仙决不会这样重手重脚。当晚夜深,大家只在衙前衙后,查勘一番,见着没有什么行迹,也就算了。约了次日,大家在十字街一品轩茶楼上,共商一个办法。
到了次日清晨,这些捕快们,一早在茶楼上聚会。找了临街的一副茶座,大家向外面坐,正谈得有点头绪。这捕快班里有个范承才,却是他们队里的领袖。他衔着一根旱烟袋,两只手臂抄抱在胸前,正自出神。他的旱烟袋,忽然由口里落将下来。同时他将桌子一拍,指着楼下道:“要破这一桩案子,除非是去问他!”大家看时,只见张三公子带着一批新招练的兵,骑了马过去。范承才有个把弟余老七,也学习过一些武艺,他心里忽然省悟过来。笑道:“是了,大哥说的这话,我已经明白。以为张少爷从过明师的,一定看得出江湖上高一等人物的行藏。但是是人呢还是大仙?他能帮助我们的忙吗?”范承才道:“据我看,十成之八九是人所为。我们这种人哪里亲近得他?只好找个能手出来试试了。”大家都觉得这法子笨,但是除此之外,也无良法,于是把喝茶的时候展长。等着张三公子下操回来,大家就一阵风似的,走出茶楼,拦着张三公子的马跪下。护从有认得范承才的,就告诉张三公子,这是本城的捕快头。张三公子用马鞭指着他们笑道:“你们的事情,我明白了,你们捉不了狐狸精,要来求我,是不是?我姓张,可不是天师,你们怕挨板子,不会上龙虎山请张天师去吗?恐怕也没有用呢?”大家一听这话,分明是他很知道这事情的内容了。范承才连忙道:“少爷,这事就求求你罢!少爷既然知道,小的们也就不多说了。只是求你救我们一条命!”张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们先起来,让我今天晚上和你们到府衙前后走上一走。我生平不信什么鬼怪,你看他今天晚上还来不来?”捕快们听了这话,将信将疑,都站了起来,给他请安。张三公子也不等他们再说话,一扬马鞭子,就走开了。
知府衙门里闹狐仙的事,这时大街小巷,本来无人不晓。现在看到一班捕快围着张三公子的马这一段事,大家更觉闹狐仙乃是千真万确的了。这些捕快来求,他在马上从从容容说着大话,很像今晚上狐仙就不会出现。大家虽知道张三公子武艺很了得,不信他会降妖捉怪。今天晚上,府衙里是不是有大仙出现,那就可以看出他的本领怎样了,因此大家把这事都当了一桩奇事去传说。范承才这班捕快,相信张三公子总不会撒谎的。但是怕他和大仙交起手来,不免要上大他的当。因之这晚上,也不敢在家里睡觉,都带了武器,悄悄的在府衙前后巡哨。但是巡哨一夜,确是不见什么动静,这些捕快们也不回家,就一直到参将衙门来,打听张三公子昨晚可曾出去。据跑差上的人说,他昨晚二更前后,在衙外喝得烂辞回来,一回上房,就睡觉了,并不曾出去。这里头更不能无原由,大家就在号房里等着。打听张三公子起来了,大家就央告传号进去回禀,要见张三公子,求他指教办这案的法子。张三公子只叫范承才余老七两个人到小签押房里来,其余的都让回去。
范余二人到了小签押房里,只见张三公子向着太阳光的纸窗下临帖,二人便蹲着身子,请了安下去。张三公子将笔向笔架上一放,笑了起来道:“你们以为我把大仙打跑了吗?昨天晚上喝酒,今天早上写字,我哪有工夫捉妖?来来来!你们也来写两个大字。”范余二人以为张三公子和他们开玩笑,站了不动。张三公子遂将那支笔交给范承才看道:“要破案,就在这一支大字笔上。你们不会写字,怎样破得了案?”范承才按过那支笔,在手上却是重颤颤的,仔细看时,这笔管却是熟钢的。只得笑道:“小的实在不懂,求少爷明指教我们吧。”说着,退后一步,又给张三公子请了一个安。张三公子笑道:“我料你们不懂,我老实告诉你们罢。当我由玉山回来的时候,半途路上,曾碰到一个骑马的人,他和我马上马下都交过手,本事十分了得。我就想着,土匪窝里,不会钻出这种好角色来,但是他是由哪里来的,我倒猜不出。前两天我一人走大街上过,看见一个外乡人,站在街边买东西,声音却是很熟,可认不得那人。后来我想起来了,那岂不是和我交手的人吗?我正看着他,他一回头见了我,像是认得,就笑着说:‘张少爷不认识我吗?我请你喝杯酒去,肯不肯赏脸?’”范承才道:“这贼不怀好意了,少爷去了吗?”张三公子笑道:“那怕什么,他真是要算计我,就不去喝酒,哪里又躲得了?当时我就和他一路到酒馆子里喝酒,一谈起来,不但不是贼,而且是个大大的好人。他姓柴,单名一个竞字。他的师傅尤其闻名,是长江上一个大侠客,名字不要去提他了。他到广信来,不是为他自己的事,不过要和一个朋友作媒。和这里府大老爷,一点不相干,白扰他的事作什么?他随身没有大武器,除了一把刀,便是几十支真假笔。他倒送了我几支,我故意拿出来,看你们识不识?原来你们也不懂呢!”
说着,他接过笔去,将笔头一扭,只见毛笔头和一个短套,脱了下来,里面另露着一个尖而且白的针头。他手一扬,那笔啪的一声,插在画梁上一个双凤朝阳的凤眼睛里。范承才看到,心中暗暗喝彩,脸上自然也就现出一种欣慰之色来。张三公子笑道:“据你们看,这就了不得了,其实这位姓柴的本领,要比这个强过十倍。他站在树下,能用这个去打树梢上鸟雀的眼睛。像你们这种的人,他何须多费事,一个送你们一箭,也就了事。这是他师傅的传授。他师傅本人,能够用芦杆子当袖筋用,变轻为重,这暗劲就更大了。这种本领的人,我见了都要五体投地,我不信你们有这种本事,可以去捉他?你们可以回复府大爷一句,就说不是狐仙是个人,这人也就走了。只要府衙里再不闹事,我想府尊也不和你们为难。我自去对那姓柴的说,请他早早出境,你们看是怎样?”范余二人见张三公子说得那人如此厉害,他又保了不再来,只要无过,也就不敢望赏了。当时便谢了谢张三公子。他又道:“你们不要对人说这话是我说的,若说出了,下回再闹事,我就不管。”范余二人,只要府衙不闹事,这一层自当遵命,很高兴的走了。
张三公子于是在家里寻出一把收藏的倭刀,一个橙色葫芦,带在身边。独自步行出衙,却到西门外一家客店里来拜访柴竞,到了店中一直向房间里排闼而入。只见柴竞在桌上放了一大荷叶包猪头肉,又是一大捧落花生,手里拿了一大瓦碗烧酒,正自吃喝着解闷。一见张三公子,便迎上前来,笑道:“兄弟昨晚不敢失信,他们向张少爷说了什么?”张三公子就将对捕快说的话,叙述了一遍。因笑道:“他们就是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到这里来拜访阁下。只是阁下这个媒人,我看可以暂时不作也罢。无论那位德小姐你没有法子把她引出侯门似海的知府衙,就算你能够引出来,试问孤男少女,你有什么法子,可以送她到浙江去?”柴竞笑道:“我在朋友面前,没有答应此事则已,既然答应此事,就是国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惜。”说着,端起碗来,咕嘟一声,喝了一口酒。张三公子微微笑道:“就算你老大哥决意这样办,那德小姐年轻,也不肯放了胆子跟你走,你又当怎么样?”柴竞踌躇着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没有法子,我要是这样走了,我受了朋友之托,不忠朋友之事,那都罢了。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是一走了之,我这未免对不住自己了。可惜上次我到二龙山去,没有找着我的师傅和师妹,若是找着了他们,我的事情就好办了。”张三公子笑道:“我既然劝阁下走,我自然也有个办法,不能让你阁下一走了事。要晓得虎头蛇尾,和神龙见首不见尾,却是两件事。阁下依我办,把那位姓秦的学生找了来,我可以荐他到府衙里去做一点事。万一全府尊不允,就是敝处算个冷衙门,添这样一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幕宾,兄弟总可以作主。那个时候,再来设法做媒,当然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费事吧?”柴竞道:“张少爷,你能断定那姓秦的来了,不至于落空吗?”张三公子道:“这件事和我又没有什么相干,我若是办的不到,我就不必多此一番唇舌。我又何苦撒一个无所谓的谎呢?”柴竞把酒碗举起,就一吸而尽。笑道:“这就痛快多了,我自身在这里并没有事,现在和张少爷痛饮几杯。放下酒杯,马上就走。”张三公子于是将那葫芦放在桌上,然后把那柄小倭刀向桌上一插,笑着拱了一拱手道:“这葫芦罢了,送阁下盛酒喝。这把倭刀,真是早年进贡来的,却是出门一件轻便利器,请一齐留下,就不另送程仪了。”柴竞笑道:“这是在府上就预备好了的,分明是催我走了。有了这个葫芦,就可在城里买了酒,索性带些食物,出城五里有个玉皇阁,那里大树参天,我和少爷到那里一醉而别如何?”张三公子连声叫好,就提了葫芦出去,灌满了酒,又买了一刀咸猪肉,两只大薰鸡,用荷叶包了,提回店来。不曾进店,恰是柴竞背了包裹在店口张望,于是二人一同出城,向玉皇阁来。
一路之上,听到路上行人说话,都是说着知府衙里闹大仙的话。有的说大仙身长三丈,非常厉害。有的说,这几天大雷大雨,都是为了这妖怪,但是五部雷神,大战三日,都没有奈何他。听说后来关圣大帝亲自出马,才把那妖怪降伏了。柴张二人一路听了这话,都不由得暗笑。到了玉皇阁外,就在大树下石头上,摆上酒菜,二人席地而坐,把葫芦盖当了酒杯,传递着喝。将倭刀割鸡肉,大块的咀嚼。
正自兴酣,忽然有人在身边哈哈大笑道:“大仙在这里了!我不曾进城,倒先见着。”柴竞啊呀了一声,站起来道:“原来是师傅。”张三公子看去,见一个五十上下老者,穿着黑衣,背着包裹。脚下的大布袜子,齐平膝盖,上面沾染遍了黄泥,分明是一个走长路的。张三公子曾听柴竞说过,他最得意的老师,是长江大侠朱怀亮。看人虽然是老者,两颊还有红光内隐,正是精气内练,神光外发的原故。因为柴竞一站起来,就给他师傅行大礼,先未便插言,默然站着。柴竞见礼已毕,就回转身来,对张三公子道:“这是我朱师傅。”张三公子笑道:“果然是朱老前辈,难得到此地。”说着恭恭敬敬的三揖。朱怀亮将包裹从肩上溜下来,他搓着两手,向张三公子脸上注视着。笑道:“这地方不会有多少人和我徒弟交朋友的,莫非这是张参将大人的少爷吧?”张三公子谦逊一番,也就请他席地坐下。朱怀亮对柴竞道:“我上个月送你师妹到皖南去完婚,就听到这边二龙山起事,道甚传言,说有我的朋友在内。我就不相信,因此独自到这广信来,打算去看看。不料今天一路之上,就听知府衙里出了大仙,闹得如何如何,我就有些疑惑。现在看到了你,莫非是你干的?”柴竞因就把自己由四川出来,和秦德二人同船,以及受了秦学诗之托,和他们作媒的话说了一遍。朱怀亮道:“既是张少爷能帮你的忙,这事不愁不成功。由这里到浙江,要穿过玉山县,我现在没有你师妹挂虑,闲云野鹤,哪都可以去,我就陪你到浙江去走一趟。这玉皇阁外有两家小客店,我这几天走得累了,今天权且在这里歇息一晚,明天再走罢。”柴竞本也无一定行期,就依了师傅的话。三人将酒菜用完,柴竞向张三公子拱手道:“诸有打搅,不劳久陪。阁下衙中有事,就请自便,半月之后,我们再相会罢。”张三公子一见朱怀亮,遇到这样一个老前辈,本想多攀谈几句,也好领教些武艺。转身一想,他们是江湖上人,自己是宦家之子,他们师徒会面,或有私话要说,自己夹杂在他们一处,或有不便。好在他们还是要来的,到下次会面再谈罢。于是和他们拱手而别,自回城去。
就在这时,二龙山的土匪,正在和孙道法的军队交战,浙赣边境,十分不安,过了半月,却也不见柴竞师徒回来。心想路途不好走,他们不能穿过战场,这也是人情中事,却也未曾去注意。又过了十天,那带军平匪的孙道法,忽然自前防来了一道公文,说是需要一位熟知匪情的军官,随营助理军务,就要请张参将调了张三公子到前防去。张参将见一个湘军头领会来调他的儿子随营助理军务,正平了他一口湘籍以外无才之气。当日就叫着张三公子到前面,教训了一顿,立派他到前防去。他只去了三天,却有人到号房里来三次请见。号房里说我们少爷到前防出发去了,要军事平息了,才能够回来。那人听说,就垂头丧气的走了。
这时值着黄梅天气,在江南乃是一年阴晴的日子。有一天下午,忽然起了大风,飞沙走石,终夜不息。到了天亮,飞沙里夹了几点雨,才把风息了。这一日一夜大风,广信城里吹倒树木房屋不少,知府衙门和参将衙门,是两所古署,衙里有许多古树,也有吹折的。全太守总算关心民生的,一早就派人到四城去调查灾情,同时也在衙门检点损失。不料,就在检点声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损失,就是睡在卧室里的德小姐,忽然不见了。全太守一听这话,毛骨悚然,心想难道真有什么妖怪,刮了一天一夜大风,把她摄去了?只得放了胆子,调齐十几个仆人,各拿家伙,拥进德小姐卧室去。只见床帐高挂,被褥叠得好好的,桌上一盏西式的铜胆油灯,兀自点着,灯芯草结成一个很大的灯花,这分明是未安眠以前就失踪了。德小姐所睡之处,左隔壁是全夫人房,右壁是女仆房,若有一点响动,就可以惊人的,然而却全不知道。全太守一想,像德小姐这样的女子,决计不能私奔,更也不会无故寻短见。若是让人劫了去,这上房岂是轻易能进来的?若是妖怪,自己生平就不信这件事。他想着完全不对,只将两个指头,在半空中画个圈圈,连说怪事。全夫人也是满衙内乱撞乱找,并无踪影,儿呀肉呀的,嚷着哭起来。全太守就吩咐下人,这事与体面攸关,不可张扬出去。一面传捕快马快,进衙问话,却叫全夫人不要啼哭,免得扰乱自己心事。
全夫人哪里禁得住,索性走进房来,倒在德小姐床上,抱枕大哭。她一个翻身,忽然指着帐子顶上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大家走上前来一看,原来是一张白纸,大笔涂抹,画了一些黑云。将那画揭下,仔细一看,满幅云影,里面藏着一条龙。这龙只有一个龙头,半个身子半隐半显,尾子却完全不见。纸边却有一首四言诗道:“天马行空,非妖非鬼。记取一言,神龙无尾。”太守将这十六字,默念了几遍,摇着头道:“天马行空,这是一个非常之人,如精精儿空空儿之流了;非妖非怪,自道之矣,神龙见首不见尾,然则又在何处见过他的头呢?”他自这样揣摸了一遍,只却是之乎者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其余那些幕宾衙役,都相信道是妖怪作祟,将德小姐摄去了。甚至有人说,就是河里龙王摄去的,所以画下一条龙为记。这话一传,满城风雨,都说知府大老爷有个小姐嫁了龙王了。全太守明知谣言不可信,或者是被江湖上异人掳去,也未可知。在古人笔记上,曾读过虬髯客、昆仑奴这些人传记,料得不是这些捉小偷的捕快所能擒获,责罚他们也无益,只得叫他们访访罢了。
但是事有奇怪的,同时张参将衙门里,也发现了一张神龙图,只记取一言——“神龙无尾”四个字。著书的一口气写了二三十万字,委实觉得吃力,就借那“神龙无尾”四个字,断章取义,作个结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