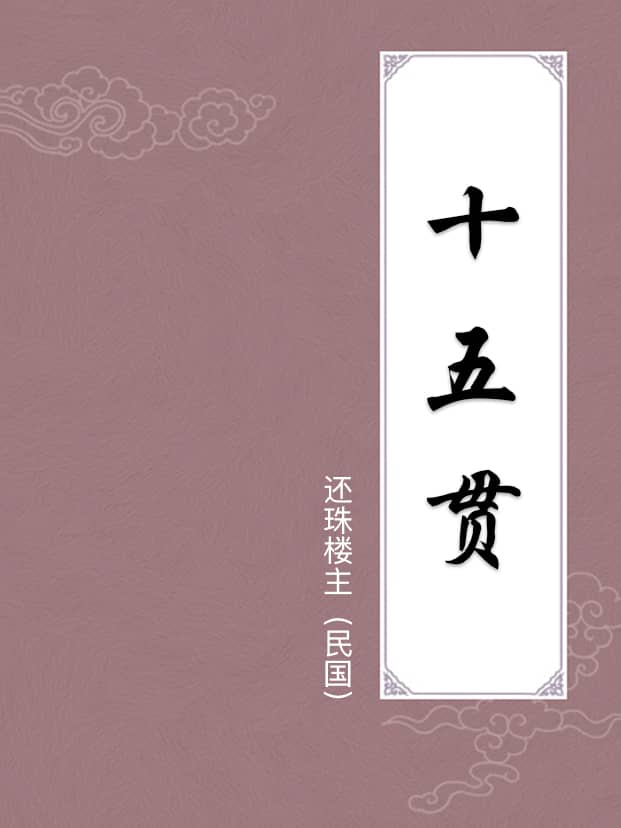况钟往回走不多远,便见任健肩上搭了两双新草鞋,由身旁越向前去,嘴里还故意咕哝道:“今天竟会扑了个空,这货色会没找着,生意也做不成,真个气人。”知他示意娄阿鼠未在当地,急于回去査问,又赶了半里来路。
赵珍正在道旁等候,见本官走来,装着问话走近,悄说:“请大人先回,下役还要到北港去看一下,今天也许赶不回来了。”
况钟知他人甚机警能干,故意把手朝北一指,笑说:“这样走就行。”
赵珍会意,忙道:“多谢先生。”说罢,脚底加快,一会走远。住健仍借买茶为由,尾随在后,进了南门,方始赶向前去。
况钟回到行馆,问知倪阿根比任健到得还早,现坐简房屋内等候,连衣服也没顾得换,便匆匆寻去。
倪阿根仗着两家亲友在斜桥住,一到便问出娄阿鼠果在当地住过,只是前天一早,人便离开,由此便未再见。赵珍命他和任健赶回报信,抄近路先到,见况钟走进,连忙下跪。
况钟将他扶起,笑道:“你辛苦了。我们有话坐下说。”说罢,见任健、况福分拿了自己的便服鞋帽和茶水走进,将手一壊,任健、况福放下茶杯,带了他的鼓板小包,算命招子退了出去。
况钟喝了口茶,便向倪阿根笑问道:“你们虽扑了个空,有点线索没有?”
倪阿根道:“这个该死的赌鬼!他大概一出城到的就是斜桥。收留他的人叫吴阿三,也是他们赌场朋友,比他先回去一天,鬼头鬼脑的连门都不肯出。前四天又来了一个姓邱的,说城里有生意做,约吴阿三同去。吴阿三本人没有家,借住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好婆屋里,本就勉强,定要娄阿鼠另找住处。后因娄阿鼠再三说好话,才答应他再住两天。上前天一大早,娄阿鼠忽说要进城凑点本钱去做生意,就离开了。吴阿三的好婆又老又聋,病在床上,什么也问不出来。我想娄阿鼠决不会进城,也许藏到他老家西桥头去了。”
况钟想了一想道:“你猜得对。娄阿鼠不会回城。吴阿三也不一定是本案凶手,否则不会不同娄阿鼠做一路,连他好婆家都不愿他住。由此人身上寻找线索,也许有望。你人熟地熟,多帮我留点心,可在城内外先打听邱、吴二人的下落行径,随时来报。明早起我还要亲自到北港去一趟,仍照今天行事便了。”
倪阿根辞出之后,况钟又把任健细问了一遍,才回上房换了衣服。又把当天的事仔仔细细想了又想,觉着新发现的三个人虽不一定是真凶,总可找出一点线索。想着想着,不觉倒在床上蒙昽睡去。醒来,见桌上灯花业已结成如意,床前光线甚暗,估计天黑已久,便起身穿鞋。
门外守候的况福闻声走进,禀道:“回大人的话,黄昏后,差人回报,萧二相公名叫萧化文,因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把祖遗大片家业荡尽,以聚赌抽头为生。邱福、吴阿三都是他的赌友,前三月劝他把这所大房子卖掉,另搬—所小房。萧二房刚卖妥,吴、邱二人忽然不辞而别。萧二之妻已死,更无其他亲属,交房那天,还向新房主强讨了十两银子,才垂头丧气,说要谋求功名,雇了一顶小轿,一个挑夫走去。左右乡邻都说他几年工夫,把大片祖产糟得干干净净,白当了两三年赌头,害好些人倾家荡产,自己却闹得连一个老婆也没剩下,这是他祖上刻薄成家的现世报。有的还说他所收房价大概被流氓骗掉,去向却都不知道。因见大人连日辛苦,今天起来太早,饭又吃得晚,想让大人多睡一会,没敢惊动。”
况钟没想到新发现这三人也都无从查找。见任健先把茶泡好,又将饭菜端进,暂时想不出主意,便先吃饭。
次日,况钟又扮作算卦先生,带了任健,未明起身,和在途中守候的倪阿根照了照面,前后零散着往西桥头那面走去。刚走过北港半里来路,快要上桥,便见前面的赵珍、任健,一前一后,对面迎来,便同走向无人之处。赵珍说:“北港这一带,姓萧姓娄的最多。谁提起娄阿鼠都摇头,说他已有两年多没回家了。”况钟问完前情,又亲往当地查看了一回地势,并代人算了两个卦。见天已不早,只得扫兴而归。
刚走上北港桥,见侧面有一片大坟地,树木甚多,坟前的石人石马业已残破。左近还有一座祠堂,规模不小,对面一座大影壁却坍倒了半边,房屋残破,炊烟不起,仿佛里面已无人居。再往前走,见林内坟头甚多,蓬蒿丛生,衰草满地,还聚着二三十人在伐树,到处都是残枝碎干。斜阳返照中显得这一座故家巨冢,分外荒凉,偶问路人,说:“这是有名的萧家坟地,祖上曾作过尚书。因为子孙不肖,家业败光,现在正卖坟树。”
连来带去这一整天,人已饥疲交加,顺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北门附近,再步行进城,回到行馆,已掌灯了。饭后打算稍微歇息,忽然接到喻子诚专人由苏州送来的一封密信。连忙拆看,原来况钟自来无锡,过于执毎隔两天必向抚、藩、臬三大宪密禀。
公文都是专人投递,大意是:“况钟到后,并未和他商议,也未派人访查,先摆架子装病。到了第六七天,才会同地方官往现场复验,随即发现了几个制钱和人家常有的两粒骰子,便认定凶犯是冤枉,偏又不能自圆其说。近日又在装病,闭门不出。明是好名心盛,自知此案人证俱全,无法反复,势成骑虎,难于交代,为此缓兵之计,使人莫测高深。本县百姓本极‘刁顽’,又为他过去虚名所惑,茶坊酒肆议论纷纷。照此情势,凶犯亲友已难保不买出人证,串通翻供。而时日太久,也许还要生出枝节,和那年苏州罢市,不让他去任一样,甚而发生别的变故。是否仰请宪台令饬况钟,不论是捕风捉影,听信凶犯一面之词妄加臆测,或真发现线索,有了反证,均须及时呈报,不应这样拖延时日,以致谣诼纷纭,滋生事端,致干未便。”并还提到“复验时,在尚未证明冤狱以前,先将主凶熊友兰的镣铐囚衣脱去,也似有过于宽纵违法之嫌”等情。臬台首被激怒,往见抚台力争,要将况钟调回,藩台也跟着去随声附和。抚台虽因已向朝廷奏报,不便收回成命,对于况钟也极不满。如今官场中均把此事传为笑谈,连一向佩服况钟的喻子诚也都代他担起心来。特地专人函嘱:“……如见此案真冤,固以速办为妙。如因一时看错,或是找不出别的反证,便应急速回省(苏州),自请处分。这样至多降调,到底还好一些。倘若旷日持久,真个发生枝节,吉凶祸福就难说了。”另外还加了一页,说现在由藩台起到常州府对他都不大高兴,千万留神。况钟把信看过两遍,微笑了笑,便自收起,也不给喻子诚回信,仍旧带了那几个可靠的人四出私访,去处都在城外,行踪无定。
光阴易过,不觉又是十来天。斜桥和西桥头,况钟已前后去过两三次,连水陆码头都由倪阿根和他代约的近邻好友吴金生去访问过,并还安了眼线。后来访出娄阿鼠以前曾在水码头上干过结伙偷骗的勾当,夜航船上的人多认得他,又命任健连向船夫们打听,均答未见。
秦古心和另一干差连去茶馆设法探询多日,也只访出娄阿鼠在况钟来到无锡的第二天早上,有人见过,连萧二和邱福、吴阿三等三人也都访査不出下落。众从人见一点眉目都还没有,全代本官着起急来。赵珍等四名捕快虽颇机警能干,因连守候带跑腿前后忙了十多天,见所访问得的情形仍和头两次一样,别无线索可寻,都觉人已逃往远方,再去乡下也是徒劳,觉着这场功劳已得不到,由不得就松懈下来。倪阿根虽然最肯出力,用尽心思,还找了个好帮手,怎么都打听不出这几个人的去向,也是无法。
况钟第六天查案回来,早就暗中行文各州府县和浙江一带,査访娄阿鼠的踪迹。这原是防备万一,并没认定娄阿鼠会逃往别处。因接派往淮安和杭、嘉、湖一带查传陶复朱的差人回报:陶复朱并无下落。据他家里的人说,近一年来,陶复朱只托人捎过一封家信,大意是,要他妻子好好度日,本人手边有点事,事完即回,不必悬念等情。由此更无音信,也不知人在何处。
况钟心想:“陶复朱査传不到,还有别的反证。娄阿鼠如不拿获,决难辨明真相,救这一个无辜少女出狱。”正在作难,忽想起:“娄阿鼠单在我到的第二天早上就不知去向,再细査他的抢当干证和秦、倪诸人所说情形,可疑之点甚多。此人从未离开过本地。现已査明他曾在斜桥吴家住过三夜,又赶回老家住了一夜,其心慌意乱,无处投奔,可想而知。看神气,许是吴家不让他住,老家又不敢久留,逃往附近乡村之中隐藏也未可知。记得第一次私访回来,过北港时,曾见附近大片坟地上有人伐树,左近还有一所业已残破的大房子,路人说是萧尚书祠堂。赌头萧二正是官家之后,虽然早把篙师巷祖遗房产卖去,但照秦古心所说‘娄阿鼠以前就常跑这家赌场,今年正月起才没有再去’的话,如能寻到萧二,也许访问出一点线索。即使本人不曾回乡,前去试上一试,总比疏忽过去为是。”
主意打定,忙命任健速往篙师巷打听萧二是否真是北港萧家的子孙,乡下还有什么亲族来往?再去相隔北门十里的陶朱里村口等候。又命况福急速命人通知倪阿根,仍照前定,在陶朱里照上一面,分头行事。并命赵珍等三名捕快,去往附近乡村中便服査访。
任健、况福分头走后,况钟吃饱早点,换上便服,把算卦的东西打成小包,悄悄掩出。绕过两条小巷,雇上一头驴,赶出北门,快到陶朱里附近,将驴子开发,趁着地僻无人,添上一件旧罩衫。正往前走,任健、倪阿根已对面迎来,悄声禀告:“方才听倪阿根的近邻吴金生说,醏头萧二是萧尚书的曾孙。萧家本是全县最有名的大绅士,可是由他父亲在日就败落起。他父母刚死头三四年,县里头还把他当绅士看待,后来田产渐渐荡尽,在家中开设赌场,和流氓搞在一起,闹了不少笑话。前月刚把自住的一所大房卖掉,便被坏人把钱骗走。才赶回乡下,打算连祖坟里大片树木和七亩多坟地卖作盘川,进京去向世交戚友求告,谋取功名。他家老坟丁萧水生,人甚忠厚,是他曾祖的书童,在萧家当佣人已经四代,因为萧家坟大开销多,赏给他的墓田原有三十多亩,还有十亩果园。前三年萧二强把果园卖掉,又把他的墓田卖去二十多亩,并将萧水生的儿子用名帖送往县衙,押逼了好几天。萧水生迫于无奈,只得把田交出。不久,他那年将五十的儿子连急带气,得病而死,只剩下一个孀居的老媳妇,随他勉强度日。这次见萧二回来,又要变卖他仅剩的七亩田,想起前仇,几乎要拼老命。后经旁人解劝,坟地树木由萧二自己去卖,下剩几亩墓田归萧水生所有。就这样萧二还把老头子留来买棺材的几两银子逼了出来,作为田价,才算了事。萧水生从此恨透了他,再不到他面前来。萧二无人服侍,自然万分不便,不料当天晚上竟来了一个帮忙的,自称姓苏,算是萧二雇的佣人,口气却不对头,并且懒得出奇。由到的一夜起,就向萧水生说好话软磨,是东西都托人代买,从来没有自己去过。吴金生听出那人的身才貌相竟和娄阿鼠简直—样。”况钟问明地势,便命任健、倪阿根分两路往萧祠堵截过去,以防此时来不及寻找捕快,万一被他警觉,因而漏网。自己仍作行路人,快要到达,再假装算卦先生前去查访。布置停当,各自上路。
况钟恐吴金生说话时稍微露出马脚,打草惊蛇,事更棘手,一口气走了十多里。正觉周身汗湿,腿脚也有点酸,当地已离萧祠不远。便把气沉稳,朝着一条通往萧祠的偏僻小路上走去。到后一看,整座大祠堂只剩下一间间的空房架,上面零零散散盖着一些残瓦,四外好些已枯黄的野麻荆棘,约有一人来高,大门仅存一扇,倒在地上;遥望里面前厅的四扇门,也歪倒了两扇;院子里的柏树,株株高矗,故家乔木依旧茏葱,人却不见一个。
取出卦板打了—阵,并无丝毫回应,再看门内院落虽极宽大,但是芜秽不堪,那地也好似多年没有扫过。不肯冒失走进,正想主意,忽然发现门边内留有几个泥草鞋印,另外还有好些足迹,仿佛里面进出的人颇多。心想:“这里除了破落户子弟,就是流氓歹人。先前不曾想到,连捕快都未带来一个。鼠辈若敢拒捕,吉凶已是难测。即使不敢,光凭同来二人,也不免要被他逃走。此后再想捉拿,定更艰难。”为难了一阵,决计孤身冒险,以算卦为名,到里面去看事行事。
进门一看,两廊房舍,外表还保留着一点原样,哪屋住得有人,却看不出。惟恐对方生疑,只得经敲卦板,并用南方口音喊道:“阿要算卦?阿要算卦?”一面似进不进,慢腾腾地走动,暗中留神查看,见到处阶沿廊栏上都积着不少灰尘,只有通往西廊一面留有足迹。暗忖:“既为办案而来,怕些什么!”刚要试探着往廊上走,忽听身后脚步之声甚急!仍装着没事人一样,口里喊着:“阿要算卦?”刚要转过身去,来人已自赶到,正是任健、倪阿根。
倪阿根首先气急败坏地说道:“这个‘赤佬’,大概是逃走了!”
况钟低声笑问道:“那萧二呢?”
任健插口道:“也都不知去向了。”
况钟问道:“这些人几时离开这里的?”
倪阿根接口又道:“少说也有两三天了。萧二用的这个人,一定是娄阿鼠!所以他买东西从来不肯到镇上去。前些日,萧水生代他在镇上买了两斤肉、一只鸡,钱也隔夜先收,还有一点剩钱。第二天不见来取,给他送去,室中已无人在。最奇怪是,萧二卖坟树,还有好几十两银子没有收齐,下余一百多株坟树,价也没有讲妥,娄阿鼠全知道,怎会就在前几天要交割时,忽然不知去向?吴金生先前话没打听完,一听出娄阿鼠藏在这里,惟恐再问下去露出形迹,忙着就往回跑。我们却闹了个空欢喜。”
况钟问知二人已往萧二室中去过,便命隐伏在外,自往里面探看,见东廊一列五开间大敞厅,里墙已多倒塌,好几处房顶均见天光。萧二住的是尽南头外有一列紫檀隔断的小间,果有一扇大门板和砖搭的床,对面放着一摊稻草,一床旧被褥,当中一张旧半桌,桌上一盏油灯,还有油瓶、粗碗、毛竹筷之类。内中一把宜兴茶壶和三个茶杯却是上品,与其他东西极不相称。
正在查看,忽然发现稻草缝中露出一段红绳。拾起一看,竟和梁大嫂用作钱串的头绳一般无二,两头绳结均已松开,上面还有一些污泥和原来打过的旧结印。拿手试了试,并不结实,用力一扯,仿佛要断,连忙揣起。再细查看,破褥子底下还压着几件衣服,单夹都有。室中脚印较多,好似曾有多人来过。靠里墙的石灰早已剥落,近地面的西墙角有几处砖缝较稀,外面有一小坛挡住,内中还有半坛米,不移开看不出来。伸手一试,那砖竟可移动。忙用炉旁火钳拨开两块砖一看,都是又厚又宽的上等水磨好砖。
随由洞内夹出一个旧绸巾裹好的银包,大小银锭约有一百三十多两,想了一想,见任健在外守候,点手唤住,命将银数重行点过,记好数目,仍照原样包好,塞进壁角小洞之内,将砖还原;并命转告倪阿根,仍托吴金生借拾树枝为由,在附近村中寻一人家寄住。如再发现娄阿鼠踪迹,随时来报,或是约人扭送到官均可。一面转命赵珍等三个捕快,除往附近乡村随时査探外,还是要注意北港这一带。
任健刚刚领命,倪阿根也由外走进,苦笑道:“共总差了不到几天,就被他逃掉,真个气人!”
况钟微笑道:“我们虽扑了个空,不要失望,我们早晚一定将他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