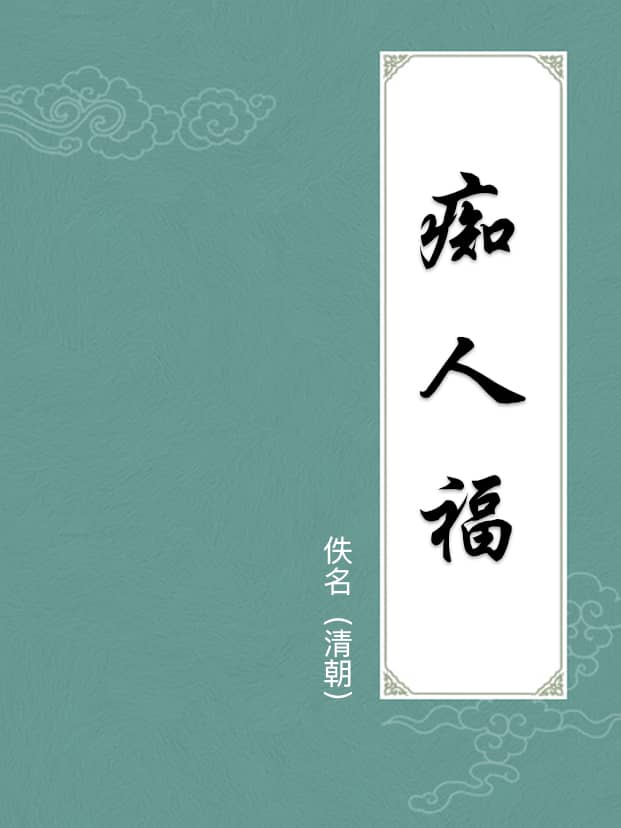及到第三日,清早起来,梳洗已毕,自说道:“奴家何氏,不幸遇了奸谋,失身非偶。进门的时节,看见那副鬼魅形骸,急欲求死。怎奈丫环侍婢,罗列满前,无从下手。又兼他装威使势,鞭挞丫环,不由人不心惊胆慑,只得借他酒杯消我垒块。醉中理乱不闻。赖有中山千日酒,醒后贞元已失,空余白璧一身瑕。仔细想来,好不令人切齿。想我前生作孽已重,实难轻赦,因此上罚来,今生伴这猿猴。就把猿猴比他,这也还形容不尽。岂不闻古语有云:沐猴而冠。那沐猴兀自解风流,预知湔沉毛中垢。谁似这猴而不沐,要傍着温柔,把脾臊引得人儿呕。当初许他的时节,并不曾查访根由,只说他是头婚正娶。及至嫁过门来,听见有木鱼钟磬之声,细问丫环,才晓得娶过一房,是邹家小姐。只为嫌他丑陋,过了一月,就往静室参禅,不肯同床同宿。所以设下诡计,又来骗我。我如今思想起来,难道那所书房别人住得,我就住不得的?少不得也想个法子出来,过去依傍她便了。假若我明对他说,就过去不成了,须要想个妙法,骗得脱身才好。避秦翻恐被秦收,那焚坑内法网难轻漏。”
说语之间,只听咳嗽之声,又听得吩咐丫环取茶。“那个厌物来了,待我装个欢喜的模样,才好骗他。”
只见北平走进房来说道:“娘子,我和你成亲两夜,辜负了多少风流。今日是三朝,那些贺客纷纷,缠个不了,一连作上许多揖,不觉有些腰疼起来。快替我捶他几拳,捏他几下。”
何小姐笑道:“你原来这等不济。”遂替他捶腰捏背一会。北平道:“难为你。这叫做妻肥能使郎君瘦。腰倒不曾捶得好,被你这笋尖样的指头一连捏了几下,又捏上火来了。没有人在这里,和你做他一出。”
向前去搂何小姐,被何小姐推开说道:“现在要成痨病了,还要来没正经。”北平道:“便做道痨平其病,我还要风而且流。”又去抱何小姐亲嘴。何小姐闻见臭气,遂呕起来。北平道:“你那里呕乎其吐,我这里涎而尚流。哎,可惜可惜,还不曾解带宽衣,我这裆里面,又早已春风一度了。这叫做花心未点春先透。”
何小姐道:“请坐了我对你说话。”北平道:“有何话说,请见而教之。”
“我闻得丫环们说,你当初曾娶过一房,叫做什么邹小姐,现在静室里面看经念佛,可是真的么?”
北平道:“是真的,你问她作什么?”
何小姐道:“此人可谓无情之极。古语道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我和你只得两夜夫妻,何等恩爱。闻得她成亲一月,也可谓恩深义重了,就舍得抛撇你过去。这样不贤之妇,为什么不休掉了她?”
北平道:“他既不情,我也不义,一世不与她见面,弃了几碗闲饭她吃,只当喂猪喂狗罢了。”
何小姐道:“我替你气愤不过,几时走将过去讥诮她一番才好。”北平道:“妙妙妙,若肯如此,我感激不尽。”何小姐道:“亏了你的度量宽宏,能受她这般讥诮。把我如此,设身处地,委实难留。”
北平道:“不曾娶你的时节,我对她夸过了大口,说定要娶个绝世的佳人。如今应了口了,你若肯过去,他看你这副尊容,也就要惭愧死了。如花娇的面貌,她一见自羞,再加你如刀样的狠话,听了更闷。”
何小姐道:“是便是了,我闻得那边有一尊佛像,须要备些香烛,先去礼拜了,然后与她讲话才好。”北平道:“这也是少不得的。我明日亲自送你过去。”
田北平哪里晓得何小姐心中之事,被何小姐一番诈伪之言,说得他天花乱坠,满心欢喜。有诗为证:
从来新妇到三朝,苦尽甜来兴始高。
今日对君开笑口,只愁乐尽变号啕。
却说邹小姐自从拒绝了田北平,与宜春二人在静室里念佛看经,不理外事。一日,在静室叹道:“奴家邹氏,自从那日逃禅之后,且喜俗子另觅婚姻,不来缠扰,终朝打坐参禅,渐觉六根清静。闻得他聘了一位何小姐,也是宦家之女,未曾过门的时节,我替那女子十分担忧,又与这村郎再三害怕,不知进门的时节,可曾吵闹,须要设出什么法子调停,方才能够上床就寝。故此吩咐几个丫环,就像摆塘报的一般,轮流探听。谁想所见所闻,甚是奇怪。头一报来说新人的面貌标致异常,比我更强一倍;第二报来说新妇合卺的时节,豪呼畅饮,不但不懊恼,且没有一毫羞涩之容;第三报更奇,竟说新人吃得烂醉,欢欢喜喜的上床安眠稳睡,直到天明,并不见一毫响动。你说这桩事奇也不奇!种种新闻,都迥出奴心逆料之外。姿容比人甚美,因甚的性格这等温存,襟怀如此宽宏。还亏他一副肚肠皮,善藏臭气。”
自己叹息未完,只见宜春一面走一面说道:
旧客出走迎新客,新亲进来访旧亲。
你今欲知山下路,须要问我过来人。
只见宜春走到邹小姐面前说道:“大娘,方才大爷吩咐,叫一面去料理香烛,一面去打扫神堂,要送新人来拜佛。”邹小姐道:“如此甚好。等她过来看是怎么样一个人儿,就有这般的度量。”
那田北平不知何小姐的就里,叫了丫环捧了香烛,他自己携着何小姐的手,摇摇摆摆,兴兴头头,走过西廊。痴心想:那邹小姐会学微生之直,有意乞怜求他,即使要同归我也不收覆盆之水。
二人走到静室,便吩咐宜春道:“点香烛来,等这位簇簇新新的大娘拜佛。”又对邹小姐说道:“请你睁开眼来把这新人看一看,这副尊容可比你强几倍么?”
邹小姐背面暗道:“果然好一位新人,怪不得他夸嘴。”
何小姐向前参拜大士,说道:“阿弥陀佛,弟子今日忏悔,伏乞把前生孽障消减。”拜完了菩萨,遂对宜春问道:“这位就是邹师父么?”宜春道:“正是。”何小姐道:“师父在上,弟子稽首。”
邹小姐道:“如今我虽在田家,已是逊位的闲人了,与你并无统属,不消行礼。”
何小姐定然要拜,遂拜下去了。邹小姐扯她不住,遂一同拜了几拜。
何小姐道:“我今莫把俗缘来说起,愿师父大发洪慈,受我来皈依。”
北平大发怒道:“好没志气,她只因没福做家婆,所以叫我另娶。你如今是一家之主,为什么拜起她来?”
何小姐道:“老实对你说,今日这番大礼,是徒弟拜师,不是做小的拜大,你不要错认了。”
对邹小姐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只因前世不修,堕了奸人之计,嫁了个魑魅魍魉,料想不能出头,情愿皈依座下,做个传经听法之人,从今以后,朝夕不离。若有人来缠我,”遂厉声道:“我就拼这条性命结识他。”
北平听了,便痴呆了半晌,说道:“怎么好好的一个妇人,走到这边,就变过了!这也好跷蹊!为甚的菩萨平空竖了眉,我劝你的声音休大厉,难道等闲发一怒,就摄得往时威!你昨日在我的面前,还数着她许多的不是,劝我休了她;如今见了面,倒要做起徒弟来了。”
对邹小姐说道:“她那张嘴是翻来覆去,没有定准的,你切不要听他。”又向邹小姐作揖道:“还仗你劝她转去。若还项缺无新吏,就是你这卸事的官儿也离不得印。”
邹小姐笑道:“我笑你难争气,泼天大话才离嘴,就要来求仗我。我替你惭愧,替你好生惭愧。”遂对何小姐说道:“奴家只因生有善愿,故此立意修行,况且又与田家无缘,一进门来就有反目之意,所以退居静室,虚左待贤。闻得新娘与他相得甚欢,正是新婚宴尔的时节,为何出此不祥之语。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可保耳根清净,若还如此,将来的静室,竟要变做闹场了,连三宝也不得相安,快快不要如此,还是转去的是。”
何小姐道:“弟子的念头已立定了,不是言语劝得回,威势逼得转的。不劳师父劝诲。”
北平道:“这等说起来,你当真不肯转去的么?”何小姐道:“不是当真,难道是当假!”北平背面暗道:“她是怕凶的,待我发起性来,她自然会转去。”回转脸来骂道:“你这个泼妇,欺负我没有拳头么?”遂摩拳擦掌对邹小姐说道:“你们不要来拉劝,等我一顿毛拳打去,断送了这个泼妇。”
邹小姐大笑,相劝道:“休要提起打字,料你这有限的毛拳,只好回下处去打。”
何小姐道:“师父不要来劝,弟子不敢求生,只望速死。等他打就是了。”邹小姐道:
“话虽说得是,当不得我见了犹可怜,怎忍得教你受这般摧折!”
北平道:“也罢,看在她拉劝的面上,且把拳头收了转来。如今没得讲,快快同转去。”
何小姐道:“若要我同回,不是你脱胎变做潘安美,就是我换骨翻成嫫姆媸。若还是各受原形,只恐怕今生断难成对。”
北平道:“我权且避一避待你好去劝他。若还劝他不转,依旧要扯你过去,问你怕不怕。”
正是:
男子汉心肠易测,妇人家诡谲难防。
有绳索系她不住,这两次走去一双。
邹小姐道:“新娘你这逃禅的意思,决与不决,可明白对我讲来。”何小姐道:
“师父是过来人,何须问得弟子。师父耐得过,当初定不过来。弟子若耐不过,如今也定不肯转去了。”邹小姐道:“讲便讲得是,只怕日子长久,你熬不过这般寂寞。”
何小姐道:“这个中之情,你知我知,又何须说出口来。论什么是非恶姻缘,悔恨已经迟了,这个迷途怎肯久滞?纵然伴孤灯,偕单影,闭长门,挨永日,也甘心受;况且有明师高道,可以倚靠,少不得莲台狮象,共坐同骑。”
邹小姐道:“这等说来,你是立意不去的了。我在此间正少一个侣伴,得你同伴,彼此都不寂寞。只是一件,我们参禅原是虚名,避秦乃是实意。这师弟之称,也可以不必,竟是姐妹相呼便了。”
何小姐道:“仅依遵命。”邹小姐道:“我和你照凄凉有这禅灯,少不得话相投了,也变愁成喜;伴孤单有这禅床,少不得梦相向了,也当鱼得水。强过似对村郎,偕俗偶,嗅奇腥,观恶状,把薄命来催。到今夜权收苦泪,且舒皱眉,把香肌相贴,较瘦论肥。我和你把门儿紧闭,须防中夜有人摧。从今后就听见了他的声音,也叫人皱眉。宜春,你把门窗仍旧紧紧的闭锁,不要使那村郎又来缠。”
话分两头。却说唐子才得了京报,收拾行囊赴任,把家中事务,一概付与唐夫人管理。想那唐夫人心事不在家务上计较,心总是两姬妾身上做工夫,立意要寻两个受主,打发她两个出去。也曾把这段心事吩咐了家中一个老院子。
一日院子叹道:“妇人诸病可治,只有妒字难医。要使妇人不妒,除非阉尽男儿。自家唐老爷府中一个院子便是。我方才为何说这几句话?只因我家老爷是个风流才子,娶着一位夫人,十分丑陋,心上气愤不过,只得另娶两位细君,一来追情怀,二来图子嗣。娶来不上半年就出门赴任去了。谁想夫人心怀妒忌,要乘老爷不在家中,遣他这两位爱姬,叫我遍谕媒婆,快寻两分人家,打发她出门,完了这桩心事。哎,夫人哪夫人,你的心事倒完了,日后老爷知道,叫我这助纣为虐的人,如何受得罪起。”
说话之间,只听得内堂唤道:“院公在哪里?”院子道:“在这边,有什么话讲?”
内堂道:“夫人问你,说前日吩咐的话,为何不见信?若再过三日没有人来说亲,就要和你算账哩。”院子道:“知道了。替我回复一声,说再过几日,自有分晓。”
“哎,夫人夫人,我闻得这两个女子娶便娶将来,不过是镜里的鲜花,水中的明月,你又不曾有实在便宜被她占去,就留在家中做两匹看马也好,为什么定要遣她出去?我笑你假人情也不放些儿空,却好似画饼也将来把饥充。把巫山卖到十三峰,才好使襄王断绝游仙梦。我想如今从了夫人,就要得罪家主;为了家主又怕得罪夫人。叫我怎么处!左思右想,好叫我踌躇莫定。”
又想了半晌,方才道:“说不得了,俗语讲得好: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得罪老爷,将来还有可原之罪;得罪主母,跟前就有不赦之条。况且夫人的性子老爷是知道的,就是老爷在家,他要打发,也只得由他打发,料想不敢强留。这蹈尾批鳞之事,做丈夫的尚且不能行于妻子,叫我做奴仆的怎么好行于主人,竟去吩咐媒婆便了。我想那两个姨娘,他的虚名空有鸾风,却真似参商夜夜不相逢。何不及早分开,省得眼波浓。须知道零星积痒也能成痛。夫人,你如今遣了出去,不知紧要,明日老爷回来,岂不切齿。就做官的人要惜体面,不好怎么样,只怕你比往常恩爱,也要略减几分。便做道顾纲常不致夺封诰,只怕你挂虚衔也要略减些儿俸。到那时悔之晚矣。”正是:
背夫遣妾理难容,叛主寻媒罚与同。
若使原情都可恕,只将罢软罪家翁。
却说田北平自从那日携了何小姐的手,同到静室,只望何小姐去争口气,不想何小姐一去又不肯回来同宿,于是气上添气,说道:“洞房花烛处处起风波,命犯孤鸾,却怎奈何。年纪二十多,依然没老婆。叫我这双手,如何权当得过。我田北平娶了一双新人,弄出两番把戏。一个方才满月,一个止得三朝,都生出法来骗走了。”
如今合起来一算,共做了三十三天新郎。在我看起来,我竟做了三十三天的活神仙;在她两个说起来,堕了一十八重的苦地狱。你说这样煞风景的话,叫我如何受得起!她们在静室之中,好不绸缪缱绻,两个没有孵的,倒做了一对好夫妻,叫我这有孵的,反替她们守寡,你说从古及今,何曾有这般诧事!难道我一个万贯财主,为这两个妇人不服,就绝了后代不成!少不得还要另娶。俗语说得好:三道为定。料想这等狡而且恶的妇人,世间也没有第三个了。只是一件,当初娶这两房,原是我自家不是,这等的一副嘴脸,只该寻个将就些的过过日子,也就罢了,为什么定要有才有貌!都是才出来的烦恼,貌出来的灾殃。如今须要悔过自新,再不可心高志大,娶一个老老实实的,只求她当家主子,连追欢取乐四个字,也不敢说起了。已曾叫人去唤媒婆,为什么还不见来。
不时,张一妈自言自语走得来田家,你说她讲些什么?她说道:“媒人主顾不须多,但愿夫妻两不和。旧人换了窠,新人往后挪。让出房来作成了我。来此已是,不免进去。你看大爷正在中堂坐着,大爷万福!闻得你与第二位新人又不十分相睦,今日唤我,还是要劝解她,还是要出脱她,还是要我另访佳人。”
北平道:“她们主意立定了,料想劝解不来。我这样的人家,也没有卖老婆的道理,被你第三句倒说着了。我还要另娶一房。”
一妈道:“这等不难。现有两个凑口的馒头在那里,任你啃哪一个。我羡你良缘忒多,未曾思娶,早有娇娥。只是一件怕你不中意。”
北平道:“哪一件?”一妈道:“这两位佳人都不是原来头了。虽然是白壁微经玷,还喜得蝇头迹易磨。”北平道:“我这个新郎也做过两次了,就是再醮的也不妨。但不知可肯嫁我?”
一妈道:“说哪里话来,这样才郎也嫁得过。”北平道:“是那一分人家,为什么就两个,你且讲来。”一妈道:“是经略唐老爷的偏房。一个是姓周,一个是姓吴。成亲不上几日,唐老爷就上任去了。大夫人慈悲好善,见她是好人家儿女,不忍留做姬妾,所以都要打发出门。”
北平道:“相貌何如?可会当家理事么?”一妈道:“周氏的才貌虽然不济些,却有治家之才,唐老爷的家事都是她管。那一位姓吴的竞有满肚文才,又标致不过。不是我得罪,讲你以前那两位夫人,就拿来倾做一绽,还没有她的成色哩。”
北平道:“罢罢罢,我被才貌两件弄得七颠八倒,如今听见这两字,也头疼起来。既然如此,那吴氏不必提起,单说了周氏罢。我年来活活受磨,都只为才生风波,貌起干戈。到如今只求免遭这风流的祸,情愿与嫫姆来结丝萝。讲便这等讲,我还要亲自相一相才肯做亲。不为别的,还怕她忒标致了,娶将过来,又要生灾起祸。休怪我这病鸟伤弓顾忌多。”
一妈道:“另有一位游客是西川的解元,约定明日去相吴氏。你既要相,也就是明日罢了。”北平道:“这等极好。是便是了,你为我一家亲事做了三次媒人,也可谓有劳之极了。”正是:
我求婚屡次相劳,你耳边莫怪哜嘈。
一妈道:“田大爷怎好说这等话来。”正是:
你既是定门主客,我何妨下顾十遭。
田北平与张一妈约定了,亲自去相亲。不知这周氏成与不成,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