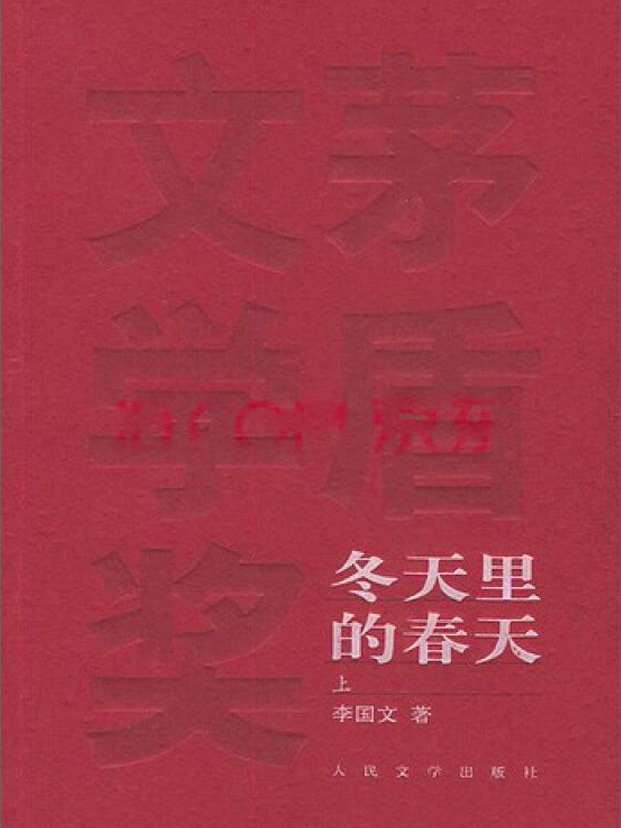石室思归土,仙携出洞天。万重沧海渡如烟。顷刻燕京,相遇至亲缘。麈战争先捷,锦衣两两旋。门庭里马自翩翩。知己倾怀,丹药救婵娟。
右调寄《南柯子》
却说那卫旭霞在云林夫人宫中宴罢,紫阳引归石室,一连住了五六昼夜。一日,心中焦躁起来,乃对张紫阳道:“蒙大仙渡凡子封来,避灾脱危,今已五六日,不识灾星曾过也未?欲往京都会试,去迟有误功名。请问大仙,归期定在何日?”紫阳道:“目下你的灾星已退,荣华渐至。今试期将迫,若到了家里起身,一时去不及了。莫若一径送你至京,会试了归家,倒觉便捷。”旭霞道:“承大仙美爱,是极妙的,但乏盘费,怎处?”紫阳道:“我渡你去,自有安放之法,不消忧虑盘费得。我且问你,昔日在雨花堂授你丹药,如今回去,要用着它了呢。”
旭霞听了这句话,惊讶果想一回,乃道:“凡子在仙界这几日,竟不晓得就是紫阳大仙!”连忙跪下拜求道:“向日蒙赐金丹,岂敢有违教命,至今牢佩在身,只这四句仙机,难于解悟,未审大仙肯明示否?”
紫阳道:“那个玄机,你的姻缘该成就时,自当显然应验,不必先晓得的。我今原备小舟在山麓水涯,渡你到京。”旭霞心中惶惑,暗想道:“倘然到京时,京中并无亲戚故眷,弄得进退两难,何以为计?”紫阳见他迟疑,乃道:“我仙家之法,是随机变化的,目下难以明言。我引你到的时节,自有奇遇,不必细究。”旭霞听罢,遂拜谢了。紫阳仍化作舟人模样,引了旭霞,纡回曲折的走出坡。将近水之际,真有一叶泊于岸边。紫阳说:“请登舟。”
旭霞心里想道:“怎的又不是前日来时泊船的所在了?”更远远一望,但见茫洋大海,波浪滔天,忽然害怕起来,乃问张紫阳道:“莫非要从此海面渡去?”紫阳道:
“正是。”旭霞战兢兢的道:“若如此,必得大舟方好。”紫阳道:“我这里艨艟巨舰是用不着的,只有那小小轻舟,倒觉便捷。你不消害怕,下船去,原是前日渡来时一般的睡在舱里,包你稳便到京。”旭霞听了,只得颤巍巍心惊胆战的下了船,遵着紫阳之言,睡于舱内。那紫阳如前替他冒好了,扯起云帆如飞的去了。正是:
仙帆破浪乘风去,弱水蓬莱顷刻过。
看官们,你道张紫阳渡卫旭霞到仙界去,好不诧异,才住下五六日,凡问已是三足年。到京时,谁知已是下科,那个吉彦霄已发甲去了,杜卿云也乡荐了,带了鹧儿,来京等会试,作寓于莲子胡同。其时二月中旬,卿云在寓无聊,偶然假寐榻上,叫鹧儿在外看门。那张紫阳竟将卫旭霞从空负至门首,对旭霞道:“这便是你安身会试处了。”
旭霞此时正惊疑未定,回头一看,那紫阳忽不见了,心里想道:“怎的几千里之遥,如此迅速?真个是飞仙,变幻英测。但是他许我有安顿之处,如何并不指示一言,竟自去了?”踌蹰四顾,皇皇失色。
不意定睛一看,只见一家门前坐一个人,在那里打吨,近前细看,竟像自己家童鹧儿的模样。旭霞想道:“这里既是京师,去苏州有三千里路,缘何我家鹧儿得到此间?但面貌何故十分厮像?”欲待要叫一声鹧儿,又恐不是,便觉不好,只得走近门首,观其动静。
谁知那鹧儿一个瞌睡撞在门上,撞痛了头皮,这才醒来。张眼一看,只见那门首立个人儿,俨然家主模样,蓦地吃惊,如拾绝世异宝,不觉乱跳乱嚷,急奔进去,叫:“杜相公,我家大相公在外边!”卿云道:“青天白日,又来见鬼。”鹧儿道:“真个是大相公,杜相公可出去看便是。”
卿云见鹧儿如此,遂急忙走出看时,实是旭霞站在那里,将要上前开口,岂料旭霞始初见了鹧儿,还着些狐疑,至此见了卿云,遂想着紫阳所嘱,“到时自有奇遇!”
之言,更不疑惑,便信口叫:“卿云表兄,你如何在这里?”卿云亦问道:“表弟你一向在何处?”旭霞道:“做表弟的几乎死于他方,不想今日在这里得见亲人之而。”卿云道:“这也奇怪得紧,人人道你不知漂流何处,今日缘何知我在此,得以寻来?”
遂同旭霞进去,相见过,那个鹧儿也不免来家主前殷勤一番,旭霞亦不免抚怜他几句。卿云道:“表弟这三足年,亏你在哪里过日?”
旭霞听他说了“三足年”,呆了。卿云见他如此光景,问道:“表弟,你一向起居如何,难道年月日时也不省的?”旭霞道:“说起来,甚是可骇。我为本山凤来仪家诱去,强逼成婚,余心不愿,坐了一夜,黎明遁出他家。本欲渡湖到表兄家躲避,岜知是早航船尚未出来,见一白头老翁泊舟岸侧,弟招而登之。他把船舱冒好,教我睡在里边。弟因隔夜通宵不曾合眼,觉得神思疲倦,竟尔睡去。不知不觉,被他渡至一僻幻之处,泊舟上岸,到那深谷磨云中住下。后复引至一万仞山椒上边,什么云林夫人宫中去,有无数聘婶仙女在此,遂召弟进去,赐宴赋诗,后复引归石室处。他道我这时有难,渡去避脱,目今灾星已退,试期已迫,故渡我到京。然在山中盘桓,只得六日耳,缘何表兄方才说三足年?”
迩来丁了父艰,回在家里。他三年前更有一段美意为着表弟,不料你不见了,遂尔中止。旭霞道:“什么事情?”
卿云道:“是年小春中旬,我同他支硎去看枫叶,偶有兴,同到那尼庵里去望望了凡。谁料适有昆山乡宦人家的老夫人,领了小姐,在庵做预修。那个老夫人是彦霄的嫡亲姑娘,叫他进去,相见过。出来返棹时,在路上谈及她们这些衷曲,他的表妹闺字叫做素琼。”
旭霞慌忙问道:“这素琼便怎么呢?”
卿云道:“彦霄知表弟尚在未娶,欲为执柯。我实欢喜无任,着实纵臾他几句。他便特至昆山与姑娘说了,竟是一诺无辞,遂写年庚付与彦霄持归。即到舍来,转叫我送到贵山,恰恰是表弟做新闻的时候。询之鹧儿,晓得了这些情由,遂去拜见凤老。他把始末根由,细细述与我听,道这节事体,都是那花遇春划的计。这日不免埋怨着他,他也似表弟一般逃走了。以后我归来回复了彦霄,即差人四下找寻表弟,靡有寻处。这时真正急得家父家母日日寝食不安,又怜着鹧儿在家孤形吊影,命我到山去,将宅子封锁好了,烦地邻看守过,随领尊使来家住下的。”
旭霞听了那番说话,道:“是这样好机会,当面错过了,今已过三载,谅必作他人配合了。”不觉放命的捶胸跌脚,一急一气,竟自目瞑口歪的死了去。倒吓得卿云、鹧儿面如土色,乱唤乱叫一番,才是气息恹恹的醒转来。
卿云道:“表弟岂不闻书中有女颜如玉,若是命里该娶佳人,不用心去求,无意中竟是得了如花似玉的;倘命中该配丑妇,随你着意拣选,哪里有美貌的到你!我道还该看淡些儿,何必如此着相!”
旭霞道:“这也不是为她,只恨着这花遇春狗才,弄这样事来,弄得七颠八倒。不惟负了彦霄兄之美意,更兼害了那风小姐的终身,于心何忍。”
卿云道:“那个花遇春,当时亦不过撺掇成了,要赚些花红钱钞,谁料表弟如此执性,弄出这大风波来。去冬被尊使在刘御史案下叫喊了,责过二十板,拟杖在狱,等候表弟着落定罪。”旭霞又听了这一席话,愈觉稀奇,不免细细查问卿云。卿云遂把鹧儿阴告遇官并瑞珠死信,细细述与旭霞听了。
旭霞乃赞叹道:“不料这鸱儿蠢然一物,倒有一片义心。那个花遇春邪谋诡计,害了风家,也该受罪一番。但是那个瑞珠小姐,为了我含愧而死,归去时必要拜祭她一番,以盖前愆。”卿云道:“这也是表弟的好心,心理上必该行的。”
说罢叫鹧儿出去买办,收拾酒肴,与旭霞压惊遣闷。不一时摄来,摆于桌上。
两人饮过一回,卿云乃道:“表弟在仙家饮了琼桨玉液,只怕凡间之昧,难上口了。”
旭霞道:“表兄说那里话来。若是今日相遇不着,就是一饮一酌,望那一家去设处。”卿云道:“正是。这个机缘,来得奇怪异常,连我也还道在梦中哩。”又饮过几杯,天色已晚,吃过些饭食,收拾毕,都去睡了。正是:
三秋离别重相见,万种风波一刻倾。
到得明早,旭霞只等卿云熟睡那边,先穿了衣服起来,坐在窗边,袖中取出画扇摊开,对了索琼之面,哭一回,叹一回,想到伤心之际,几乎又死了去。正在痴思呆想,恰好卿云起身下床来,只得袖过,拭干泪眼,乃对卿云道:“表兄也起身了么?”
卿云道:“正是。心中欣幸,不觉十分睡着了些。”旭霞道:“表兄欣章恁的?”卿云道:“我与表弟别离三载,顷刻之间,原得同堂相叙,联床夜话,纵使铁石人儿,也不免快活。”
旭霞听了,乃叹口气道:“弟之承母舅、表兄见爱,真正视为已子胞弟,并无异情,不知何日报答此恩!”卿云道:“试期甚迩,表弟之才智,虽非平常者比,然星日不弹,手生荆棘,当着实研穷一番。进场时,博得个纱帽笼头回去,尽有许多得意事儿,所以轻觑不得的呢。”旭霞道:“承表兄金玉之言。”说罢,两人各自的钻研文史,日去夜来,无少间断。
直至三月初三,已是开南选之期。旭霞同了卿云,连进三场,幸得文章俱中试官,并登黄榜。候殿试过,卿云授了户部主事,旭霞授了嘉兴司李,荣归故里。正是:
他乡重遇别离亲,共跃龙门拜紫宸。
脱却白袍更衣锦,荣归骇鬼又惊神。
却说那杜老夫妇二人,为着卿云到京会试,因是独养爱子,日日悬念不忌。后来见得报过了,是一天之喜。更是卫旭般外甥忽然间也来报中,无不错愕喜欢。吉彦霄晓得了,更加快畅,亲到门来询问贺过。杜老夫妇在家商量,他们两个回来,要备酒邀宾,做兴头事。
正说得热闹之际,只见门外那山鹧儿得意扬扬的进来,启口道:“大老爷,小奴快活得紧!梦里也不想我家主,也到京中来会试,中了进士,今同大老爷一齐归来。”杜老道:“如今在哪里?”鹧儿道:“船歇在葑门外灵官庙前。两个家主叫小奴先归。”说向太老爷道:“快些收拾家里,唤齐乐人、伞夫、旗手、轿马迎接。”
杜老听了,不觉鼓掌踊跃,连忙进去,差人去唤齐役从支值停当,唤鹧儿领出城去,迎上岸来。不一时到了门首,真个热闹之极。有一曲《黄莺儿》为证:
双贵锦衣旋,闹街坊,鼓乐阗。三檐盖伞随风转,绣鞍儿色鲜,蓝旗儿粲然。摩肩擦背人争羡,赛登仙。亲年来老,及第乐无边。
旭霞道:“母舅这番教训,愚甥焉敢有违。但婚姻之事,虽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目下论之,稍可迟缓。甥回去时,先要择吉行了葬亲大事,然后为此。”杜老道:“这也是。”当时传杯换盏,畅饮几巡。恰好抵暮了,打点旭霞到书房中去睡过,卿云也进房去了。他夫妻二人阔别了儿时,又且荣贵双全,毕竟各自畅怀,与平日之情兴,自然加倍不同的。正是:
名成博得家庭乐,不比苏秦下第时。
却说这吉彦霄,是夜晓得他两个荣归了,渴欲会晤,竟自侵早起来,打了轿,一径到卿云家来。恰好那表兄弟二人,正在那里打点要到彦霄处谒拜。使者进来通报了,两个连忙出门迎接进去,各自揖过坐定,叙过寒温一番。
彦霄向旭霞道:“谁想年兄三载萍漂,原得与令表兄同登金榜,锦还故里,亲戚朋友,复所相叙,话旧谈新,岂非吉人天相!”旭霞道:“弟于三年前,不料随犯颠沛,几乎死于他方,不得相见故人。”彦霄道:“敢问年兄屑迹何处?请道具详。”
旭霞乃将前事曲曲折折述与彦霄听了,又道:“前者家表兄道及,年兄曾欲为弟执柯,岂期无缘,有负雅爱,至今心实不安。”彦霄道:“这是家袁妹没福做夫人也。”旭霞听了,道是索琼已经适人,不觉呆坐椅上,绝口无言。
卿云见他如此光景,乃替他问道:如今令表妹曾出阁否?彦霄道:“不要说起,也是一桩极古怪的事。”旭霞惊问道:“什么古怪呢?”彦霄道:“小弟自从那日闻兄遁迹之信,回复了家姑娘,即北上了。及至丁艰返舍,乃知前年有个詹乡宦家大吉了。将及送礼,家表妹忽然生一急症,暗哑不能言,延医献神,无所不至,究不能愈。”旭霞又惊问道:“莫非令表妹兰摧玉折了?”彦霄道:“这也倒不曾,竟成一个痼疾,因此詹家就中止了。”
旭霞听得中止之言,心里想道:“虽则生病,幸而还未曾适人,犹可稍慰万一。”
不觉失声道:“这也还好。”彦霄又道:“我听见家姑娘说,病虽淹留日,喜得饮食如旧,容颜不减。若得医他开口一言,依然是个好人了。近日又有一新奇之说,家姑娘因女儿生了此疾,镇日切切愁烦,恍恍惚惚。偶一夜间睡去,梦见一个道人来对他说:你家女儿生病,可要医好他么?家姑娘道:怎的不要医好!那道人道:就要医好也不难,我四句诗词在这里,可以医好。念与你记了,写来贴于门首,自然有人来医。家姑娘梦中听熟了,觉来遂写帖外边,后面又增上一行:若有人来医好小姐者,即送酬金一百两。”卿云、旭霞两个齐声问道:“这诗,年兄可记得么?”
彦霄道:“怎不记得!”乃念道:
九日秘藏丹药,云头一段良缘。
舍外无人幻合,携来素口安痊。
旭霞听彦霄念毕,倒吓得魂飞魄散,一头裂开衣带,取这丹药出来,一头向彦霄道:“世间不信有这样奇事,难道令姑娘的梦正合着小弟仙人所授的金丹秘语?”彦霄吃惊问道:“年兄有甚仙授金丹秘言?”旭霞道:“若但说,盟兄怎的肯信,待小弟与兄讲。”便启金丹纸包,付与彦霄。
身,就道是写来哄小弟了。这是家表妹病体当愈,旭霞兄这头姻事原有可成之机。卿云乃道:“怎的表弟在京,再不见说起,今日忽然拿出来,又是暗合他人之梦的?莫非在仙家住了三载,亦有了仙术,一时造来哄我们?”旭霞道:“表兄休得取笑。”彦霄道:“敢问旭霞兄,这丹是何等仙人授你的?”
旭霞遂将三年前太白托梦,寻仙授药之说,述与彦霄、卿云听过,两人各自惊骇。彦霄道:“既如此,是天付的姻缘了。我明日就将这丹去,即与兄述这一番奇话,与家姑娘、表妹两个听,必要撮台这头亲事的了。”旭霞道:“若得如此,弟一生志愿足矣!”
彦霄欲起身告别,卿云道:“今日承兄先施,一定要屈留尊驾,以叙阔别之衷,兼为家表弟作贺。”彦霄道:“既蒙吾兄雅爱,谅不得却,只得有费兵厨怎处。”卿云乃拱彦霄到园亭中去坐下,叫旭霞陪着,自己进去吩咐支值。
不一时治就嘉肴美酒,将来罗列亭中。三人笑谈畅饮,觥筹交错一回。彦霄忽凝神定睛的思想道:“卿云兄,弟在这里细想,那四句仙机,预藏得巧。”旭霞、卿云接口道:“怎见得呢?”彦霄道:“依鄙意解起来,奇异得紧。第一句,九日是个旭字,第二句,云头一段是个霞字,这显然是卫兄的尊甫了。那第三句台外无人,岜非是个吉字,恰好台着小弟贱姓,又是我今日来谈起这事。那第四句索口安痊,家表妹闺字叫做素琼,又是个口病,明明里说小弟将此丹去与家裘妹吃了,就安痊了。这岂不是仙机预藏得幻妙么!”
旭霞听了,不觉手舞足蹈,说道:“小弟得此三年不在心上,今事机凑合,且有彦霄兄一番剖诀,真神仙能发神仙秘矣。若得仗年兄在令姑娘面前,亦如此解说一番,撮合了小弟百年姻眷,此恩此德,至死不忘!”那表兄弟两个,又轮流敬过彦霄儿杯,共谈些世事,彦霄起身,作别而去了。
却说那杜卿云、旭霞到得来日,就去答拜了彦霄,回家于合郡中乡绅任官,也都去拜谒了。旭霞遂收拾荣归故里。此时就有许多俊仆来投靠,随意收用几档,唤了极大的船只,由胥口出湖,大吹大擂的回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