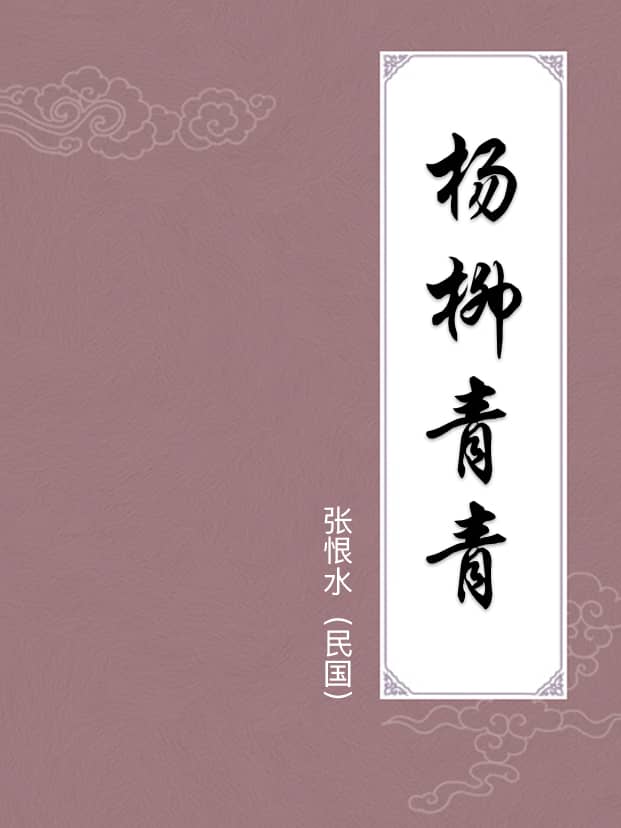赵翁接到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心里倒好生不解。这位甘先生自己投军,写信告诉我这么一位生邻居,做什么?想到这里又把信从新看了一遍,还是看不懂,也就随手放在桌上。赵翁的屋子,是和桂枝的卧室对门,中间算是隔了一间小堂屋。为终日的敞着两扇双合门,在堂屋里就可以看到靠窗户的一张三屉小桌子。桂枝在堂屋里进出,已是看到赵翁手拿了一封信,站着看了出神,似乎有点奇怪的样子,后来看到他把信向桌上一扔,便在暖屋子的白炉子上,提了一壶开水进来问道:“老爷子,你沏壶茶吗?”
说着,把三屉桌上的一把茶壶移到桌子角上,眼睛是很快的,向桌面上那信封一扫。信下款,甘缄两字,看得很清楚。同时,也就认清楚了,这是甘积之的笔迹。立刻脸上飞红一阵,心里砰砰乱跳。但自己极力地镇定着,将壶里残茶倒在痰盂里,找出抽屉里的茶叶,给赵翁新沏一壶茶。在这些动作中间,偷偷地看了赵翁两次,见他倒也一切自然,口里闲衔了旱烟袋,斜靠在一张垫了旧皮褥子的睡椅上。他向桂枝笑道:“孩子,你别为我操劳了。你的身体不大好。家里有小林这么一个粗人,凡事我都找他。”
桂枝将开水壶放在地上,斜靠了桌子站定,望了赵翁笑道:“你是太慈爱了,我这么大一个人,开水壶会提不动?”
赵翁道:“不是那话。我看你这程子,老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好像身上有点毛病。昨天你呕吐来着,今天你又呕吐了,你吃坏了什么吗?”
桂枝红着脸,微笑了一笑,摇摇头道:“什么也没有吃坏。”
赵翁道:“你可是呕吐了。”
她提着开水走了出去,低了头避开公公的视线,却没有答复。赵翁那两句话,本是有心问着的。她这样的有点难为情?越发的给了赵翁一种更深的观察。从这时起,就注意着她的行动。便是在这日同吃晚饭的时候,小林端上香油炒的菠菜,桂枝坐在桌边,闻到那股香油味,立刻一阵恶心涌起伏在桌子角上,就连续地呕吐着。赵翁道:“你这是怎么着?”
她伏在桌子角上好一阵,然后抬起头来道:“老爷子,你只管吃饭吧,我不吃了。小林这个人,真是记性不好。我老早地对他说了,不要拿香油做菜,我闻不得这味儿。”
赵翁听了这话,一切证明,他忍不住笑,就向前院里走。
隔着江氏的窗户,就叫道:“亲家太太,你怎么不去吃饭?”
江氏道:“我收拾点儿东西,就来。”
赵翁拉着风门走进屋来,见江氏正在打开着一只旧箱子,亲理着破布片。便笑道:“亲家太太,我得埋怨你,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信儿呢?”
江氏手里拿了布片,倒站着呆住了,问道:“老太爷,你说的什么事,我不明白。”
赵翁手里拿着长柄旱烟袋呢,便把烟袋斗子指了布片头,笑道:“亲家太太,你拿出这个来干什么?”
江氏也笑了。因道:“老太爷,你是瞧见什么了?”
他道:“少奶奶这一程子像病不病,像乏不乏的,我就疑心了。我虽然这一大把年纪,究竟我是公公,自强不在家,我怎么好问她?今天她可透出消息来了,前后呕吐了好几次。刚才一碗香油炒菠菜没勾引着她吐出黄水来。你是知道我的心事的,我要抱个孙子,比人家当了大总统还要高兴。她有了喜了,想吃点什么,忌点什么,你都得老早地给我一个信儿,你也当好好照应着她。抱个外孙子,你不是个乐子哇?”
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江氏道:“还早着呢。知道是不是呢?她再三地叮嘱着,不许我说。”
赵翁道:“哦!我想起来了。亲家太太,快去吧,她还伏在吃饭桌子上呢。”
江氏听说,这才赶到后院里来,将姑奶奶挽到卧室里去。
赵翁隔着房门,是不住地问长问短。一定问着桂枝要吃什么,桂枝难违拂老人家的情面,答应了吃一碗白菜煮面疙疸。汤里希望加点醋,不要油。赵翁听说,亲自下厨房,指挥着小林办。面疙疸送到卧室里去,桂枝吃了一大碗,还希望再添一点儿。这么一来。把赵翁那番思想,是百分之百地证实了。自这日起,脸上算加了一分笑容,而对于桂枝也是招待得格外殷勤。同时,也就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自强。
赵自强自离家后,照例是每星期写一封信回家,倒不问有事无事。可是在这个农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自山海关起,长城一带,军事一天比一天紧张,整个热河都让日本占领了。也就是这样过了二月,赵自强忽然停止了写信回家,赵翁写信去问,也没有答复。赵翁看了这情形,心里十分不安定,也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一个商家出身的人,向来是不大看报的。这时,甚感到消息的隔膜,就特地在报贩子手订了一份报,逐日的研究。
桂枝在初次怀孕的情形中,起坐都是不适意的,人也说不出来是哪来的那份疲倦,只是要睡觉。十分无聊的时候,也就拿着桌上的几本鼓儿词消遣消遣。在几天之后,发现赵翁屋子里带放着一份日报,也就偶然地自行取过来看看。她是个旧式女子,小时在半日学校里念了三年书,知识很是有限,就没有一个看报的习惯。自从赵家搬来,他们也是偶然看报,桂枝是偶然中之偶然捡着报看。这时,看到公公逐日地看报,她很锐敏地就感想到老人家的本意,必是在报上去找儿子的消息。当然,自己也就可以在这里去找丈夫的消息。因之自此以后,等赵翁把报看了,就悄悄地将报拿过来看。赵翁对此也没说什么。
一天,她隔了门帘子,见赵翁左手拿了旱烟袋杆,要吸不吸的,衔到嘴里抿着,可并没有呼吸。右手举着一张小型报,只管仰面呆看了。揣度那神气,已是看得入神了。桂枝放在心里,也不向他要报看。过了一会儿,赵翁照例出门去散步,空着堂屋里那张睡椅。桂枝照着老例,向老先生屋子里去找报,桌子上放着,全是前些日子的,本日的报纸,怎么也找不着。桂枝也还感不到什么特别之处。等着赵翁回来,便笑问道:“老爷子,今日的报,哪儿去了呢?我天天瞧报,瞧上瘾来了。”
赵翁道:“没什么瞧头,我随便一扔,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别瞧了。”
说着,他立刻把旱烟袋塞到嘴里去吸着,放缓了步子,向屋子里走着。看那情形淡淡的,好像是不愿把这话说下去。她心想,老头子都是这样地撅,不愿意的事,说都不肯说出来。也许是报上登的那些社会新闻,什么大姑娘跟人跑的事,不愿儿媳妇看着。不给看就不给看,倒也不放在心上。
可是到了第二日,赵翁的态度更是可疑,他由门口拿着报向后院来,在鼻梁上架起老花眼镜,一面走着,一面看着。到了堂屋里,他不在睡椅上躺着,拿到卧室里去了。桂枝正是拿了针线活,在堂屋里坐着,看到老人家脸上神色不定,便更是对着屋子里注意了去。过了一会,却听到屋子里唉了一声。随着又听到屋子仆仆两声,好像是赵翁在那里轻轻地拍了桌子。桂枝手拿了针线活,却做不下去了,偏着头向屋子里听了一会,然后问道:“爸爸,报上有什么消息吗?”
赵翁在屋里答道:“没什么,没什么。”
桂枝道:“你瞧完了,给我瞧瞧好吗?”
赵翁答应两个字:“好吧。”
那话音好像有些勉强,并不自然。因为这样,也就不敢立刻进去拿报。过了好久,赵翁没出来,也没有作声。桂枝伸着头向里面看了看,见赵翁横斜地躺在床上,两手摆着放在胸面前,仰着脸望着屋顶。便道:“爸爸,你盖上点儿吧,别招了凉。”
赵翁道:“我躺一会儿,不会睡着的,没关系。”
桂枝因他始终是这样地躺着的,虽然他年纪很大,究有翁媳之嫌,却也不便走进屋去。自然,也就不便向他要今天的报看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同桌进餐,江氏说:“老太爷,今天那个送报的来了,我在门口遇着的,他说报现在是先给钱,后瞧报,明天把报钱给他留下。”
赵翁道:“好吧,给他就是。”
桂枝道:“大概是现在瞧报的人多了,报贩子拿俏。若是拿了钱去,他不送报怎么办?”
赵翁正掀起碟子里一张烙饼,放在面前,筷子夹了大叉子豆芽韭菜在烙饼上,两手将饼卷着,一把捏住向嘴里塞着,好像是吃得很香。同时,就向江氏道:“咱们熬了小米粥吗?”
江氏道:“知道你喜欢喝这个,总是预备下的。桂枝,给你老爷子盛一碗来。”
赵翁道:“亲家太太,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吗?我家里还有两顷地,这辈子喝小米粥的钱,总是有的。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叫你和姑奶奶分开不成。干脆,你也到我们家里去住。我那庄屋虽不算大,比这屋子可强得多了。”
江氏倒不料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因道:“老爷子,你打算回保府老家去住吗?”
赵翁把那张烙饼已经吃下了。他把桂枝给他盛的一碗小米粥放在面前,将筷子慢慢地和弄着,眼光望了碗里道:“我是早有这个意思的,我搁在心里,可没有和你提过。你想,我们住在这里,除了出房钱,开门七件事,哪一项能够不花钱。若回到保府,什么全不花钱,省多了。我们住在北平,一来是为了我做生意,二来是就为着自强。现在我已不做买卖了。自强又到口外去了,咱们住在北平什么意思?”
桂枝道:“可是将来自强又调防回到这儿来了呢?”
赵翁点点头道:“当然这也顾虑得是,不过他们当军人的,东西南北调防,哪里不走。这不过是我一个计划,将来再说吧。”
说着,便端起碗来慢慢地喝着稀粥。江氏对于亲家翁这个提议,倒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桂枝在赵翁屡次看报发愁之后,忽然有了这个提议,好像是料着以后的生活有些变化。便看看公公的颜色,也是很平常,就没有把话继续的向下说。
饭后,借着送洗脸水,将盆端到赵翁屋子里去的时候,见赵翁斜靠了小条桌坐着,口角里衔了旱烟袋,只管出神。在他手胳臂下,正压住了两张报纸,便道:“爸爸,你把报瞧过了吗?”
赵翁道:“瞧过了,我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桂枝虽是和他说着话,眼睛可看着他手臂下的那两张报。老太爷倒明白了,手臂移开,将两张报拿过来,在桌面上推移了一下,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可看的,过去好几天的报了。”
桂枝站着桌子角上,出了一会神,望着他笑道:“我可以拿去瞧瞧吗?”
赵翁口衔了旱烟袋,望了那报纸,做个沉吟的样子。他已把眼光将那报头边的大题目看得清楚。一张报上是长城一带情形紧张,一张报上是华北形势或可好转。他记得这题目里面的新闻,也登载得很仿佛,这里并没有提到古北口。因点点头道:“好吧,你拿去瞧吧。”
桂枝将报纸拿到屋里,就在灯下看着,倒也找不出什么关于赵自强部队的消息,看那报上日期,可是过去五六天的报,这消息是过去的事了。不过她也知道国家大事,都登载在头两条消息里的,这消息说着长城一带吃紧,古北口必定在内。古北口不就是长城的一个城门吗?这是自强说过的,绝没有错。她捉摸了一阵,也猜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她在公公将当日的报藏起来,以及打算回保府乡下去过日子的这两点猜度着,料着消息是不大好的。心里想了个计划,次日上午,就拿了针线在堂屋里做活计。装成一个晒太阳的样子,敞开了风门,端了一把小椅子,拦门坐着,上身坐在阴处,两只脚伸在太阳里面。她低了头只管做针线活,却没有顾到别的。赵翁坐在睡椅上,衔了旱烟袋,眼光四处巡望着,也没有说什么。翁媳两人各自沉默地坐着,并没有作声。很久,赵翁才道:“你该活动活动,别一天到晚老坐着。”
桂枝微笑了一笑,因道:“我就不爱动。爸爸,你说将来咱们要回到老家去,我倒想起一件事。乡下粗活,我可全不会干呀!”
赵翁道:“乡下不照样地有大姑娘有少奶奶吗?也用不着每个人都干粗活呀!”
桂枝道:“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赵翁道:“我也就是有这么一个计划,哪天走,那还说不上。你看这时局,一天是比一天紧急。北平城大概也不是久恋之家吧?”
他衔着旱烟袋,倒是很无意地说了出来的。桂枝这可抓着一个问话的机会了,将针线活抱在怀里,眼望了赵翁道:“时局是不大好呵,报上登着长城一带全吃紧。”
赵翁衔着旱烟袋哼一声,点了两点头。桂枝道:“自强很久没有信回来,是不是部队移防了呢?”
赵翁道:“军队的行动,是难说的。我想这两天也就快来信了。”
桂枝望着他的脸色,见他的筋肉紧张一阵,好像是心里受了一下打击。她依然注视着这可怜的老人家,且不说什么,再等他加以详细的说明。赵翁不管旱烟袋里面是否有烟火,在嘴唇皮里吧吸了几下,然后点点头道:“我知道你是很挂心时局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顶大的变化,我们也不必为这事太担心,这是国家大事,光靠哪一个人着急,那是无用的。”
桂枝微笑道:“我也得配呀!为国家事担心?我只是要常常得着自强的信,我就什么也不想了。”
赵翁道:“这个我倒也想了。自强为人虽是十分忠厚,可是当了这多年的兵,在军营里行军,可十分内行。我信得过他,不会吃人的亏。再说,他良心好,老天爷也得保佑他。”
这几句极不科学的安慰话,桂枝听了,倒是很中听,连连地点了几下头。同时,她心里想着,该是报纸送到的时候了,等着赵翁出去拿报的时候,拦着门将报硬要下来,总可以知道报上说些什么。不料这个猜法,却是不准。赵翁在屋子里吸着旱烟,喝喝茶,走出门去,也只在太阳地里转两个圈子,又走进屋子了。桂枝知道老人家不愿提,也就不提。
从这天起,报也就不送来了。但是街坊来往,谈话之间,时常提到时局不好。赵翁如在当面,就插嘴说:“在北平城里住家,没什么关系。现在虽然不在北平建都,到底还是个京城呀。小日本若要闹到京城来了,那还了得?政府对这件事一定有办法的,咱们小百姓发愁什么?”
他说是这样说了,可解答不了桂枝心里那个难题。她只觉越等着要赵自强的消息,越是寂然无闻,心里实在不能着实。怀孕到了六个月多了,肚子完全出了怀,生平初次的事,又不好意思出去见人。三天两天的,就感到周身不舒服,非躺下不可。自己向来是能够忍耐的,现在就觉得所见所闻,总是不如意,很可以让人生气。但家里除了那个小林而外,一个是婆家公公,一个是娘家妈,根本不许可对之发脾气。而且这两位老人也十分可怜,不能再给他们难堪。那只有闷着吧。
她母亲江氏,可不知道她会担心时局,总以为她怀孕在身,一切都是害喜的现象。江氏虽然很有几岁年纪。可是她生平只生过两胎,经验并不丰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天下午,便把饱有经验的邻居刘家妈请来瞧瞧。这事是和赵翁说过的,他十分赞成。江氏引着刘家妈来了,他悄悄地就走出去了。在院子里还故意地打了个招呼,道:“刘奶奶,你请坐一会,让我们少奶奶代表着招待了。”
他的话越说越远,那不啻是告诉了她们,已不在院子里了。
刘家妈走进卧室门,首先看到桂枝挺出来的那个大肚子,这就笑着拉住她的手,对她脸上眉毛上眼角上,各端详了一下。她穿的是件青布旗袍,脑后挽个长圆的小髻粑儿,还压着蚕豆大的小红花朵儿呢。那十足表示着一位变态的在旗老太太。她转过身来,两手扶着大腿,向江氏半蹲着,算行了个礼。笑道:“杨家大婶儿,我先给你道喜。你家姑奶奶,是个宜男的像。过两个月,你抱外孙子了。”
桂枝搭讪着给倒茶,没有说什么。刘家妈坐在床沿上,对桂枝望着,不免问长问短。桂枝靠住桌子站着,有的答复,有的笑而不言,有的是江氏代答复了。刘家妈将桂枝拉过来,同在床沿上坐着,左手托了她的手,右手按了她的手脉,眼睛凝着想了一想,笑道:“没什么,脉象挺好。”
江氏坐在旁边椅子上,可就望了桂枝道:“可是一天到晚,她就是这样茶不思饭不想的,总是要睡觉,我看她就是终日皱眉不展的。”
桂枝道:“什么终日皱眉不展?谁害个皱眉不展的病吗?”
说着,撅了嘴,将身子一扭。江氏隔着玻璃窗户,向外边张望了一下,便回过头来笑道:“刘家妈,你也不是外人,有话瞒不了你,我们姑奶奶这个双身子,她年轻力壮,倒没什么,她扛得过去。只是外面说的这样兵慌马乱的,我们姑爷又好多日子没写信回来,所以她总是担着一层心事。”
刘家妈听到这话,脸上也就挂起几分忧虑,那在额角画着年龄的皱纹,闪动了两下。故意哑着嗓子,把声音低了。望了她母女道:“你们应该比我知道的多吧?你们家赵老先生,天天都在斜对门油盐店里瞧报,瞧完了,就唉声叹气和那掌柜的谈着。就是昨天,他说,日本人要想灭亡咱们中国,说不定北平城里都要开火呢。这可怎么好,我这一把年纪,哪瞧过这个呀!”
江氏道:“是吗?老先生有这些话,可不在家里说,他怕骇着我娘儿俩。”
刘家妈点点头道:“那倒也是,你年纪这样大,姑奶奶又是双身子,告诉你们没用,反是让你们着急。可是事情是真不大好。我家小七子,不是在西直门赶火车吗?这几天,改了行了。帮着他的把兄弟,在东车站给人搬行李。说是北平城里有钱的主儿,都搬家往南边去。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说是走快些才好,走慢了,小日本占了天津,就过不去了。”
江氏母女关着大门过日子,还不曾听到过有这样严重的消息,彼此面对着望了一下。刘家妈见她报告的消息,很是让人听着出神,也就继续着向下报告。
约莫是半小时,却听到窗子外有粗鲁的声音叫了一声妈。刘家妈回转头问道:“小七子,你今天回来得这样早。”
他在外面屋子里答道:“人家全说,今天城里怕要戒严,城关得早,这几天,西苑大营,又调来了很多军队,我怕你惦记,就早点回来吧。”
刘家妈道:“回来就回来吧,你还找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么大人,还要吃乳吗?”
小七子道:“你不在家,我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西苑不是又来了军队吗?人家要大车运子弹,由西直门车站,运到大营。”
刘家妈道:“人家没抓你们,就算造化,你还多什么闲事?”
小七子道:“人家是中央军,不白拉,拉一趟给一趟钱。怕你不去,而且是先给两趟定钱。我特意来问你,去不去?若是去的话,现在就可以去领钱,到了晚上再去拉。”
桂枝听到说大营拉子弹,又不免心里一动。掀开一个门帘,向外屋子张望着,见小七子脱了长衣,上身穿了件薄棉袄,拦腰系了,胸襟上挂了一张白布条,上面还盖有红印呢。脸上和额头上,都是汗渍透着油光光的。这就知道已是应承了给大营运子弹了。便点着头道:“七哥,你不坐一会儿?外面风声很紧吧?”
她说着话,可是把门帘挡住了下半截身子。小七子道:“咱们穷小子怕什么?可是……”
他说着,眼光射到门帘下面桂枝那个顶起来的肚子,接着道:“像姑奶奶这样的斯文人,离开北平也好。昨天在大酒缸上,和你们家老爷子聊天,他说要搬回保府乡下去过日子,这倒使得。”
刘家妈道:“回去吧,别在这里瞎扯了。”
小七子道:“你也得回家去做晚饭,吃了饭,我还得打夜工呢。”
他说着话,就走出去了。刘家妈跟着说了几句话,也就回家去了。
桂枝望了她母亲道:“听了刘家妈的话,倒让我担着许多心事。”
说着,把眉毛皱了两皱,斜靠了床栏杆坐着。惟其是这样,那出了怀的肚子,格外是顶得很高了。江氏在她对面椅子上坐着,对她周身看了一看,见她面色黄黄的,不觉噗嗤一笑。桂枝道:“人家心里烦着呢,你倒笑得出来。”
江氏笑道:“你知道什么。我听见人说,双身子的人,脸上长的有红似白,那就是怀着姑娘。反过来,脸子变得丑了,那就是怀着小子。我看你这样子,准是怀着一个小子。”
桂枝把脸色沉下来,手一拍床沿道:“你真是心宽,你没有听到刘家妈说的那些话吗?”
江氏道:“时局不好,那有什么法子呢?发一阵子愁,日本鬼子,那就不造反了吗?”
桂枝道:“不是那话,你看我们老爷子什么意思,有话不在家里说,报也不在家里瞧,事情都瞒着我娘儿俩。不要是这里有什么变故吧?”
江氏低着头想了一想,摇摇头道:“我也说不上。从今以后,我们留点儿神,也许就瞧出来了。”
桂枝沉着脸子也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倒在床上睡了。
江氏也觉姑奶奶顾虑得是,等着赵翁回家来,老远地就看到他把眉毛和脸上的皱纹,郁结到一处,两手回挽在身后,倒拿着旱烟袋,进门就先咳了一声。在外面屋子里并没有坐着,直接就回卧室去了。当日和小林做好了晚饭,赵翁说是有点儿头晕,桂枝是照例着闹着胎气,都没有上桌。江氏勉强地吃了一碗面条子,也就走到桂枝屋子里来,见她躺在床上,便问道:“今晚上你又不吃点儿东西吗?”
她和衣躺在床上,身也不翻,随便地答道:“我心里烦得很,你别问我吃什么不吃。你和我少说几句话,我就谢谢你。”
说毕,扯开叠着的被子将身子盖了。一点也不作声。江氏在屋子里静静地坐了一会,既没有话可说,又没有什么事可做,静坐了一会,到前院里自己家里去收拾了一会,又到桂枝屋子里来。桂枝躺着,微微地有点呼声,似乎是睡得很香了。江氏坐在床边上,给桂枝牵牵被子,塞塞枕头,也就在她脚头和衣睡了。
桂枝虽是不作声,却是不曾睡着。斜躺在枕头上,不断地想着心事,也不断地静听着窗子外的响声。这夜色也不算深,却仿佛由半空里传出一种嘶嘶的声音。那正是似剪的春风,由前院的老柳树梢上经过。这是白天不容易听到的声音,由这声音上,可以证明夜色的寂寞。她回想到去年这个日子,和赵家还在提婚的时候,而自己还是个黄花幼女呢。那时,身子是自己的,虽然是不大出门,可是这颗心却是海阔天空,不受任何拘束。到了现在的这个身子和这条心,全是赵自强的了。赵自强现时在哪里,却不得而知。也许现时已不在人间了。假如真是这样,肚子里还揣着个小自强未曾出世呢。那怎么办呢?正想到这里,静寂的夜空里,却咕咚咚传来一种车轮的转动声。同时,也就听到马蹄子得得的踏着路面响。起初以为是偶然的事,却不料这响声一阵跟了一阵,由初更达到深夜,始终不息。桂枝也就想着这是小七子说拉运子弹的事了。便轻轻地喊着道:“妈!你看这外面大车拉得哄咚哄咚的响着,是过大兵吗?”
江氏翻了一个身,微微地哼了一声。桂枝又叫了两声,她并不答应,于是继续着斜靠了枕头睡着,听着门外的车轮声。那车轮子响声,远一阵子,近一阵子。不但证明了那是运子弹而且可以听到哄隆哄隆的炮声。以及劈劈拍拍的枪声。在海甸住家的人民,是常常经验过实弹演习响声的,桂枝并没有什么意外之感,以为这又是西苑驻军,在实弹演习。
这就睡着沉沉地听了下去。忽然紧密的枪声,就发生在大门外,看时,一群大兵,正端了枪,背靠了院墙,向外射击。吓得自己周身抖颤,四下里张望,找不着一个藏躲的地方,只有向床头的墙角落里站着。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只见赵自强全副武装,手提了一支步枪,跑进屋子来。桂枝哎呀了一声,接着道:“你回来了!”
上前去抓着他的手道:“你回来了,我等得你好苦哇!”
赵自强摇摇头道:“我不能回来了。回来的是我的灵魂。”
桂枝道:“什么?你阵亡了!那我怎么办呢?不,你是拿话骇唬我的。”
赵自强道:“不信,你看我身上,我全身都是伤。”
说着,他真的就脱下了衣服,露出身体来。但见他上半身血渍斑斑,全是刀伤,此处还有几个窟窿眼,全有洒杯子那般大小。桂枝看着,心里一阵难过,不由得怪叫起来道:“我的天,这是怎么弄的?”
赵自强用手指了那眼道:“这是子弹穿的。由这眼里,可以看到我的良心,不信,你向里面望着试试看。”
桂枝望着那伤眼,已是周身抖颤,哪里还敢向里面看去。偏是这时,那轰隆轰隆的响声又起。赵自强举着手上的步枪,大声叫道:“我要杀日本鬼子去!”
桂枝抢向前拉住他道:“你刚才回来,怎么又要走?”
赵自强道:“你听听这炮声,我能不去吗?”
桂枝死命地拉着他的手,哪里肯放?但听到那炮声轰隆轰隆,只管响来。一个炮弹落在面前,但见满眼烟雾弥天,那炮弹仿佛也就落在身上,将人压倒在地,喘不过气来。挣扎了许久,睁开眼来一看,原来是一场恶梦,那轰隆轰隆的响声,兀自在窗户外响着,搬运子弹的大车,还在继续不断地经过呢。
桂枝看看窗户上,还不曾天亮。远远听到有几声鸡啼桌上那盏煤油灯,油点得快完了,一线带红色的光焰,在玻璃罩子里,微微地闪动着,要向下沉了去。她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是母亲半边身子,压在自己的右腿上,让自己转动不得。并没有炮响,更没有炮弹打在自己身上。推想着梦里见赵自强,都不会是真有的事了。但仔细想想那个浑身带伤的样子,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心里总蹩着一个想头,他老不写信回来,不会是阵亡了吧!这个念头,不但是不敢说,有时还不敢想,现时在梦境里,可是看得那样活龙活现,怎样教人不留下一点影子呢?她越回想到梦里的事情,心里却越害怕,不由得一阵伤心,又涌出一阵眼泪,而且息息率率地,还放出了低小的哭声。这可把江氏惊醒了,猛然一个翻身坐起来,问道:“桂枝,你这是怎么了?”
她哽咽着道:“我刚才做了个梦,他……他……他完了!”
江氏怔了一怔,低声道:“别小孩子似的了。你们家老爷子,也不大舒服,半夜三更,别惊动了他。”
桂枝没有说话,回答的依然是一阵息息率率细微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