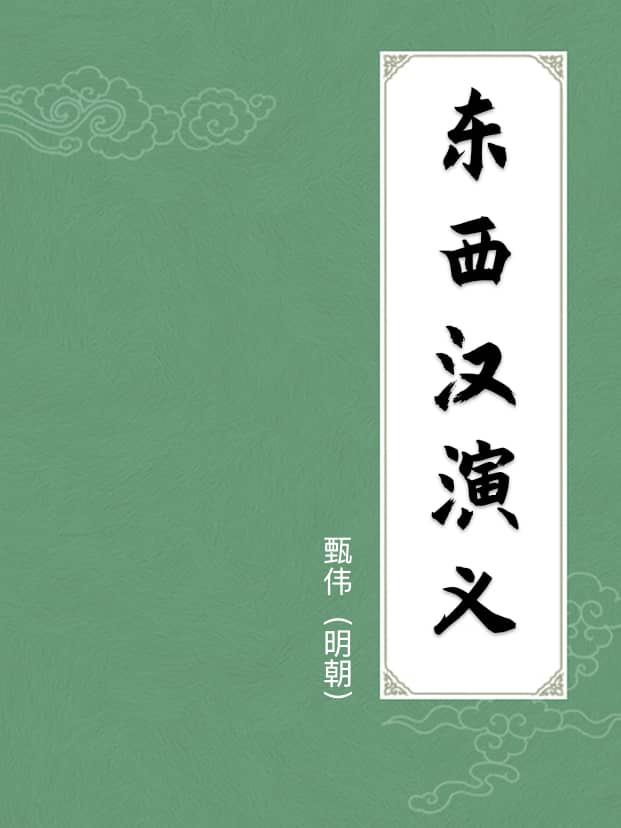杨桂枝虽是躺在床上,两手捏得紧紧地,捶着自己的大腿,那两道眉毛,也就皱着锁到了一块。她整整地苦闷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实在无可忍耐了,便将这事偷着告诉了江氏。江氏到了现在,处处觉得亲家老爷不错。何况他们对于婚姻态度,乃是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主义。慢说对姑爷是很满意了。便是不满意,也不能有一点话给人家说。无论如何,得把那手绢弄了回来。她也是和她姑娘一般,为了这事,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宿。
到了次日上午,故意闲着在门口眺望,看到甘家有个女仆出来,便笑道:“王妈,你过年好哇!你们老爷在家吗?”
王妈笑着说:“老太太,给你拜年,我们老爷上衙门去了,太太打牌去了。家里没人,我给太太送东西去呢!”
说着把个翡翠烟嘴子举了两举,笑道:“给她送这个去。”
江氏道:“你们家忌门不忌门?若不忌门,我就到你家看二爷的病去。”
(注:平俗,一部分旧家庭,自农历元旦至元宵,禁止妇女入门。)王妈笑道:“我们太太还上别人家打牌去呢,忌什么门?”
说时,笑着去了。江氏在自己门口犹疑了一会子,就慢慢地走向甘家门口来。徘徊了许久,依然是那个送烟嘴子的王妈回来了,托着她带到积之的屋子里去。积之正睁着眼睛,向窗户上看了出神呢?忽然看到江氏来了,这倒出于意外的一件事,连忙由被里伸出手来,向她抱了拳头拱了几下。江氏推门来,先不看他的脸,却看了他的垫褥,站着床前问道:“咱们听戏回来,都好好的,怎么你就不舒服了?”
积之道:“感冒病是很容易招惹的,不敢当,还是老太太来看我。”
江氏道:“街坊邻居,这也是应当的。”
积之连连点着头道:“老太太请坐,老太太请坐。”
江氏退后两步,离着床很远了,这既无法伸手去偷那手绢,自己又不便直接向积之说,自己是来要手绢的,问问积之烧不烧,吃了些什么没有?心里起了好几个念头,总不能够说明。约坐了十几分钟,自己感到无聊,也就走了。
但是她人虽走了,心里对于这件事,却绝对不能放下,一人闷在心里,在家中走进走出,却打着主意,要怎样地把那条手绢取回来。到了下午,她究竟想得一个主意了,便在瓦罐子里,取出了十个柿饼包着,又到甘家来。到了大门口,并不见人,只好在院子里咳嗽了两声,却听到积之在屋子里叫道:“院子里没人呢,老太太请进来吧。”
江氏手上托着那十个柿饼,走进书房去,却见积之手撑了椅子靠背,慢慢地站了起来。江氏道:“哟!你就起来啦,怎么不多歇着歇着?”
积之笑道:“这感冒病,来是风,去是雨,不会有好久时候的。”
江氏笑道:“上午来得匆忙,我也忘了。我们亲戚在山里住,去冬送了我一些柿饼,我挑了几个干净的,转送给二爷吧。”
说着,将柿饼放在桌上。积之连说多谢多谢,自己叫了两声王妈,是让她倒茶,因为没有人答应,自己走出书房去了。江氏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也不拦阻,便坐在床上,眼望着积之的后影,见他转过弯去了,立刻掀起这床上的被褥,找那手绢。仿佛看到垫褥下面,有块白的东西,还不曾分辨得清楚呢,却听到窗户外面,一阵脚步响,立刻将被褥放下来,在床沿上坐着。同时,积之带王妈进来了,张罗了一阵茶水。王妈不说什么,提开水壶走了。积之向江氏说了几句闲话,便笑道:“这柿饼家嫂倒是喜欢吃,我送到上房里去吧。”
说着,他拿着柿饼走了。到了这时,江氏又觉得是个很从容的机会了,再把垫褥掀起来,要拿那块手绢,不想第一次掀垫褥掀得太匆忙了,把这方手绢,不知道掀到什么地方去了,找了许久,也没有看到手绢的影子,自己心里又很害怕,若是检查人家的被褥,让人家知道了,那成了什么话?所以一番找不到手绢之后,立刻就把被褥依旧放好,自己只坐在床上出神。积之因为有客在书房里,哪里敢久耽搁,匆匆地就回书房了。江氏坐在这里,觉得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老坐在这里,很显着无聊,便起身要走,当她正这样一扭身躯的时候,却看到床的角上,露出半截白手绢,那正是桂枝失落的东西,本待伸手去拾起来,这事就很显着太鲁莽了,顿了一顿,结果还是空手而去。
积之将江氏送到院门口,方始回转身来。他心里这就想着,杨家老太太何以突然变得这样殷勤,这定是桂枝让她来的无疑。桂枝何以会让母亲来,那必是惦记着我的病了。这样看起来,她始终是不曾忘记我的了。对于她这番盛情,却是不能不加以感激的。于是坐在椅子上手撑了头,慢慢地沉思了起来。虽然她已经嫁了人而且身怀有孕了。但是我和她交个婚姻以外的朋友,那也不要紧。那么在杨老太太来过两次之后,我应当有一种回答的手续,而那条手绢,也许她有意失落的了。可惜!我竟是把这条手绢又丢了。他心里想着,脚下就不由得顿了一顿,然而他一顿脚一回头之间,把手绢看出来了,原来不曾失去,在自己的床角落里呢。于是赶忙伏到床上,将手绢拿在手里,颠之倒之地,只管看着。看了许久,又转身睡到床上,头高高地躺在枕上,右手举着手绢,在半空中连着不断。那手绢拂动了空气,香味又只管向鼻子里送来。由这种香味,他更联想到桂枝身上,便觉得她那丰秀的皮肤,敦厚的态度,另外有一种安慰人的所在。她既不曾绝我,我又何必绝她,对了,我决计和她交个朋友。假使她毫无意思于我,今天她母亲连来两次,也就毫无意义了。在他这种思想之下,步步地进行。吃晚饭的时候,居然喝了两碗粥。这精神格外振奋起来,他就有了工作了。在书桌上,一盏明亮的瓷罩油灯之下,放着笔墨信笺。那信笺是仿古式宣纸做的,盒子盛着,很厚的一叠,一张一张离开了信笺盒子,放到桌子正面,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了楷字,在一叠信笺,减少一半厚度的时候,油灯里的油,燃烧着只剩了一半,茶杯子里的茶,也和冰水一般凉,屋子里铁炉里的黑煤,也成了白灰,这信笺上的楷字,也就不得不停止了。在停止了这字时,可以看出这全文,和楷字的功夫是一样深。乃是:
桂枝:
我自己做梦想不到,还有写信给你的机会,因之我猜不着你看了这封信是什么感想。但是我由最近的事实来推想的,你收到了这封信,必定是很欢喜的,所以我考量了一日一夜之久,到底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来给你了。在一年以前,我们是决不想到做朋友为止的,到了后来,偏偏是朋友都有点做不成,这不是我的过失,可是这也不是你的过失,彼此都曾有些误会。何以都会有了误会,这也只好说是天意如此吧?我到于今,我还是后悔,为什么不下决心,把这个计划,早早地实行了呢?假使我在去年今日,我就把这件事情办到了,我想今年今日,决不会有这种苦恼了。就是以其小者而言之,昨天我这场感冒病,也许不会发生。蒙你的情,今天请令堂来探我两次病,我非常之感激。非常之感激这五个字,并不是平常客气话,你要知道,我感激的程度,几乎是要哭出来了。因为前天我无意中捡到你一方手绢,已经有些心动了。等到我随便地得了一点感冒,你又是这样惦记着,这决不是平常朋友所能办得到的,半年以后,我以为你忘情于我了,这完全是我的错误。现在我明白了,你不但没有忘情于我,而且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苦衷,你心里是越发地悲痛了。桂枝,我现在忽然明白了,黄金时代的机会,虽然,是已经错过去了,但是只要彼此明白,在精神上还不难彼此互相安慰吧!好了,只能写到这里为止了。因为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慎之又慎,以免再发生什么误会,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已经撕了二十几张信纸了。我又怕你不认得行书字,所以又端端正正地,写了楷字,只看这一点,你可以知道,我把这封信看得怎样的重大了。我希望你接到这封信,仔细看上几遍,然后回我一封信。能够约会着在一个地方面谈,那就更好。我这样指望着,大概不算过分吧?祝你好!
好友甘积之上
这封信写好了,积之写了一个杨桂枝女士亲展的信封,揣在内衣袋里,就上床睡了。
次日在枕上醒来,第一个念头,便是这封信要怎样送到桂枝手上去呢?由邮政局寄去,那当然是不妥,因为怕落到赵翁手上去了。让女仆送去吧?那至少要多一个人来参与这秘密。想来想去,那还只有亲自送到桂枝手上去为妙。至于要用什么法子亲递到桂枝手上去,这却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事,只好等机会了。他下了这样的决心,就迟了两天不曾走,一日要到大门口来徘徊好几回,在第二日下午,居然遇到桂枝上大门口来了。他也没有工夫再顾虑一切,老远地鞠着躬,掏出信伸着递了过来。桂枝见他递上信来,心中已是突突乱跳,本待不接收,又怕拉扯着耽搁工夫,等别人看见,只得接过信来,立刻向袋里一塞,脸也就随着红起来了。当她接那封信的时候,便知道这事有些不妙。但是拒绝不收,彼此在大门口撑持着,若让第二个人来看到,这件事可就更了不得。所以不顾一切,赶快地就把那信接过来。在大门口,也不愿多事耽搁,掉转身,便走回自家屋子去。
这时好是赵翁不在家,于是掩上了房门,将积之那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她不由冷笑着,自言自语地道:“这不是梦话吗?”
手上拿了那封信静静地沉思了一遍,想着,这件事不应当瞒着母亲,直接告诉了她,有什么风潮发生了,也可以母女商量着来对付,多一个年老人指挥着,总多一番见识。于是毫不犹豫地,拿了那封信冲到江氏屋子里去。将这信一举,沉着脸道:“妈!你瞧,这不是笑话吗?甘二爷好好地写一封信给我,啰哩啰嗦,说上一大堆。”
江氏立刻也就红了脸,喘着气道:“你瞧什么?你嚷什么?”
说着,她就站起身来,抢着先关上了门。这才低声道:“这可胡闹了,他写信给你,信上说了些什么?你念给我听听。”
桂枝红着脸,先不念信,便绷着脸道:“这真是一件笑话。”
江氏想了一想,因道:“信也不必念了,你只把信上的大意告诉我就得了。”
桂枝道:“我过去的事,你总也明白,虽然认识甘二爷,不过因为他是街坊,我可没有别的。”
江氏道:“过去的话,我们都不必说了,只说现在吧。”
桂枝道:“他这封信,就是提到从前的。这要不是我娘儿俩个自己说话,把从前的事提了出来,人家可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
江氏道:“信上怎样说以前的事呢?反正你也没有把身子许配给他呀。”
桂枝道:“哼!他可就是向这条路上想着。你看,这可不是和人开玩笑吗?若是让赵家人知道了,我自然是不成人,可是你也要让人家道论着,为什么会教养出这样子的姑娘来呢?”
江氏道:“得啦,别嚷了,以后不理他也就完了,我也不说这些废话了。”
桂枝道:“光是不理他还不行啦。”
江氏道:“你不理他,他又能够怎么着呢?”
桂枝道:“我就是不理他,也料定了他不敢怎么着。只是若不把他回断了念头,好像他写了这封信来,我就默认了似的,这样下去,那要纠缠到哪一日为止呢?所以由我想着,光是不理他,那不是个办法。”
江氏听了这话,不免睁了两眼,向桂枝很注意的看,凝神了许久,才问道:“依着你的意思,还打算给他回一封信去吗?”
桂枝正色道:“你可也别把事情误会了。回信尽管回信,哪还有什么好样子的回法。譬如我老老实实地在信上说着,他不应当这样,再要写信来,我就宣布出来。请问我这样地说着,他还好意思再写信给我吗?反正彼此也不见面的,就是得罪了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江氏道:“你若是要回信的话,那也可以,但是把信写好了,你必得念给我听听。假如不对的话,我可以叫你改过来,你别瞧我认不得字,我到底比你多吃几斤盐,你见不到的地方,也许我还能见到。”
桂枝道:“那也好。本来,我也认识不了三个字,还写得什么信。不过这种信,我也没法子去求人写,只好自己凑付着来吧。”
说毕,立刻就带了那封信,到自己屋子里去,掩上房门,慢慢地写了起来。约莫写了二小时之久,翻查着千字课,小学教科书,七拼八凑,总算造好了一封信。然后拿了信到前面院子里去,向江氏报告。江氏见桂枝拿了信进来,知道是念给她听的,于是牵了桂枝的衣襟,一直把她拉进里面小屋子里,然后让她坐在炕沿上,自己对面坐定,向她轻轻问道:“你念吧,别嚷。”
桂枝于是捧着信念道:
积之二爷台鉴:
接到你的来信,我是奇怪得很。我现在和赵连长感情很好,谁都知道的。俗言道得好,马不配双鞍,女不配二郎。我虽是穷人家的女儿,倒也晓得一些礼义廉耻。世上岂有做贤妻的人,和别人通信的。自强是个爱国军人,你既然是个读书人,也当敬重这为国尽忠的军人,你不应当这样对待军人的太太,不过你既然写信来了,我也没法子拦着,我可望你以后不必这样,若是让人知道了,那可是一件笑话。你是个君子人,别做没出息的事,最好你有能耐,你打日本去。此外还用我多说吗?望你多多原谅吧。我家母也知道这事,给你问好。
赵杨桂枝拜上
江氏听了,点着头道:“也不过如此。可是这封信怎么样子送了去呢?”
桂枝道:“咱们是大大方方的,就派人送去,也没有什么关系。要不然就贴二分邮票,由邮政局里送去罢。”
江氏道:“虽然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这事闹大了。邮了去也好,可是信封面上,你别写上姓名。”
桂枝道:“我也不上街了,你去寄吧。我想他若是讲面子的话,接到了这封信,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江氏不听到这些消息则已,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感到精神不安,便接了这信,到街上邮局投寄了。
到了次日早上,这封信已经到了甘积之的手上。那信封上虽没有姓名,但是看了下款署着内详两个字,又看到那笔迹,极是幼稚,这就料定十之八九,是桂枝回的信。居然能盼到桂枝写来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不必有人在面前,也就笑嘻嘻的。自己也怕把这信胡乱拆坏了,将来不便保存,于是找了一把剪刀,齐着信口,慢慢地修剪了一条纸线下来,才将信瓤取出。只看到“马不配双鞍,女不配二郎”两句话,已觉脸上发烧,红潮过耳。及至看完了,心里便说不出来那一分难受。先是坐着看那信的,后来索性躺在床上,两手高举了信纸,一个字一个字,向下看着,把信全看完了,两只眼睛对了那信纸,只管注视着,他腾出一只手来,将床板重重地拍了一下道:“这事太岂有此理,而且也太与我以难堪了。”
随了这一下重拍,他也就站了起来。说着,又用脚顿了几顿。摇头道:“人心可怕,从今以后……”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窗子外面有人问道:“二爷你是什么事,又在一人发牢骚呢?”
积之脸上的红晕,刚刚退下,又拥上脸来了,便笑道:“我埋怨大正月里,不该害病呢。这话怎么就让嫂嫂听了去了?你进来坐一会儿。”
甘太太口里这样说着,人闪在窗户后面,可没有走开。积之这时,正在那怒气填胸的时候,哪里就肯把这件事揭开过去。跟着又叹了一口气道:“宁人负我罢了。”
这句话算是甘太太听得最清楚,她也不再说什么,点点头就这样走了。
积之坐在屋子里,很感到无聊,将桂枝寄来的那封信,重新由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自己冷笑着一声,两手撕着信封信纸,一会子工夫,撕成了几十片,落了满地,这还不算,自己又用脚着力踏了几下,笑道:“再见吧,赵太太!你谅就了我不能打日本?”
说毕,自己就爬到床上躺下来了。他这样的举止,自然有些出乎常轨,积之家里男女仆人也都看在眼里。
吃中饭的时候,积之躺在床上,不曾起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才感到有些饿。而且想着,若是再不去吃饭,也恐哥嫂疑心,所以也就坦然到堂屋里去,与哥嫂同席吃饭。厚之当他进出的时候,眼光就在他脸上注视着,及至他坐下来,还注视着不断。甘太太坐在他对面,看了这样子,便笑道:“厚之,你为什么这样老注意着你兄弟?”
厚之道:“他刚刚病好了的人,我看他气色不大好,疑心他又是病犯了。”
积之道:“我明天就回学校去吧,免得闹出病来。”
厚之道:“身体不大好,你就该多休息一两天,怎么倒急于要走呢?”
甘太太笑道:“你让他走吧,在海甸街上,他不免受到一种刺激的。”
甘太太说到这里,不表下文,厚之心里也就明白,这话就不便随着向下说了。于是自扶起筷子来吃饭,并不作声。甘太太笑道:“二爷,你别嫌我做嫂子的喜翻旧案,以前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咱们那芳邻不是你的配偶,我可以和你另外找一个好的,可是你那时嫌为嫂子的多事,很有个不以为然在心里。现在你对于这件事,大概十分清楚了,我就不妨再提起来。”
积之拦着笑道:“得啦,嫂嫂,还提这件事做什么?”
甘太太笑道:“你别慌,我说的,不是过去的话了,提起来怪难为情的,我还说什么?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许的愿,应该还愿了。凭了你哥哥在这里,能替我证明。”
厚之道:“你说起话来,总不肯干脆,啰哩啰嗦这一大套,我哪里明白?证明更是谈不到。”
甘太太瞅了厚之一眼,笑道:“这也不是你的什么事,你瞎着急做什么?我不是说过,二兄弟的婚事,自办不成的话,我可以替他做媒吗?现在就是时候了。”
于是向积之仰着脸道:“我说的这位也是贫寒人家的,不过身份还有,她的确是位小姐,我觉得这种人最合于你的条件,因为家境稍困难一点,家庭教育,不见得就好。若要习惯良好,又知道吃苦,就非娶这种人不可。而且她还是个中学堂的学生呢,这不比以前你所选择的人,要强过十倍吗?”
积之笑道:“嫂嫂说起话来,真是叫人无从答复,一提起来便是这样一大套。”
甘太太道:“我当然得说这一大套,不说这多,你怎样地明白?现在我问你,对那位已经死心了没有?若是死心了,我这个媒人,就做得成功了。”
积之道:“不问死心不死心,嫂嫂说到做媒这一层的话,我是心领敬谢。”
甘太太将筷子头点着他道:“也未免太傻了。难道人家做了太太了,你还老等着她不成?”
积之红了脸道:“嫂嫂说的话,我有些不明白。可是我能下句断言,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有这种权威,可以让我这样死心踏地等她的。”
甘太太生气道:“你别忙呀。现在你没有见着那个人,你若是见着了那个人,你就知道世上有那种人可以让你死心踏地的;说起这个人,也是一层缘分,有一次我由城里到海甸来,和她同坐着长途汽车,就谈起来了。据她说,也是到海甸来看一位什么女朋友的,我倒没有打听那女朋友是谁。不过问起她家底来,才知道她和我二妹妹婆家是亲戚,年底到二妹家去。恰好又和她碰到一处,我二妹妹当了她的面和我说,要我替她做媒,分明她是没有结婚的。那时我想着了你。”
积之摇摇头道:“这话不然。人家既是个女学生,大概不怕人当面提亲,也很文明。文明女子,凭着有人做媒,就能够成功的吗?”
甘太太道:“那是自然,先得介绍你两个人做朋友。不过我想着,她决看得中你。若说她呢,反正比海甸街上的人漂亮些,你也应该看得起。所以在这两下里一凑合的中间,这事必然可成。”
积之也没有作声,只管扶筷子吃饭。把饭吃完了,厚之走开了,甘太太又低声笑道:“刚才对了你哥哥,你有些不便说,现在可以对我说实话了。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假使同意的话,我就给你介绍。”
积之向甘太太鞠了一个躬笑道:“得啦,我谢谢你。我对你实说了吧,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不够交朋友的资格,更谈不到结婚,我要守独身主义。”
甘太太听了这话,不由噗嗤一笑道:“你趁早别提这个,提起来,那会让人笑掉牙。实对你说,我从前也是守独身主义,于今做太太可多年了。”
积之对于嫂嫂这个说法,倒是没有什么可驳的。因笑道:“现在我说也是无用,咱们往后瞧吧。家里没有什么事吗?明天我可要回学校去了。”
甘太太道:“现时还在寒假期中,你忙什么?难道你对哥嫂,还存着什么芥蒂不成?”
积之被嫂嫂这样反驳着,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笑道:“我是因为在家里无事可做,又没什么娱乐,实在无聊得很。”
甘太太道:“你不是会骑马吗?我告诉你一个消遣的法子,这新正头上,海甸到西直门,有一批溜马的。这两天天气很好,你到赶牲口的手上,赁匹马跑跑,既可以消遣,又可以锻炼身体,这倒是个好玩艺。”
积之只答应了“那也好”三个字,却也没有怎样深加研究。
到了次日,坐在书房里,觉着实在也是无聊。带了一些零钱在身上,戴上帽子,披上大衣,就走出大门外。走上海甸街头,太阳黄黄的,照着一片平畴。隔年的冬雪,还零落地撒布在平原上,向半空里反射着金光。一条通西直门的大路,也零落地有些摇撼着枯条的柳树。这日不曾刮什么风,人站在平原上,没有那刮着脸上毫毛的寒气,首先感到一种舒适。北方的气候,不冷就是表现着春来了。积之两手插在那半旧的青呢大衣里,大衣敞着胸襟,慢慢儿地走着。果然,迎面常有人骑着马跑来。骑马的人,到了海甸街头,又骑着跑回去。他是个喜欢骑马的人,看别人骑马,就引起了自己一种骑马的兴趣。站在路边,只是看那些骑马人的姿势。但这些人都是新春骑着马好玩的,也许这就是第一次骑马呢。他站在旁边,带了微笑的样子,望着骑马的人陆续过去。后来有个人,骑着一匹白马,马蹄子跑得卜笃卜笃乱响。只听这蹄声,就是一个兴奋的样子,立刻向迎头跑来的那马望去。只见那马上坐着一位青年,上穿对襟皮袄,下穿灯草绒马裤,紧紧地将两只皮鞋,蹬着马蹬子,两腿夹住了马腹,身子半挺着,两手兜住了马缰绳,马昂着长脖子,掀开四蹄,踢着尘土飞扬。那人戴了护耳的暖帽,看不出他的脸色。那马擦身而过,却缓下了步子,只有几丈大路远,马就停止住了。随着那马上的人,很矫捷的,向下一跳,手挽了缰绳,将马牵着过来。另一支手却抬起来连连地招了几招马鞭子,口里叫道:“过年过得好?”
积之立刻向那人点头还礼,因为不知是谁,却怔怔地答不出话来。那人越发地走向前,伸手把帽子摘下来,又点了个头。积之笑道:“哦!原来是洪朗生学长,今天高兴,到郊外来跑马。久违久违!”
洪朗生到了面前,笑道:“我正想找你,不料在这里遇着,好极了。”
积之道:“有什么事指教的吗?”
说着,看他脸色黑黑的,长得很是壮健,浓眉大眼,两腮带了许多胡桩子。他笑道:“你看脸色怎样?满带了风尘之色吗?”
积之道:“是有那么一点,你刚出门回来吗?”
洪朗生回头看了看,笑道:“实不相瞒,我已经投军了,刚从口外回来。这次回来,并无别事,只是想多邀几个有心人,一路出关,干他一番事业。我记得我们同学的时候,说起天下事来,都是激昂慷慨的,你也是个有为的青年。你有没有这意思,也和我到口外去。”
积之望望他,又望望他那匹马,脸上现出很踌躇的样子,笑了一笑。洪朗生道:“你结了婚吗?”
积之道:“你何以突然地问这句话?”
洪朗生道:“我怕你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呀。”
积之道:“我根本没有结婚。”
洪朗生道:“没有太太,也可能有情人。老朋友,我们不要为妇人孺子所笑才好呵!”
他这本是一句因话生话的语句,而在积之听来,恰好中了心病。便笑道:“老朋友,我还是同学读书时代的性格,并没有更改。不过你只简单对我说两句到关外去,我知道你所选择的是一条什么路径,我又怎样地就答应你的邀约?”
洪朗生道:“好!我可以和你详细谈谈。这里去海甸不远,我们找个小酒馆喝两盅。”
积之道:“那倒用不着。我家就住在海甸。”
洪朗生不等他说完,便道:“那太好了,我就到府上去畅谈。”
于是牵着马和积之一路走回家去。
积之将客人引到自己小书房里,泡上一壶好茶,摆上了四碟年果子,足谈了两小时。到了夕阳西下,客人骑着马走了。积之一人坐在屋里想到桂枝信上所说:“别做没出息的事,你有能耐,打日本去。”
这就不由得昂头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声音很大。正好厚之由外面回来,经过他屋子的窗户外,向里面张望一下,见他是一个人,便问道:“你一个人为什么哈哈大笑?”
积之无端被哥哥一问,倒没有预备答词。因道:“没什么,看笑话儿书解闷。”
厚之也不见有什么异状,自走了。
到了次日上午,洪朗生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马,再来拜访。积之一切都预备好了。因厚之已办公去了。就到上房向甘太太道:“大嫂,你昨天不是劝我骑马吗?今天天气,依然是很好。我一个老同学,带了两匹马来,我得陪着他在大路上跑跑。假如天气晚了,我就不回来了,和他一路进城。我若回学校的话,我会写封信回来。”
甘太太道:“你若是能回来,还是回来吧,你哥哥明日请春饮呢。”
积之笑着,没说什么。他告辞出来,和洪朗生各骑一匹马,顺了海甸到西直门的大路,掀开八个马蹄子,拍拍拍,跑着地面一阵响。平畴上的残雪,益发是消化了,只有地面阴洼的所在,还有不成片段的白色。天空里没有云,太阳黄中带白,照着平原一望不尽,乡村人家。没有一点遮挡,在平地上或草丛中堆着。路边的老柳树,在阳光里静静地垂着枯条子,等着大地春回。路边的小河塘,化了冰,开始浮着一片白水,水里沉着蔚蓝色的天幕,和几片白色的云。在北国度过冬季的人,也觉得是春天到了。积之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将马缰松下来,骑在马鞍上,让马缓缓地走。就在这时,看到赵翁在大路边上迎面走来。他敞开灰布皮袍子的胸襟,肩上将一根木棍子,扛着一只小布口袋,是个走长路的样子。便手握马鞭子,拱了拱手。赵翁见他马鞍后,拴住着一个布包袱。将皮带束了皮袍子的腰,将底襟掀起一块,塞在皮带里。四平八稳的,骑在这匹棕色的马上。便笑道:“二爷骑马的姿势挺好。”
他笑道:“对付着试试吧。我倒也不是那样真没出息的人。”
赵翁听了,觉得他后面一句话来得不伦不类。路上相逢,也不便多问,自送他跟着前面白马走过去了。这件事赵翁并没有怎样放在心里。
过了两天,却接到由城里来的一封平信。信的下款,署着甘缄二字。他想着亲友中并没有姓甘的这么一个人。只有一个对门住的甘积之。前日还在路上遇着呢。写信来干什么。在可疑的心情下,把信拆开来一看,果然是积之写来的。信上道:
赵老先生尊鉴:
日前马上相逢,甚为欠礼,但晚有远行,亦不愿下鞍详道也。当今国家多事,正男儿有为之日。晚虽无用一书生,爱国并不后人。该日即偕同学某君,投笔从戎,不久即将出关。晚与赵连长有数面之雅,颇敬重彼为一爱国军人。转念既敬重军人,我亦何不自为军人。一枝毛笔,今日何补国事,故一念之间,即愤起抛去。从此区区小吏,亦为国人当重视者,颇觉自得。如得生还,他日当再趋前候教,详叙塞外风光也。特此驰告,并祝
春祺!
晚甘积之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