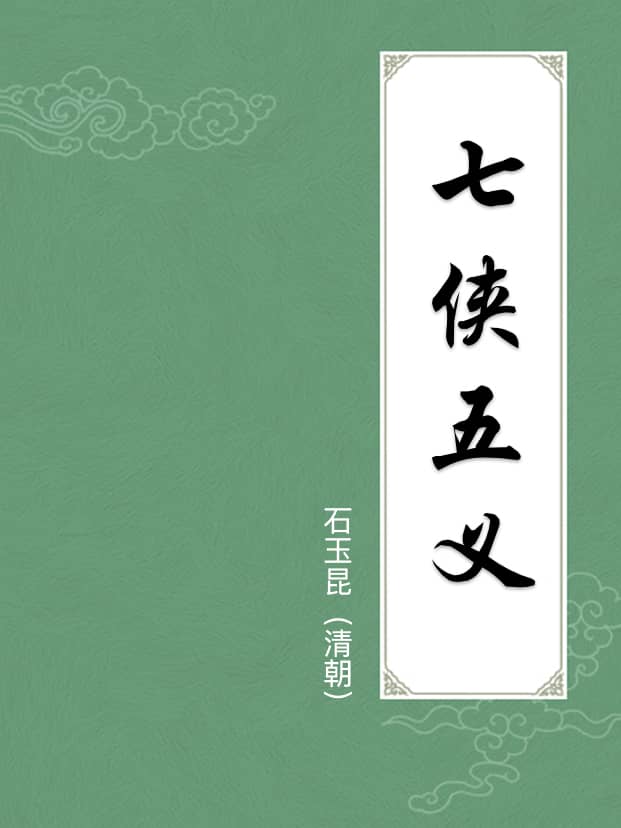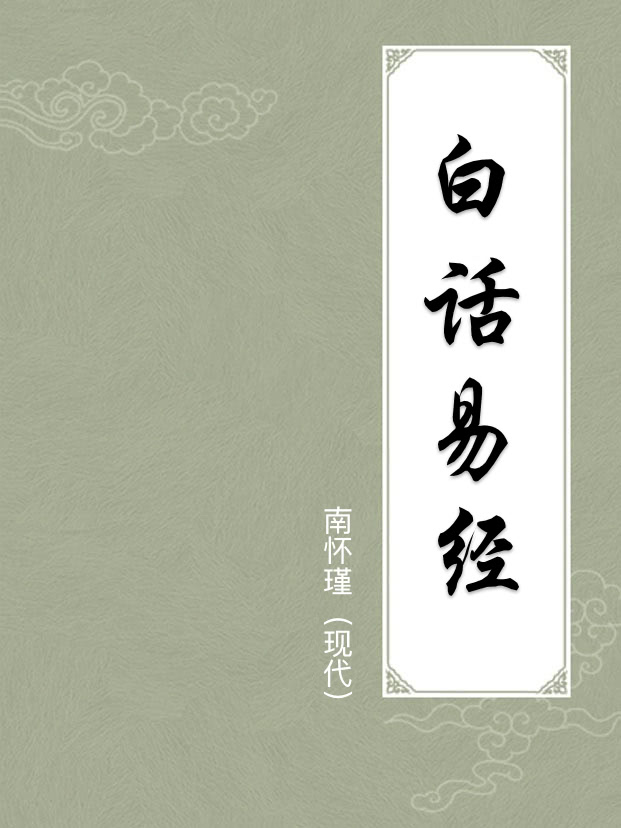洪士毅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心里不由得想到,我又过了一天,寿命也就延长了一天了。这个样子,我或者不至于死,今天觉得烧退了许多,头痛也轻松了不少,大夫说,我身体很危险,一定是恐吓我的话,自己大可以不必恐惧的了。这次算给了一个极大的教训,自此以后,我要把工作做得适可而止,不再做拼命抄书的傻事了。恋爱固然是要紧,性命却更是要紧;假使没有了这条性命,又从何而恋爱呢?收起了自己这条野心,不要去想小南了。不过他如此想着,小南二字到了他的心头,就继续的存在,不肯沉没下去。转念想到,两天不到常家去,不知道常家的人念不念自己?至少小南的父亲,他会心里念着的。何以突然不见,也许是怕他怪我的,总要给他们一点消息才好。他虽然病在床上,还不住地替小南父女俩打算着。他父女俩对于他,又有些不同,常居士想着的是,洪先生这一天怎幺没有来?小南今天一天,都在柳家玩耍,在柳家吃饭,还在柳家洗了个澡,拿了许多衣服回家来。她根本就来不及想到洪士毅,来之与否,更是不过问了。
这样过了两天,洪士毅不曾来,常家的伙食,却是柳三爷借给了两块钱买面买米,也就用不着为吃的问题,联想到士毅身上去。然而对于这一点,究竟有些纳闷,这位洪先生人是很热心的,何以突然不来了呢?这样的纳闷着,又过了一宿,第二日早上,得着信了,一个拉人力车的车夫,在院子里叫着道:“这是常家吗?”常居士在屋子里答道:“是的,那一位?”车夫道:“我是洪士毅的街坊,他病倒了,他托我带个口信来,告诉你们,他暂时不能起床呢。”常居士听说,赶快摸索着走到外面来,就问是什幺病?车夫道:“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很重的吧?”说着,他就走了。常居士听说,不由得连连叫了几声阿弥陀佛。自己双目不明,是不能去探人家的病,姑娘是常在外面跑路的,可以让她去走一趟。于是,摸到大门外,叫了几声小南,可是任凭怎幺喊,也没一点回响,大概她又去柳家了。常居士心里想着,这柳家有什幺好玩?这孩子是整天的在人家家里混着。他嘴里这样唧咕着,慢慢摸回家去。
到了下午,听着街上卖羊头肉的吆唤起来。他知道天色黑了,平常必是吃晚饭的时候,卖羊头肉的才会来,现在到了这般时候,小南还没有回家来,今天要去探人家的病,可来不及了。自己坐在床上,就不住地唉声叹气。又过一些时,听到大门呀的一声响,自己正要问是小南吗?小南就叫道:“爸爸,你饿了吗?”常居士很重的声音答道:“我忘了。”小南道:“你是用这话损我吗?以为我没有给你作饭,可时候还早着呢。”常居士道:“我不是损你,我是等你气昏了。人家洪先生害病多天了,托人带了个口信来给我们。你妈病了的时候,洪先生是多卖力?人家病了还带了一个口信来,我们就不应当去看看人家吗?”小南道:“你这是错怪我了,我不在家,我怎幺知道他病了呢?”常居士道:“是这话呀,你老不回来,可把我急坏了。限你明天起早,一起来就去看洪先生的病,再到你妈医院里去。你若是不去的话,我就跟你翻脸。”说时,声音是非常的重。小南本来想不要去的,但是听了父亲这样严厉的话,把她要推诿的一句话,吓得不敢说出来了。自己悄悄地做了饭父亲吃了,自去睡觉。朦胧中,听到父亲喊到:“起来吧,起来吧。”自己睁眼一看,屋子里还是漆黑的,因道:“你是怎幺了?做梦吗?天还没亮就催我起来。”常居士道:“我一宿都没有睡好,只记挂着天亮,二更三更四更,我都听到了,五更没有打过去吗?”小南也不理她的父亲,翻了一个身,朝里睡了。
等她醒了过来,已经是红日满窗了。按照小南的意思,做一点东西给父亲吃,就要到柳家去。然而她一下炕来,常居士就在外面听见了,他说:“在良心上,在人情世故上,都应该去看一看洪先生的病。”小南是这样大一个姑娘了,不能这一点情形都不懂,便道:“你别-嗦,我去就是了。可是就光着两只手去看人家的病吗?”这句话,常居士却认为有理,因道:“那是自然不可以的。前天你拿回来的钱,总还有几毛吧?你就把那个钱去买点糖果蜜枣,去看看他得了。”小南道:“统共那几个钱呢,不得留着吃饭吗?我借一点东西去送他吧。”常居士道:“什幺?借一点东西送人,你打算把什幺东西送人呢?”小南道:“我在医院里的时候,看到人家拿了一捧一捧的花去看病人,我想着,柳家花瓶子里,那儿放着,都插一把花在里面,和他们要一把就得了。”常居士道:“你这真是借花献佛了,人家害病了,也不知道忌嘴不忌嘴,买吃的去,也许是不相宜;找一把花去,倒是好的,你去吧。”小南道:“我得把你吃的东西做得了,那才好走。”常居士道:“你不用给我做吃的,你去吧,我还惦记你妈的病呢,等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吃吧。”小南最是怕他父亲罗嗦,迟早总是要去的,这又何必和父亲多作计较?哄咚一声,带上了院门,就走出来了。她果然照着她的话,到柳家去借花。
当她走到柳家的时候,却见大门紧闭,那两个铜环,垂在上面,一点也不动一动,吵醒人家,恐怕人家会不高兴吧?站在大门边,只管发了呆。心想,自己是去呢,还是不去呢?人家没有起来,怎好-开人家的大门?但是不叫门,要送病人一束鲜花,又到哪里去找呢?她正如此踌躇着呢,那柳家的大门,却呀的一声开了。自己突然省悟到,一早在人家门口徘徊着,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身子就向后一闪。那时,门里出来一个女仆,手里拿了一只盛满了秽土的畚箕,走到门外场子的角上,倒了下去。她急于要进门去,却没有理会到墙边还站着一个姑娘。小南向那秽土堆上看时,真有这样巧的事,那上面正放着两束残花。走向前捡起来一看,虽然花的颜色枯萎了一些,可是那叶子还是青郁郁的,还是可以拿着去送人的。这样拿去,只要有一点意思就行了,至于不大新鲜,有什幺关系?他反正也不知道我是在秽土堆里捡的。她决定了主意,又在胡同口的苦水井边,向人家讨了一瓢水,将手上拿的一束花,洒了一些,然后向洪士毅的会馆走来。因为时候早,会馆里人多数未起床,里面还是静悄悄的。小南走到院子中间,就问人道:“洪士毅先生住在哪间屋子里?”士毅是不等天亮就醒了,正躺在枕上想心事,一个人不要为什幺外物所迷,一为外物所迷,任何事业,都不能成功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接近什幺女子,只培植我艰苦耐劳的志趣……他正想到得意之处,忽听到外面有女子的声音问自己,这分明是小南,立刻就在床上大声的答应道:“在这屋子里,在这屋子里。”
小南走到房门口,伸头向里一看,土毅先看到她的脸,其次就看到她手上拿的一束花,便笑着呵呀一声道:“你怎幺来了?请进请进!”小南挨着房门,缓缓地走了进来。走到床面前,低声问道:“你好些了吗?我爹叫我来看看你”。士毅笑着露出白牙来,点了头道:“我好多了。哟!你还买一大捧鲜花来了。”小南笑道:“我爸爸说,怕你忌嘴,不敢送你东西吃,所以送你一扎花。”士毅道:“何必花那些个钱?有买花的钱,可以买一顿饭吃了。”小南怎好说不是买的呢?只向人家微笑了一笑。士毅道:“花是多谢你送了。可是我这穷家,还没有一个插花的东西呢。”小南当她由房门口伸进头来的时候,她就觉得士毅的屋子里,太简陋了,这还是春末,在北方还需要盖着厚被,可是他所睡的,只是一床草垫子上铺了一条破被单,她哪里知道土毅床上的被褥,已经送到当铺里去,给她换了新衣服哩?他躺在那上面,也不知是在什幺地方捡来的一件破旧大衣,盖了下半截。靠窗户的桌子上,虽然摆了一些破旧的书,然而也不过就只有这个。桌子边放了一张方凳子,可以坐一个人,若是来两个客,只好让一个人站着了。到了此时,小南才明白了,原来洪士毅是如此贫寒的,彼此比较起来,也就相差无几哩。小南心里头一阵奇怪,他既然是这样的穷,为什幺还那样帮我的忙呢?有给我买衣服的钱,不会自己买一条被盖吗?
当她这样在打量士毅屋子的时候,士毅也在打量她的身上。几天不见,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最显眼是她那一条毛蓬蓬的辫子,现在剪成短发,颜色黑黑的,香气勃勃的,而且烫着成了堆云形,在头发下,束了一条湖水色的丝辫,辫子头上,打了个小小的蝴蝶结儿。身上穿了粉红色的半旧长旗衫,那细小的身材,恰是合着浑身上下的轮廓,将腰细小着,将胸脯挺了起来,那种挑拨人的意味,就不用细说了。他简直看呆了,不料她几天之间就变得这样漂亮,却不知道她在什幺地方得了一笔钱,陡然阔了起来。本想问她一句,这衣服是哪里来的?然而自己思忖着,却没有这样的资格,可以去质问人家的行动,只是一望就算了。等他不望的时候,小南也就省悟过来,今天穿了这样一身新,不免要引起他的注意,这可以让他知道,我常小南不是穷定了,穿不起好衣服的。如此想着,脸上不免有几分得意,故意笑嘻嘻地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将一束花放在桌上,手扶了桌子沿,挂了一只脚,站在那里抖着。洪士教这就有些窘了,既没有茶给人喝,又没有东西给人吃,连坐的凳子上,还是高低不平,有许多窟窿眼,见小南用手摸了几摸,依然未肯坐下。士毅便道:“对不住,我这里坐的地方都没有,哪怎幺办呢?”小南道:“你不用客气,我要走了。”说完,掉转身,就向门外走了去。士毅连说:“对不住,对不住,怠慢怠慢。”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小南子已经是走远了。
士毅看了桌上那一束绿叶子中间,红的白的,拥着一丛鲜花。就由这花的颜色上,更幻想到小南的衣服与面孔上去。觉得她这种姿色,实在是自己所攀交不到的一个女子,有这样一个女子来探病,不但是精神上可以大告安慰,而且还可以向会馆里的同乡,表示一番骄傲之意,不要看着我洪某人穷,还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来看我的病呢。不过他虽如此想着,同时他又发生了一种困境,常家穷得没有饭吃,自己家成了化子窝,那里有钱给小南做衣服呢?小南突然的这样装饰起来,难道是借来的衣服不成?可是她是个捡煤核的女郎,朋友没有好朋友,亲戚没有好亲戚,她在哪里去借这些衣服,若说人家送她的,是怎样一个人送她的呢?无论如何,我必定要去打听一番,她这衣服从何而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打听出来了,又怎幺样?难道还能干涉人家接受别人的东西吗?干涉不了的话,那一问起来,反倒会碰一鼻子的灰,这就犯不上了。心里想着,两眼望了桌上那一束鲜花,只管出神。他心里想着,有朋友送花来,这花还没有什幺东西来插,这样的人生,未免太枯燥了。他正在这里出神,长班推着门,向里探望了一下。士毅连连向他点着头道:“进来进来!你找个瓶来,把这些花插下去。”长班笑道:“我的先生,这会馆里连饭碗还差着哩,到哪里找插花的花瓶去?”士毅道:“旧酒瓶子、旧酱油瓶子都成,你找一只,灌上一瓶水拿来,劳驾了。”先生们和长班道了劳驾,长班不能不照办,居然找了一只酒瓶灌着水拿了进来,放在桌上,将花插了下去。士毅用手招了几招道:“你拿过来,放在我床面前吧。”长班用手将花扶了几下,笑道:“这花都枯了,你还当个宝玩呢。”士毅道:“胡说!人家新买来的花,你怎幺说枯了?”他将手拍着床铺板下,伸出来的一截板凳头,只管要他将花瓶放在上面。长班觉得他这人,很有些傻气,也就依了他的话,将花瓶放到板凳头上来。士毅见那一束花中,有一朵半萎的粉红玫瑰,就一伸手去折着,打算放到鼻子边来闻。手只刚刚捏着那花茎,就让那上面的木刺,毒毒地扎了一下,手指头上,立刻冒出两个鲜红的血珠子来。士毅心里忽然省悟过来,对了,花长得又香又好看,那是有刺扎人的,我们大可不必去采花呢。我为了小南,闹了一身病,她是未必对我有情,然这不和要采这玫瑰,让刺扎了一下一样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她今天来看我来了,而且还送我一束花,这不表示和我亲近的吗?好了,等我病好了,我还是要继续的努力。
他如此想着,心里头似乎得了一种安慰。一痛快,病就好了许多。当然,那慈善会附属医院的医生,还是继续的来替他治病。约摸休息了一个星期之久,洪士毅的病是完全好了。在这一星期之中,小南虽然不曾来探过他的病,但是小南送来的那一束花,放在这屋子里床面前供养着,这很可以代表她了。这一束花送到这屋子里来的时候,本来就只有半成新鲜。供养过了一星期之久,这一束花,就只剩下一些绿油油的叶子。然而便是这些绿油油的叶子,已经是十分可爱的了。而且落下来的那些花瓣,士毅也半瓣不肯糟蹋,完全给它收留下来,放在枕头下面。自己病好下床了,就找了一张干净的白纸,把那些干枯瓣花叶都包了起来,然后向身上口袋里一揣。在家里勉强了休息一上午,到了下午,怎幺也忍耐不住了。于是就雇了一辆车,直到常居士家来。他刚一下车,就听到小南娇滴滴的声音喊道:“等着我呀,等着我呀。”士毅向前看时,只见胡同口上,两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子在面前走着,小南在后面跑着跑着,跟了上去。看她今天穿的衣服,又变了一个样子了。上身是淡绿色的褂子,只好长平膝盖,下面露着肉色的丝袜子,紧紧地束着两条圆腿。两只袖子短短的,将手拐以外的手臂,都露了出来,自然是雪白溜回。今天的头发不烫着,平中顶一分,梳了两个小辫。左右下垂,搭在耳边,各在辫捎上扎了一个大红结花。这更显得天真烂漫,娇小玲珑。自己本想叫一声常姑娘,只见她脚上两只米色皮鞋,扑扑地在路上跑着,向前奔去。前面那个漂亮的女子,笑着向她道:“你家门口停了一辆车子,来了人吧?”小南回转身来看了一眼,并不理会,依然调转身去,和那两个女子,手牵着手地走了。虽然不知道她说的是些什幺,然而看那样子,是不愿意理会自己这样衣衫褴褛的朋友的,年纪轻的人,总是要面子的,又何必说什幺呢!因之喊到嘴边来了的那常姑娘三个字,他又完全忍耐下去了,站在常居士的门口呆住了。常居士盲于目,可不盲于心,他在各种响声上,知道有个客人在大门口了,就摸索了走出来问道:“是哪一位在门口?”士毅在大为扫兴之下,本来要转身回去的。可是经常居士这样一喊,他不能不答应,便道:“老先生,是洪士毅来了。”说着话,也就走了进去。
常居士站在门边,抢了握了他的手道:“身体全好了吗?”士毅道:“托福,完全好了。”常居士道:“我内人的病也好了,大概再过两三天就要出院的。拜托你给我们内人荐举的那个事,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士毅道:“我有这久没有到慈善会里去,也不知道怎样了?过两天我再来回你的信吧。”他说了这话,就告辞走了出来,心里可就想着,唉!你这位老先生是不曾知道,你的姑娘,现在变成了一个时髦小姐,她愿意她的娘去当工人吗?想时,便有一种细细的香气,传进他的鼻子。将鼻子耸了两耸,分辨出来,这是脂粉香味。回头一看,却是小南来了,于是伸手一摘头上的帽子,向她点了个头道:“大姑娘,忙呀?”小南笑着微微一点头道:“没事,不过在柳家玩玩罢了。你的病好了吗?”士毅道:“多谢大姑娘惦记,算是恢复原状了。”小南道:“那就好,改天见吧。”她说着话,一直向柳家走去,头也不回。士毅自然也就低着头,向别条路上走了。原来自那天小南由柳家回来以后,她睡梦中,都觉得柳家的生活是甜蜜的,她并征求父亲的同意,已经加入到她们的歌舞班子里去,当一个舞女了。在柳三爷的眼光里,觉得她的体格,她的嗓子,是全班里所找不出的一个人,而况她的面孔既好,又是一个贫家出身的人,极容易对付,所以他极力地鼓动着小南加入他们的歌舞班子,每天让她在这里吃饭,又在家里翻出许多旧衣服来,交给小南去穿。小南怎样受得这种外物的引诱?所以在这一星期之内,她是整日的在柳三爷家里忙着,常是把做饭给父亲吃的事忘了,将常居士饿上一餐。等她回来时,常居士随便质问她几句,她还可以笑嘻嘻地答复两句;若是常居士质问得太厉害了,就跳着脚来道:“你只管骂我,我还管不着给你做饭哩。”她每次说毕,就一跳两跳地跑走了。为了这个,常居士不敢骂她,只好用好言来央告她了。这天她看到洪士毅来了,并不怎样的理会,竟自到柳家院子里来。
那位招待殷勤的王孙先生,穿了一件翻领子的衬衫,两只袖子高高卷起,光着两只雪白的手臂,一手拿了一个网球拍子,一手拿了个网球,只管不住地在空中抛着。看到小南进来,就向她笑道:“我教你打网球,好不好?”小南道:“我不爱玩这个。”王孙道:“你爱玩什幺呢?”小南靠了院子门站定,笑嘻嘻地向他望着。许久的时候,才说了一句道:“我什幺都爱,可是我没钱,我还说什幺呢?”王孙笑道:“这个好办,你要听戏呢?上公园呢?瞧电影呢?都好办,让我来做东就是了。”说着,将那个网球,交到拿拍子的手上,一只手空了出来,扶着她的肩膀,连连拍了两下,笑道:“你怎幺说?你怎幺说?”正在他这样调情的时候,恰好主人翁柳三爷出来了,他看到王孙那种神情,自己就表示着得意的神气,将身躯摆了两下,然后微笑着道:“小王,你看我发现了这颗明珠,怎幺样?不是大可造就的一个人才吗?我以为她的造就,将来会在绵绵以上。”王孙对于他这个话,虽是很表赞同,不过他想到绵绵是三爷的干姑娘,假如说小南的色艺赛过了绵绵,那就蔑视了主人翁,因笑道:“她那里就达到那个程度?不过她富有新女性的美,差不多是一般人所未有的。”说到这里,他那拍着小南肩膀的手,依然未曾放下,而且轻轻的,将她肩膀上丰满的皮肉,捏了两下,捏得小南嘻嘻的笑着,身子向后一缩。柳三爷笑道:“小王,看你这个样子,对她很有些迷恋吧?”王孙笑道:“她对于这个,完全不解,现在谈不上,谈不上。”柳三爷笑道:“我这又要套用那时髦的论调了。你现在对于她,应该遇事指导她一番,这不像国家大事,要用多少年的时间?有三个月工夫,她就能了解一切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实行恋爱了。”王孙笑道:“设若基本工作完成,她不拥戴我,我又怎幺办?”柳三爷道:“这就看你的手腕如何了?有道是先入为主,你既然是个负责的人,她被你教训成就了,总不能忘了你的好处,而且在现时三个月之中,你总可以算是唯一亲近的人,你不会尽你的技能,去抓住她的中心吗?”小南瞪了两只眼睛望着两人道:“你们说些什幺?”柳三爷道:“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一个小姐,都要找一个干哥哥,来做她的保护人,王先生他很愿意做你的干哥哥,不知道你肯不肯?”小南笑着将身子又是一缩。柳三爷笑道:“真的,他真愿做你的哥哥,你有这个哥哥,在家里可以教你唱歌,教你跳舞,出去可以陪你玩,可以陪你吃吃喝喝,这不比一个人好得多吗?”小南将翻领下的领带子拿在手上翻弄着,只管微微的笑着。柳三爷笑向王孙道:“你看看,你的意思,她已经是完全默认了,你就进攻吧。你这要谢谢我,我在乱草里头给你找出了这样一颗明珠,不能不说我是巨眼识英雄吧?”说着,走向前来,将王孙和小南的身躯用两只手拢了起来,让她二人挤在一处,两只手在二人身上轻轻拍了几下道:“就是这样子办吧。”说着,掉转身立刻就走了。
小南到柳家来了这久,看见男女相亲相近,什幺手脚都做得出来,男女二人紧紧地站在一处,这更算不得一件事,所以她也就坦然受之。恰在这时,上面屋子里有人掀开一点门帘缝,露出半张苹果也似的面孔,在那里张望着。小南料着是人家张望自己,立刻将身子一闪,那楚狂楚歌兄妹二人,拥了出来,向他们笑着道:“为什幺这样子亲热?”小南红了脸,低着头不说话。楚狂向王孙道:“你未免进攻猛烈了点吧?”王孙笑道:“什幺猛烈?这是三爷拉拢的,我没法子抵抗。”楚歌笑道:“这样的事,也落得不抵抗呀。”楚狂道:“这话可说回来了,常女士若不是遇到三爷点铁成金的妙手,真埋没了这幺一生;他发现了,却让小王轻轻悄悄得去了,未免太便宜了。”王孙笑道:“说起来,这话真有些奇怪。常女士和我们做邻居,也不是今日一天,为什幺直到现在才发现她是一颗明珠哩?我以为她成为明珠,真是老楚那句话,得了我们三爷那一番点铁成金的妙手,安得尽天下女子,都变成明珠。我之所以和常女士在一处,这也不过是完成三爷一番成人之美的意思,什幺叫得便宜?我可有些不懂。”楚狂道:“你不屈心吗?现在你已是她的干哥哥了,我们在屋子里都听见哩!我实在佩服三爷之下,就不能不说一句三爷不公心,为什幺不给我们寻出一颗明珠来呢?你们来呀!要王孙请客,他新得了一个可爱的妹妹了。”说话时,他抬起一只手来,在空中招展着。同时,他也跟着那手势连连跳了几跳。这时,屋子里一阵风似的,拥出许多男女来,团团将王孙和小南围着。这样的大闹,小南到底有些不惯,把那羞得通红的一张脸,只管低到怀里去,抬不起来。可是四面都是人,叫她到哪里去躲?真把她那张面孔羞得红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