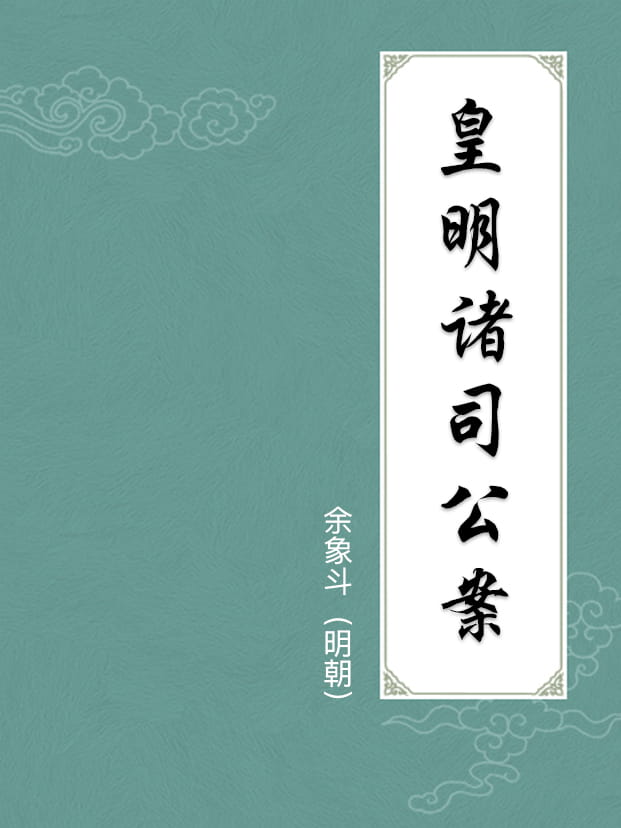河池县民俞厥成,家亦殷富,爱财吝啬,娶妻鲍氏。鲍家贫难,厥成毫无相济,虽时或求借,亦分文无与。鲍氏因此背夫,时私运谷米与父母,尝遣佣工人连宗送去。连宗是奸刁之徒,彼见鲍氏私顾外家,后复遣送米谷,积了三次不送去。
待主人远出,突入房中,强抱鲍氏曰:“我为你接送劳苦,今日必与我好一次,后日早差早行,晚差晚行,任你呼唤矣。”
鲍氏斥曰:“我遣你接送,尝赏你酒肉,何曾空劳,你安得如此无礼!我明日报主人,看你如何!”
连宗曰:“你所偷米谷我都留在,并未送去。明日我先报出你私顾外家,你虽说我强奸,主人必不信,只说是你诬赖也。”
鲍氏妇人无见识,被此挟制,恐他真报,又见米谷现在,况夫是个细毛之人,必有打骂嫁逐之事,虽指他奸,又无证据,必不见信,因随意任他所奸。
既罢,连宗以手摩其阴曰:“这边缘何有个疥堆?”
鲍氏曰:“非疥也,是一大痣。”以后亦时或有奸,搬送米谷益多矣。及冬,俞厥成与连宗上庄取苗租,到一佃支秩家。秩与连宗乃姑表兄弟,又兼同主人,来夜盛设为席。酒至半酣,说及相法及男女生痣上去。
厥成曰:“凡妇人阴间边有痣者,非贵亦富。”
连宗忘形,答一句曰:“你娘子阴边有痣,果然是富也。”
支秩视厥成微笑,彼料工人何知主母阴边痣,必是有奸也。厥成亦便觉得,心中甚怀愧恨,遂佯作不闻,说向别事去。少顷,推醉而罢。
次日,谓连宗曰:“我约人明日交田价,今收租尚未完,当急回去。”
到家即诘其妻曰:“你何得与连宗有奸?”
鲍氏曰:“那有此事?”
厥成曰:“你怎瞒得我?昨晚在佃客席上,说妇人阴边有痣者必富,连宗即答你娘子有痣。你不与他奸,何由知你阴边痣?你好说出因由,我自治此刁贼;不说,我将你二人都杀死。”
鲍氏泣曰:“是我偷你米谷送与爹娘,连宗全不为送,来挟我奸,说不允他,将出米谷报你,定把我嫁逐。我知你是纤细人,恐报必不便,因此被他挟制成奸,悔之无及。今日甘受打骂,任你再娶一妻掌家,我甘作婢妾,终身无怨。惟愿勿嫁,恐嫁贫人则难度日,人又知我失节无耻也。”
厥成曰:“似此乃是刁奸,依官法,妇人亦不至死。今依你说,我另娶一妻,降你为婢。但今夜要致宗贼于死,可治些酒菜与他食,然后杀之。”鲍氏依言,整好酒馔。
厥成谓连宗曰:“今日归路辛苦,与你同饮数杯。”
连宗尽量而饮。将醉,厥成有意算他,先故不饮。
至此,又曰:“你陪我几瓯。”主人说陪,连宗安得不饮?又饮数瓯,遂醉倒于地。
厥成乃用麻绳绑于大板凳上,推醒之曰:“你奸主母,今夜要杀你。”
连宗虽醉,犹知辩曰:“安敢如此?”厥成曰:“你说他阴门有痣,他已认了,在此证你。”
鲍氏从傍,一一证出。
连宗醉里应曰:“你既肯认,我死亦无冤。”厥成以湿布缚其口、蔽其目,用利刃于胁下凿一孔,即以滚水淋之,令血勿荫,须臾死。解脱其索,丢于床上。
次日,令人去赶其弟云,连宗中风而死。弟连宇邀表兄支秩同去看收贮。
支秩疑曰:“你兄前日在我家饮酒,人甚强壮,岂至遂死?”
连宇曰:“中风岂论人壮?”支秩曰:“你不知也。你兄昨说主母阴门边有痣,俞主人便失色。今日之死,安知非毒死也?须去看其面青黑何如。”
二人到俞宅详看连宗之体,见胁下一孔,因喊曰:“你谋死我兄!”
厥成不由他辩,遣众人将尸抬往连宅去,曰:“你自做伤安能赖我?若道谋死,任你去告,我家岂容你搅闹也!”
强赶二人出去。连宇赴县告曰:“状告为杀命事:土豪俞厥成猎骗成家,横行乡曲。哭兄连宗,为豪佣工,撞突伊妻,捏报调奸。豪信触怒,制缚手足,利刃胁下,凿穿一孔致命伤明,支秩可证。乞亲检验,律断偿命,死不含冤。切告。”
俞厥成去诉曰:“状诉为刁佃仇唆事:刁恶支秩,佃耕主苗八桶,积欠三冬,该银二两四钱。累往理取,抗拒致仇。今年雇工连宗,中风身死,恶唆表弟诬告杀命。且佣工贫民,谋杀何干。纵有触撞,小过可骂,大过可告,何须行杀。牵告成妻,无非故陷。乞台亲检有无凿胁伤痕,情伪立见。斧断完租,刁佃知儆。上诉。”
黄太尹吊审,连宇执胁下有伤,俞厥成执中风有征,安有胁伤。
黄太尹曰:“有伤无伤,只一检便见。”及去检胁下果有一伤,只肉色干白,并无血荫。
黄太尹把《洗冤录》指与连宇、支秩、俞厥成三人同看,曰:“凡生前刃伤,即有血汁,其所伤处血荫,四畔创口多血花鲜色。若死后用刃割伤处,肉色即干白,更无血花。盖以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今胁下虽是致命处,而伤痕肉白,是汝假此赖人明矣。”支秩曰:“连宗说主母阴边有痣,次日即死,胁又有伤,因此知是厥成疑宗有奸,故杀之。”
厥成曰:“凡富家人妻室,决羞与跪官厅。他挂我妻名,小的用尽银买差牌人,故得不到官。今又说阴门有痣,指难证之事,以惑在上,真奸人之尤也。”
黄尹曰:“奴才全不知法,若说与主母有奸,他碎斩亦该得矣。今只须辨伤痕真假,何须论奸情有无。”
将支秩打二十,拟诬唆,追苗租三年,与厥成领。连宇打二十,拟诬告。俱问徒去。俞厥成供明无罪。
黄尹判曰:“审得支秩、连宇皆表兄弟也,而连宗则支秩之表弟,连宇之亲兄。佣工俞宅中风身故,于主人何与哉?支秩不合积欠主苗,又不合挟恨教唆。连宇信惑谗言,不合将已故兄凿穿其胁,图赖俞主。以杀命欠租,惟应还主,安得乘隙以售中伤。兄死自应收埋,何可听唆以行图赖。若诬连宗以主母阴事,诛死犹为罚轻。如谓凿胁是阙成所谋,伤痕何无血荫?谋杀既假,奸情决无。支秩的系教唆,连宇难逃诬告。俱应摆站,仍追苗租。”
按:此明是凿死,而检者未得其情。盖以方凿之时,即以滚水灌其伤处,故无血荫,此《洗冤录》中所未载,附之以补所未备。后之检伤者,其详之。
或曰:“水灌虽无血荫,其皮肤必有热水皱烂之痕可辨。”惟连宗刁奸主母,罪应当死,死不自冤,故检不出者,天理也。后人勿谓此计可掩伤而效尤之。是亦一见,故并记以待明者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