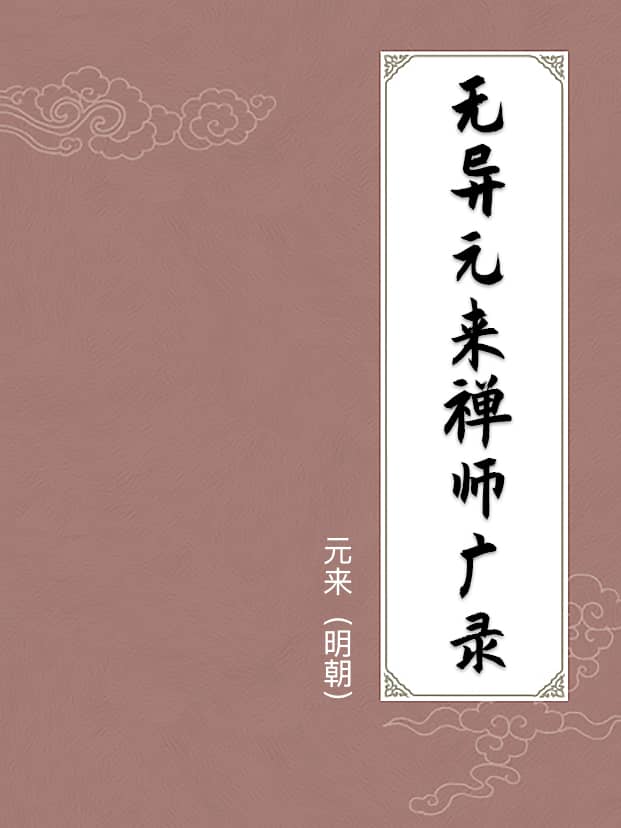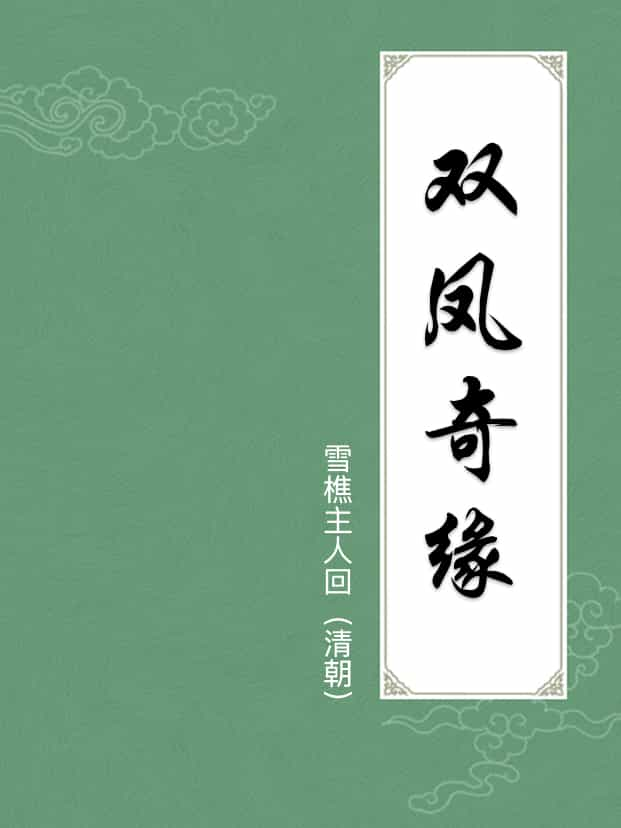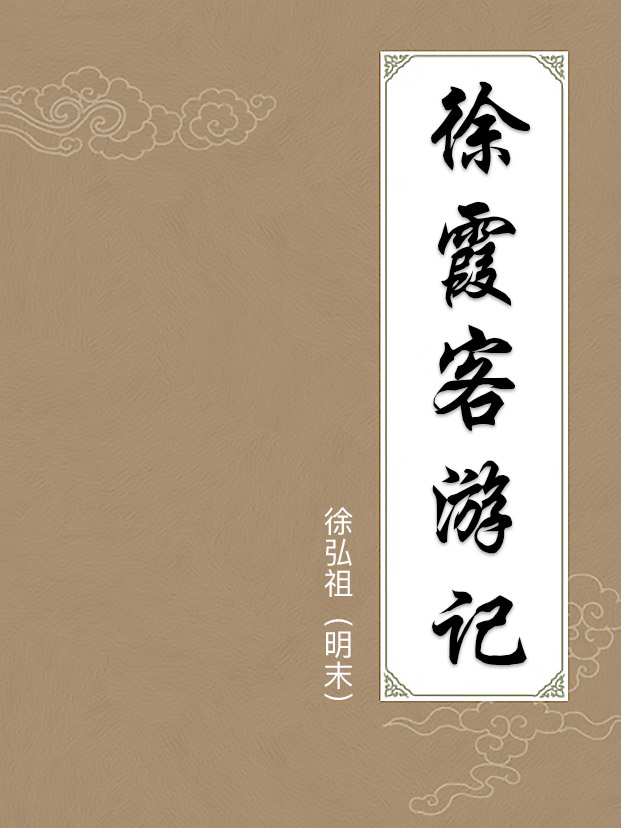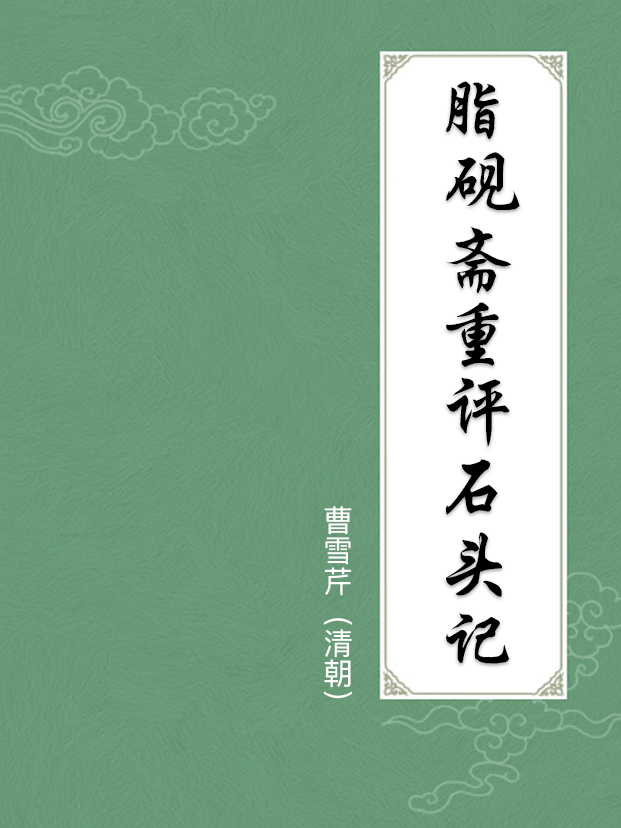本讲从希腊之爱(善乐其生的美术)与耶稣之爱(善用其死的宗教),说到罗马之大(美术、宗教、与政治的集合体)。
欧洲文字中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字,这字我们姑照普通的说法译做“爱”。从淫秽的下流直到神圣的天国,从普通的酬应(你爱罗马么?你爱吃意大利菜么?)直到人生的大故(为爱情人而结婚,为爱国家而战死,为爱人类而牺牲)都包括在这个字里。它的微妙,甚于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伟大,可以弥漫宇宙。我想用中国文字来扼要地说出它的来去之迹,终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爱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爱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后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语,就是这意义)德者虚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生,所以爱之根苗就种在生之最初,可称为世界成立之原动力,也就是孟子所谓“赤子之心”。现代婴孩心理学与生物学上得到的种种科学的见解,对于啼饥号寒等本能动作,都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明,便是生命之延长、种族之绵赓。生活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环境的阻碍力,于是而有奋斗、啼饥号寒以求生,这是奋斗的序幕。而牺牲一切以至于死,却是奋斗的最高峰,牺牲到极点至于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后和最大的大事——死,于是爱就功德完满了。(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
希腊之爱就代表爱之初,它充满了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着快乐的现在。它的美的艺术品,白石的塑像,从形式与姿态上充分表现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间的欢情。然而我们离开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内心时,就发现他潜在意识中有一个魔鬼;这魔鬼姓“未”名“来”,道号“不可知”,别字“运命”。希腊人觉得自然太威严,人太渺小,人会一下子给命运颠倒,不管你贤愚美丑,给你一个大破坏、大灭裂,至于将来是怎样、死后归何处,却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个魔鬼是常在潜意识里作怪的。他们不得已就皈依于古代的迷信,所以他们虽然活泼,终脱不掉原始人的那种困恼——对于未来的困恼,而他们的文化纵称卓越,仍未摆脱原始的色彩。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的《俄狄浦斯》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苏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他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苏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苏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苏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身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苏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的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苏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的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他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幅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字,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
(1)耶稣降生(生),
(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
(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留连忘返么?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似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转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惨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罢,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罢,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如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
当歌德看见罗马的大水渠从一个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说:“咳,到底我见解不错,我最恨的是一切矫揉造作,小刀细工,因为它没有一点真的内在的存在,就是没有生气,就是不能‘大’,不会‘大’。”他自己告诉自己,在这里人们应当充实了!
歌德看见了水渠发感慨,我却游了斗兽场——大世界才感动,一个戏园子在几分钟内可以容八万七千人进去。中世纪来把他当作矿山看
(如同中国偷城砖一块一块地搬走),拆了它七八百年的台,还是不倒,巍然存在。椭圆形的外面分作四层,而地底下伟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线空气一点不感困难。罗马人要不是具有一种伟大精神,怎样会遗留下如此伟大的成绩。
歌德说大就是真,其实也不用请外国老师,中国的孟夫子就最会说明这个“大”,他满口总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太多了,恕不备举)。他不仅赞美“大”(充实(真)而有光辉(美)之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说看见了一个小孩子望井里跑,大家都会心里一跳,看见一只牛在受宰的时候发抖,大家也会眉头一皱;这一跳,这一皱,就会皱成一个世界极乐大帝国(是心足以王矣)。这种奇迹在乎“推”,在乎“扩而充之”,他还说得极其容易,如同火烧起来,如同瀑布冲出来一样大起来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这几句话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运动的精神状态形容出来。
这种伟大无疑就是罗马文化的特色。按罗马人最初不过是一个武勇的蛮族,当一世纪时候,凭他的公平占领了地中海一带。希腊爱生的艺术,与希伯来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后输入罗马,于是法律、宗教、艺术三者互相融合结了一个胎,成为罗马文化。后来北方、东方的蛮族虽屡次侵入,而这个酵母的力量,终究能克服它们,世界各国的生活基调全都陆续受了他的陶熔。白种人今日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俨然天骄,其由来早在纪元之初。不错,现代文化是有一个伟大的开始的。
在这种宗教、艺术、政治的汇流中,我们发现它与他种文化有特殊不同之点二:
一为世界性。古罗马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主力的发展,在南而不在北。恺撒虽曾经营高卢(今之法兰西),用兵撒克逊(今之英格兰),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乐于南征,密迩的地中海就成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于陆地,则东西面向各方发展,而以筑路为统御边疆的唯一要领,所以各方驰道以罗马为中心,像太阳的光线,辐形四射。君士坦丁既定教宗,复能躬率士卒建都于东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为家,而适与宗教的保罗精神相符合。保罗就是打破种族观念,而以传教于异族为事的。
二为平民性。政体固无论其为王政专制或为贵族共和,而“媚于庶人”的精神是始终不变的。斗兽场一方面是表示罗马人的残忍野蛮,一方面可见英雄外征,犹不忘设法取得国内群众的欢心。西方人之喜欢活英雄者,或即由此。圣彼得寺固然穷奢极华,但其本意,实欲以外形的美丽庄严以肃穆群众的身心。至于一乡一市必有广场,以为群众集合之所,得一宝物必列之于群众瞩目之所。不像东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娱乐而已。这种风气,果远在卢骚《民约论》以前千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