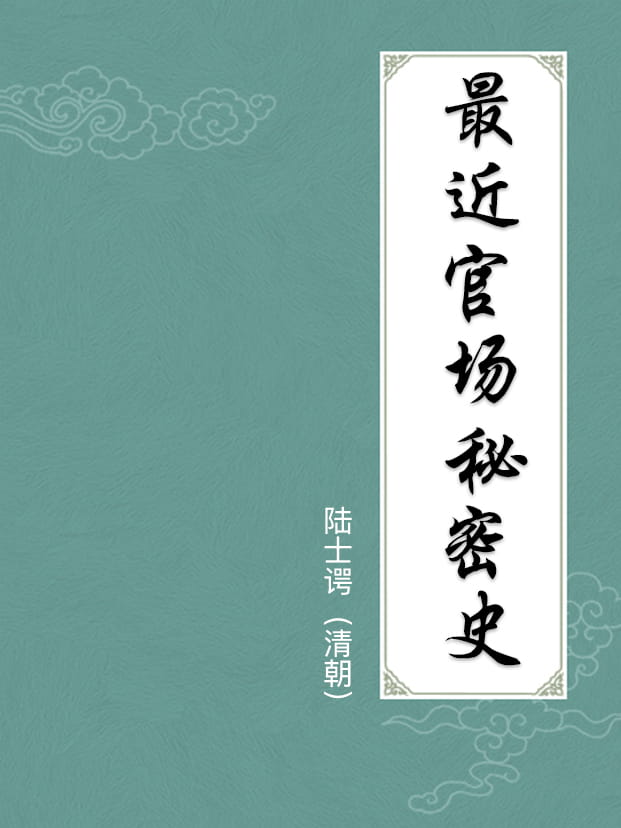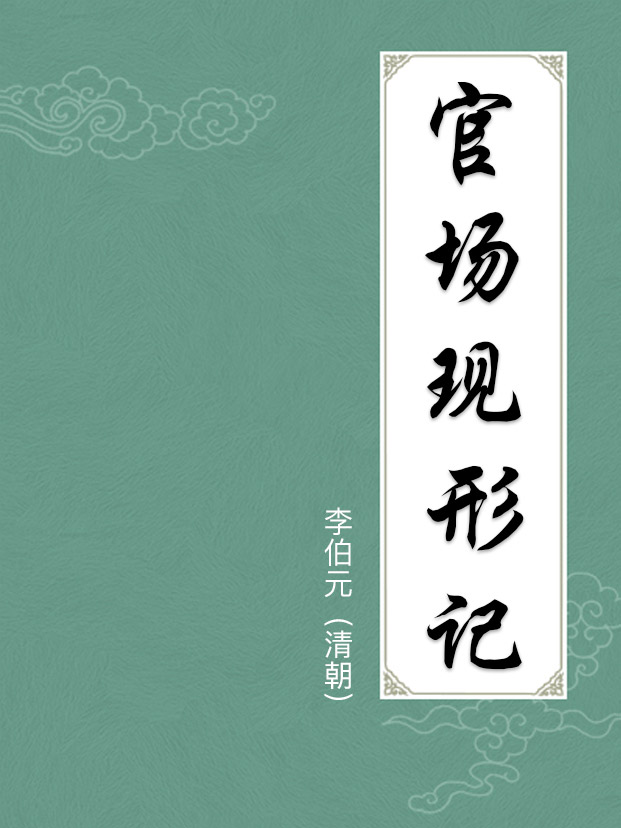话说尤大人同舅老爷饭罢,严胡子把一切公文案、卷稿由交代已过。忙了一阵,不觉已是张灯时分。舅老爷道:“我们薛家班小素那里去找温大模子,把公事弄稳帖了,可以很乐几天哩。”
尤大人忙道:“很好,很好!”于是坐轿到浣花溪明月桥堍下薛小素家。尤大人是头一次来,只见薛小素是徐娘了,风姿很是不坏。屋子里的陈设非常精雅,四壁琳琅,临窗设著一张画台,堆著好些的纸绢、扇册。尤大人道:“原来是位法家!”
舅老爷道:“小素是不会这些儿的,这是他的妹子小涛挥翰之处。”说著向小素道:“小涛姑呢?”
小素道:“妹子,张翰林接去了。还是昨儿去的,今儿回不回,还没一定哩。”
尤大人恰瞧著一幅半身的小照,竟对着出神,自言自语道:“天下有这样的美人吗?这是谁呀?”
舅老爷接口道:“这便是小涛的肖影。亲翁瞧著怎样?”尤大人道:“嗳!但愿他今儿别回来,从今而后,我也不到这里来了。不是这人也罢,省得没个开交。”
舅老爷同小素都笑道:“尤大人什么说?可不奇吗?”尤大人摇著头道:“翠子,翠子,竟是粪土一般了。……”说犹未了,只见薛小涛跚跚其来。尤大人见了,果然是“镜里佳人,画中爱宠”。不觉神魂飘荡起来。一手牵住了小涛的手,笑嘻嘻的问:“今年几岁?那里人?”
小涛答:“十八岁,眉山人。”又搭讪著问长问短,小涛一一对答,宛转娇娜,颠倒人意。小素看出眉目,便笑道:“尤大人替妹子结个线头,肯赏光吗?”
尤大人涎著脸道:“只怕你的妹子嫌我……”小涛接住口道:“嫌你尤大人什么来嗄?”尤大人嬉著嘴道:“嫌我俗、俗、俗。”
舅老爷笑道:“俗倒不俗,只怕没有胆量。”小涛听着舅老爷这般说,以为是个怕老婆的先锋。便含笑低声说道:“我不是‘琴操’,你倒是‘陈’”。说著又瞟了一眼。尤大人急道:“瞎说,瞎说!我又没带着老小来。听舅老爷瞎说,你去相信他?”
舅老爷笑道:“小涛,他是翠姑娘的心上人,翠姑娘不是你的姨姨吗?你简直的姨夫也敢鬼迷吗?”小涛听了,仿佛兜头一勺冷水似的,呆著脸不声响,想道:翠姨著名的雌虎儿,她的心上人,敢勾搭吗?尤大人忙又分解道:“又是舅老爷的瞎说了。我又到不了三四天,翠姑那里拢总去了两趟,那里说是心上人哩?她不知道我几多长,我不知她几多宽。一点儿交情都没有呢。她好管住我不跳槽吗?”
小涛道:“嗬!尤大人是才到这里来,不过三四天吗?”尤大人道:“可不是吗?你多早晚四川省城里见我这样一个人哇!”于是马上叫小涛端整一席酒,替他开个局面。舅老爷也着实赞成说:“我不再一搭儿走走,越发的有兴哩。”
须臾,温大模子到来,尤大人是初会,只见那温大模子的形状,是个确黑颀长,脸大目小,其形如獾,发声尖细。尤大人见了,不禁诧异,想道:这种样子的一个人,怎说是个富豪?真真人不可貌相哩!舅老爷忙着拉拢道:“这位是亲家尤大人,现当着院上文案老总,同中丞是有两层的亲戚,尤大人又是闻名盖世的有名人物。前儿福中堂的‘寿序’,便是尤亲家的笔墨。”
温大模子道:“嗬嗬!原来就是中翰公,前儿在江西湖北。我们盐务中人很有道及呢。台甫就是心迥了?”尤大人谦了一阵。舅老爷又道:“如今是观察公了!”温大模子着实恭维。须臾入席,尤大人推温大模子坐了首席,舅老爷次之,自己主位相陪。渐渐谈到那件公事上去,温大模子满口答应道:“既是观察说了,兄弟还有别的话吗?一概遵命。明儿兄弟打票子过来,观察公是……”
尤大人答道:“兄弟就在院上住,没有借房子。”温大模子愈加放心了。于是欢呼畅饮,夜分已深,才方各散。次日,尤大人一早到院上办事。饭后,温大模子穿着行装,来拜文案,尤大人便呈上一个禀帖,百十张,每张一万两的银票。尤大人检点清楚,同禀帖一齐收了,谈了几句。温大模子又面约晚上相好那里喝酒,开转致阮调笙阮舅老爷一起来叙叙。尤大人答应了,且说禀帖马上批出来。温大模子又殷勤了一泡,辞去不提。
且说尤大人拿了一大包的银票,又一五一十的数了一回,瞧瞧每张都是一万两,既无畸零,又不短少,整整足足百十万两银子。眼里看着心中发火,想道:银子来得这么容易,所以都想做官。譬如我只消有了这么的一二十张,一辈子的希望也就罢了。又想到自己这里头只有三千两的名分,又大为不自然起来,头里只道是拢总是十万两数目,假如舅老爷提个九扣,也不过一万银子,同我三七分拆也不算什么差远,这个还是我单做个居间人的话头,今儿也不是这等说了。何以呢?今儿我是文案老总了,他的我偏偏批的不准,瞧他们怎样?那怕上头亲自交代,这种禀帖原该不准的。我这里据理力争,当仁不让,不怕不同我讲过价钱了再说。肝火一动,便想一笔批倒,再放几个死绝的字眼上去。我也不希罕三两吊银子。既而一想:不好,不好!假如不会了这件事,我那里会得这阔差使?就是抚台太太,也未必这么要好。岂是真真念著亲戚的情谊吗?其实也不过会了这件大买卖嗄。我如今有钱赚,有差使当,别人心里不足。又不敢落笔。如要准呢?心里实在三吊银子终竟不够的……。正在委决不来的当口,舅老爷走来,笑嘻嘻的道:“温大模子来过了呢?”
尤大人道:“恭喜!恭喜!通统送来了。”说著,又一五一十的,又一张一张的点数着数目,数给舅老爷瞧。舅老爷笑得眼都没了缝。嘴里只说:“不错的,不错的!亲翁点过了,终不会错的。”好一回,方才检点明白。舅老爷又连说几声“费心、费心”,捧著银票飞也似跑进上房去了。尤大人心上又是一气,倒说三千两头就不提起了?光说了一通儿的“费心、费心”,就算完了不成?直至傍晚,不见舅老爷出来。忽然想起温大模子约著吃局,但说相好那里,不知他的相好是谁?嗄嗄!舅老爷同他玩惯了,终知道呢。便叫尤福到舅老爷房里说明原委,并说一块儿去赴约。尤福去了一会儿。只见舅老爷泪容满面的,匆匆跑出来,只嚷着:“怎了,怎了?”
尤大人大吃一惊,不知为了何事,急忙的接着道:“做什么?做什么?”舅老爷拿出一张电报来,尤大人瞧著只有五个字是:“母病危速回。”舅老爷跺脚道:“方寸已乱,只有连夜动身,赶程回去哩。”尤大人道:“老太太有多少高寿了?”舅老爷道:“七十多了。”
尤大人道:“年高很了,亲翁原该赶紧回府呢。”明知温大模子那里决计不去。便问了温大模子的相好是谁,那里住着。舅老爷道:“就是小涛的对门,姓花,叫做花魁的便是。”
尤大人顿然想着昨儿舅老爷在小素那里,写条子去请温大模子,原是这个所在!又怪自己粗心、不玲珑。舅老爷又忙忙的进去了。尤大人便一直来到小涛那里。小涛已知尤大人是有鸦片烟瘾的,忙端烟具,帮着烧烟。尤大人道:“打发个人到对门花魁那里瞧瞧温老爷到也没有?”
小涛连忙打发人去瞧,回来说:“温老爷坎坎才到……”说犹未了,温大模子的请客条子送过来了。尤大人说声:“知道了。”便抽了一泡鸦片烟,带了小涛,过对门花魁那里。温大模子同著四五个人先在那里了。尤大人一一招呼已过,便知都是盐务中人,少不得同他拉拢。温大模子道:“阮调翁怎地不来?”尤大人道:“坎坎有电报来,阮亲家的老太太病势濒危,年纪又高,七十多了!所以连夜赶回。这分际,只怕已动身了。”
温大模子道:“敢是祖母呢?调翁不过二十二三岁光景,太夫人忒老了,只怕养不来呢!”这一句话把尤大人问住了。既是亲家,又不能推说不晓得。算算年时只怕勉强还可以养得出,然而五十左右会生育的妇人,实在少有。便顺口儿道:“阮亲家是庶出的。”
温大模子也就没说什么。并且如今既拉拢了尤大人,权力不亚于舅老爷,所以舅老爷回去,也不在他心上。须臾入席,自然是尤大人占的首位。不料,内中有个姓洪的叫的翠子的条子,一时翠子到来,却见尤大人事著小涛的局,心里已不自然,明是小涛夺了他的客。等到散席,便硬逼着尤大人到他家去。尤大人一心迷著小涛,早把翠子抛向东洼里去了;并且没有交情,不过喝过一回酒,便跳槽也没有什么规矩。所以推三阻四的不去。翠子却死活的要尤大人去。一来知道尤大人是个阔人;二来小涛是他的幼辈,吃她夺去,很不舒服。心上又不勉动了一个“醋”字,忘其所以。姓洪的在旁边,面子上过不去,头里还不敢什么。看着翠子忒煞丢他的脸,未免动气。便道:“翠子,你们打把势的也有个规矩。尤大人既然不愿意去你家,你何苦硬逼着呢?”一语提醒了翠子,这儿原是姓洪的带的局,便瞅了姓洪的一眼,道:“那么洪老爷去我家坐一会儿,赏个脸罢。”
姓洪的“哼”了一声道:“我够得上赏你的脸?承你说一声儿叫我家去坐一会儿,承你赏我的脸了!”
温大模子拍手道:“老洪的话比刀还厉害。翠子,你也本是忒不当洪老爷人看待了。”小涛插一句道:“翠姨,那会有错节,斗着我孩子家玩哇!”
温大模子还不知其中委曲。小涛便道:“尤大人原在翠姨那里,不过喝一回酒,无别的交情。我是问的明白了,才敢留下尤大人来。这么著,可不是他同我小孩子家玩吗?”
温大模子道:“嗬!昨儿尤大人在你处过夜的?”小涛道:“可不是吗?我们这么嘴脸的人,大人老爷们赏一个脸下来,请一会儿客,敢拿架子不留下吗?我们仗那门子的腰,敢拿架子,吃人家夺去吗?”
翠子听着小涛仗着已是有了交情,力量足以敌得过,便句句奚落他,不禁无名火一旺,便喝道:“小涛,你别要人仗狗势,不放长辈在眼里。我便管教得你!”
顺手一个巴掌打过来。小涛躲在尤大人身边哭起来。尤大人怒道:“谁没规矩?在这里放肆!我尤大人带来的局,那个敢欺负他?”
翠子道:“尤大人别护里头,他是我的姨甥女儿,姨娘管教姨甥女,是家事,用不着外人干涉。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四川省里没见过青天大老爷呢,即使青天大老爷还断不得家务事情哩!尤大人,你干的公事我又不是糊涂虫,什么不知道?”
尤大人做贼心虚,其实温大模子的一局,翠子并不知细,这一套话,不过大概而论罢哩。尤大人却道是翠子知细原委,拿话来堵他的嘴。官场中却最忌这一门子。于是气黄了脸道:“翠子!这是明明和我过不去了!所以把狗仗人势的一句话,颠倒过来说什么‘人仗狗势’”。温大模子同众人也觉著“人仗狗势”的一句话,翠子忒煞没情理了。都说这是翠姑娘说忙了,说错的,并不敢得罪尤大人呢。翠子原是著名的泼货,还不见机,顶一句道:“得罪了,也没杀头的罪嗄!”众人一听,决计要闹乱子,犯不着和在里头,只有温大模子是主人,溜不得,其馀都溜得一个也没了,连着姓洪的也走了。尤大人冷笑一声道:“明儿有人来找你说话!”拉着小涛走了。翠子拍手道:“逃的不是好汉。”说著也走了。花魁咋舌道:“翠姑娘念地狂到这么地位?”温大模子道:“尤大人只怕不肯甘休呢。”花魁又道:“那尤大人人前儿没见过他,敢是初到省吗?”温大模子道:“他是抚台的亲戚,到不了三四天,已委了院上文案老总了。你想这种人,岂肯吃姑娘们白糟蹋一泡的吗?”花魁道:“原来是个阔人,所以翠姑娘拼命的争了!”温大模子道:“平心而论,翠子那里争得过小涛呢,小涛一来年轻,再者名望又好,一点子书画原是不错。翠子究竟三十来往的人,又生了这种性格,吃亏得算不清呢!”花魁道:“可不是吗?只怕洪老爷也不敢请教了。岂不又丢一户花钱的客吗?”
议论一番,我且慢表。且说尤大人同了小涛回去,挑拨了许多言语,尤大人其实放他不过,明日想个计较,把首县马大老爷传到院上。这马大老爷是南直隶人,顶会的是迎逢拍马屁。当日马大老爷马上上院,一径来见文案老总,晓得是个道台,照例上手本禀见。尤大人着实谦和,讲了几句官话。马大老爷又欠著身道:“大人呼唤卑县有何吩咐?”
尤大人陪笑道:“请老哥过来有一点小事情麻烦老哥,莲花池后面张家堂子班,有个婊子唤做翠子的,兄弟不愿意她在这里。老哥想个法儿赶掉她。还得给一点子利害她尝尝!”马大老爷连忙答应着,又道:“妓娼本干例禁。但是如今科派了他们捐项,地方应有保护之权。大人明鉴,当婊子的有甚依著本分的人,如今指了两个钱,直是奉宪开办的营生似的,傲慢的人样都没有了。不瞒大人说,卑县没有署缺的当口,也有点应酬,所以深知的。卑县回去立刻办就是。”
尤大人又灌了几句米汤,便端茶送客。马大老爷回到衙里,想道:这翠子似乎是一个老妓,稍微有点子些小名声。不知他有护法的人吗?这个倒要弄明白的,不然得罪了旁边人,我落了不是,其实合不来。想起钱谷上尹老夫子,天天玩在堂班里的,作兴知道翠子的历史。便来到尹师爷房里,把尤大人的意思说了一遍。尹师爷道:“翠子,却有两个翠子,不知是那一个翠子?”
马大老爷道:“莲花池后面张家的那一个。”尹师爷道:“这样翠子,只怕动不得!他有铜元局老总沙观察的护法呢!”马大老爷道:“嗬嗬!沙壳子的心上人吗?”
原来这铜元局的总办姓沙,同马大老爷同乡,也是南直隶人。他的祖老太爷是个有名的画师,“恽南田后,一人而已”。曾经供奉内廷,名望颇重,因此儿孙辈都做了官。如今祖老太爷是死去多年了。就是沙观察的老太爷也没了近十年哩。这沙观察由同知分发到四川来,仗了里头沙公公的提携,连保带捐,过了道班,当这铜元局差使,已是三五年了。随便那一个摇动他不得!在铜元局上发了算不清的财,所以大家提他一个绰号叫做“沙壳子”。沙壳子原是私板小钱的别名,赠到这个绰号,足见沙观察的政绩事。沙观察为人粗糙,性格莽撞,唯有当面叫他“沙壳子”,不但不怒,还且欢喜,因此上下三等都叫他“沙壳子”了。他的真名号,大家倒不知细的多,只是“沙壳子”三字通省皆知,妇孺共晓。前儿曾经吃都老爷有过闲话,沙公公的力量,不但没有参掉他,反把那都老爷赶回原衙门去。于是有谁高兴同他做对头呢?闲言少叙,且说马大老爷道:“沙壳子护在里头,倒不好弄他。尤大人那里又是将就不得。那末怎么办?”
尹师爷道:“东家别慌,晚生是有道理。停儿,晚生去问明白,设法儿同他们解和了吧。”马大爷道:“解和最好,‘和为贵’。老夫子说到这‘和’字,足见办事得了妙诀哩!”尹师爷笑道:“且慢欢喜著。这事儿其实不好弄的,倘使和不来,岂不难为了中间人?”马大爷道:“瞧著吧!老夫子的大才没有弄不好的事情哩。”说罢进去了。尹师爷盘算一会儿,也不带着底下人,一个儿跑到莲花池后翠子那里。翠子见是尹师爷,常见他和沙壳子做淘的,便请到房里坐了。尹师爷道:“沙壳子没有来吗?”
翠子道:“咦!沙壳子宜昌去了,尹师爷还没知吗?去了三天哩。”尹师爷道:“没有知道呀!他去宜昌做什么?宜昌是湖北省地界,不见得是公事呢。”翠子道:“你们做淘的难道不晓得吗?为了宜昌盐引的事情,只怕有一二十天耽搁呢!”尹师爷道:“他在宜昌包著盐纲的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自己去瞧过一回的。这会子,只是自己去瞧看,敢是出了什么乱子吗?”
翠子笑道:“尹师爷亏煞你是首县衙门的师爷,地方上的事,简直的一点儿不知道。如今温大模子禀准了抚台,他独包呢。”尹师爷笑道:“这种事那里会准哇!不过温大模子打他自己的如意算盘罢哩。”翠子冷笑道:“如今还有公道吗?看谁的手长罢哩!”
尹师爷到底不信,便道:“沙壳子不在这里,倒有点费手了。”翠子道:“你要找他做甚?”尹师爷道:“找他呢,也是为了你的事情嗄!”便把尤大人如何传见首县,嘱咐设法儿倒你的蛋;首县如何同他商酌,及知你有沙壳子的护法,如何为难……,说了一遍。又问翠子到底怎样得罪了尤大人呢?翠子冷笑一声道:“尽他罢哩!看谁有脸嗄!尹师爷,你也犯不着网在里头。我是穷姑娘,没有钱塞狗洞的,要想弄两个也要有点知识呢。”说罢又冷笑了几声,只顾自己抽鸦片烟了。尹师爷道:“阿呀!你缠错了。我是一片热心,谁指望要弄你钱哇!要想弄两个,不先设个儿把你圈起来了?弄两个怕不爽快些儿!”
翠子“哼”了一声道:“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尽请你圈吧。”说著又朝空中啐了一啐道:“笑话吗!”尹师爷瞧这情形,又羞又恼,那里还坐得住?由不得拿脚就跑。跑回衙里,直撞到签押房里,只喘气。马大爷道:“什么事?气得脸都黄了。歇一会儿。”等尹师爷说合话来,便把翠子的情形益发的装花缀叶的说了一遍。马大老爷听了,也觉生气。道:“天下竟有这么蛮横的婊子!……”
尹师爷道:“恰好沙壳子不在省里。不给点利害他瞧瞧!这个衙门简直的可以毁了;官也不用做了。一个婊子,有多大的头衔嗄!”马大老爷吃尹师爷一激,也恼得破了顶门,便道:“罗织他一个什么罪名好呢?”尹师爷笑道:“晚生想在心上了,翠子是抽大烟的人,他原仗着沙壳子护法,堂而皇之的把烟具放在屋里。只消入他一个‘偷食禁烟’,便打也打得,枷也枷得。顶真起来还可以办一个递解回籍哩。”
马大老爷道:“也好。还是便宜他的事情呢!”立刻标差。没顿饭工夫,只见差役一条链子锁了翠子来。又交上两支烟枪,一盘烟具,一大蜜缸膏子。马大老爷升坐大堂,把翠子提到案下,怒吼吼的问道:“你偷吃禁烟。可知罪吗?”翠子不慌不忙从身边取出一张执照来,呈验道:“小女子吸食大烟,原领过照的,并没违犯禁令。”
马大老爷冷笑一声道:“好辩的干净!据你的执照上每天只吸得三钱膏子,这一缸怕不止三两膏子呢。并且要两支烟枪,什么用处?明明是私售灯吃。”翠子辩道:“执照上虽然填著膏子的分量,如今没有开办官膏,原许买士自煎自吃,若是每天里煎熬三钱膏子,每天里吃,大老爷的告示在那里?小女子没有见过。大老爷要在小女子身上寻些事故,还请换个题目吧。”说罢冷笑。朝着两旁差役啐了一啐道:“笑话吗!这是皇上家的法堂,并不是……”
马大老爷大怒道:“就换个‘顶撞官长’的题目来问你吧!”喝打五十皮鞭。翠子到这儿才慌了,求免责打,情愿重罚。马大老爷笑道:“你说的‘不到黄河,不死心’,如今到了黄河,不自由哩!”到底打了五十皮鞭,又饶上了二百,共是二百五十皮鞭。打得翠子“一佛出世,二佛涅盘”,紧咬牙不啧一声。打罢,马老大爷道:“你心上可服?”
翠子不充耳闻,闭眼低头,只装作睡去的样子。马大老爷把案儿一拍,又喝:“再打!”翠子抵拼着打死不答话。掌刑的心上倒老大不忍,悄悄的道:“求求大老爷,谢了恩板。不然,又要打了。法堂上不是使性儿的去处。”翠子哼哼啧啧的道:“这里怎说是法堂嗄!强盗的众议厅还讲的情理哩,没这样黑暗!”马大老爷转怒,乱拍案儿,一迭连声的喝着“实给我打!……”翠子放起泼来,向地上一滚道:“不打死我,不算好汉!咱的舅子!”差役吆喝道:“别乱说。敢是疯了?”
马大老爷见他这个样子,名儿叫作“拼死撞了”。倒奈何他不得!究竟“酷刑死命”,担著老大的处分。拿功名同他拼,其实划算不来。马大老爷原是个滑吏,眼见得顶下去没个收场,借势收科道:“果然疯了。且押下去!明儿叫他尝尝拶指的味儿。”翠子道:“明儿做什么?要拶就拶,明儿就轮不着你使威了!难道除了沙壳子,再没有人同你答话了吗?”马大老爷也不理他。只喝着:“押下去!押下去!”
马大老爷便退堂下来,同尹师爷商议道:“这么著尤大人那里也可以销差了。但是他说除了沙壳子,还有人同他出场哩。老夫子想想,看他还有谁是硬腰子呢?”尹师爷思索一会儿道:“他只有沙壳子是顶恩不过的。除他之外,都嫌他性格不好,没有同他说得来的。而且他是明日黄花,没几多客。同沙壳子也是前世里的缘法,凭他闹什么脾气,另人总觉难堪呢。沙壳子总是对他笑笑就完了。光景他故作大言,吓吓人罢哩。”
马大老爷便安了心。连忙上院,禀覆尤大人,顺便请示如何结案。尤大人道:“够他受用了。凭老哥的意吧。”马大老爷道:“凭卑职的意见,索性递解回籍,省得沙壳子回来另生枝节。给他个一辈子不得会面,也是防微杜渐的一法。大人以为如何?”
尤大人模拟了一会儿道:“虽然。只怕堵不住沙壳子的枝节。横竖我这里是有法儿呢。”马大老爷答应了几个“是”。尤大人仰了一会儿脸道:“兄弟明儿造一份札子送给老哥,只算中丞的访案。沙壳子有胆量同中丞闹乱子吗?”
马大老爷道:“大人主见,很好!决计这么办吧。”于是辞了下来。回到衙里,接着藩台的三少爷送来一封信,措词很不自然,立刻要把翠子交出带回。马大老爷看了,慌了手脚,急忙的请尹师爷来商议办法。尹师爷皱着眉道:“这倒棘手了。怎地弄出藩台的三少爷来讨人呢?晚生素知藩台的家教极严,断不容三少爷在外边嫖妓宿娼,硬来讨人。若是这封信靠不住,那末翠子该死了!可以办得他一辈子不出头。沙壳子也没办法护他哩。”马大老爷道:“这信,若说是假造呢?也未必;要是瞒着他老子写的?情或有之。这样吧……”附着尹师爷的耳根子道:“如此这般,瞧著好吗?”
尹师爷连连点头道:“这是金锺罩的法儿,使得着,使得着!”即便打发人去了。次日,果然尤大人送到一个札子,倒填日子。马大老爷于是有恃无恐,便把翠子提了出来,办了个递回眉山原籍。唉!翠子只为了一点耐性儿,倚著沙壳子的势派,起初得罪了尤大人,继而又得罪了尹师爷,及至签差提案,还不知饥,当堂顶撞了马大老爷。全不想沙壳子恰正离省,远水救不了近火。自以为藩台三少爷是个硬腰子,岂知又是私窝子出不得场,白白的把一个门户弄得五分四散。等到沙壳子回来,也没法奈何了!真真是“倾家县令,灭族都堂”。中国的官生生的把人吓死。无缘无故有本事可以弄倒怎么个田地!只怕地球上打不到第二个中国官似的利害。虽然翠子一案,大不了是个娼妓,算得什么?简直的割鸡而用牛刀哩。闲话少说,且归正传。有天沙壳子回来,忙着去瞧翠子,却见门庭如旧,人物已非。原来缪家的趣凤搬来住了。沙壳子和趣凤也是熟人,忙问:“翠子搬在那里去哩?”
趣凤道:“沙大人请坐了,朝你说……”便把始末根由说了一遍。沙壳子骇然道:“那得来这等事?难道凭空的可以把人坑了吗?至于抽大烟,又不是他一个。别说印人,就是抚台大人不是一样,依然抽吗?你说什么个‘尤大人’,同寅里面不曾有这个人,那一门子的热屁?首县只是捧著当做八珍羔似的,简直的把我沙壳子都不放在眼里呢!”这当儿,沙壳子的面皮气的黄了。趣凤道:“沙大人,别这么的著恼,气坏了身子是不值的。我们知道的不过表面上情形罢哩。打量还有别的内容呢?”沙壳子道:“这事儿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薛家的小涛。我也有法儿,既是那姓尤的会收拾我的翠子,我也会收拾小涛呢。”趣凤道:“这个只怕冤了小涛呢。”
沙壳子道:“翠子到底也没有犯法呀!”又说了些闲话。次日,沙壳子写了一封信,叫当差的送到首县衙门去,马大老爷连忙开看,说“薛小涛私卖禁烟,留人过瘾,应提案从重严究”等语。马大老爷看了,心里想着:不好了!沙壳子来倒我的蛋了。不想沙壳子是粗躁的人,这儿倒也会使些乖儿,给个难题我做。满口应承,把来差打发去了。同尹师爷商量,尹师爷道:“这个举动,沙壳子还没知细我们有上头的公事下来,所以办的。只知道我们捧了尤大人的热屁,因此假手我们,同尤大人寻事哩!既如此,顶容易办了。一面签差去拿人;一面先把薛小涛送到尤大人那里去。尤大人见得我们办事有能耐,等到差人去扑了个空。那末面覆了沙壳子,提明翠子一案,是上头访案,让他去寻中丞的事吧。我们云端里看厮杀,岂不有趣?”
马大老爷拍手道:“老夫子竟是智多星吴用了。”尹师爷笑道:“这个说不得。若说晚生是智多星吴用,堂堂知县衙门怕不成了强盗窝哩!”马大老爷笑道:“老夫子,如今我们这件营生,老实说强盗同我们比起来,强盗还是慈善会的会长呢。”于是如法炮制。等到差役空手回来,据情禀覆。马大老爷勃然大怒,马上升堂,把一个差头绰号儿唤做“长脚詹仁”的,说印得钱卖放重要犯罪。不由分说,连连“打!打……”,打到二千板子,打得长脚詹仁皮破血流,两条腿儿仿佛一个血饼儿似的,两次三番昏了过去。醒了过来,方才押去牢里收看。退下堂来,马上到沙壳子公馆禀见。沙壳子接见道:“老哥,兄弟交办的事怎样了?老哥是著名的能员,一定已办稳贴哩。”
马大老爷道:“回大人的话,卑县接到大人宪札,立刻签差长脚詹仁率领看班捕役、民壮、团丁前去捉拿要犯薛妓小涛。不料,该差得贿卖放该妓,声言:‘知风在逃’等语,前来禀覆。卑县也不管他,该差是否得钱卖放,还是该妓实在闻风逃遁……。”沙壳子道:‘疾雷不及掩耳’的公事,有谁去‘知风报信’呢?一定是该差得钱卖放,兄弟只问老哥要人,别的不管!”
马大老爷站着答应了几个“是”。又回道:“卑县也是这样的主意,因此立提该差当堂重责二千五百板,随委典吏一员,会同营讯,四处兜拿,务获要犯,一名薛妓小涛,以伸国法,而体宪意。”沙壳子到底是粗鲁人。听到“而体宪意”的一句话,明明是猜着自己的意思替翠子报仇。因道:“兄弟办的是公事,并无别的意思,老哥别这么样说,假如谣传出去,你我的名声儿有点不便吗?兄弟做到监司大员,难道要平白冤一个妓女吗?”
马大老爷答应了几个“是”。又回道:“譬方翠子的一案,原是中丞的交件,外人那一个敢说尖闲话?说是翠子得罪了中丞,交到卑县手里,以公报私呢;和大人交到卑县手里的公事,原是一个样子的呢。”沙壳子愕然道:“嗬嗬嗬!翠子一案,原是中丞的交件吗?”
马大老爷道:“是”。沙壳子仰著脸,白着眼,嬉开了嘴,摇了几下头,歇了一会儿道:“我还有脸做官吗?我同他疙瘩去。”马大老爷暗暗欢喜道:那末你这沙壳子要还炉了?支吾了几句,只等著送客。沙壳子竟忘怀了,立起身来,一迭连声的“看轿!伺候着……”上院去。马大老爷只得禀辞下来,差人到院上去打探沙壳子怎样的胡闹?这且不表。且说沙壳子怒吼吼的上院禀见。方抚台正在签押房里看《玉历警世丛钞》,齐巧看的是莲池大师“放生篇”。巡捕回道:“铜元局沙道禀见!”
方抚台抬起眼皮把巡捕瞧了一瞧,悠悠然道:“有公事吗?今是癸酉金危满黑道的日子,又是天巫主日,不宜会客。叫他明儿来。”巡捕道:“据沙道说有极要紧的公事回大人。”方抚台皱着眉道:“今儿的日子,其实会不得客。你且把黄历来看。”巡捕连忙呈上黄历,翻出当日的日子。方抚台瞧了一会儿,又把指儿抡了一会儿,沉吟道:“嗬嗬!今儿的天巫是‘民日天巫’。若是会客,到底万分的勉强。但是沙道当着铜元局的差事,乃是财政上有关系的,他又是同钱铺、银号交往最热,或者我的存项上有甚关系,也未可知。”点了点头,说声:“请!”
巡捕咬著嘴要笑,又不敢,只得退了出来,爽爽快快的笑了一阵。须臾,沙壳子跟着巡捕西花厅请见。方抚台一见沙壳子一脸的不高兴,只道是倒了那个钱铺子?忙道:“老哥在外头,可听得钱铺子有甚不稳当的风声吗?兄弟谦裕了存进一大票款儿,还只有十来天哩。看看如今的市面,兄弟其实不放心。给合言之,究竟外国银行家来得稳当多呢!兄弟想汇几笔到汉口‘汇丰银行’去存放。老哥高见,以为如何?’”
沙壳子听了,又气又好笑,只得忍了气道:“回大人的话,职道没有听到甚钱铺出什么乱子。”方抚台合掌道:“阿弥陀佛!这也罢了。兄弟别的事情都不怕,顶怕的是这一门的风险。既这么著,老哥不在家快乐,老远的跑来做什么?”沙壳子道:“职道跑来要请问大人,如今朝廷虽说是禁烟,飭令很严,以符立宪的基础,然而到底是瞒上不瞒下,官禁私不禁。不要说职道欢喜抽几口玩,就是四川一省而论,督抚藩、学臬、巡警、劝业盐茶、分巡各道,以至差道府同通州县佐腻,大中小三班,不止四五千人,或是素无嗜好,或是遵旨戒除,其实有限。倒是仍要抽几口,才能过日子,只怕十分里头,还占著七分呢。”方抚台道:“慢来,老哥在这里咭咭■■的说些什么?兄弟弄不灵清。”
沙壳子发起牛性来,也不当他是个抚台,高声道:“职道说的灵灵清清的。大人别假作痴聋!职道说鸦片烟禁者自禁;抽者尽抽。原是公公平平的勾当。我们官场中既然一样在那里抽,就管不得百姓不准抽烟哩。就叫‘其自不正,虽令不从’,‘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普通的俗谈,如今大人是通省人员的表率,还是一天没有一两马蹄膏就过不得日子。翠子不过一个婊子罢哩,蚂蚁似的一个人,何苦来捉他缺子?别的缺子尽多著,何苦捉吃鸦片烟的缺子呢?真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上了话谱哩。大人有什么同职道过不去,尽同职道说,何苦来捏这软货?大人怎样说?给职道说一句。说!说!说……”
方抚台听罢,朝巡捕一个巴掌,巡捕蓦地里吃了一巴掌,摸不著头脑,连忙倒退几步。方抚台抬起腿子又是一靴脚,道:“王八生的!逃到那里去?我原说日子不好,会不得客。生生的撮弄我出来,横说有‘公事面回’,竖说‘有公事面回’。这种公事我找不到。你瞧,你瞧……这个情景,不是拿口舌来同我倒蛋吗?如今是好了,破过了!晦气了!”
说著又朝着沙壳子道:“今儿是不宜会客日子。假如会了客一定多口舌。所以兄弟拿他来打上一个巴掌、踢上一靴脚,终算应过这晦气了。老哥说的一泡话,兄弟实在找不到。但是老哥的气色实在不好看,同兄弟斗口似的。老哥不妨删繁就简,说一个明白。然而老哥当着兄弟面前这么放肆!兄弟是白简无情的。”说著放出一个动气面孔来道:“你说,你说!”
沙壳子冷笑一声道:“职道也没脸做官了。要参,请参!自己干的事,假装着不知道,哄谁?”说罢,站起身来,拿脚就走。方抚台追上去,一把拖住了沙壳子道:“说个明白再走。这种样子,官场上其实创见。到底老哥同兄弟怎地过不去?”
沙壳子道:“嘻!不作兴不说吗?要说就说,也使得。大人交首县马令办的翠子一案。职道其实气不服!”方抚台诧异道:“翠子一案是什么的案情?兄弟到任如今,也没有交马令办什么案子呀!”沙壳子倒愣住了。方抚台又道:“阿弥陀佛!冤枉人是罪过的!念一辈子的《金刚金》,也忏悔不来的!到底什么案子?兄弟一点子因由都没有呢。”沙壳子虽然莽撞到一万分,忽觉其中有点儿蹊跷,怕不上了马令的当吗?禁不住心里著慌,这个乱子倒闹得比天还大。忙道:“职道其实发了昏了,求大人恩鉴。这翠子的案情是……”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方抚台大诧道:“这是那里说起?何曾有这件事情呢?”冷笑一声道:“老哥,办事的理路,其实灵清之至。老哥差委,预备交卸吧!”
沙壳子这个当儿弄得个六神无主,搔首不著痒处,撤差还是小事,严查看光景也免不来哩。里头虽有沙公公的扶持,然而,这个乱子闹得忒希奇了,只怕沙公公寒了心。那末不得了哩!想到这里,惶恐万分,少不得乱磕头求开恩。方抚台气极了,也不理他,朝里一踱。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