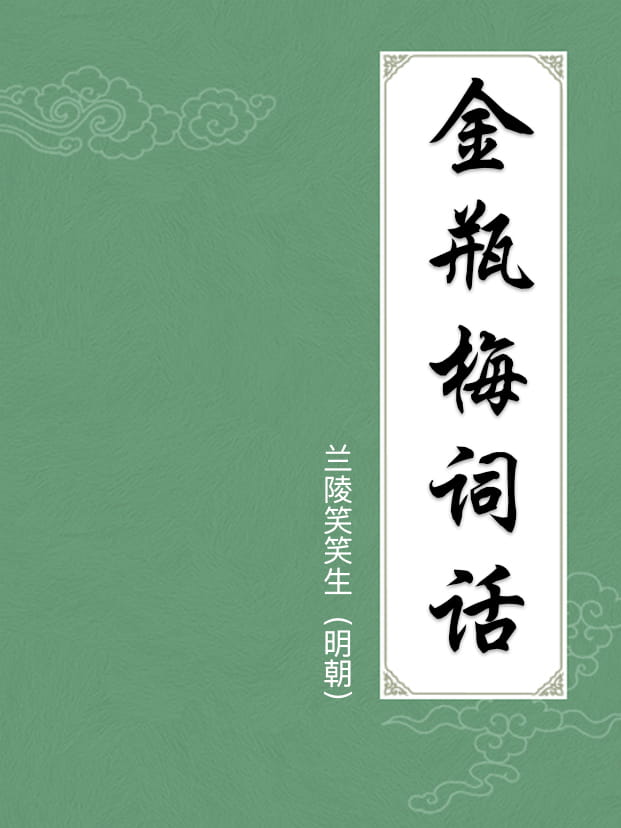「赤绳缘尽再难期,造化焦端敢恨谁,
残泪惊秋和叶落,断魂随月到窗迟;
金风拂面思儿处,玉烛成灰堕泪时,
任是肝肠如铁石,不生悲也自生悲。」
话说当日孙雪娥、吴银儿两个,在旁边劝解了李瓶儿一回云云,到后边去了。那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李瓶儿死了生儿,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的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都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都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吊泪。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自从坟上葬埋了官哥儿回来,第二日吴银儿就家去了。老冯领了十三岁丫头来卖与孙雪娥房中使唤,要了五两银子,改名翠儿,不在话下。这李瓶儿一者思念孩儿,二者着了重气,把旧时病症,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一遍,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药越旺。那消半月之间,渐渐容颜顿减,肌肤消瘦,而精彩丰标,无复昔时之态矣。正是
「肌骨大都无一把,如何禁架许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气凄凉,金风渐渐。李瓶儿夜间独宿在房中。银床枕冷,纱窗月浸。不觉思想孩儿,欷歔长叹。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弹的窗棂响。李瓶儿呼唤丫鬟,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来,倒靸弓鞋,翻披绣袄,开了房门,出户视之。彷佛见花子虚抱着官哥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这李瓶儿还舍不的西门庆,不肯去。双手就去抱那孩儿。被花子虚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惊觉,都是南柯一梦。吓了一身冷汗,呜呜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
「有情岂不等,着相自家迷。」
有诗为证:
「纤纤新月照银屏,人在幽闺欲断魂,
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根。」
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单税银两。西门庆这里写书差荣海拏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段礼物谢主事。就说此船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铺面完备,又择九月初四日开张。就是那日卸货,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那日亲朋递果盒、挂红者,约有三十多人。乔大户叫了十二名吹打的乐工,杂耍撮弄。西门庆这里,李铭、吴惠、郑春三个小优儿弹唱。甘伙计与韩伙计都在柜上发卖。一个看银子,一个讲说价钱。崔本专管收生活,不拘经纪买主进来,让进去,每人饮酒二杯。西门庆穿大红冠带着。烧罢布,各亲友都递果盒。把盏毕,后边厅上安放十五张桌席,五果五菜,三汤五割 ,从新递酒上坐,鼓乐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礼花红来。西门庆回了礼物,打发去了。在座者有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韩姨夫、吴道官、倪秀才、温葵轩、应伯爵、谢希大、常时节。原来西门庆近日与了他五十两银子,使了三十五两,典了房子。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了个小小杂货铺儿,过其日月不题。近随众出分资来,与西门庆庆贺。还有李智、黄四、傅自新等众伙计主管,并街坊邻舍,都坐满了席面。三个小优儿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吕红衲袄:「混元初,生太极」云云。须臾,酒过五巡,食割三道。下边乐工吹打弹唱,杂耍百戏过去,席上觥筹交错。当日应伯爵、谢希大飞起大锺来,杯来盏去,饮至日落时分。把众人打发散了,西门庆只留下吴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温葵轩、应伯爵、谢希大,从新摆上卓席,留后坐。那日新开张,伙计攒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晚夕收了铺面,把甘伙计、韩伙计、傅伙计、崔本、贲四连陈经济,都邀来到席上饮酒。吹打良久,把吹打乐工打发去了,止留下三个小优儿在席前唱。那应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来。出来前边解手,叫过李铭,问李铭:「那个扎包髻儿的清俊小优儿,是谁家的?」李铭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说道:「他是郑奉的兄弟郑春。前日爹在里边他家吃酒,请了他姐姐爱月儿了。」伯爵道:「真个?悝道前日上布送殡都有他!」于是归到酒席上,向西门庆道:「哥你又恭喜,又抬了小舅子了。」西门庆笑道:「怪狗材,休耍胡说。」一面叫过王经来:「斟与你应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吴大舅说道:「老舅,你怎么说?这锺罚的我没名。」西门庆道:「我罚你这狗材,一个出位妄言!」那伯爵低头想了想儿,呵呵笑了道:「不打紧处。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从来吃不得哑酒。你叫郑春上来唱个儿我听,我纔罢了。」当下三个小优,一齐上来弹唱。伯爵令李铭、吴惠下去:「不要你两个。我只要郑春单弹着筝儿,只唱个小小曲儿我下酒罢。」谢希大叫道:「郑春你过来,依着你应二爹唱。」西门庆道:「和花子讲过,有个曲儿吃一锺酒。」于是玳安旋取了两个大银锺,放在应二面前。那郑春款按银筝,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儿十六七,见一对蝴蝶戏。香肩靠粉墙,春筝弹珠泪。唤梅香,赶他去别处飞。」
郑春唱了个:「请酒!」伯爵刚纔饮讫,那玳安在旁连忙又斟上一杯酒,郑春又唱道:
「转过雕阑正见他,斜倚定荼{艹縻}架。佯羞整凤钗,不说昨宵话。笑吟吟,捏将花片儿打。」
伯爵吃过,连忙推与谢希大,说道:「罢,我是成不的,成不的!这两大锺把我就打发的了。」谢希大道:「俊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来?我是你家有〈毛皮〉的蛮子?」伯爵道:「俊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儿,少不的是你替。」西门庆道:「你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个韶武。」伯爵笑道:「俊孩儿,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让与你就是了。」西门庆笑令玳安儿:「拏磕瓜来打这贼花子。」那谢希大悄悄向他头上打了一个响瓜儿,说道:「你这花子,温老先生在这里,你口里只恁胡说。」伯爵道:「温老先儿他斯文人,不管这闲事。」温秀才道:「二公与我这东君老先生,原来这等厚。酒席中间,诚然不如此,也不乐。悦在心,乐主发散在外。自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门庆说:「姨夫,不是这等。请大舅上席还行个令儿,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诗词歌赋,顶真续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这个庶几均匀,彼此不乱。」西门庆道:「姨夫说的是。」先斟了一杯,与吴大舅起令。吴大舅拏起骰盆儿来,说道:「列位,我行一令,说差了,罚酒一杯。先用一骰,后用两骰,遇点饮酒。」
「一百万军中卷白旗,二天下豪杰少人知,
三秦王斩了余元帅,四骂得将军无马骑,
五諕得吾今无口应,六衮衮街头脱去衣,
七皂人头上无白发,八分尸不得带刀归,
九一丸好药无人点,十千载终须一撇离。」
吴大舅掷毕,遇有两点,饮过酒。该沈姨夫起令,说道:「用一骰六掷,遇点饮酒。」说道:
「天象六色地象双,人数推来中二红,
三见巫山梅五出,算来花有几人通?」
当下只遇了个四红,饮过一杯,过盆与温秀才。秀才道:「我学生奉令了。遇点要一花名,名下接四书一句顶。」
「一掷一点红,红梅花对白梅花。二掷并头莲,莲漪戏彩鸳。三掷三春柳,柳下不整冠。四掷状元红,红紫不以为亵服。五掷腊梅花,花迎剑佩星初落。六掷满天星,星辰之远也。」
温秀才只遇了一锺酒,该应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识,行个急口令儿罢!」
「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拏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拏着一条绵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个黄白花狗,咬着那绵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黄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黄白花狗。不知手鬬过那狗,狗鬬过那手?」
西门庆笑骂道:「你这贼诌断了肠子的天杀的,谁家一个手去鬬狗来!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谁教他不拏个棍儿来?我如今抄化子不见了拐棒儿,受狗的气了!」谢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柴,说他是花子。」西门庆道:「该罚他一锺,不成个令。谢子纯,你行罢。」谢希大道:「我这令儿比他更妙。说不过来,罚一锺。」
「墙上一片破瓦,墙上一疋骡马。落下破瓦,打着骡马。不知是那破瓦打伤骡马,不知是那骡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话我的令不好,你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儿刘大姐就是个骡马,我就是个破瓦。俺两个破磨对腐骡。」谢希大道:「你家那杜蛮婆老淫妇,撒把黑豆,只好喂猪拱狗,也不要他!」两个人鬬了回嘴,每人罚了一锺。该傅自新行令。傅自新道:「小人行个江湖令,遇点饮酒,先一后二。」
「一舟二橹,三人摇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齐唱八仙歌。九十春光齐赏翫,十一十二庆元和。」
掷毕,皆不遇。吴大舅道:「总不如傅黟计这个令儿行得切实些。」伯爵道:「太平锺,也该他吃一杯儿。」于是亲下席来,斟了一杯与傅自新吃。如今该韩伙计。韩道国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门庆道:「你每行过,等我行罢。」于是韩道国道:「头一句要天上飞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贯串,遇点照席饮酒。」说:
「天上飞来一仙鹤,落在园中吃鲜桃,
却被孤红拏住了,将去献与一提学。
天上飞来一鹞莺,落在园中吃朱樱,
却被二姑拏住了,将去献与一公卿。
天上飞来一老鹳,落在园中吃菱芡。
却被三纲拏住了,将去献与一通判。
天上飞来一班鸠,落在园中吃石榴,
却被四红拏住了,将来献与一户侯。
天上飞来一锦鸡,落在园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将来献与一尚书。
天上飞来一淘鹅,落在园中吃苹波,
却被绿暗拏住了,将来献与一照磨。」
掷毕,该西门庆掷。西门庆道:「我只掷四掷,遇点饮酒。」
「六口载成一点霞,不论春色见梅花,
搂抱红娘亲个嘴,抛闪莺莺独自嗟。」
掷到遇红一包,果然掷出个四来。应伯爵看见,说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转加官,主有庆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与西门庆。一面唤李铭等三个,上来弹唱顽耍,至更阑方散。西门庆打发小优儿出门,看着收了家火。派定韩道国、甘伙计、崔本、来保四人轮流上宿。分付仔细门户,就过那边去了。一宿晚景不题。都说次日,应伯爵领了李智、黄四来交银子,说:「此遭只关了一千四百五六十两银子,不勾还人。只挪了这三百五十两银子与老爹。等下遭银子关出来,再找完,不敢迟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说了两句美言。西门庆把银子教陈经济来拏天平兑收明白,打发去了。银子还摆在卓上。西门庆因问伯爵道:「常二哥说,他房子寻下了,前后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就卖了。他来对我说。正值小儿病重了,我心里正乱着哩,打发他去了。不知他对你说来不曾?」伯爵道:「他对我说来。我说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乱乱的,有甚么心绪和你说话?你且休回那房主儿,等我来见哥替你题就是了。」西门庆听了便道:「也罢,你吃了饭,拏一封五十两银子,今日是个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来罢。剩下的教常二哥门面开个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勾他两口儿盘搅过来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顾他了。」不一时,放卓儿,摆上饭来。西门庆陪他吃了饭道:「我不留你。你拏了这银子去,替他干干这勾当去罢。」伯爵道:「你这里还教个大官,和我两个拏这银子去。」西门庆道:「没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这等说。今日我还有小事去。实和哥说,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礼儿去。他使小厮来请我后晌坐坐,我不得来回你。教个大官儿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儿好来回你。」说罢,西门庆道:「若是恁说,教王经跟了你去罢。」一面叫了王经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时节家,常时节正在家。见伯爵至,让进里面坐。伯爵拏出银子来与常时节看,说:「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闲,杜三哥请我吃酒。我如今了毕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儿跟了我来。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话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时节连忙叫浑家快看茶来,说道:「哥的盛情!谁肯?」一面吃毕茶,叫了房中人来,同到新市街兑与卖主银子,写立房契。伯爵分付与王经,归家回西门庆话。剩的银,教与常时节收了。他便与常时节作别,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门庆看了文契,还使王经:「送与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话下。正是:
「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一切万般皆下品,谁知阴德是良图。」
正是:
「玉光有影遗谁系?万事无根只自生。」
毕竟未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