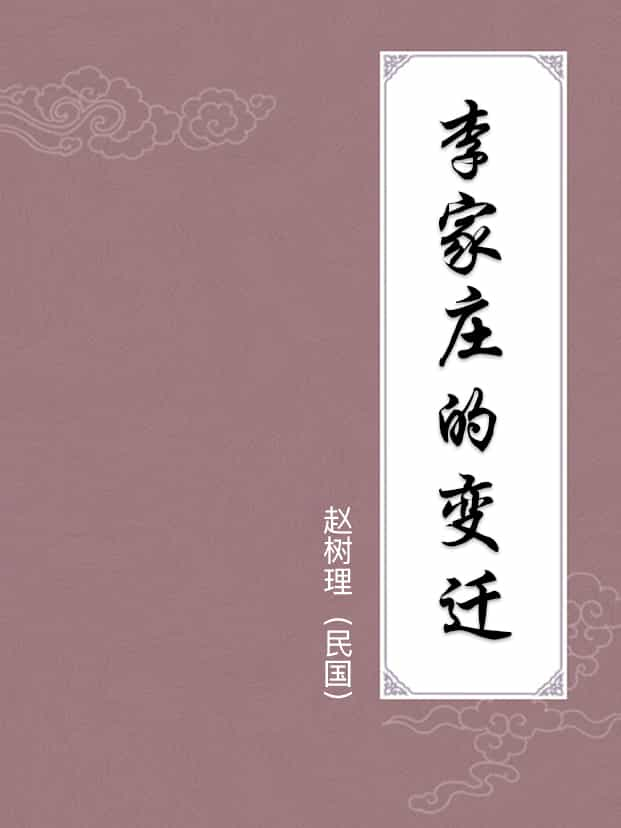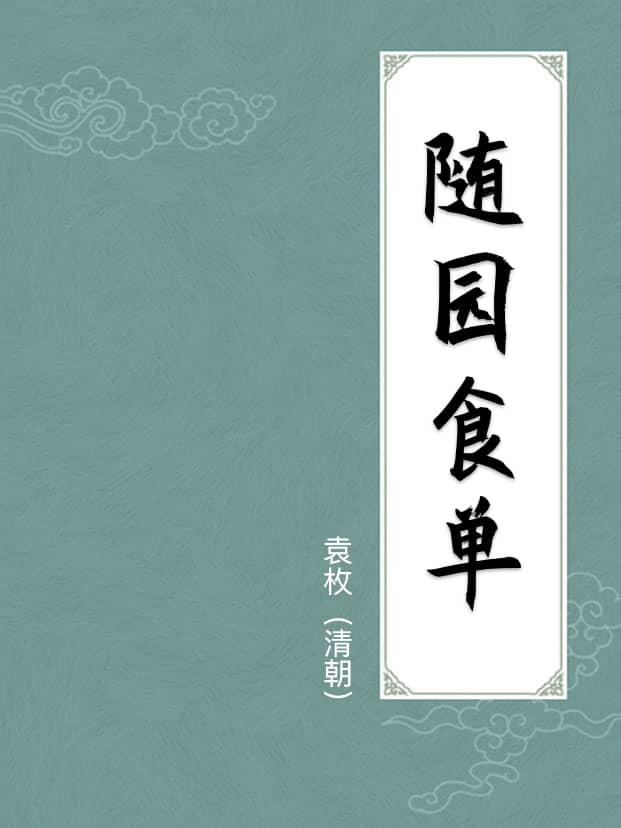是一个密阴的午后,催雪的北风吹着奇仙山半坡上的松树争吼出令人惊恐的声音。山下的沙河虽未结冰,却是冷度日增,流水已凝结了,不似秋日的一泓清鉴可以照人毛发。山野中被风吹散了的各种树叶也不多了,只有些断根枯蓬随风团转,向无垠的冬原中投散开它们各人的生命。河上的渡口中若在夏日入山游玩以及避暑的人多的时候,十几只小划子来回不歇还忙不了。现在却只有一只缺了尾巴的划子横搁在冷黄的水上,独自无力地摇摆着,与沙岸相摩荡发出轧轧的叹息。奇仙山是这地方的一个名胜,到这时水落木脱全像个秃了头发的老人坐对夕阳,自伤它那近黄昏的命运了。
行路的客人似乎都很聪明,他们都似不愿看这冬来又瘦又皱的面目,轻易不从这里经过,只那噪晚的乌鸦一队队的飞来飞去哑哑哀啼。
沿着弯曲的河岸向东北走,转过这山坡上的密松林,在许多沿山搭盖的村舍南端,有一带积棘编成的篱墙。正中是用山中的栝木做成的圆门,门上横挂着一个落了粉的木牌,用郑文公碑体端端正正地写着奇仙第二公立小学校几个字,正在上课的时候,并没见个儿童在门外游玩。
栝木门内对正西的山麓上有七八间茅檐的低矮屋子,窗子上也没有玻璃,只是用油纸糊在方形的木槅上。这自然是乡间的建筑,也是因为天气过冷,教室内没有炉火,故用纸糊窗以求御冷。室内有五十几个学生正在仰着头,骨突着小嘴,听他们的教师讲书;教给他们精神上的食粮。
三十岁左右的教师,自前两天受了过度的风寒,正在鼻塞声重地为他们讲一课国语。这课国语正是讲的英国讷尔逊风雪中读书的故事。有风也有雪,这时期中恰好顺序讲到这一课应景的玩意,不能不令人佩服编辑教科书先生们的聪明。不过在这感想冲撞的教课时间中,却使为生活所压迫的教师添了好多困难。他按着教授法用“提示”的工夫向儿童们问答着。五十几个山村装束的小孩子,红红的脸儿方在忽仰忽俯地看书上画图的风雪中的小英雄,又凝望着他们那位皱了眉头穿着破袖子冻红了手的先生。这正是一幅神圣的画图。他们全部的心意似是全为书上的英雄故事摄收了去。他们的发现性,好奇性,冒险性,以及天生成的与大自然的争斗性,全在这一小时内动荡出来。他们小小的心中忘却了教室内的冰冷,忘却了教课的束缚,并且忘了去听山上的风声,草场中的各种游戏。他们天真的表情,他们赤裸的心,全为过去的人物所夺取了。全室中充满了静谧的空气,只听见教师与儿童们清晰,明简的问答。教师在小学教育上的确有了多年的经验,他自从二十二岁在初级师范毕业以来,十年的光阴全在与儿童为伍中度过。他认识儿童的心意比每个儿童的母亲还要清白,还要明了,所以他这时儿由这一课书中,也可以说由他的讲解中,引起儿童们全部的注意力。他也似乎因此忘却一切,——忘却他终日的烦愁,而尽力在这样的启发中了。
“谁怕风怕雪?”他指着一个年纪最小还不过九岁左右的孩子问。
“讷……讷尔逊不怕,……我也不——怕!”这个大眼睛的孩子便立刻答出。
“讷尔逊为什么不怕……风与雪?……”他音调迟缓而清晰,向一个剪了发的女孩子说。
女孩子在这四年级中算是成绩很好的一个。她穿了深蓝本地布的套褂,项上还斜披着一条灰色粗绒绳织成的毛巾。她立起来,不即时解答,却向书上看了一看,慢慢地道:“因为风雪是冷的,……他不怕……他怕被人家笑话……他不勇敢!——不热心!所以不怕风雪,怕……”究竟怕什么?她没再说出便坐下了。
教师因为深深了解儿童的言语,尤其知道两性中言语表现根本上不同,所以他并不以这伶俐的女生所答的话为难懂。他很赞成她会说话,会有曲折的表现。他并不再追问,便点点头任凭她坐下。
于是他开始讲本文,示生字,告诉读法。他今天特别欢喜,特别愿意与这些天真未凿的孩子们来谈谈这段有趣而英伟的故事。在种种的讲解之中,不但儿童们是全部心意表现出来,就是这久经生活困苦的教师也从潜意识中钦佩着这战胜困难达到成功的英雄。从他的口语中可以听出他的兴奋与感动的心声。他一边讲着,一边若断若续地联想起他幼时在村塾中从师走读的景况,以及在师范学校时所读的《送东阳马生序》里面那几句形容苦学生的话,因此他反复的讲说便分外有力,分外生动。
这样过去了几十分钟,铃声响了。在这个教室对面的东房中的两班学生都下了班,于是他快快地说完了这一课最后的一句话:
“讷尔逊的精神就在不怕风雪!——这是什么意思?下一回你们回答我,——想想看!”
粉笔上的碎末从他的破袖口的乱絮中飞扬着,扑落下来。他昂昂地走出教室。即时一群“英雄式”的儿童们跳跃着出了这窄长而光线幽暗的屋子。有几个勇壮地高呼着:“不怕风雪是英雄!”的重复句子,或者有几个笑着道,“打倒风雪!打倒风雪!”表示出他们摹仿的本能。
不过两刻钟的工夫,儿童们在校内闲场上乱玩了一阵,便各各由松林中回到他们的穷苦家庭中去了。
“今天真冷!好不好?我要特别破钞了!我方才从王家店打来了两角钱方出锅的‘锅头’,还有一包花生,咱也乐一乐。这样天,不喝点酒,不要说咱们,——就是泥瓦匠,上码头的工人还要到小店里喝一两壶呢!”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一嘴鬈腮胡的先生,他是教五六年级的主任教师,是奇仙小学里有名的魏胡子。
二十多岁初出学校的青年,——他是最低年级的教师,本来是极反对喝酒,而曾经与他的同学们组织过进德会的主要分子,但是自到这学校当教师以来也早被魏胡子所感化了。他不但不反对喝酒,并且时常在课余之后好做新诗,更觉得酒味醇醇了。这时听了魏胡子这样说,便慨然道:
“‘今我不乐!’……这样生活真干而苦。不喝酒,干吗?早知道当小学教员是这么样,……哼!不是家里教我来,死也不干!”
“死也不干?……然则么,干什么?”魏胡子的态度常是保持着悠悠的神味。
这么有经验的问题,确有些难于回答,所以青年的教师暂时默然了。
魏胡子表示着经验战胜幻想的快乐态度,将粗硬的手指执着砂质的酒壶,倒满了三只空杯子,却从容地道:“小王你且不慌,问题是问题,喝酒还是喝酒。你先去将颖甫招呼过来,咱们就以这问题做下酒物。我说,就是咱们共同讨论。本来什么问题只可做下酒物!”他没等说完了先喝了一杯。
小王苦丧着脸子道:“颖甫这个人奇怪,我说他是一个文学上的颓废派,你懂吗?他忧郁而且神秘,……”
“什么?你再说这些话,我的酒可没有你的分儿!我愿意同种田的老人同喝,却最不高兴同你这班‘酸文假醋’的新名士在一块!”
这可算是魏胡子的大政方针了,他说时,不知为了什么真像义气填胸似的。小王瞪了他一眼,便怯怯地走出。
直待小王将颖甫——就是教讷尔逊一课的教师——拉了来,都在魏胡子那间比较暖和的屋子中坐下,魏胡子一边给他们倒上这满壶的浊酒,他自己却剥着花生皮很痛快的发表主席的言论。
“我说,你不必妄想,——你也不必回想,天生成我们的穷命,你便得对付它!你不对付它,你就丢掉它。干什么?值得唉声叹气。我终是说你们不知足。哈哈!中国惟一的好主义——别笑我够不上谈主义,就是知足!‘知足不辱’,真是不可磨灭的名言。反过来一句话,不知足就得解决。——解决啊,你们可又不干。干也是白干……‘理无二致’,还是喝酒好。哈哈!”
他说这几句话,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他是充分的佯充滑稽,是苦痛深沉后的享乐的解脱。
小王将破尖的皮鞋顿了一顿,“说是说,行是行。你老人家鬼混得来,像我几乎还是小孩子,就关在这牢狱里做囚徒,值得不值得?不要说一个月二十二元的薪水七折八扣,还有三个月的拖欠,就是按月整发,除掉吃白菜汤以外还够不上买一两部书看的。况且出去向人家说,不过是个‘小学教员’,什么教员?‘教书匠!’‘看小孩子的工人!’”他说着,少年兴奋的热血便涌上双颊,同时他用左手摩抚着他头上中分的黑发。
颖甫原来沉默,这时只有一口一口地喝酒,眼望着屋子里贴的一张教育画出神。那是张《祖逖渡江》的石印粗糙彩色画。他看见英气勃勃的祖逖正在抚着船舷,眼望着滔滔滚滚的长江,表示出他那种一往无前,为了祖国戮力同心的精神。这时魏胡子听了小王的一段话后,将他的鬈曲的下胡撂了几撂道:“好小子!你真明白,是一月的薪水岂但不够你买书,还不够我喝酒呢!你不要看轻白菜汤,这还是‘教书匠’才够上吃的口味儿;也是读书人的本色。等我想想,‘咬得菜根’便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你不知道那些码头上抬货,马路旁边拉车的兄弟们,不见得吃到!这不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占的便宜吗?”
“可是,老头子你贪说忘了计算,你知道他们劳工是天天给现呢。”
小王这句话反驳得颇有力量,能强辩的魏胡子几乎要在青年的人的话下停止了他的机锋,可是他少停了一会便道:
“得啦!你不知道吗?他们是劳工,——是劳力的工;咱们也是劳工吧,却是劳心的。‘劳工便是神圣’这话但是说劳筋动骨的生活的,那末,他们给现一定是这个原因。我们呢,‘劳心者治人’,且是‘君子谋义不谋利,’好啊,这是个再确当没有的论断。”
小王不与这好强辩的同事再说话了,为了要喝酒吃花生的要求上,他只好暂且放弃了一切幽幻的理想,饮着白干听那山涧中的松啸声。
即时一个六十多岁,反披了粗黑羊皮袄的老年校役端过一盏光明的矮磁座的油灯进来,放在白木案上,又将全校惟有的一个煤球炉子搬到房里来,于是他们骤觉得来了光明与温暖了。
魏胡子将一本旧教科书的封面撕了下来,就案上摺卷起来,即时成了一根纸火筒。他便将窗台上几乎是生了绿锈的旧铜水烟袋取来,呼噜呼噜的吸起水烟。通红的炉火,一口口的青烟,一杯杯强烈的酒气,充满了这万山重叠中的一间茅舍。
小王的酒量原不很好,这时已经有点醺然了。他见魏胡子撕了教科书做纸火筒便得了机会报复了。“你真太随便了!校长来了,如果看见书被你撕去吸了水烟,看你怎么回答?”
“我说你是小孩子,初出学校门的学生!颖甫你说对不对?告诉你,不但是撕个把本教科书算不了一回事,就是劈了破木凳做柴火,校长他再不能责备你。什么事都是个招牌。他不是为了这个官衔肯到这里来?他是终天终日到市董局,到统捐处,到县长公署。他顾得了这些?好,不高兴,咱给他一齐走,一齐‘罢教’,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话又说回来,他算不容易找到咱这几个‘劳工’。小王你不知道,颖甫你还不明白?就是这样苦生活谁干?况且县上的扣压,教育局里迟发,结果还得向校长,——那秃头的东西的利钱包中走一趟,三回九转才到咱这应得的手里。谁还不知道?他还敢来管咱们!好不好,咱给他都告发出来,拚一个‘鱼死网破’!……”魏胡子的酒力在他的四肢百体中发作开了,这时他也保持不了他那滑稽的尊严,而几乎是在谩骂。
小王这才恍然了,不觉激动了他的义愤,“你真教人不明白!……那末为什么平日不到局里告发他?”
“这叫做‘手法’。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告发,还不是他们这几个人,‘以暴易暴’倒还是小事,就是这个位置也一定保不住。像你又懂这个,那个,志高气傲可以不在乎,我们呢?家里几亩田地,不够捐税的,孩子,妻连吃的没有,……颖甫呢,更困难,你问问他!……”
小王的青年的生活理想,被魏胡子酒后的几句话全打碎了。于是他交互着握着手对了火炉,默然无语。
颖甫始终没多说话,静听着这经验与理想的争论;深深地怅望着这生活的空虚。在他看来,这纵酒的魏胡子与朝气勃勃的小王同事,在生活方面都比自己安定,比自己有希望,而且沉着。自然不论是玩世,或是愤世,更不论是为了经验,而图生存,或者企求理想而鄙视现在,无论如何说,总之都还有他们得已的勇气与态度。至于自己呢?真是十足的灰色,而且纯净得搀杂不上一点点别的色彩。就是既然不能如阅世已久的胡子先生的无可无不可,尤其不能对一切事实耳无闻目无见任凭著“人造的自然力”播荡。然而自己是吃过生活苦痛的人,又有环境的挂碍,想如小王的放言一切,鄙视一切,振发出青年的精神来,不但不能,而且觉得什么事没个究竟,还不是白白的“白热”。本来颖甫自从二十岁由旧制中等学校卒业之后,当时迷于教育救国,与小学教师之高尚等等的理想,又加上他自己的生性恬静,不惯与人到纷乱的社会里去斗争,所以就投身到这最清苦的教师生活的深渊中来。自然,他得了不少的良好经验,也尝惯了这种生活的味道,十年的光阴真是如同飘风似的过去了。人事的变迁,和家庭的衰落,只余下了他的妻同四个小孩子,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只是付予儿童们的“良心”了!他的妻子,永远随着他移来徙去消度这悠悠苦辛的岁月。他不能有存蓄,而生活费却一天天高涨起来。头两年在省城里当过一年多模范小学校的教员,可是那里只有日向虚伪奢靡方向走去。同事们是洋装,缎领带,衔了香烟上课堂,校长又是拿人当礼物的酬赠,所以终日是向“老爷”之类的家里去打牌,去当零差,虽则每逢开什么教育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登台说几句“义务”“天职”的话。至于薪金,所发的全是打五折的不兑换纸币,因此他不能再羁留在那里,又费了若干情面才从都市跑到这幽僻的山村中来,却想不到也只不过如此!
幸而还有谨朴的儿童们的心还可以使他留恋,使他慰安。他将妻子寄寓在邻村的同乡人家里,便与魏胡子,小王作了亲密的伴侣。
因此在学校内除去与儿童们谈话游玩之外,他似乎是隐士一般。而且为了月薪的困难,他每顿饭连两样以上的菜蔬不敢吃,而所俭省出来的还不够家中孩子们的用度。然而他对这样的情形,却与他那一老一青年的同事们如何表示同情?他处在这样生活之中不能低头,又不能反抗。所以这完全灰色的态度,虽是自己也憎厌,却只是变不了。
北风劲吹的黄昏中,这三个心意不同而受同等苦闷的先生,在纷呶与叹息中吃过粗糙的小米饭,暂时的饥肠中有了容纳,便也暂时止住了他们的谈锋。
纸窗上的油纸被风吹打得声响很大,不知是落雪了没有?而静夜的寒度却越重了。颖甫睡在木板的床上,起初借了酒力颇觉温暖,但是酒力消了,血液不能很旺盛地流动,于是他便觉出十分严冷了。过度的寻思,使他不能入梦,况且扰人的山中松声,这时听来如有好多兵马在咆哮着惊人的沉迷。他反复想起着晚上谈论的问题,又想到自己生活的前途与希望。冬夜是用思的时候,他受了生活的压迫,因而激起的感想,更使他不能安眠。
“生活不讲意义”,他想:“还要相当,像现在维持下去,自己虽是可以不至饿死,然而妻与子的衣食呢?况且到处是一个样的寂寞与黑暗,又怎么办法?”他想来想去,越没有解答,却越觉得薄薄的两层布衾如堆了冰雪在上面的酷冷。他再不能睡了,咬咬牙根,披衣起来摸了火柴,将床头的木桌上的油灯点着,将大衣半掩着,取了一枝钢笔便想写一封决绝的辞职书,表明他再不作这样生活的奴隶了。他这时从种种的思考中得到了一时的解决方法,便是为了人格起见,不再在这样的教育界中鬼混,他以为这么维持下去是耻辱,是勉强,是媚人而苟安,是给这万恶的社会中制造罪恶。总言之:是自己蔑视自己的人格,而不知解脱。他又想:一切的迟疑是事业的阻碍力,十年以来自己全在敷衍中度日子,便葬送了自己的华年。他执着破尖的笔,兴奋地毫不迟疑,即是便在坚硬的白纸上面写下来。
他写的完全而有力,首先叙明教育事业的重要,与近年以来小学教育的堕落与种种弊端,其原因全在一般人的玩视教育,以及教育界人士自己丧失了他们的人格。笔锋推扬开去,更说到社会的不安,与为了许多外因,教育遂至破产。中间表明他自己的人生观,是“不完全则宁无”;是想献终身于教育而不得,为了生活与人格的维持,所以情愿抛弃了十年的粉笔生活,跑向十字街头去。他写得很快,很畅达,明白而活泼。无论谁看了都得赞赏,感动,并且一定给予他充分的同情。他一气写完之后,顾不得手指僵冷,又重看了一遍,像久经伏卧于恶劣空气之中,初走到无边的郊野似的。他想这决定很有价值,可以为他一生的大纪念。此后冻死,饿死,都顾不得。但这可是为人格而战胜一切的重要关头。他又想:勇敢的小王,是志有余而气太弱,明知其不可,而必为,还不“回头是岸”吗?
写完后又看了看土墙上贴的日历,他以为这一夜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便在纸尾上添上一行小字:“颖甫书于奇仙山中之小学校。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深夜。”
他看看再没有更改的地方,便将书信折叠好放在外衣袋内,预备明天下午好往校长家去交代。同时想,或者明日晚上,他就可以一肩行李走回家去,这么光明奇异的行动,魏胡子与小王定必一齐瞪着眼不了解,也想不到。
他重复躺下之后,朦胧中听见远处的鸡啼,然而在过度的兴奋与疲劳之中,竟然沉酣地入了他的生活与人格斗争的梦境。
当颖甫第二日早上起床时,大小的儿童们已经满了院子。第一班铃打过了,颖甫忽而想到这是他教师生活最后的一天了,无论如何,为责任起见,也应须分外尽心,方不负他这十年不断的努力。
他带着十二分庄重的神情,毅然拿了粉笔匣与教科书入了教室。可巧这天早上又是国语的功课,当他走上讲台时,不知怎地许多小人们低声地说着“讲故事,讲故事”,“还是温习第三十五课”,“你听听这位老师才会讲不怕风雪的故事呢”!在嘁喳的儿语声中,含着深深的快乐与天真的希望。颖甫呢,正自盘算着夜里的计划,但是在冷风横吹的夜中勇敢的计划,到了白天现实的景象之下,他不觉有些怯怯地了。这样心理的变动,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只觉得这事还可“从容打算”呢。况且失眠与酒力的过分疲劳,使他在台上看见这几十个红颊的儿童,不免有点自觉惭愧。他方打开书本,踌躇着要先尽这半点钟复习昨课,然后再与他们说明他要离开他们的意思,忽然昨天与他问答的那个女生,首先立起道:
“我问问,……讷尔逊……是个什么人?”
颖甫没即时回答她,便用了他惯用的启示方法向全班中复问这一句。
“讷尔逊是什么人?是哪类的人物?你们,谁说?”
于是好说话的儿童,便争着说:什么他是英国人,海军大将;或者说他是能打仗的;是有大胆的;是个小孩子?又有低能一点的孩子立起来,却不知要说什么好。颖甫都听着,不加可否。末后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农家孩子,大的眼睛,圆的下颏,一脸活泼的表现,他等得许多人发表了对于讷尔逊的批评之后,他便道:
“我知道:讷尔逊是个不怕风雪的人!——是个不怕难的人!……”他还没有说完,那个首先启问的女生若有提示似的道:
“哎!我也知道了,我说他是个勇敢又负责任的人……的人物!是吧?老师!……”
这两个学生的肯定话,不但使全班的人都惊奇,就连在怅惘中的教师也如从脊柱骨上浇下一桶冰水,几乎全身的血液都在惊颤!他半晌没得话说。两个学生还立在那里听他的批评。他从“良心”上发出利益与希望的拚争,并且心中十年的辛酸泪几乎被这两个孩子的话激引着要掉下来!这即时心理上的复杂,交互,说不清晰,他呆立着没得话说。全教室里的儿童们都奇异的了不得,竟不知他们的先生是什么意思。这样过了有五六分钟。
末后,他才着实称赞了这两个学生几句,定一定神便重行将这课的重要意义与句子,尽力地讲得淋漓尽致。好奇的儿童们,都仰着头,听得入神。
及至一班下后,他终于没有将昨夜的计划勇敢地讲出,并且他下课之后,回到自己的屋里,将袋内那封情理兼至的信,撕成碎片,丢在字篓里去。
在窗前仰望着还是欲雪不雪灰色的天空,他同时回念着多年来同等生活的经过,与人生的苦况,他止不住一颗颗的热情的泪珠,从眼角上流下来,湿透了破絮的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