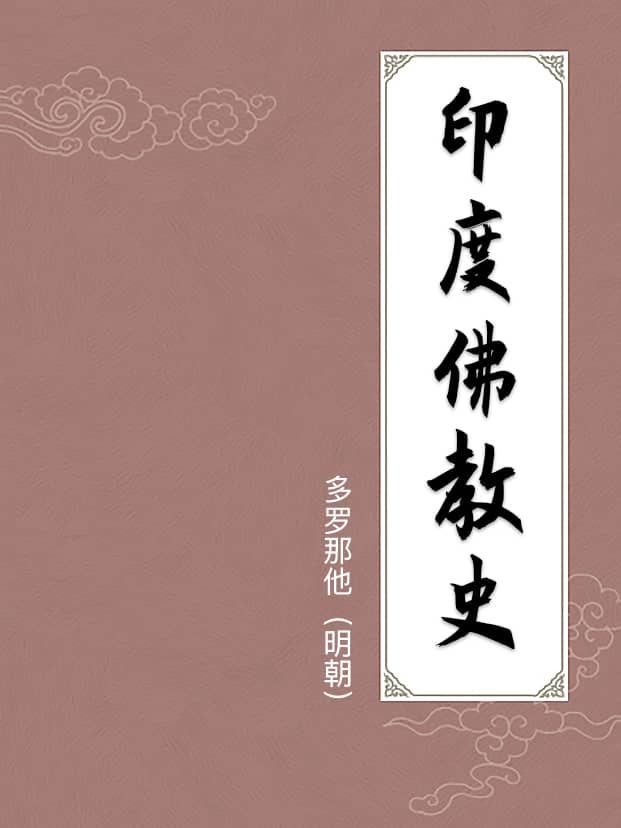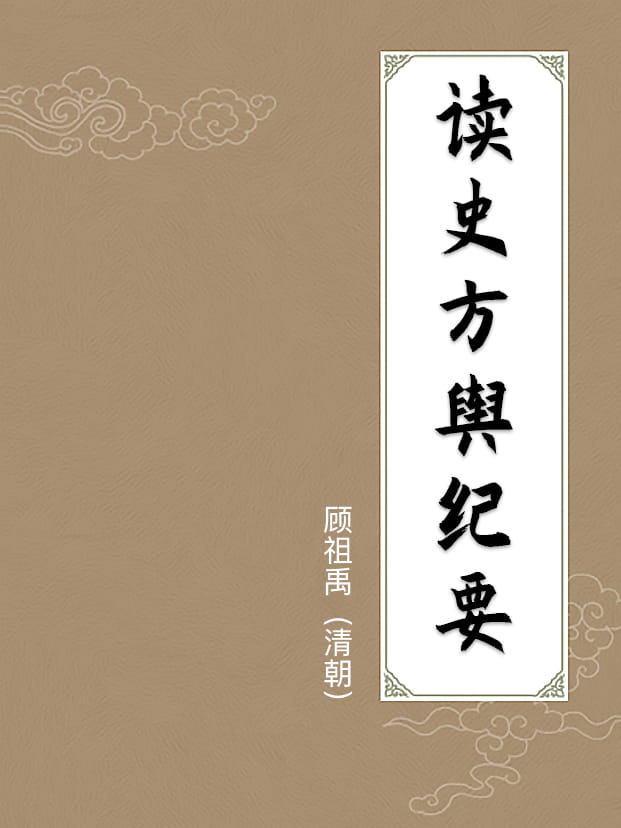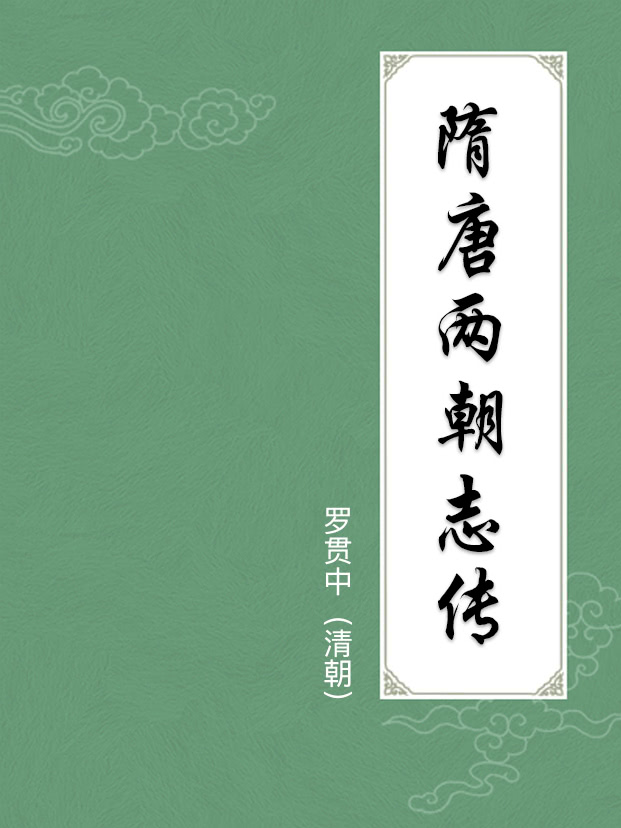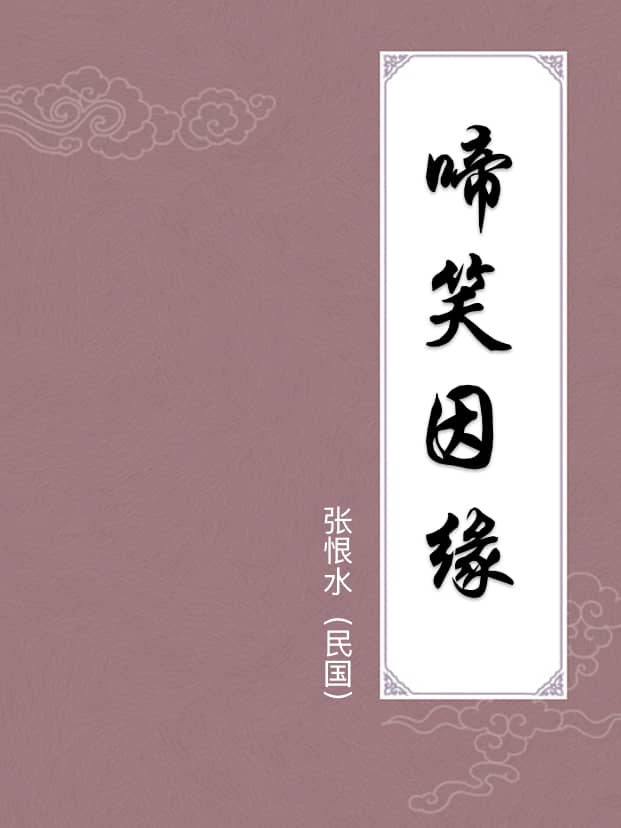诗曰:
世情反复欲如何?闲是闲非日日多。
架上有书慷展卷,樽中无酒莫高歌。
漫搜往事消愁况,偶述新闻慰病魔。
岂学荒唐恣胸臆,奸淫种种易生波。
话分两头,且说证空所见的妇人,娘家姓陆,丈夫就是赵诚甫。做亲六载,只生一个女儿,年方周岁。那赵诚甫只有二三十两本钱,亏他勤谨,出外贩线为生,一年倒有六个月不在家里。陆氏年才二十八岁,虽则小户人家儿女,倒有五六分姿色。
只是生性轻浮,多言多笑。
隔着十余家西首邻居,有一丘大,年将四十,未曾娶妻。因窥见陆氏美貌,又探知赵诚甫时常出外,心下怀着不良之意,往往借件没要紧的事头,闯进陆氏家里,坐着闲谈。及语到热闹之处,每带谐谑,陆氏笑谈自如,并不嗔怪。因此丘大认着陆氏有心。
一日黄昏时候,丘大悄悄地潜立在门外,将门轻轻一推,犹未拴上。不敢骤然推进,只得伏在门边。里面陆氏,吃完了夜饭,收拾碗盏,方欲烧汤洗脚,忽记起前门未关,慌忙将着灯草,点火出来照着。
丘大听见脚步走响,板缝里露出亮光,只得大着胆,推门进去。陆氏惊问道:
“夜深了,丘家伯伯你来做甚么?”丘大推说道:“讨火吃烟。”陆氏道:“要点火,外面没有灯草?伯伯可立在街上,等我就把手内的火与你。”丘大等得陆氏递火过来,便趁势伸手过去,将那奶边一摸。陆氏用力推开,急急的关门进去,并不做声。
丘大又认着陆氏十分有意。到了次日傍晚,捉空挨身进内,一堆儿蹲伏在柜台里面。候至夜静,陆氏出来关门,便走到背后,拦腰一把抱住。陆氏惊喊道:“你是哪一个?”丘大低低应道:“是我。”陆氏听得是丘大的声音,便乱声叫喊,早惊动了两边邻舍,都起身开门出来。丘大知事不谐,急欲走脱,反被陆氏扭住不放。
当下众人看见,俱愤愤不平道:“人家一个内眷,好端端坐在家里,你怎么起那不良之意,就要把他强奸。真正投有地方,没有皇法的了。”
内中有一张老亲娘,再三苦劝道:“赵家娘娘,我便与你贴壁邻居,哪一个不晓得,你是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放得马过的。想是丘大官吃酒醉了,所以冒犯了你,你只索息怒,饶恕了他。万一声张起来,必要到官审问。一则娘娘也要出头露脸,二则外人不知,认道奸情勾当,带累赵官人面上不好意思。老身只要没事,所以苦口相劝。娘娘若肯依允,我叫丘大磕头赔礼。”众人齐声说道:“张老亲娘劝得极是,丘大虽则不通,念他平日做人也是好的。赵家娘娘把一个天大的人情,卖在我众邻舍面上,待他赔个礼,饶放了他罢。”
陆氏也便将机就机,放松了丘大。丘大满面羞惭,只得向着陆氏,磕了两个头,又向众人逐一拜谢,抱头鼠窜而去。
隔得半月,赵诚甫自外县回来。陆氏依着众邻相劝,搁起不提。赵诚甫置完了货,又欲出门。只见邻舍内几个老辈过来,商议证空化斋一事。
赵诚甫平索最敬神佛,最肯布施,随即满口依允道:“若要小侄做个领袖,其实没有工夫。若每月要小侄斋供一日,有何难事。设或小侄不在家里,自当叮嘱寒剂,照众轮供便了。”众老者看见赵诚甫允诺,无不欢喜。当即合齐了三十家,把证空轮流供养。
证空每到一家吃饭,低头闭目,口中只念着阿弥陀佛。就有内眷将他张视,他便掇转头,并不偷眼一看。所以众人愈加敬重道:“他是个有来历的真僧。”
话休繁絮,只说证空。每夜打坐在赵家门首,到了五更时分,敲着木鱼高声念佛。及在日间,捉空就溜到陆氏家内,讨茶吃饭。陆氏因道:“他是有德行的长老,亲手递送,并不闪避。”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陆氏独居在家,容一游僧出进,岂无地邻看见,没有说话的么?原来那一街,是个僻静去处。四边邻居,不在衙门,就是肩挑生理,各自门各自户,谁肯管这闲事。所以丘大敢于黑夜用强过奸。自丘大闹了一番之后,就值证空打坐化斋。那证空又是朝暮念佛,假做老实,自然没有人疑心他的了。
闲话休提,且说证空,暗暗察探陆氏,日逐动用,十分淡泊。遂将银买下花纱一匹,趁着左右无人,推门进去,见了陆氏,台掌施礼,嘻嘻地笑道:“小僧有缘云游至此,幸遇娘娘及各位檀越,施斋救度。又日逐在此打搅,无可报答。适有王居士将着花纱一匹,施与小僧。念小僧是个出家的人,惟穿戒衲,要此花纱何用,特敢奉与娘娘,少答茶汤之费。”言讫,即向袖内取出花纱,双手递奉。
那陆氏若是一个有见识的,严声厉色,将那花纱掷还,便可以绝了证空的邪念。
谁想陆氏没有主意,竞把那纱儿接了。证空心下暗暗欢喜,想来已有三分光景。过了两日,又去买些茶枣,送与陆氏。陆氏殷殷谢道:“只因拙夫出外,没有什么好素菜供养师父,反要你出家人坏钞,教奴家怎好受得。”再四推辞了一会,便伸那嫩尖尖的玉指,接了进去。证空心下愈加欢喜,想来觉有七分光景。
又过两日,只见街上卖布的,背着布包走过。证空叫进到陆氏家里,买取白布二匹。陆氏看见,要赊青布二丈,那卖布的不肯道:“倒是现买,情愿让些。”证空便又将银买了二丈青布,送与陆氏。
陆氏笑嘻嘻地接道:“待拙夫回来,即讨银子送还师父。但不知师父买这白布何用?”证空道:“要做一件衬里衣杉。”陆氏道:“若不嫌奴家的手段不好,就替师父做了罢。”证空道:“娘娘若肯剪裁,定当以工金奉谢。”陆氏道:“只是日间没有工夫,且待夜来,与师父做罢。”证空道:“娘娘临做之时,小僧须要当面看裁,方不长短。”陆氏微笑道:“只怕夜间不便。”证空慌忙合掌道:“阿弥陀佛,小僧极是一个志诚的,娘娘何须疑忌。既如此,且到晚间裁剪,快些出去,省得外人看见不雅。”
证空暗想,事已挨到十分光景,心下大喜。看看黄昏时候,各家俱已闭户,便即踅进里边,等候陆氏点出灯火,将那布来量了长短。
那陆氏若是一个正气的,就该把证空打发了出来,关上了门,也就没事的了。
谁想陆氏看见证空,半纪后生,人物秀丽,又且有些油水,所以心上早已着邪。那证空又单为着陆氏,费尽心机。当夜剪裁完时,已是更深人静,禁不住欲火如焚,向着陆氏,双膝跪下道:“娘娘若肯见怜,万死无憾。”陆氏掇转头,掩口而笑。
证空即便胆大,急忙向前搂抱。陆氏用力推开道:“我好意替你裁衣,怎生反来缠我。可见那出家的,不是好人。”证空又再四哀求,紧紧地搂住不放。陆氏假意将手放松,凭着证空抱到榻上,霎时间云雨起来。
但见:
金莲高耸,玉腕斜勾。闭星眸而杨柳轻摇,翻红浪而桃花无主。一个是恋色淫僧,惯会怜香惜玉;一个是空闺少妇,何妨骤雨浓云。光头与缘鬓,偷谐并蒂之莲;施斋兼台体,总发慈悲之念。正所谓:和尚常闻三件妙,佳人愿费一条心。
有顷事毕,证空踅出门外,依旧敲着木鱼,高声念佛。自此更静而人,五更而出。往往来来,将及月余。那赵诚甫,已经回来两次,只因做得稳当,并无一人知觉。
单有丘大,一心思要勾搭那陆氏到手,谁想好事不成,反受了一场没趣,心下十分怀恨,无由发泄。忽一日傍晚,偶在陆氏门首经过,只见证空坐在檐下,陆氏掩立门内,露出半个身体,笑嘻嘻地与证空讲话。丘大闪在一边,瞧了好一会,陆氏方才掩门进去。
那丘大,若是一个有作用细心的人,只消暗暗察听,寻出破绽,把证空赶了开去,出了陆氏的丑,也便可消那一口气了。谁想丘大登时性发,揪过证空,掀倒在地,两个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的乱打。街上走过的人,并两边邻舍,看见丘大势头凶猛,向前力劝。证空得脱,乱嚷喊冤。丘大亦向众人,备将证空与陆氏嘻笑讲话的缘故,说了一遍。
那看的人,有个说着丘大不是:“证空是个有德行的长老。”又有个说道:“游方和尚,见了人家的内眷,探头探脑,油嘴嚼舌,原是个极不长进的,只嫌打得他少了些。”又有劝的道:“只消赶了他去就罢休,何必与他计较。”丘大又把陆氏着实骂了一顿,众人互相劝解,一哄而散。
证空打得遍身青紫,戒衣扯碎,木鱼念珠,俱被夺去,坐在阶沿,只管叫痛不绝。
到得夜深,陆氏轻轻地开门,放了进去,将酒劝着证空吃道:“师父为着奴家,遭那恶少之气,使我心如刀刺,坐立不安。惟恐尊体被伤,特央隔壁小厮,买下红花煮酒,你可多饮几杯,方能做血。”
证空道:“我被那厮打坏,亦不足惜。但虑自此一番之后,不能仍前相会,如之奈何?”陆氏道:“奴家亦如此想念,不惟与你不得欢会如初,只怕我丈夫回来还有说话。”证空道:“小僧即使远去,怎能将你割舍得下。”陆氏道:“奴家也放你不落。”
两个唧唧哝哝的,话了一会,不觉泪下如雨。
既而陆氏又问道:“你在我家往来,已费了好几两银子,如今身还有些么?”证空道:“自淞江带至嘉兴,原有二百余金。今自嘉兴来到这里,约共费了五十二三两之数,所存尚有一百五十余两。”陆氏道:“既有许多银子,尽可过活,但不知你会得营运么?”
证空道:“要做生意,其实不能。但习得外科医业,遍识无名肿毒,并一切疗疮发背,俱能救治。据我想来,这一项道路尽可到处去得。”
陆氏道:“有了这样本事,何必做个和尚,被人欺侮。”证空道:“小僧来至湖州,初意原要还俗。只因遇见娘娘十分美貌,所以假托化斋,逗留不去。”陆氏道:“俺家丈夫,生性粗暴,稍拂其意,非骂即打。所以出外去了,倒也自由自在。他若回来,时刻战兢,不能安稳。不料前番丘大,黑夜潜入在家,强要奸我,被我喊骂不从,又被四邻羞辱了一顿,因此挟仇,今日将你出气。只怕那厮还要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那时有口难辩,必遭毒打。幸遇你这冤家,虽则是个长老,性格温存,人物俊雅,你今要去,教我怎生舍得。所怕你身边乏钞,又没有随身技艺,还俗之后,难以过日。今既有了一百五十余金,则数年之用,不消忧虑。又有那外科医术,则随他可以行道。据着奴家,到有一条妙策,你可允否?”
证空道:“不知有何主见?”
陆氏道:“你到明早,向着二十九家施主,都去辞谢一声,就把满帽买了一个,扮做俗家,随去雇了船只,我和你半夜下船,逃到他州外府。你行医业,我做针线相帮,尽足快活过日。等我丈夫回来,问起根由,那些邻舍,见你去来明白,决不疑你,自然把丘大强奸事情说起,必致告官追究,使那厮有口难分,顶受罪罚。此计你道好么?”
证空拍手大笑道:“妙计妙计。”当夜无话。到了次早,一一依着陆氏而行。随路换船,逃至杭州府城内,贡院前小巷居住。且把按下不提。
却说赵诚甫家的四邻,那一日到了午后,不见陆氏开门。又过一日,寂无响动。众人三三两两,互相猜疑不决,又不敢撬进门去。直到第六日,赵诚甫回来,把前门一推却是拴上的。远远的抄从后门一看,只见铁锁锁着。
赵诚甫大惊,细问左右邻壁,俱说道:“五日之前,夜深时候,微微听得你家尊阃,若与人唧唧哝哝讲话的一般,到得次日,门儿紧闭,就不闻有响动的了。日间并不闻有什么亲眷来往。即向来,尊间每到亲眷人家去,必对我们说一声的。惟独今番,竟自悄然而去,事有可疑,大官人你须遍行查访才是。”
赵诚甫呆了半晌,遂从后门,抻锁进去。一看:什物家伙,件件俱在,惟陆氏的衣服,并几件铜锡器皿,俱不见了。赵诚甫便把后门关上,遍向城里城外和亲戚人家寻问,俱说不知,只得又到各邻家备细访查。内中有个老年的,便把丘大黑夜躲在屋内用强逼奸、以后又与和尚相打、并将陆氏辱骂之事,备细述了一遍道:“我们邻里共闻共见者,惟此一事,其外并不得知。”赵诚甫听毕,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便去央人,写了一张状纸,到归安县里,当堂投递。县官问了情由,登即批准,差役行提。
那一日,丘大闲坐在家,忽见两个公差走进,将出火票看了,吓得面如土色。当即请着公差吃了酒饭,送了些差使钱,也央人写下一张诉状。投文之日,哀哀哭诉。
县官当面批准,候审质夺。随即挂牌,午堂厅审。当晚,拘齐了一干犯证,跪在阶下,候那县官审理。不知何如?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