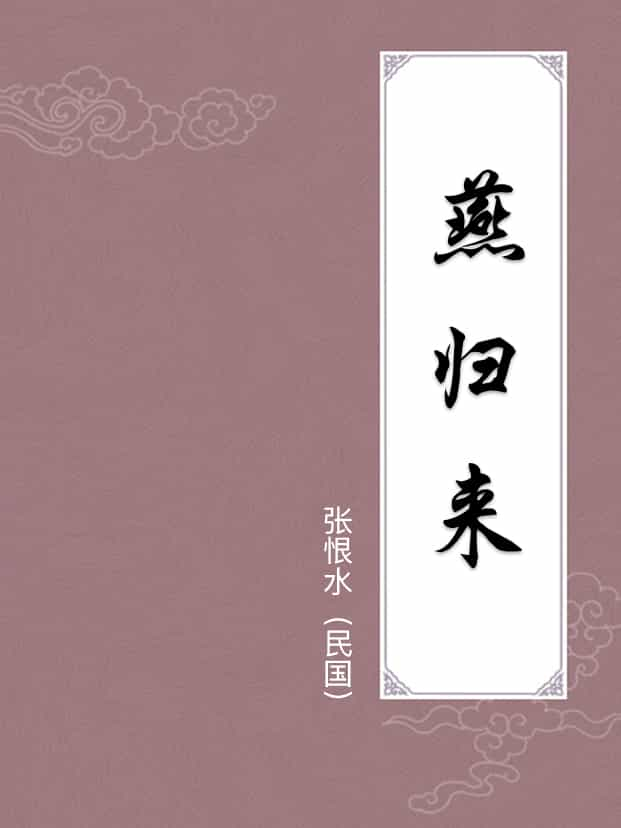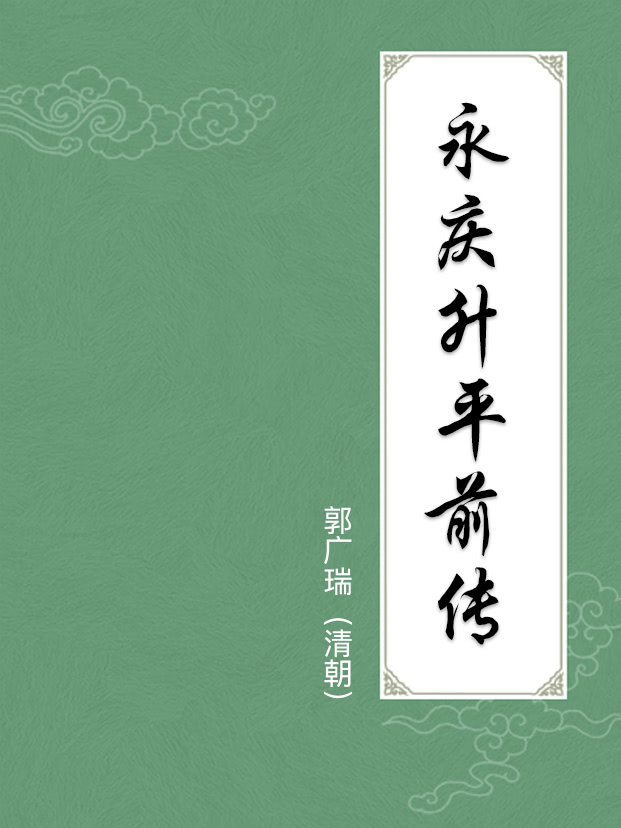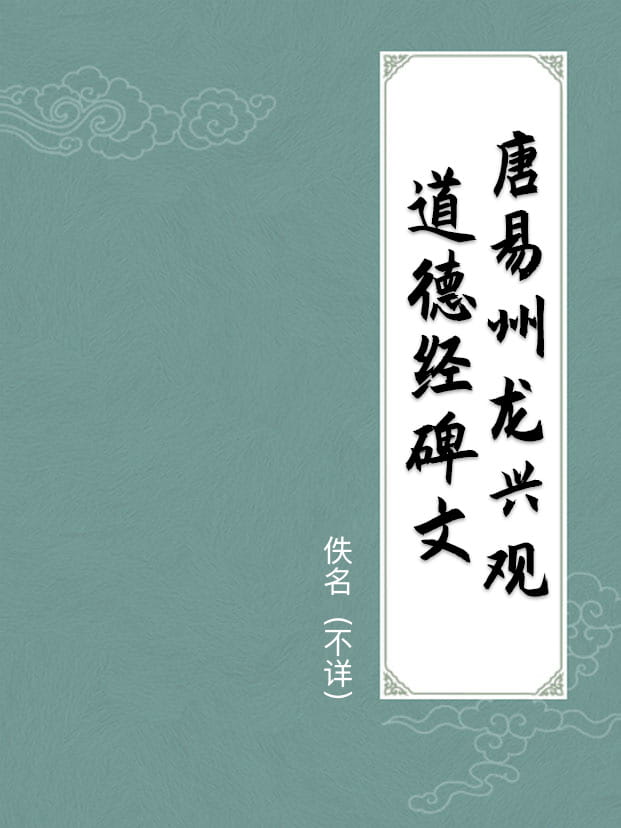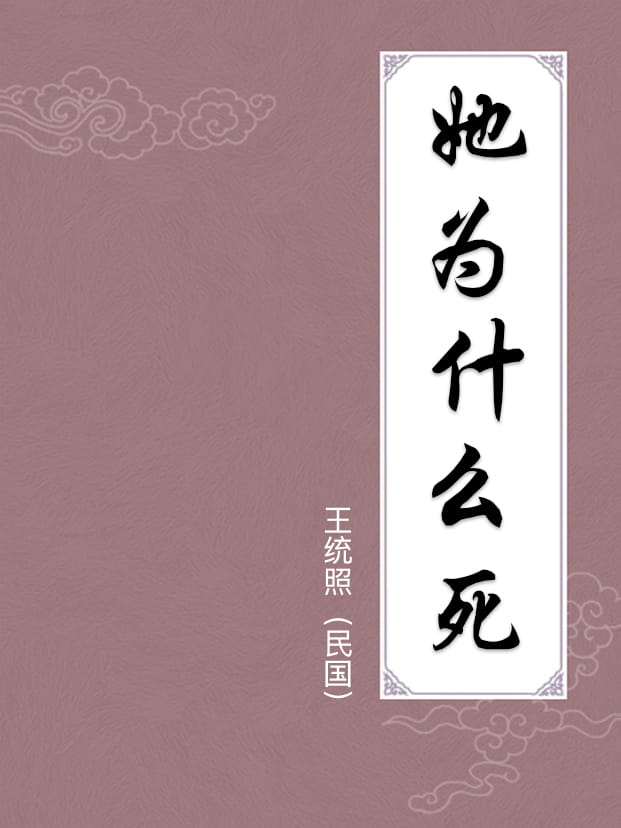在这一天上午,不过两小时之间,高一虹和同伴三个人,差不多都发生了一点友谊上的裂痕。燕秋究竟念着人家弃学业,万里奔波,是为了自己而来的;无论如何,自己对于他,总要格外的容忍些。本来吃了两块肉,喝一点汤,就要退回旅馆去休息的,现在想到果然走了,一虹言前语后,若是和费、伍二人说僵了,当了陈公干的面,倒有些难为情。这就依然坐下来,殊不料一虹和昌年顶嘴以后,他也默然无语。燕秋这就提起精神来,不住的和陈公干谈话。健生笑道:我说怎么样?劝你到这儿来大家谈谈,提提精神,比在旅馆里闷坐好的多。现在你不是精神复原了吗?
燕秋道:复原了就好,那我们可以快一点走。西安逛够了,水盆大肉也吃了,还有什么可以留恋?
公干也就放下了筷子碗,在袖笼里抽出一条手绢,两手捧着将嘴一抹,唉了一声,笑道:美哉!水盆大肉。
大家都跟着吃完了,让到旁边一副座位上来休息。燕秋笑道:陈先生吃完了之后,还连夸两声。一个南方人对于这清炖羊肉,这样的感到兴趣,这倒是我出乎意料以外的。
公干在身上摸出一包哈德门的卷烟,笑道:人是要走到什么地步说什么地步的话,就像这哈德门香烟,在扬子江一带,我们这当小老爷的,总不好意思抽;可是在西安就很普通。过了西安,县太爷款待省城去的佳宾,也就是这个。在这地方,还想过南京上海的生活,那如何能够?
公干一面说话,一面擦着火柴抽香烟,眼睛实是不曾向哪里看了去。健生却在一虹身上连连打量好几遍。一虹勉强的笑道:论起这一点来,我是非常之惭愧。我到了西安,还不免过着南京生活呢。
公干捧了两手,连连拱拳道:惶恐惶恐!失言之至。
燕秋道:陈先生也太客气。你不过是一句譬喻的话,怎么说是失言了。
说着,就睃了一虹一眼,一虹正是在打量燕秋的态度,看得明白,只觉脸上的肌肉紧张,脊梁上是阵阵向外冒着汗,便觉得坐也不是,站着也不是,只扭转了身子,向这楼上四周看了去。公干到了这时,也就看出了他们的裂痕,在墙钉上取了帽子在手,向着四个主人作了个罗圈揖,笑道:多谢多谢!我到省政府里去,有点公事要交代,先走一步了。
他笑嘻嘻的走了。
这里四个人,也都感到乏味,无话可谈。燕秋笑道:哪位带了钱,请把帐会了。我也急于要回旅馆去洗把脸。
她一面的说,一面走了。回到了旅馆里,坐在屋里想着,倒是有点发呆。一会子工夫,听到昌年在门外问道:燕秋睡了吗?
燕秋道:刚吃饱了回来,怎么又睡觉?请进来。
昌年进来,见她斜靠了桌子坐着,一手托住了头。昌年道:我听着房里一点声息没有,我以为你是睡了呢。
燕秋还是那个姿式,许久没有作声。却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昌年也不作声,在她对面椅子上坐了。燕秋微微的摇了两摇头,又叹了一口气。昌年明知道她是为了一虹的事,心里不自在,依然装成不知,向她微笑道:自从到西安以来,没有看到你痛痛快快过得一天,这是我们不无遗憾的。
燕秋禁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因道:我没有过得一天痛快日子,这和朋友们什么相干?要朋友认为遗憾呢?
昌年道:这话猛然一听,好像是不对。可是转身一想,也有理由。我们陪着你一同到西北来,这四个人总也可以算是同舟共济,就自然是要甘苦与共,现在我们都还平常,只有你一个人只管发愁;也许是我们对于同舟共济这一点,没有十分做到。
燕秋点点头道:你的话,倒是说得很委婉。你或者也知道我心里难过是在哪一点。我和一虹,平常的友谊也不算十分泛泛,就是他的性情,也很是温和的。不想他这几天性情大变,慌里慌张,整天不知要忙些什么?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总不把人家的话当作好意,板了脸子,立刻给钉子人家碰。我虽是十分容忍,他总不把态度改善。我心里疑惑着:他不愿意再向西走了,失了一个同伴,这无所谓,我们照样的可以向前走,不过这样一来,倒好像是我不能容人,把他气走了。我的意思,想请一虹来把话说破,假使他实在不惯这西北生活,打算回南京去,那可尽自便。只是希望他依然保持住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又怕当面把话说僵了,没有法子转圜。所以我还只是在这里为难着呢。
昌年沉吟了一会,答道:说一虹这两天有些态度改变,我也倒是承认;不过说他有心要回南京,那或者也未必;你这番意思,自然也顾虑得很是,我可以替你去问问他的。
燕秋道:那不大妥吧。我看你和他,很有点隔膜。你便是有十二分的好意去和他说话,恐怕他也不肯当着好话去听。
昌年听她如此说着,没有答话,斟了一杯茶,慢慢的呷着。他的两条腿,是架着的,不住的在桌子下面摇撼;眼睛只管看了杯子上那几笔粗线条的花纹。燕秋望了他道: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将来他要是走了,倒要说是你和健生不能容他,你怎能背上这样一个恶名!
昌年依然将眼睛望了杯子上的花纹,很随便的答道:我想不至于吧。那么,就是换了健生去劝他,他也不见得会高兴的。究竟让谁去和他说呢?
燕秋皱眉道:因为如此,所以是我为难透了,这话还是搁一搁的好。或者…………
燕秋于是将一只手臂撑在桌上,把一个食指点了嘴唇皮,她两只眼睛皮微微下垂。昌年看着,觉得她的态度是那样自然,又是那样柔媚可爱,不觉对她看出了神。燕秋猛可的抬起眼皮,看到他这样子,便笑道:你怎么也望着我出了神?
昌年搔搔头发笑道:并非别的…………
没说完,又搔搔头发。燕秋微笑了一笑,却是坦然,因道: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压下,什么不用说了。明天再休息一天,后天我决计走。假如高先生是不愿再向西走的,他一定会有表示。我们再根据了他的表示,看事说话。我可以坦白表示的,就是姓杨的人,决不作损人利己的事,也不能强人所难。
昌年笑道:你何必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我向来主张,以为一个人,无论做大小事,不做也就罢了,若是既然做了,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总要得个结果,决不能半途而废;一路走到西安,你总也看得出来,我决没有一丝一毫消极的样子。所以我这回西北之游,就陪你走到目的地为止,前途的成功和失败,我是在所不计的。
燕秋笑道:成功和失败,虽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但是我们这回旅行,除了我是希望找着家庭而外,你三位是游历性质;出门游历的人,只要你肯去,就可以到你所要到的地方。到了,自然是成功;不到,是自己不去,并无所谓失败。好像一虹吧,他现在若是不愿前进,回南京去,那是他自己愿意的,这里面似乎说不到什么失败二字。
昌年听她这样解释成功失败两个字,却是出于意料,便笑道:很好!我努力去作到成功吧。
在这时,恰好一虹走进来了。看到杨、费两人的脸色,都有猛吃一惊的样子,却不便对燕秋注意,只是向昌年微笑了一笑。昌年手上还拿着那个空杯子呢,这才觉得手上拿着这东西近于无聊,放了下来,也报之以微笑。一虹见桌上有几张报纸,拿到手中看看,因为发现到许多新闻,仿佛都是很熟的。看看报头上的日子,乃是昨日的报纸,这就悄然放下。燕秋将手伏在桌上,头枕了手臂去睡。昌年也是左手搭在桌上,右手在抚摩左手的五指。一虹想了几句话问道:长安城里的名胜,我们也算领略得不少了。但是汉唐两代的宫阙,多少总有些遗迹可寻,可惜我们始终没有去游历一回。
昌年笑道:你说到这个,我倒是领教过了。你若怕失望的话,就不去看也罢。
一虹道:一点遗迹都没有吗?
昌年道:在这城西北角,有几个五六丈高的黄土墩子,于今叫西五台。台底下到处是土沟,有几处破屋可以点缀。据传说就是唐朝的宫城,那还有什么可以赏鉴的呢?
一虹答应了一个哦字,也就觉得无话可以说的。说了声,我一个人去走走。
自出去了。他就为了出去寻找汉唐故宫遗址的原故,直到傍晚方才回来,连晚饭也不曾同大家在一处吃。
燕秋究竟是个主脑人物似的,硬和一虹这样僵持着,也是不妥,于是向他迎着笑道:一虹!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
一虹听说有消息相告,不能不吃上一惊,立刻就站定了脚问道:又是…………电报。
燕秋笑着摇手道:非也!那位陈公干先生不愿白白的吃我们一顿,今天晚上,请我们到匡俗社去听陕西梆子。
一虹换了一口气,笑道:原来如此。
健生道:听你的口音,好像在今天还有电报来,又是请你买碑帖吗?
一虹笑道:也许是。
他这句话,是驳得大家都无话可说。
还是陈公干已经来到,他说秦腔戏每晚唱一整本,要看全本,只有趁早去;于是大家随着陈公干之后,同向戏馆子里来。其实也并不是特设的戏馆子,乃是一所大会馆。进了大门,还走了两个院子的黑路,才摸索到了戏场子里,一到便感到这情调确乎又是一样。这戏场子里全是平座,没有较高的座位,也没有楼;位子的设置,是长条板凳,更配上长条板桌。人由后面走过来,首先看到的,便是满眼人头滚滚。因为城里没有电灯的设备,只是戏台口上,点了两盏较大的汽油灯。至于座位顶上,却只有一盏小型的汽油灯点着。座位子四周,却是那草帽式罩子的煤油灯,虽然也很是点了几盏,可是那光亮不大,所以在那空气不良,烟雾腾腾的灯光中,便使人的形影不清,只见人头乱动着。所幸西安虽有古风,戏馆子里却已办到男女同座。陈公干倒是这里的老主顾,他在前面引导燕秋一行人,由人腿相碰的一条路线上,引着到正中的座位上来。立刻有两个仆役样的人,起身让了开去,这就因为西安没有对号入座的规矩,公干预先买了票,派人来占了座位。大家侧了身子坐下,公干却是得了茶房的招待,得了一条一尺长的小板凳,放在桌子头,大家就是凑付着,斜了身子向台上看去。台的正中,倒也有一幅绸底子的绣幕,只是大红颜色,都变成深紫了。上面所绣的红花绿叶,金色狮子,也有若干部分零落着线头,挂穗子似的垂了下来。所有文武场面,都是拥在绣幕下方。至于正中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却也和京戏一般。
在台口柱子上,挂了一块木板,上面贴了红纸,写着黑字:今晚开演全部五典坡。大家看到这个牌子上的报告,就不免相视而笑起来。公干问笑什么?燕秋道:前两天,我们曾讨论过这一出戏,所以今晚看这戏,很是对劲。
公干笑道:要在西安听五典坡这出戏,那就机会太多了。陕西人对于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是特别感到兴趣。这里有三家秦腔班子,总是轮流的唱这种戏,差不多隔三天就有这戏可听的了。你瞧,这是秦腔皇后,扮着王宝钏上场了。
大家向戏台上看时,那个皇后,是位三十附近的男子,一张瘦削的脸,又是很长的,在稍远的地方看,几乎会疑心到这是人的侧面。他身上的装束,倒也和京戏里差不多,也是青衣白裙子,只是穿的鞋子,是一种剪刀口的青布鞋,不大雅观。他上场来,也说了几句道白,却是十分道地的长安话,而且也不用小嗓,不过比平常男子说话的声音,略微要窄些。一个装扮女子的人,用着本嗓子说话,在未曾听过秦腔的听了,立刻就觉得视感与听感非常不谐和。随着王宝钏也就开口唱起来了,在衬托的乐器里面,是两把梆子胡琴:大的有两尺多高,拉弓快到三尺长,下面的琴鼓,几乎和三弦子的鼓面同大;小的呢,也比平常的梆子胡琴要大过一倍。此外还有两个人吹笛子。那笛子很短,调门可很高。这四种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是呜呜高叫,加之还有两个敲大梆小梆的,剥剥乱响,便是狂风暴雨,也形容不上这乐器的紧张。所以唱的人,要尽嗓子的能力去发挥,要不然,就不听见人唱了。秦腔的尾声,多半是用张开嘴的喉音。一虹他们听着,只分别得呜哦哎三个字,唱得是什么戏词,一点不懂。那位皇后,又极其卖力,张了大嘴,不住的拖出那呜哦哎的尾音。健生低声道:当年的王宝钏若是这样子说话,薛平贵会爱上了她,你说怪不怪?
一虹道:我们南方人听不惯秦腔,可是西北人更是听不惯昆腔,当年李闯得了陈圆圆,让她唱昆曲,只听了几句,李闯就皱了眉头,说是惹起了他浑身的疙疸,立刻叫人奏乐,他自己唱起秦腔来了。
燕秋笑道:一虹高兴了,又在发议论呢。
一虹看到她那种样子,真不便说些什么,只好仰了脖子向台上去看戏。那个王宝钏,这时正有一个极卖力的动作,伸了右手一个食指,向前指着,两眼看定了这个手指,将眼珠左右乱转。当他转眼珠的时候,场面上金鼓齐鸣,情形十分的紧张。一虹虽是想笑了出来,念到燕秋对于自己的态度,这时很注意,他就忍耐着不笑出来。
王宝钏唱了一顿,进了后台,接着便是二姐大姐上常二姐是个十几岁的黄脸男孩扮的,胭脂粉全没有搽匀,整大块的剥落,因之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还外带黄一块,加上那突头凹眼,很少构成美的条件。至于那个大姐,年纪确是大,几乎有五十附近。他脸上是否抹了胭脂粉,不得而知;反正是一张长而又黄的脸,一看就看出来了。昌年看到,也就发生了一些感慨。因笑道:怪不得那位王宝钏被称为秦腔皇后,照着这大姐二姐相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大家一面看戏,一面议论,虽然对秦腔不十分懂得,说着有些意思,也就可以增加听戏的趣味。好在这秦腔戏场里,决没有台上唱戏,台下听不见的道理。所以大家小声谈话,却也并不碍及旁人的视听。
大家约看了两小时的戏,看到戏文里的情节,到本戏终场,似乎还很早。燕秋笑道:我们走吧,反正五典坡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全知道的。
公干笑道:我请各位来,也不过要各位知道秦腔是怎么回事。若是坐不住的话,尽可以听便。
大家对于这秦腔声音的高亢,还在其次,只是五典坡戏的内容,很令人生出一种烦腻。公干既不强留,大家都站了起来。公干这就把衣袋里揣着的一只手电筒,交给一虹道:这样东西,在西安是不可少的。我已经和四位预备好了。
大家起身,和公干点个头,也就走了。
果然的,离开了这戏场,就觉得是满眼漆黑。一虹亮了电筒,在前引路,到了大门口街上,只见星光下黑沉沉的两排屋檐,一条直街,不见一星灯火。家家都紧闭着两扇大门,露出那店门外突出来的土柜台,更显着这街上是分外的萧条。昌年道:长安城里,以前也曾极度的繁华过。在唐人的著作里,常是形容到城开不夜,现在多冷淡。
燕秋笑道:你怎么说得这样远?你不想想,我们在南京前后住几年,简直就变成两个世界了吗?几年还有很大的变化哩,何况是几百年哩!
大家说着话,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虹在前面引路,顿了一顿,四处看看,全是黑沉沉的直街,看去是越远越黑。一虹道:盲人骑瞎马,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去?晚上,每条街都是漆黑的,分不出个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这是大街,这是小巷。
燕秋道:西安城里的街,大致容易分别。不是直的,就是横的。我记得我们来时,只管向西走,就到了。现在我们反过来,只管向东走,自然就走到了。
大家在这里议论,于是人家屋檐下黑暗里走出来一个人,一虹用电筒向他射照时,是个穿青制服的警察,他道:你们几位是要到东大街旅馆里去的吗?
一虹说是。他道:你们一直向东走,倒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直走去好了。
一虹就照了警察的指教,直向前走,夜是更觉得深沉。
大家经过了几条寂寞无人的小街,似乎走到了大街上。在人家的门板缝里,露出灯光来,听到人的说话声;而且在两所比较高一些的屋檐下,垂下来有两盏檐灯,那灯是玻璃罩子的,里面还装的是棉油灯盏,点出来的光,黄黄的落在这沉寂的街心上,远远的看到一个伟大的黑影子,崇立在暗空里。原来那是长安中心点的旧式鼓楼。走到鼓楼下,是个半圆形桥洞式的门洞,而且是很低。一虹道:这一大截路,我都觉得离开了现代社会,实在值得留恋。可惜这是一场幻梦,到了明日白天,一切都没有了。
昌年道:我真想不到,你会迷恋着这十七世纪的夜市。
一虹道:你哪里知道?天下决没有什么事再比关起门来做皇帝快乐的。你想当年海禁未开,中国人老以为天下就只有中华是一个大国,没有汽车,坐骡车也很阔;没有电灯,点大蜡烛也十分光亮。西安到南京,要走一个月,也没有见得耽误了什么大事。自然,一切物质文明不如现在,可是精神上痛快极了。
燕秋道:这话是对的。一虹今晚上好作极端之论,受了什么刺激吧?
一虹笑着,可没有答复这一句话,手里电筒向前射着,已经看到旅馆前那个高楼门。这就停止了谈话,叫门进去。
只一进门,茶房迎着一虹道:高先生!有你的电报来了。
一虹道:是哪里来的?
昌年暗里替他捏了一把汗,茶房若答复着是开封来的,这事情可就僵了。可是茶房答道:是上海来的。
一虹道:电报呢?快拿来我看看,上海来的电报?…………
口里说着,作出那沉吟的样子,向屋子里走。随着茶房也就把电报送到屋子里来了。一虹接着电报,用手抓抓头道:真来了电报,这是透着麻烦的。
他伸手在床头枕底下一摸,摸出一册电码本子来,就到灯下去翻译电文。可是费、伍二人好像避着嫌疑一般,都闪到一边去,只当不知道这一件事。他一人在灯下译文,过了一会子,忽然呀了一声。费、伍二人,依然没有作声。直到把全篇电文译完了,一虹这就自言自语的道:怎么好?怎么好?
昌年道:老高!为什么惊慌?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一虹举了电报纸道:这实在让我感到不安。上海方面,转来家父一个电报,叫我不要向西前进了,你看这电文。
说着,将电文送了过来。昌年听了他的话,也是猛可的吃了一惊,怎么他真会有了这种电报到了?接过电文来一看,上面除了地址而外,文是:
兹接到令尊港电,嘱转告兄,希以学业为重,勿再西行,即归校。令尊不日来沪,否则恐有他变。庸。
昌年哦了一声道:这署名庸的,是什么人呢?
一虹道:是家父的朋友。我因为家父时而在香港,时而在新加坡,所以没有和家父直接通信,只是打电报给这位先生。因为他们在商业上差不多是每日有电报往还的。我想不到已经来到了西安,家父会不要我前进,而且这电文的口气是很严重,我没法子违抗,这可怎么好呢?
昌年道:你说的是否则恐有他变这六个字吗?是一种什么变故呢?
一虹道:这件事,牵涉到了家庭问题,我是不好说出来。不过华侨的思想,并不是别人能揣想的,像欧美人士那样崭新。有时和人的理想相反,乃是极端的旧。所以这变故两个字,是关系很重的。
昌年对于他的话,也没有置可否,就把那电文交给了健生去看。健生就道:那么,照着你这个电报看来,你是非东回不可了。
一虹作出踌躇的样子,嘴里吸了两口气。昌年道:人生是难说的,想不到我们到了西安,还有分手的可能!
一虹沉着道:这件事我自己也是拿不定主意,等我和燕秋商量好了,再定去留吧。
健生说道:这个主意当然是由你拿。你要回学校去,事关你的前程,她还能拦阻你吗?
一虹道:那是自然。不过…………
他说着话,打开房门,向外探望了一下,因道:燕秋已经睡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费、伍二人看他那情形,是十分不安,谁也不敢插嘴说什么,只好听之。
到了次日早上,费、伍二人,知道一虹必然会去和燕秋开谈判的。拿了几份报,自伏在桌上看,却不向燕秋屋子里去。偷眼看到一虹拿了那封电报,向燕秋屋子里去了。健生低声道:你看一虹能决定回南京去吗?
昌年道:你以为燕秋能留住他吗?
健生道: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决不肯说留老高的话。
昌年道:却原来一个要走,一个不留,还有什么话说?
健生笑道:我们两人,再有一个抽梯,这事就妥了。不过我现在倒不好说转去的话了。
昌年将看报的眼睛抬了一下,向他微笑着,这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约莫有一小时,一虹很懊丧的样子,皱着眉走进房来,右手拿了那封电报,不住的在左手心里打着。叹气道:对不住,我们要分手了。燕秋的意思,以为我若再向西走,引得家庭发生了问题,她很感不安,极力主张我回南京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要我再向西走,我是没有这种勇气。燕秋说:她明天决计搭车子走。我听了这话,真是黯然,不但是心里不安而已。我看她那样子,一定是不能即刻回南的,我送你们到咸阳吧。咸阳的东岸,就是渭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千古不朽的诗,就在那里作的。
昌年道:那末,你要实行唱那阳关三叠?
一虹道:不如此,我心里过不去。
昌年道:你坐了我们的汽车去,你怎样回来?
一虹道:那好办,那里天天有西南两路的车子,随时可以搭坐回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费、伍二人互看一眼,也就莫逆于心。
这一天,燕秋和平常一样,并不带着什么难堪的态度,把旅行需要的东西预备得充足了,和一辆到平凉的货车商量好了,二十五块钱一个人,各人带三件行李。一虹附车到咸阳,并不要钱。次日七点来钟,这汽车就由车行里开到旅馆来接客。一虹帮着三人同搬行李,出去看时,却是一辆大卡车横门停着:车身四周,是板子围着的,不但上面没有什么遮盖,而且车上的行李货件,堆着有五六尺高,已经有四五个客人都坐在行李上。车身本来有三尺多高,人再坐在行李上,倒仿佛有些像江南出会时抬阁戏。便向燕秋道:坐在这上面,不但有相当的危险,而且风吹日晒…………
燕秋手提了一只小箱子,抓了木板,爬上车去,答道:没关系!向西去的客商,谁不是这样走的?
她爬过了行李堆,将小箱子向行李缝里塞了进去,人就在一卷铺盖上坐着。随着费、伍二人也爬上去了。一虹对于他两人,这时倒有些钦佩,也就更增加了自己的不安。爬上车子,便道:我不能和三位同甘苦,我十分惭愧。我回到南方去,一定把你们这吃苦的情形发表出来。
燕秋笑道:由陕西到甘肃去,盼到有汽车可坐了。天理良心,这是一步登天的事了,怎么还说苦呢?
同车的几个人,也带了笑容,似乎对这句话表示同情呢。
这时汽车司机生在车下问着各事已经停妥了,他就开车。出了西安的西关,公路很是平整。南北两面望着,全是莽莽的麦田。约莫走有十里地,在公路的北边,有一个黄土高坡。有几户人家的颓墙,带了些野草。据燕秋说:那是汉代未央宫的故址。又过了一道和灞桥相像的长桥,叫做沣桥。桥下的沣水,也和灞河一样,河床里全是沙。这桥只有灞桥一半长,却是它的桥基,完全用许多柱磉一般的圆石头叠起来的,倒显得别致。过了沣水,就是秦都咸阳故城,依然是些高下的土坡杂在平原里。又不远,汽车越过了一块高地,这就看到了渭河的水,由南向北,黄流滔滔,拦住了去路。在河这边,是一片泥滩,没有什么点缀。河那边,北段是高原的起点所在,只见那平地,慢慢向西北高了去。南段是咸阳县城。那城东南两角,紧靠了渭河的岸上,低低的黄土城墙,拥起两个残破的小箭楼,倒有些像江南大路边的小古庙。渭河那浩浩的横流,由那水平线上的黄尘中流来,也向北端黄尘中流去。这咸阳城在太阳下面照着,没有一些山林陪衬,便有些那黄沙白草古人出塞的情调。燕秋在车上,首先喊着到了咸阳了。一虹道:怪不得唐朝人送客到西安去,总送到渭城。实在的,这个地方送别,不同灞桥了,很有些苍凉之感的。古来的渭城,是在渭河东岸的,大概送客到河边为止。于今咸阳县城,倒在西岸了。
说着,汽车把泥滩跑过,停在河边。汽车夫招呼大家都下车,好过渡船。
大家下得车来,见渭河两岸,斜对着,都停泊了几只渡船,还有两只渡船正对开着。这渡船和在潼关所看到的黄河渡船,相差不多,只有平舱板,没有篷舱,也没有桅竿;头尾都是方的,仅仅是后艄有个二尺高的舵楼,然而也并没有舵;乃是将一根弯曲的树料,下半截拖在水里边,上半截斜伸在艄上。燕秋笑道:一虹!你前晚上说:古代的城市,都可以留恋,你看这渡船怎么样?我相信这渡船,还保持着汉唐时代的形式。
在河那边,有个木牌坊,上面有字是咸阳古渡。一虹已经走到水边上,见渡船上的人,正向岸上放着三四副跳板,放车马行人上去。便答道:这倒是不愧那个古字的。不过它是运车马的,不保持着这种原有的精神,也许不行。
这时,那汽车在两块跳板上,缓缓的移上船去,随后坐车的人,还有其他渡河的人,都向船上走着。
一虹也要跟着上去时,那个汽车夫看见了,就向他摇着手道:先生!你不是送客的吗?你就不必过河去了。
一虹道:为什么?送客的就不能过河的吗?
汽车夫道:不是那样说,你看那边有只船正要向这边开。那上面不有一辆大汽车吗?那是由宝鸡开回西安的客车,你先生正好搭了车子走。宝鸡到西安的客车,每天都是一两点钟到这里,今天不知道怎样早来了,也许今天下午没有车了;你若过河去,车就过来了。
一虹道:这样一条大路,有的是车,我可以搭别辆车子走。
燕秋道:不必了,一虹!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不是说了吗?古来人送行,大概是不过河的,你就到这里为止,好早早的回西安。明天,你可以赶早坐汽车上潼关了。
说话时,费、伍二人都已上了船。燕秋站在跳板头上,拦了一虹,昌年站在船边挥着手道:一虹!你果然不必送,你现在搭汽车就走,还好一点,回头你一个渡河回来,很凄凉的。
这句话说得一虹心里一动,退了一步。燕秋就伸出手来,向一虹握着,强笑道:我没别的可说,只有永远记着今天在渭河岸上。
一虹顿了一顿,望了她道:我很对不起你。
那声音很细微,而且断续着;但是他怕会哭出来,收回了手,立刻高声向费、伍二人道:这里又没有酒,我不能劝你一杯,我念两句诗送你吧。
于是高声念着王维送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两句诗。燕秋走上了船,船家就抽了跳板。他们三人站在船上,都向他点头。一虹并非不想上船,只一发呆,跳板就抽了,现在要上船,已经是来不及。眼见船家将木篙子点着岸,船已离开了两三尺。燕秋点头道:一虹!你立刻坐车回去吧,到南京问候朋友们。
一虹说道:希望你一切原谅。
这船慢慢到了河心,三人还是向他望着,不住的点头呢。